來自匈牙利的大冒險家,因緣際會踏上了十八世紀的台灣
寫下一段驚險、驚異、精彩的福爾摩沙傳奇史詩……
貝紐夫斯基(Benyovszky Móric)原為匈牙利的貴族,因參與波蘭的抗俄軍事行動而被俘入獄,成功脫獄並劫船逃逸之後,一路航行返回歐洲。這段冒險經歷不但至今仍為匈牙利人津津樂道,貝紐夫斯基在返航途中因緣際會來到福爾摩沙,展開十幾天驚險、驚異而精彩的台灣之旅,更與台灣原住民有多次接觸。雖然貝紐夫斯基與原住民頭目歃血訂盟,重返福爾摩沙展開殖民計畫的想法未能付諸實現,但是這位幻滅的「福爾摩沙之王」仍舊在台灣歷史上留下了屬於他的一頁傳奇。
本書深入介紹貝紐夫斯基其人其書,將《貝紐夫斯基伯爵之回憶與遊記》中有關「福爾摩沙」的內容詳譯為〈福爾摩沙紀實〉一文;同時,本書亦依據完整譯文,修正過去相關譯著略譯、錯譯而產生的謬誤,並重新描繪貝紐夫斯基台灣行旅的細節,及其所見的台灣人事物。不但是目前最為詳實、完整的中譯本,也是當前以貝紐夫斯基登陸事件為主題,進行最多討論的專著。
這片撲朔迷離的歷史拼圖或許未臻完整,但它將告訴我們更多關於這段異人冒險的始末,也為18世紀台灣原住民族與台灣史的討論激發更多可能。
本書特色
1. 貝紐夫斯基伯爵台灣探險紀事首度逐日、逐句、逐字完整中譯。
2. 相關匈文圖資首度披露,貝紐夫斯基登台之人事時地物詳細解謎。
3. 專家專文導讀,台灣史研究的深度對話與探索。
作者簡介:
莊宏哲
Chuang Hung-che
1955年生於彰化,輔大大眾傳播系畢業,美國美利堅大學進修。曾經服務於行政院新聞局,任職期間曾兩度派任駐匈牙利新聞外交官。2011年底退任公職後,潛浸水彩繪畫興趣成為自由畫家,目前任教於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淡水社區大學。
著作:
《匈牙利—走馬不看花》
《布達佩斯—走馬不看花》
Email: chuanghungche@yahoo.com.tw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致讀者推薦文
貝紐夫斯基是位18世紀的探險家,也是自由鬥士、軍人、學者、旅行作家、殖民者,他的足跡遍及歐洲、亞洲、美洲及非洲。他曾參與波蘭的獨立戰爭,因而遭到俄國人俘虜並被流放到勘察加半島,而後自獄中逃脫,駕乘「聖彼得與聖保羅號」船艦經過一番冒險歷程,於1771年抵達福爾摩沙島,他是第一位登陸福爾摩沙的匈牙利人。
貝紐夫斯基在他的回憶錄中,對於福爾摩沙島有令人憧憬與景仰的描述。根據他的回憶,他對福爾摩沙第一印象的形容:「她是已知世界中最美麗最富庶的島嶼之一。」
之後,他也前往美國,最後則身亡馬達加斯加。他的聲名在匈牙利、斯洛伐克、波蘭、馬達加斯加備受尊崇---我希望從此以後,也能在台灣受到同樣的愛戴。
本書的作者莊宏哲曾經是派駐匈牙利多年的新聞外交官,也是我的至交好友。他對於貝紐夫斯基的著作以及歐洲世界,有相當程度的了解與認知。此書的出版具有重大意義,因為它是第一本較完整介紹這位匈牙利探險家的中文著作;而這位匈牙利探險家的一生,已將遠方國度的人民、文化拉近在一起。因此,我希望讀者也能喜歡莊宏哲所寫的這本書。
致上 誠摯敬意
匈牙利地理博物館 館長
Kubassek János博士
謹誌於 匈牙利 Érd市
Benyowsky航海回憶的再回憶
翁佳音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
研讀台灣史的人,鐵定都會知道有兩位奇特的歐洲番(stranger):一是法國人G. Psalmanasaar(約1679~1763),另一個就是本書的男主角M. Benyowsky (1746?~1786)。前者冒充原住民王子,講了一大堆的話唬爛;匈牙利或波蘭人的Benyowsky則通常被罵為無恥冒險家,以吹噓行走社交界。譬如他書中一開頭便說俄國長官女兒Aphanasia(有一本戲劇則把此女的名字寫成Athanasia)愛上他;後來又說深受日本四國沿岸的領主招待,相談甚歡。研究者大都已指出,事實上沒這個女孩,而當時日本仍在鎖國氣氛中,全無這回事。
也因此,正經的台灣史老師或研究者,通常不太願意深究這件發生於1771(清乾隆36)年之事,所以國內讀者知道有此號人物與事蹟者不多。但我老是覺得,把轟動一時又流傳甚久的國際浪漫史(romance)棄之一旁,實在是有點糟蹋。我很喜歡跟學生講他吹噓航經奄美大島時,與一位應該是掰出來、名叫Tinto Volangta(我戲譯芳名為「明月」)的年輕姑娘淡淡之愛;以及他炫耀在東台灣的作戰事蹟,並高調說台灣番仔(原住民)頭目Huapo與他歃血訂盟,試圖建設歐洲人殖民地,這簡直是18世紀的詹姆士龐德(James Pond)諜報劇情,不看,太可惜。
如今,拜網路文獻數位化的恩賜,要取得Benyowsky的原書影本已輕而易舉。不過相對的,縱使仍有新研究問世,寡聞所及,具重大突破的好像還少見。很高興,終於有曾任職匈牙利多年的退休新聞局外交官莊宏哲先生,花了相當的心力蒐輯、考訂,並翻譯台灣部分,而交由前衛出版社堂堂出版這本好書。書中,他澄清了主人翁Benyowsky的國籍,以及他的船在東台灣何處登陸,跟哪些原住民互動,等等。我特別要一提的是,莊先生根據1898年的英譯本,提出登陸地點是Kaleewan,為「加禮宛」,也就是宜蘭冬山河河口,進而是蘇澳一帶,這是迄今比較少被提到的觀點。
(二)
莊先生的說法,算不算定論,並非我或少數人說了就算,這是「歷史」迷人之處。我寫這篇小文呼應他,除了佩服其認真用心外,主要仍在提醒研究界與讀者,有些看似荒誕不經的歷史敘述,若經史學的結構想像,還是可挖掘出一些若隱若現的「事實」,從而迫使我們反思既定的歷史圖像。
當然,若從謹嚴角度來看,Benyowsky的航海記錄確實糟透了。船隻明明經過奄美大島後往南走,內容說船員發現可照Anson Voyage的航線,也就是可從台灣南端的巴士海峽航行到澳門。但接下來的紀錄,經緯度與地名亂七八糟,「害」得我們的莊先生花了相當篇幅去考證;結局,看記錄,Benyowsky的船好像又折回,大費周章繞過北部海岸前往澳門。
不過,他確實到過到日本,日本研究者也老早考訂出確實地點。Benyowsky曾在琉球群島北端的Usmay Ligon,即奄美(Amami)大島,用德文寫信向長崎出島的荷蘭商館求救,並警告俄國有侵略日本之野心。出島的荷、日人把信文翻譯後,認為侵寇是無稽之談,信件束之高閣,迄今存於檔案館。然而,Benyowsky當時誇張恐嚇,居然影響到稍後的經世論家林子平(1738~1793),從而開啟日本警戒北方俄國的論述。林子平有幅著名的「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島之図」,原來也是由此產生的國防論作,如今很受中國保釣運動者鍾愛,因為該圖釣魚台的顏色與中國相同,被認為是釣魚台屬中國的如山鐵證。至於該圖台灣色不同中國,當然得蓄意漠視。就這樣,吹噓中有不易事實,事實中有肆意虛構,這是「歷史」難免的特色。包括Benyowsky之名,被當時人誤解為德文名而譯為「はんべんごろう」,後來在我們國內居然又迸出「半邊五郎」的譯名,有趣吧?
(三)
還是回到台灣的有趣事。Benyowsky離開奄美島後,大約漂航一週,才到台灣東部。由於書中提到是在23.22度靠泊,因此一般的書通常都認為是在花蓮秀姑巒溪的大港口一帶,莊先生以新資料主張是宜蘭冬山河與蘇澳等地,並提出種種的解釋,我暫不妨害讀者順著閱讀與判斷。我只希望在讀完後,不妨抽閒讓腦筋運動一下,一併思考我以下所提出的兩個問題:
一、Benyowsky在東部宜蘭、花蓮一帶約18天的活動,是否接觸對象全屬原住民?他們的對話,如:“Signor Houvritto, vai, vai.”,分析起來,倒是很像西班牙語與閩南語的混合,也許原招呼語是:“Señor Horrido, Lai, Lai. ”「大人先生,來來。」換言之,在解析他的回憶時,族群對象,不妨稍放寬一點。例如,頭目Hoapo及其屬下的行頭與武裝描述,看起來很像滿清帝國的裝備,是真的原住民嗎?進而,當時的戰鬥有千萬人參與,是否吹法螺吹過頭?Benyowsky的同行者Ivan Ryumin也留下記錄,爆料說東台灣之戰,只是小事一樁。
因此,英語版的編譯者就曾懷疑他可能是離開台灣,經澎湖(Piscatoria)後,因缺水進入Tanasoa,而與當地人爭執交戰。後來回憶,也許把此段戰事錯置到東台灣。我看這個可能性也不是沒有。Tanasoa,顯然就是西洋人海圖上的Tansoa,即福建省外小島銅山或東山。他們的船離開東山後,遇到會講一點點葡萄牙語的華人漁民篷船,而於當年9月22日被帶到澳門。
二、縱然Benyowsky東台灣戰記可能誇張或錯置,並不表示說宜蘭、花蓮一帶的故事就沒精彩事可講。其實,我們可以從日本文獻,如《華夷變態》、《唐通事會所日錄》等,得知1692~1693(清康熙31)年前後,有宜蘭原住民「漂流」到日本被遣返,內情也許不單純,東台灣應該不像研究者所說的那樣與外界隔絕。而郁永河的《裨海紀遊》又提到大約1695年時通事賴科前往東部台灣,「……東番……各番社,禾黍芃芃,比戶殷富,為苦野番間阻,不得與山西通,欲約西番夾擊之。」這段記事,看起來又與Benyowsky吹噓的情節有些神似。Benyowsky的膨風故事,還是值得再回憶。
(四)
研究界所忽略的軼事,還不止上舉之例。多年前,我就看到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士兵冒險記中,有位名叫范‧德‧哈賀(Carolus Van der Haegh)比利時人士兵,他於1704年6月時與同夥在菲律賓偷取一艘船,航經東部台灣,也看到「像華人」的漁民與村庄。這個村庄從文字描述看來(參見Zutphen, 2002. De avonturen van een VOC-soldaat.),倒很像是宜蘭的蘇澳。也因此,莊先生提到Benyowsky船有到蘇澳,我多少能同意。
最後,我順著莊先生的勞心勞力著作,既然要繼續推想東台灣的少文字時代史事,我就再提出一個可討論的史學結構想像。Kaleewan(加禮宛)與蘇澳是東台灣重要舞台,那蘇澳為何地名叫蘇澳?蘇澳在西班牙文獻上,是被命名為“St. Lorenzo”,在荷蘭文獻中,蘇澳與加禮宛都是東台灣重要的交易地點,而且是唯一可入大船的港口。我不禁開始懷疑,蘇澳這個地名是否與野柳(Punto Diablo)、三貂角(Saint Jago),以及「哆囉滿(Douroman)」一樣,都是西班牙語地名?西班牙語的Lorenzo,閩南語音大約是「路連蘇(Lō•-liân-so•)」,省略之後為「蘇」。Benyowsky在這裡碰到西班牙人,也就不那麼奇怪了。
無論如何,Benyowsky到日本之後,日本有林子平的防衛北方外犯之論;他1771年離開台灣一、二十年後,中文文獻開始有東台灣的非法移民、海盜的記錄。這本書若放在如此長期歷史文脈中來閱讀,也許會更好玩。
在真實與虛擬之間
詹素娟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貝紐夫斯基(Mauritius Augustus Count de Benyowsky)是十八世紀著名的匈牙利傳奇人物。他在1770年因涉入波蘭與俄羅斯的戰事,遭俄人俘虜,最後關押在西伯利亞堪察加半島的監獄。1771年,貝紐夫斯基與同夥奪船逃離堪察加半島,向南航向自由。在行程中,貝紐夫斯基的航海日誌曾以數十頁篇幅,描述該船在1771年8月26日到9月12日之間,在台灣東岸登陸、遭逢原住民的經歷。這一今天讀來仍相當精彩刺激的探險遭遇,儘管當時清帝國的台灣官府未必知曉,一般民眾也可能完全不曾聽說,卻是十八世紀真實發生於島嶼東部的重大事件,其紀錄更成為十九世紀來台西方人瞭解台灣風土人情的重要參考。
因此,長久以來,貝紐夫斯基的相關書寫,主要流傳於史蒂瑞(Joseph Beal Steere)或禮密臣(或戴維遜,James W. Davidson)等西方人的調查資料與台灣書寫中,不見於漢文史料;日治時期的伊能嘉矩,自將貝紐夫斯基的事蹟納入《台灣文化志》的框架後,始成為較普遍的歷史知識。針對這一事件,有人說:貝紐夫斯基在「無意中闖入了台灣歷史」,也有人把事件視為與原住民世界相關的漂流史之一;然而,貝紐夫斯基的台灣「快閃」,說明了什麼歷史現象?貝紐夫斯基與夥伴們究竟遇見了「誰」,似乎從未得到明確的討論。進一步來說,貝紐夫斯基的身世、航海日誌的書寫與版本,到目前為止還不曾獲得台灣人的注目與重視。當此之時,兩度派駐匈牙利擔任新聞外交官的莊宏哲先生,在機緣、興趣、歷史愛好與執著的努力之下,致力於這份資料的譯解,並試圖提出一套解釋的說法。
我們細看內容,全書分為四篇,第一篇說明貝紐夫斯基的人與書,第二篇是與台灣相關的航海日誌文本中譯,三、四兩篇則是作者以文本為基礎,針對來台前的海上航程、船艦兩次登島的港灣地點(第一登陸現場、第二登陸現場)、登島時間、誰是登島第一人,尤其是貝紐夫斯基一行人在島上相遇的西班牙人、原住民村落及所屬民族等的詳細討論。對讀者來說,藉由本書的帶引,除能直接讀取貝紐夫斯基〈福爾摩沙紀實〉的完整中譯外,對作者的創見,無論是否認同,應該也能各自找到理解的切入點。
就筆者而言,本書最有趣的部分,則在於作者有關登陸地、原住民族的推論。不同於伊能嘉矩對第一登陸地──秀姑巒溪口(即東海岸花蓮縣豐濱鄉的大港口)的推測,作者認為1771年8月26日船艦的首次登岸探路地點是蘇澳灣的北方岬角灣內處;其次,儘管歷次版本對8月28日停泊上陸的第二處港灣都註說貝紐夫斯基留空未寫,但作者根據1898年的英文版,則指出該處為Kaleewan Bay(加禮宛灣),即今冬山河口。而基於貝紐夫斯基兩次登陸都在宜蘭境內的假設,作者在整理文本記錄的十二次原住民接觸經驗,並歸納出五種類別──蘇澳灣原住民、交易物品原住民、Huapo原住民、汲水處原住民、Hapuasingo原住民後,對可能的對應部族盡皆鎖定於北台灣的原住民族。對前三者,作者分別推估為猴猴族、噶瑪蘭族(或疑似巴宰族)、泰雅族;對後兩者,作者態度謹慎,雖點名凱達格蘭、巴賽、龜崙、道卡斯,甚至賽夏族等,還是不敢輕易斷定。
由於資料過於稀少,加上筆者對經緯度、洋流、岬角地形、風向、海洋深度等所知有限,著實不敢斷言作者登陸地推論的可否。但作者根據維基百科「與那國島可以遠眺台灣」之說,以文本提到「此時福爾摩沙島已在視線內了」一語,猜測貝紐夫斯基船艦駛進的大岩石即為與那國島東部石岩之臆測;或未慮及今日「既寬且深」的蘇澳灣,也是日治時期即已開始整建的人工港口;或冬山河不能直接出海,必須匯入蘭陽溪一起流向海口,所以加禮宛灣未必小而美等,卻還有參酌思考的空間。
筆者雖不能完全肯認貝紐夫斯基船艦的兩次登陸地,卻也可以假設:如果貝紐夫斯基船艦的第一處登陸地真是蘇澳灣,該地住民確實可能是猴猴人。只是猴猴人並非來自大洋洲的外鄉人,而是原居花蓮立霧溪流域的在地人;他們是在太魯閣人的東遷壓力下,離開老家,並在陶賽人的驅趕下,一路穿山越嶺,北上到蘇澳一帶的猴猴高地;又因泰雅族南澳群的虎視,轉遷海岸沙丘,十九世紀中葉始返回南方澳海邊,日治時代則入住南澳。至於作者推測第二處遭逢的「交易物品原住民」為噶瑪蘭人,應該無誤。自有文獻記載,噶瑪蘭人即以划獨木舟往來於沿岸海域的活動力著稱──最北曾抵達今新北市金山區、在八里區留下噶瑪蘭坑地名,向南則越過秀姑巒溪口,威嚇阿美族人;而這樣的移動,有時會在海上與外來者交易物品,有時則是戰鬥獵首,很難以單面形象揣測他們的對外關係。同時,筆者也要指出,Kavalan(噶瑪蘭)作為平原數十個村落的集稱,需到二十世紀才發展出「民族」意涵;回歸到十八世紀,其中實包含各種文化特性、生計型態不一,且彼此不相統屬,甚或關係對立的社群。換句話說,我們若考慮到蘭陽平原內部社群的差異性,就不會以單一同質的民族性解釋十八世紀的噶瑪蘭人,也會把仍在西部發展農墾勢力的巴宰族、在中央山地活動的泰雅族溪頭群,暫時排除在相關的考慮外。
貝紐夫斯基最引人爭議的敘述,大概是馬匹、原住民動員人數、大量的金銀塊、盟約、紙張與文字書寫等,前人如史蒂瑞等均曾提出質疑,筆者也認為貝紐夫斯基有誇大不實之嫌。不過,考慮到「福爾摩沙經歷」是貝紐夫斯基對歐洲王室貴族說服募款的「文案」,為了讓金主感覺「海外投資‧物超所值」,在事實之中增補素材、誇張數據,甚至模糊化台灣已納入清帝國版圖的政治現實等,都是必要的策略。解讀文本,原就是遊走於虛擬與現實之間的考驗,在繁花異草中淘解出真相的果實,才是趣味的所在。
名人推薦:致讀者推薦文
貝紐夫斯基是位18世紀的探險家,也是自由鬥士、軍人、學者、旅行作家、殖民者,他的足跡遍及歐洲、亞洲、美洲及非洲。他曾參與波蘭的獨立戰爭,因而遭到俄國人俘虜並被流放到勘察加半島,而後自獄中逃脫,駕乘「聖彼得與聖保羅號」船艦經過一番冒險歷程,於1771年抵達福爾摩沙島,他是第一位登陸福爾摩沙的匈牙利人。
貝紐夫斯基在他的回憶錄中,對於福爾摩沙島有令人憧憬與景仰的描述。根據他的回憶,他對福爾摩沙第一印象的形容:「她是已知世界中最美麗最富庶的島嶼之一。」
之後,他也前往美國,最後則身亡...
章節試閱
第一篇 幻滅的福爾摩沙之王
第一章 貝紐夫斯基的傳奇一生
「貝紐夫斯基」這個名字對大多數台灣人而言是陌生的;但台灣對貝紐夫斯基而言卻不那麼陌生,因為早在二百多年前,他就與台灣這塊土地結下淵源。
貝紐夫斯基於1746 年(或1741 年, 詳後述)9 月21 日出生在當時還是匈牙利領土的Verbó,1786 年5 月24 日戰死並葬於馬達加斯加島上。
關於他的出生年份
貝紐夫斯基出生的年份有兩個說法:一是1777 年由Verbó 當地牧師所簽發的出生證明,文件上登載的出生年份是「1741 年」(航海日誌原書的編者序以及他的自述亦稱是1741 年)。但另一份由Verbó當地的天主教會於施洗時所登錄的出生紀錄,其登載的年份則是「1746年」。這份文件中可以看到貝紐夫斯基的名字Mauritius(拉丁文)就列在倒數第二行第二個位置,日期是1746 年9 月21 日。
一般認為,天主教會所登錄的「1746 年」才是較為真確的出生年份,因為這才是最原始的紀錄,不可能後來再更改。至於「1741 年」之所以值得懷疑,原因是這份由Verbó 當地牧師所簽發的出生紀錄文件,可能是貝紐夫斯基為了向法國進行遊說,在被要求證明身世時所造作的。再者,這份文件於1777 年才簽發,明顯是後來才出現的文件,而非他出生受洗時就寫下的紀錄。這也許是因為他當時已背離天主教改信基督教路德教派,因而與天主教會決裂,自然不便也無法自天主教會取得證明,所以才轉請基督教當地教區牧師Paulus Maczunda 來簽發這份文件。
此外,這份文件上所載的「1741 年」,也有可能是憑貝紐夫斯基個人的口述,或另有其他原因而作成的錯誤登載。亦有人認為,簽發文件的教區牧師Paulus Maczunda 在1778 年1月就因病過世,當他於1777 年5 月簽發這份文件時,應該已經病重甚或病危了。他當時的行為能力是否足夠、腦筋意識是否清楚,都相當令人懷疑。因此,他也很有可能只是按著貝紐夫斯基怎麼
說,他便怎麼寫。
關於他的姓名
貝紐夫斯基的匈牙利全名雖然有時寫成Benyovszky MóricÁgost,不過比較普遍的型態是Benyovszky Móric。他全名當中的Ágost 一字從何而來,目前並不是很清楚。有人說這是貝紐夫斯基自己後來加取的,因為在1746 年天主教會簽發的出生文件上,只登載拉丁文Mauritius 這個名字。此外,雖然1777 年教區牧師簽發的出生證明文件中登載著拉丁文Agustus,但因為這份文件所登載的出生年份「1741 年」之正確性就受到相當的質疑,因此,其所登載的Agustus 是什麼情況,也同樣令人好奇。這個名字或許也是當時根據貝紐夫斯基的自述而登載上去的。
事實上,匈牙利人通常也只稱他Benyovszky Móric,或僅以姓氏稱他Benyovszky。有趣的是,匈牙利人習慣以名字互稱,但卻不會單以貝紐夫斯基的名字Móric 稱呼他,這其實算是特例。因為匈牙利人只能從「命名曆(name day calendar)」上所列的名字來為新生兒取名(關於「命名曆」,請參閱第三篇第五章「如何看『登陸第一人』」),所以取同樣名字的人很多。如果只單稱Móric,大家可能會認為是泛指任何一位叫Móric 的人,並不會直覺聯想到是貝紐夫斯基。但如果單稱他的姓氏Benyovszky,大家馬上就會知道是指貝紐夫斯基。一來,這個姓氏在匈牙利並不常見;二來,這個姓氏最有名的人物,大概也非貝紐夫斯基莫屬了。
Benyovszky 是「姓」而不是「名」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匈牙利人自稱是「馬札爾人(Magyar)」,他們是一支來自東方的民族,並非歐洲大陸原生的種族。他們的源頭可追溯到亞洲大陸的烏拉山區(Ural Mountains)西麓一帶(現今俄羅斯境內)。西元896 年,馬札爾大族長Árpád 率領這支民族,由東往西來到喀爾巴阡盆地(Carpathian Basin),從此便定居下來。
也正因為匈牙利人的祖先來自東方,所以他們保有一些東方的傳統,包括姓名的排序習慣也跟多數東方民族一樣,將姓氏放在前面、名字擺在後面,與西方世界剛好相反。因此,貝紐夫斯基匈文姓名Benyovszky Móric 當中的Benyovszky,其實是他的姓氏而不是名字。另外,從貝紐夫斯基父親的姓名BenyovszkySámuel,也可以看出Benyovszky 就是其家族姓氏。
但長久以來,大家都已習慣西方人名字在前、姓氏在後的排序,反而就拿他的姓氏當名字來稱呼。再加上匈牙利人似乎也都約定俗成地習慣單稱他的姓氏Benyovszky,所以本書也就姑且從俗以其姓氏「貝紐夫斯基」來稱呼他。
為何中譯為「貝紐夫斯基」
不過要說明的是,為何我不採用過去許多人使用的「貝尼奧斯基」或「伯尼約斯基」等中文譯名,而堅持使用「貝紐夫斯基」呢?我在「維基百科(Wikipedia)」中文版的「貝尼奧斯基」條目中,曾看到有人引用我之前的著作《匈牙利─走馬不看花》當中的〈當匈牙利遇上福爾摩沙〉一文,來介紹這位「首名踏足台灣的匈牙利人」。但是他捨棄我書中以匈文翻譯的「貝紐夫斯基」,而採用英文翻譯的「貝尼奧斯基」;我後來登錄進去予以訂正,並添加一段文字說明為何根據匈文Benyovszky 使用「貝紐夫斯基」譯名的理由。
如前所述,由於國內習用的譯名「貝尼奧斯基」,其實是從英文Benyowsky 直接音譯成中文而來,但英文的Benyowsky 一字應是引用自歐洲語文。先從發音來看,w這個字母在許多歐洲語中都發音作v「夫」(如德語、波蘭語),而不像英文將ow連在一起發音作au「奧」。事實上,歐美人士唸讀他的名字Benyowsky時,多數也沿用歐洲語讀音,將w發音為「夫」。所以,中文將Benyowsky 當中的ow 音譯為「奧」是否得當?我個人認為應該有商榷餘地。其次,我想既然他是匈牙利人,理應採用匈牙利文的原始拼法及發音來翻譯,才較忠於原名並接近原音。再者,當匈文Benyovszky 改譯為其他語文時,其拼寫及發音難免會產生改變;假如再根據其他語文的拼寫進行中譯,其譯名與譯音自然也就走樣得更多了。
所以嚴格來說,由匈文Benyovszky 英譯而成的Benyowsky,其實已是第二手譯名;而音譯自英文的「貝尼奧斯基」則至少是第三手譯名,其發音自然就更加失真不實了。
順便一提,伊能嘉矩《台灣文化志》中的〈貝尼奧斯基之台灣探險〉一文可見「貝尼奧斯基在日本以ハンベンゴロウ(畔辨鄂羅)之名傳下」等語。此處提到的「畔辨鄂羅」,應是當初譯者自己根據日文「ハンベンゴロウ」直接音譯成中文加註上去的。還好這個轉了好幾手的「畔辨鄂羅」沒有被流通使用,否則就更加失真離譜了。
至於「ハンベンゴロウ」這個日文譯名,也有人將之轉為漢字「半边五郎」(或「半邊五郎」),我個人認為這個中譯似乎比「畔辨鄂羅」稍微高明些。因為根據資料,貝紐夫斯基有1 個sister(也有2 個sisters 之說)、2 個brothers,這應該是指他同父同母的兄弟姊妹。只是,這裡說的sister(或sisters)是姊姊或妹妹? brothers 是哥哥或弟弟?我們無法辨知。況且,若是再加上他父親與前妻所生,及母親與前夫所生之子女,據說貝紐夫斯基所有的兄弟姊妹一共有13
人之多。所以,此處「五郎」之排行根據為何?還是不免令人感到疑惑。
關於他的國籍
至於貝紐夫斯基的國籍問題,雖然目前普遍認定他是匈牙利人,但基於歷史、地緣、血統、感情等各種因素,匈牙利、斯洛伐克、波蘭三個國家一直以來對此都各有主張。事實上,貝紐夫斯基自己的國籍認同似乎也很複雜,說是錯亂也許有點沉重,但至少是「多重認同」。我們在航海日誌的紀事當中,也確實可以找到這樣的軌跡。
匈牙利的觀點
首先,貝紐夫斯基在他親自撰寫的《貝紐夫斯基伯爵之回憶與遊記》當中,第一卷第53 頁有段文字這樣寫著:“I was born of an illustrious family in Hungary, and served the states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with some distinction,⋯⋯” ,此處即見他自陳「吾出生於匈牙利的一個顯赫世家」。可見他理性地自認是匈牙利人;而世人普遍認定他是匈牙利人,或許便是以此為據。
再者,貝紐夫斯基的行跡及影響幾乎遍及全球,他傳奇多彩的一生更是充滿戲劇性,也因此,「貝紐夫斯基」這個名字在匈牙利早就是家喻戶曉的名號。一齣傳頌貝紐夫斯基事蹟的電視連續劇“Vivát Benyovszky! ”(《偉哉!貝紐夫斯基》,由匈牙利與斯洛伐克合拍)於1975 年在「匈牙利國營電視台(MTV)」首度播出,播放當時即深受匈牙利民眾喜愛。這齣連續劇曾於2119 年在電視頻道上再度重播並發行DVD;之後,也在匈國的「多瑙河公共電視台(Duna TV)」一再重播,同樣受到歡迎。
除了民間風潮之外,匈牙利官方其實也相當推崇貝紐夫斯基, 因此, 首都布達佩斯第8區有一條街道叫做Benyovszky Móric utca,就是以他的姓名來命名的。有個研究貝紐夫斯基的機構「匈牙利與馬達加斯加友好協(Magyar-Madagaszkári Baráti Társaság)」也就設在這條Benyovszky Móric utca 街上,門牌號碼是8 號,裡面設有展覽室展出貝紐夫斯基的相關文物。這機構的大門上有貝紐夫斯基的圖像,還標著B.M. 兩個大字母,即Benyovszky
Móric 的縮寫。
除了「匈牙利與馬達加斯加友好協會」之外,「匈牙利地理博物館(Magyar Földrajzi Múzeum)」在館長 Dr1 Kubassek János的主持之下,對於貝紐夫斯基的生平事蹟也有不少研究。博物館的學術專刊《地理博物館研究(Földrajzi
Múzeumi tanulmányok)》於1987 年3月出版的當期,就曾以「貝紐夫斯基」為研究專題,集輯了數篇匈牙利學者所發表的相關學術專文。
波蘭的觀點
那麼,貝紐夫斯基跟波蘭又有何淵源呢?當初,他由於宗教態度的問題(從天主教信仰改信基督教路德教派)不見容於當權者,因此離開匈牙利前往波蘭;之後又因參加波蘭對抗俄國的「聯盟陣線」,而遭俄軍俘虜流放到西伯利
亞坐監。或許是因為這段因緣際遇,使他始終對波蘭有著極深的情感投射,不過這應屬一種感性的認同而已。
例如他在5 月11 日的日誌中寫下了這麼一段話:“On my arrival on board, I hoisted the colours of the confederation of Poland,⋯⋯”。意思是當他們的船艦於5 月11 日準備離開堪察加半島時,貝紐夫斯基升起的是代表波蘭「聯盟陣線」的旗幟。這些文字多少顯示出他對波蘭的情感認同,以及發自內心自認效忠波蘭的想法。
不過,在航海日誌的「補遺(postscript)」文件當中,有段文字卻是這樣記錄的:“Yesterday arrived at Macao a vessel under Hungarian colours,⋯⋯”。這裡記載著他們離開福爾摩沙後於9 月23日航抵澳門,但船艦上揚起的卻是代表匈牙利的旗幟。由此又可看出他離開堪察加半島時雖情繫波蘭,但航程中似乎對祖國匈牙利依舊念念不忘,才在航行途中換了匈牙利旗幟。不過,這也有
可能是他當初進入澳門時,因為某些策略考量而臨時決定更換旗幟。
波蘭之所以主張貝紐夫斯基是波蘭人,除了因為貝紐夫斯基曾於1768 年參加了「聯盟陣線」與波蘭人並肩對抗俄國,以及貝紐夫斯基本人情感上對於波蘭的投射之外,其實還有別的因素。前面曾經提到,貝紐夫斯基曾自陳出生於匈牙利,但在有些場合他又會自稱是「波蘭的貴族」。這個說法也不是全然沒有道理,理由之一是他的祖先於14 世紀時曾一度移居波蘭,二是他的祖先
也確實擁有波蘭(以及斯洛伐克)的血統。
斯洛伐克的觀點
至於斯洛伐克聲稱貝紐夫斯基是斯洛伐克人,當然也持有自己的一套說詞。最直接的淵源,不外乎是貝紐夫斯基的出生地Verbó(斯洛伐克文稱Vrbové)就在現今斯洛伐克境內。他的童年生活都在Verbó 度過,而他當年的居所目前也都保存完好。另外,他的父系擁有斯洛伐克貴族的血統,這也是可以追溯的連結。
除此之外,另外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就是Benyovszky 這個家姓與斯洛伐克有著地緣關係。在貝紐夫斯基「1741 年」的出生證明文件當中,牧師稱他的父親是「尊貴之伯爵Saumuele de Benÿow et Urbanow」。拉丁文Saumuele de Benÿow et Urbanow 翻成匈牙利文是Benyói és Urbanói Sámuel,再翻成英文則是Samuel from Benÿow and Urbanow,中文的意思便是「來自Benÿow 和
Urbanow 地方的Samuel」。
有些匈牙利人是以地名為姓氏的,這跟祖先的來源地有關。從貝紐夫斯基出生證明所顯示的姓氏線索可知,他的祖先是來自Benÿow 和Urbanow,這兩個地方應該就是現今斯洛伐克境內的Beňov 及Vrbové。文件上的拉丁文Benÿow 即是匈牙利文Benyói és Urbanói Sámuel 當中的 Benyó,這個字也就是貝紐夫斯基的家姓Benyovszky 的字源。而另外一個拉丁文Urbanow,亦即匈牙利文Benyói és Urbanói Sámuel 當中的Urbanó,指的應該就是貝紐夫斯基的出生地Verbó。
基於他的祖先與斯洛伐克Benÿow 和Urbanow 這兩個地方有地緣關係,以及Benyovszky 這個家姓的字源也與斯洛伐克地名有關,斯洛伐克這一方自然也認定貝紐夫斯基是「自己人」。所以,1975 年與匈牙利合拍的電視連續劇“Vivát Benyovszky! ”(《偉哉!貝紐夫斯基》),當時也同時在斯洛伐克播出。官方甚至還在1996 年貝紐夫斯基251 歲冥誕時發行紀念幣,幣面是貝紐夫斯基的浮雕造像,另一面則是他航行所使用的船艦造型。
用傳奇寫人生
多樣頭銜的精彩人生
貝紐夫斯基未曾虛度他41 年的人生歲月,他一生經歷了許多不同的身分,因而被世人封以各式各樣的名號。這些稱號像是:匈牙利伯爵、奧地利軍人、波蘭反抗軍指揮官、法國軍團上校、馬達加斯加之王、探險家、殖民者、作家、棋士等等。
要認識貝紐夫斯基的傳奇一生,我們且從他的出生及童年說起。1746 年至1759 年期間,貝紐夫斯基在家鄉Verbó 度過了13年的童年時光。據說他的腿腳有點跛,跟童年時在Verbó摔斷腳有關。不久之後,他於1762 年加入軍旅參與奧地利的「七年戰爭」,但後來從部隊逃脫。1764 年,他因宗教理念不合,放棄天主教改信基督教路德教派,因此遭到背離教會之控訴。也因為他這樣的宗教態度不見容於當權者,以及一場家產官司纏身,迫使他於1766 年離開匈牙利前往波蘭。
1768 年,他開始與波蘭的「聯盟陣線」有所接觸。1769 年至1771 年間,他加入「聯盟陣線」與Kazimierz Pulaskio 並肩作戰,但卻在一場失利戰事中被俄軍俘虜並被監禁在俄國西境的Kazan。他於是策劃煽動以製造騷亂,並趁隙逃到聖彼得堡;之後,又試圖登上一艘荷蘭籍船隻,但遭船長發現而隨即將他送交俄方。
1771 年,他從Kazan 被流放,轉送到位於8,111 公里外俄國東境的堪察加半島(Kamchatka)上的一座監獄。在堪察加半島坐監期間,由於他的文化素養被當地的行政長官所青睞,便要求他教導女兒彈鋼琴。誰知彈琴變成了談情,長官的女兒竟然愛上了貝紐夫斯基,甚至後來跟著他一起逃亡,但過程中她卻不幸中彈身亡。貝紐夫斯基精心計畫這次的逃亡行動,煽動獄囚與他一起造亂起義,不但成功逃獄,還奪得一艘俄國船艦,並順利於1771年5 月12 日自堪察加半島的Bolshap 港逃離俄國,從此展開了他返回歐洲以及海上探險之旅。
這趟海上探險之旅自堪察加半島的Bolsha 港出發後,一路造訪了阿留申群島、阿拉斯加、日本、琉球、台灣、澳門、馬達加斯加、非洲,在1772 年7 月到抵法國,最後終於返回了歐洲。甚至也有不甚可靠的資料顯示,貝紐夫斯基的這趟海上探險之旅,也曾經到過墨西哥的Acapulco 港。這似乎意謂著其實他本來是想向東往美洲航行,但可能是風向或海流因素讓他的船艦轉向,而朝亞洲方向南下航行。
也就是這段起自1771 年5 月,止於1772 年7 月的海上航行,讓貝紐夫斯基一行人於1771 年8 月26 日得以造訪福爾摩沙,並展開十幾天驚險、驚異、精彩的台灣探險之行。甚至因為與原住民Huapo 頭目的一場「金蘭之交、盟約之會」,讓他差點就當上「福爾摩沙之王」。
第一篇 幻滅的福爾摩沙之王
第一章 貝紐夫斯基的傳奇一生
「貝紐夫斯基」這個名字對大多數台灣人而言是陌生的;但台灣對貝紐夫斯基而言卻不那麼陌生,因為早在二百多年前,他就與台灣這塊土地結下淵源。
貝紐夫斯基於1746 年(或1741 年, 詳後述)9 月21 日出生在當時還是匈牙利領土的Verbó,1786 年5 月24 日戰死並葬於馬達加斯加島上。
關於他的出生年份
貝紐夫斯基出生的年份有兩個說法:一是1777 年由Verbó 當地牧師所簽發的出生證明,文件上登載的出生年份是「1741 年」(航海日誌原書的編者序以及他的自述亦稱是...
作者序
莊宏哲
我於任職行政院新聞局期間,曾兩度派駐匈牙利擔任新聞外交官職務,前後兩任駐留布達佩斯長達8 年時間(2000年~2003年、2008年~2011年)。因為職務關係,有幸接觸不少匈國媒體界及文化圈人士,也因此機緣得知貝紐夫斯基(Benyovszky Móric)這位匈牙利傳奇人物,以及他曾於1771 年探訪福爾摩沙的這段歷史事件。既身為台灣人,又有這段匈牙利經驗,我對於這件牽繫著台灣與匈牙利淵源的歷史,自然產生了莫大的好奇心及求知慾,當時在心中便已興起撰寫本書的動機。直到2011年12月退卸公職之後,我終於得空拈起筆來著手這項計畫中的撰著。
這本記載著貝紐夫斯基傳奇事蹟的“Memoirs and Travels ofMauritius Augustus Count de Benyowsky”《貝紐夫斯基伯爵之回憶與遊記》,最早於1791 年在倫敦首度以英文編印發行,計有第一卷、第二卷共兩冊。有關台灣的紀事編印在第二卷,共計45 頁;起自1771 年8 月26 日探路登陸,直到同年9 月12 日離開台灣。這段紀事雖然只是貝紐夫斯基航程中短短的18 天,卻為台灣18世紀的近代史增添了難能可貴的一頁。
在本書第二篇〈福爾摩沙紀實〉中,記錄著這短短的18 天期間內,貝紐夫斯基一行人在島上與台灣原住民的接觸與互動,以及他們所經歷的各種事件,重要情節如下:(航往台灣)、探路遭襲、親自登陸、遇到貴人、再遭襲擊、展開反擊、軍頭來訪、頭目來訪、締結盟約、殖民之念、支援戰事、擒賊敗敵、辭別頭目、眾勸留足、殖民計畫、準備啟航、離開台灣、(航向澳門)。
這些事件當中,除了好幾次與原住民發生錯愕驚險的戰鬥以外,最重要且最具戲劇性的互動,當然就是「締結盟約」與「殖民計畫」這兩段情節了─因為「締結盟約」一旦實現,當時的台灣也許就不是漢人能險渡黑水溝遷徙屯墾的仙島;「殖民計畫」如果成真,當時的福爾摩沙就可能要再經歷一段西方強權的統治。歷史的「偶然」與「必然」,就在某個時空交會之際擦身而過,但卻又就此分道揚鑣。「偶然」就像輕風飄去,常讓人看不到結局;「必然」卻猶如洪流奔來,總教人隨波而逐流。這或許正是歷史的宿命,是幸或不幸?我們無從得知。所以,各位讀者讀到這兩段內容時,不妨放慢節奏仔細閱讀,好好瞭解一下這兩件差點改寫台灣歷史與命運的事件。
再者,我們透過這篇〈福爾摩沙紀實〉細膩而生動的文字描寫,對於這段被遺忘的台灣與西方之接觸史,或許剛好可以補上一課;關於一些鮮為人知的原住民風俗習性,也可以藉此機會有所認識。雖然平心而論,貝紐夫斯基在福爾摩沙這18 天的紀事,有些情節看似誇張而值得進一步推究。但我覺得即便不拿它們當史料看待,純粹當作遊記閱讀,也是相當有趣而值得的。
本書除了這篇〈福爾摩沙紀實〉是摘譯自原著外,其他如〈幻滅的福爾摩沙之王〉、〈登陸福爾摩沙之謎〉、〈福爾摩沙島民之謎〉等篇章,則純屬我個人的觀點與論述。這三篇主要針對〈福爾摩沙紀實〉當中的關鍵描述進行探討考究,讀者不妨視為延伸題材來閱讀。
至於本書的完成,在此我要感謝一位我十幾年交情的匈牙利老友。他是「匈牙利地理博物館(Magyar Földrajzi Múzeum)」的館長Dr. Kubassek János,他慷慨提供了本書部分的匈文圖資。也正因為某次我拜訪博物館時,經他介紹貝紐夫斯基「福爾摩沙之行」的事蹟,才啟發我計畫著手撰寫本書的動機。
個人學能有限勉強草就此書,雖難免野人獻曝不自量力;我之所以膽敢提筆撰作,純粹基於對此歷史事件之好奇及求知。但我相信它的成書,對於國內有關貝紐夫斯基之研究,多少能添注一些助益,並開啟可能的新觀點。
本書全文約十萬餘字,計經兩年時間陸續成篇,於2014 年2月終告撰作完成;感謝前衛出版社之編印出版,讓本書如今得以面世。唯自知僅憑旅居匈牙利之數年生活經驗以及有限資料的涉獵閱覽,本書之論述及觀點難免仍有未臻周全之處。職是之故,井蛙之見若或顧此而失彼,猶盼諸方大家不吝賜教。
莊宏哲
我於任職行政院新聞局期間,曾兩度派駐匈牙利擔任新聞外交官職務,前後兩任駐留布達佩斯長達8 年時間(2000年~2003年、2008年~2011年)。因為職務關係,有幸接觸不少匈國媒體界及文化圈人士,也因此機緣得知貝紐夫斯基(Benyovszky Móric)這位匈牙利傳奇人物,以及他曾於1771 年探訪福爾摩沙的這段歷史事件。既身為台灣人,又有這段匈牙利經驗,我對於這件牽繫著台灣與匈牙利淵源的歷史,自然產生了莫大的好奇心及求知慾,當時在心中便已興起撰寫本書的動機。直到2011年12月退卸公職之後,我終於得空拈起筆來著手這項計畫中的...
目錄
致讀者推薦文──Kubassek János博士
Benyowsky航海回憶的再回憶──翁佳音
在真實與虛擬之間──詹素娟
自序
前言
【第一篇】 幻滅的福爾摩沙之王
第 一 章 貝紐夫斯基的傳奇一生
第 二 章 貝紐夫斯基的航海日誌
【第二篇】 福爾摩沙紀實
摘譯自1790 年倫敦英文首版Memoirs and Travels of Mauritius Augustus Count de Benyowsky
第 一 章 航往台灣
第 二 章 探路遭襲
第 三 章 親自登陸
第 四 章 遇到貴人
第 五 章 再遭襲擊
第 六 章 展開反擊
第 七 章 軍頭來訪
第 八 章 頭目來訪
第 九 章 締結盟約
第 十 章 殖民之念
第十一章 支援戰事
第十二章 擒賊敗敵
第十三章 辭別頭目
第十四章 眾勸留足
第十五章 殖民計畫
第十六章 準備啟航
第十七章 離開台灣
第十八章 航向澳門
【第三篇】 登陸福爾摩沙之謎
第 一 章 重繪「海上四日」行蹤
第 二 章 初探「第一登陸現場」
第 三 章 再現「第二登陸現場」
第 四 章 釐清「登陸歷史時刻」
第 五 章 如何看「登陸第一人」
【第四篇】 福爾摩沙島民之謎
第 一 章 牽涉登陸事件的原住民
第 二 章 盟約文字與馬匹的疑惑
【後記】
致讀者推薦文──Kubassek János博士
Benyowsky航海回憶的再回憶──翁佳音
在真實與虛擬之間──詹素娟
自序
前言
【第一篇】 幻滅的福爾摩沙之王
第 一 章 貝紐夫斯基的傳奇一生
第 二 章 貝紐夫斯基的航海日誌
【第二篇】 福爾摩沙紀實
摘譯自1790 年倫敦英文首版Memoirs and Travels of Mauritius Augustus Count de Benyowsky
第 一 章 航往台灣
第 二 章 探路遭襲
第 三 章 親自登陸
第 四 章 遇到貴人
第 五 章 再遭襲擊
第 六 章 展開反擊
第 七 章 軍頭來訪
第 八 章 頭目來訪
第 九 章 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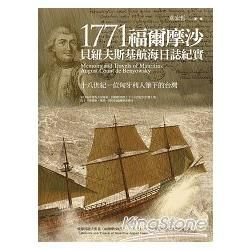
 共
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