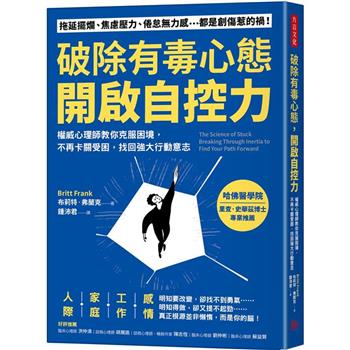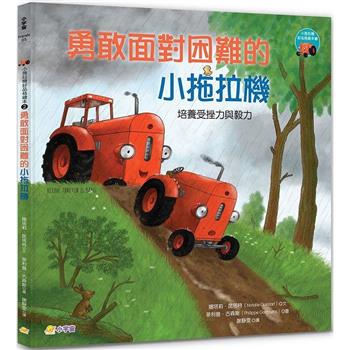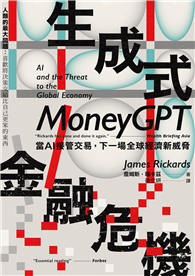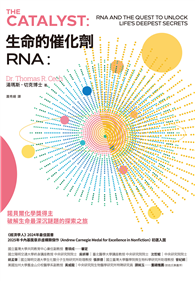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賈梅爾.吉丹尼的圖書 |
 |
$ 100 ~ 308 | 落日的召喚
作者:賈梅爾.吉丹尼 / 譯者:嚴慧瑩 出版社: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7-05-01 語言:繁體書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即使是一千零一夜,仍說不盡在這片廣闊沙漠中可能發生的故事。有一天一個人徒步穿越沙漠而來,他奇幻的旅途吸引了人們的好奇,於是蘇丹命人記下他的旅程。故事,這樣開始……
黑夜裡,不知從何處響起第一聲召喚,告訴他:出發吧!朝著日落的方向走去……於是,日幕開啟之前,他加入一支駱駝商隊,開始旅行。在商隊中,他學會了在沙漠求生的各種技巧,還獲得神祕貝督因人的奇特贈禮,一個木杯與一本古書。
第二聲召喚響起,他離開駱駝商隊,來到一座綠洲。這綠洲居民的人數永遠固定定,現在,多了一個外來者,應該如何解決人數增加的問題?而綠洲旁的神秘營地,究竟為什麼會存在?在這裡萌芽的愛情,會不會有結果?
第三聲召喚響起,他成為眾鳥之國的統治者。在這裡,所有衣物、用具都來自於鳥類,但他們從未傷害任何一隻鳥兒;所有的女子,都有令人銷魂的魅力,卻似乎隱藏著極大的秘密;還有一座漂浮的天空之城,必須具備某種能力才能入城一遊;他想得到答案,必須付出多少代價?
第四聲召喚響起,他遇上主張末世哲學、追求享樂、放浪形骸的棍子一族,儘管看慣奇聞軼事,仍然讓他難以融入。這次,在召喚未現之前,他就決定繼續追隨太陽的軌跡。
於是,他來到陸地最西方的國度,終於獲得片刻休止。他開始思考這段已經不知經過多少時日的旅程,對於故鄉、親人、路上認識的朋友、發生過的事情等種種記憶,紛紛湧現腦海,可是,這些既清晰又模糊的印象,已經難以分辨出哪些是現實,哪些是夢境……
如果召喚再起,他該何去何從?他應該越過從來沒人去而復返的大海,或者,他該掉頭回到魂牽夢縈的故土?……
雅馬‧阿德巴拉因為召喚而開始這趟不可思議的旅行,珈瑪‧阿部達蘭卻因為不良於行,一輩子不曾離開日落之國,但是,透過雅馬‧阿德巴拉的敘述,珈瑪‧阿部達蘭竟也參與其中而能對話,彼此的際遇與經驗,彷彿巧合似地相互呼應,有時候,竟讓讀者難以辨識究竟是誰在發言。
這本豐富的小說結合了神秘、性、嚴肅的省思、荒謬可笑的片段,把時間座標全然打亂(你能想像太陽高掛不到五分鐘竟然變成黑夜?夏季結束之後卻又是另一個夏季的到來?),將古埃及法老王的記憶混合可蘭經的經文,同時又充滿對於當代的觀察。《落日的召喚》是一本自傳、一本對人生苦甜的沉思集,是一本奇幻傳說,同時也是一則寓言,是對阿拉伯世界政治體制的嘲諷、也是對對自然之美的詠讚。
作者簡介:
Gamal Ghitany(賈梅爾‧吉丹尼)
一九四五年生於埃及。賈梅爾‧吉丹尼是小說家、評論家、也是新聞記者,他出版了多本小說、文集,創作跨越不同領域,被譽為當今埃及最偉大的作家之一。
賈梅爾‧吉丹尼出生於貧窮家庭,小小年紀就去當學徒,學習編織地毯。他十四歲的時候就寫出第一篇作品。十七歲,他成為地毯圖案設計者,也發表第一本短篇小說集。二十三歲,他成為記者,採訪了大小戰爭──蘇伊世戰役、以色列-阿拉伯衝突、黎巴嫩內戰、兩伊戰爭,在當記者的這段期間,也曾因為批評當時埃及總統納瑟(Nasser)的政治制度而入獄六個月。
他生命的最初三十年都在開羅度過,成長於這古老的「清真開羅」,滋養了他對阿拉伯與回教文化傳承的興趣,他特別著迷於中世紀阿拉伯文作品,尤其是埃及歷史學家Ibn Iyas的著作,這些影響都顯現在他的小說中。他的作品不同於馬哈富茲(Nagib Mahfouz,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埃及作家)的線性與社會寫實主義特色,而是具有傳散性與歷史性的書寫,試圖尋找人類在宇宙及時間的連續性中的位置,在《落日的召喚》一書中,除了可以看到《天方夜譚》的痕跡,還可以看到時空界線的混沌曖昧。
一九八○年,他在貝魯特出版馬哈富茲的傳記,同年,他獲得埃及國家小說獎(Egypt’s State Prize for Novels)。他有多部作品被翻譯成各國語言,包括:英文、法文、德文、義大利文與希伯來文。他的小說《啟蒙之書》(Le Livre des Illuminations (1990) (Kitab al-Tajalliyat))在二○○五年獲得法國年度最佳翻譯小說獎(Laure Bataillon Prize)。二○○六年,作品集《Schegge di fuoco》獲得義大利格林尚內卡渥文學獎(Premio Grinzane Cavour)。
譯者簡介:
嚴慧瑩
一九六七年生,輔仁大學法文系畢業,法國普羅旺斯大學(Universite de Provence)當代法國文學博士,專門研究當代法國女作家瑪麗‧荷朵內的創作。目前定居巴黎,從事文學翻譯,譯有《六個非道德故事》、《緩慢》、《羅絲‧梅莉‧羅絲》、《永遠的山谷》、《沼澤邊的旅店》、《口信》、《終極美味》、《灰色的靈魂》等書,並著作法國旅遊資訊相關叢書。
- 作者: 賈梅爾.吉丹尼 譯者: 嚴慧瑩
- 出版社: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7-05-01 ISBN/ISSN:986705984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其他各國文學
|
 梅爾,是義大利威尼托大區貝盧諾省的一個市鎮。總面積85.72平方公里,人口5698人,人口密度73.3人/平方公里。國家統計代碼為025034。
梅爾,是義大利威尼托大區貝盧諾省的一個市鎮。總面積85.72平方公里,人口5698人,人口密度73.3人/平方公里。國家統計代碼為025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