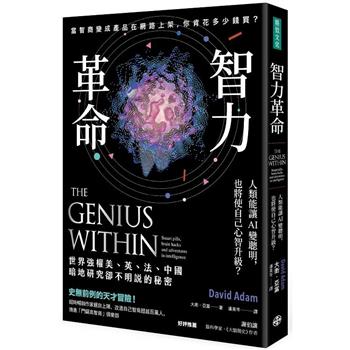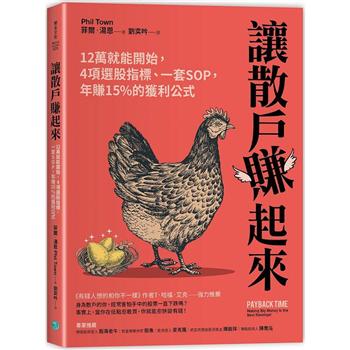序曲
我從小成長的世界,跟諸位的世界稍有差異。我的父親,是美國情報機構資深官員,換句話說,就是間諜大師。我的童年多半待在國外;很小的時候,就有一票擔任間諜的叔叔。十一歲起,我經常躲在樓梯間,偷聽父親和同事討論一些不該洩漏的機密。我從小就知道,家中電話裝了竊聽器,信件會被攔截。我具備一點認知:人人都有背叛的本能。
我很愛父親,卻不想踏上他的道路。二十三歲生日前夕,CIA主動召我加入,我敬謝不敏,想開創自己的天地。到頭來,還是走到這個下場。簡而言之,我躲在這裡,等待時機。等我的律師協同司法部與某個外國勢力達成協議,澄清對方極度關切的內幕,洗刷本人的冤屈,確保安全無虞。
在這處灘頭,我的屋子內部寬敞,但外表瞧不出來。無論從哪個角度,只能看到一小部分。純就外觀看來,毫無特殊之處。父親告誡我,這種時候要盡量放低姿態。
屋子有一座前廊,一座游泳池。屋內是西班牙瓷磚,原木梁柱,隨著陽光變色的純白泥牆。寧靜舒適,是看書、沈思、等待的好地方。我不認識附近鄰居。握手寒暄,偶爾隔著老遠揮手致意∣∣越遠越好。沿著海岸走下去,過一座橋就是大陸,有個日益繁榮的小鎮。我每週固定去幾回,買些日用品、食物、書籍等等。開車個把鐘頭,穿過沼澤和松木林,有個比較大的鎮,但算不上大城。當地有機場和一些娛樂場所。每逢律師或別人找我,就約在那裡會面。對我來說,那就是世界盡頭。我的思緒,還迴盪在另一個世界。
或許吧,追根究底,該回溯到那年夏天,我人在紐約,跟邁爾斯‧科普藍(Miles Copeland)初次見面。他是CIA元老,政戰部門的祖師爺,很可能認識我父親。他提到,政治勢力相互較勁,衍生出許多政客無法解決的問題,因為政客自命清高、標榜形象,做事礙手礙腳。針對這類麻煩,最好的方式,就是從遠方派遣特工抵達現場,不擇手段,辦完就閃。
另一次,在倫敦希斯羅機場,預定前往新德里,飛機正要起飛,卻被警車阻攔。兩位探員把我請下飛機,盤問幾個鐘頭,最後放我走。真有這種怪事!回溯逼我走投無路的陣陣狂潮,這算是第一波。
我不斷反省,怎麼會落到這種地步?從機場偵訊室,沙烏地宮殿,富豪的私人客機,跟教宗比劃拳擊,和海珊稱兄道弟,白宮的祕密會議,塵土瀰漫的阿富汗,陪著小舅子都狄(Dodi)在巴黎夜總會狂歡,朝肚皮舞孃潑灑百元大鈔……最後的下場,竟然是佛羅里達荒僻的海灘?
來此之前,我度過一個多月縮頭縮尾、心驚肉跳的日子。每晚睡在不同的地點,換不同的名字,生怕見不到隔天的太陽,那是什麼滋味?找些廉價賓館,勘查周遭環境,上床前,事先演練,萬一對方找上門,可能從這道門或那扇窗戶進來,起碼兩人以上,我插翅難逃。眼前一切正常,與其翻來覆去,不如呼呼大睡。
孤家寡人,與世隔絕,過去種種,簡直不可思議。往事如煙,那些人讓我見識了世界萬象,因為我有利用價值。我幹過的事情,證明了自己的價值。想當初,天底下沒有辦不到的事情。那個整天忙碌、環遊世界的傢伙,難道會是自己?
趁著每年此時陰雨濛濛的天氣,我待在屋內思考。我觀察天氣的變化。我該好好反省,為什麼淪落到這付田地?
雨停了,太陽露出笑臉。沙灘上漫起薄霧,船隻乘風破浪出海捕魚,風和日麗的季節,遠處傳來海鷗的聲音。此地的景象,我已瞭如指掌。我夢想乘著棕櫚葉飄向天際,飛到那些熱愛的土地,做我愛做的事情。我不應該困在這裡,任由回憶糾纏不去。
我衷心期盼這樣一天的到來,我的律師、政府法務部門,以及追緝我的若干人等,在暗無天日的房間裡,分坐長桌兩端,打字機、燈光、攝影機各就各位,有人轉向我,請我「從頭說起」。
好吧,就讓我從頭說起。我的父親是間諜,這是關鍵證據。我暗自決定,這一點我必須保密。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賴瑞‧寇博的圖書 |
 |
$ 49 ~ 343 | 我這樣一個間諜─PEOPLE 321
作者:賴瑞‧寇博/著 (Larry J. Kolb) / 譯者:韓文正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05-11-24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450頁 / 25K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賴瑞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我這樣一個間諜
一個神祕莫測的世界圍繞在我們周遭。除非知道門路,否則永遠看不到。
不是虛構的間諜故事,而是世界最頂尖的間諜實錄
現實與虛幻的差異,在於虛幻必須合乎邏輯。
比007受用的間諜守則
‧套話的最高訣竅,就是真心喜歡對方。
‧急躁容易壞事。別讓對方發現,這些消息對你價值不菲。
‧引人入殼最理想的場合,就是一對一。
‧成功的間諜只需具備一個條件──接近目標。
‧緊繃與鬆懈──循環不已。
‧祕密之戰總是在暗地裡進行。……我們看到醜陋的一面,問題是,更醜陋的真相還沒揭露。
‧特務就是間諜,間諜就是叛徒。
‧面帶笑容,輕鬆自若,畢竟,一切只是遊戲。
作者簡介:
賴瑞‧寇博(Larry J. Kolb)
出身間諜世家,父親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曾任情報官。寇博繼承衣缽,是CIA創始元老邁爾斯‧柯普蘭晚年一手調教出來的情報員。捲入印度總統大選及政爭陰謀後,上了國際刑警組織的通緝名單。直到最近,仍蟄居佛羅里達一處寧靜海灘,每天除了弄潮、聽潮,也回憶精彩的過往,把自己多年來在全球大人物身邊的所見所聞、親手主導的間諜活動,一一細述。除了《我這樣一個間諜》,目前正在進行的《夜幕美國》(America at Night)已賣出電影版權。
譯者簡介:
韓文正
資深出版人,現專事翻譯。譯作有《美國總統的七門課》(合譯)、《鏡頭下的情人》、《所謂英國人》、《人性拼圖I、II》、《蘇格蘭人如何發明現代世界》、《看見聲音》、《公共知識份子》(以上由時報文化出版)、《決策時刻》(大塊文化)等。
章節試閱
序曲
我從小成長的世界,跟諸位的世界稍有差異。我的父親,是美國情報機構資深官員,換句話說,就是間諜大師。我的童年多半待在國外;很小的時候,就有一票擔任間諜的叔叔。十一歲起,我經常躲在樓梯間,偷聽父親和同事討論一些不該洩漏的機密。我從小就知道,家中電話裝了竊聽器,信件會被攔截。我具備一點認知:人人都有背叛的本能。
我很愛父親,卻不想踏上他的道路。二十三歲生日前夕,CIA主動召我加入,我敬謝不敏,想開創自己的天地。到頭來,還是走到這個下場。簡而言之,我躲在這裡,等待時機。等我的律師協同司法部與某...
我從小成長的世界,跟諸位的世界稍有差異。我的父親,是美國情報機構資深官員,換句話說,就是間諜大師。我的童年多半待在國外;很小的時候,就有一票擔任間諜的叔叔。十一歲起,我經常躲在樓梯間,偷聽父親和同事討論一些不該洩漏的機密。我從小就知道,家中電話裝了竊聽器,信件會被攔截。我具備一點認知:人人都有背叛的本能。
我很愛父親,卻不想踏上他的道路。二十三歲生日前夕,CIA主動召我加入,我敬謝不敏,想開創自己的天地。到頭來,還是走到這個下場。簡而言之,我躲在這裡,等待時機。等我的律師協同司法部與某...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賴瑞.寇博 譯者: 韓文正
- 出版社: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5-11-24 ISBN/ISSN:9571344052
-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軍事
|
 賴瑞為一隻雄性黑白色的虎斑貓。現任英國內閣辦公廳首席捕鼠大臣,於2011年2月15日就任。目前居於唐寧街10號。
賴瑞為一隻雄性黑白色的虎斑貓。現任英國內閣辦公廳首席捕鼠大臣,於2011年2月15日就任。目前居於唐寧街10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