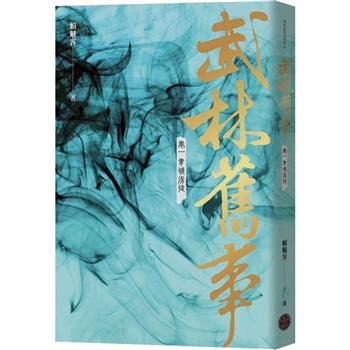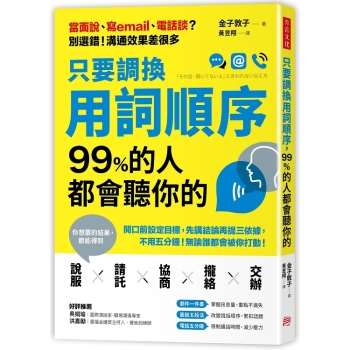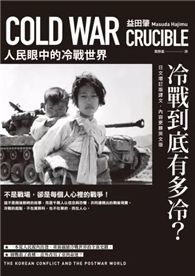霍布斯:消除真空,就是避免內戰!
一本科學史、政治史交匯處的經典作品
一段盤根錯節的科學知識誕生過程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百年精選代表作
本書榮獲2005年伊拉斯模斯獎
得獎原因:「這兩位作者完全顛覆了我們看待科學與社會的方式」
在我們生活的世界中,「實驗證明」通常就代表不需懷疑,例如「實驗證明」不含防腐劑的食物,消費者理應可以大口咬下。就像電視影集CSI,各種專家利用實驗讓證據說出真相,事實於是就在眼前。
不過你是否知道,這整套我們「信以為真」的實驗系統,曾經備受懷疑。它是經過怎樣的歷史過程,才獲得今天「理所當然」的位置?
《利維坦與空氣泵浦》帶我們回到十七世紀英格蘭這個實驗起源的年代,重現化學之父波以耳如何利用空氣泵浦展現真空的存在。更重要地,這本書向我們展示,真空的背後,如何跟權位的競逐者聯繫在一起,搶奪執政者的權力;政治哲學名著《利維坦》的作者霍布斯從這個角度,不容許任何真空的存在,以確保政治和平的使命。
觀察這個科學革命的特殊時刻,我們會發現,今天「理所當然」的實驗,其實是利用各種「社會技術」取得正當性,而非單單依賴科學家所號稱的「讓證據說話」。另一方面,現在看來「客觀公正」的操作技術,其實跟當時的政治需求密切相關。「事實」、「詮釋」、「實驗」、這些現代科學關鍵概念,其實都是建立新的政治秩序所必須的基礎。因此作者說:「知識問題的解答,就是社會秩序問題的解答。」
《利維坦與空氣泵浦》已經成為科學史的經典著作。兩位作者藉著科學爭議,撥開科學的「純粹」面孔。更利用人類學方法,將十七世紀「科學家」的工作方式,鉅細靡遺的展現在我們眼前。正如二○○五年本書獲得拉斯莫斯(Erasmus )獎時,荷蘭王室表示其得獎原因為:「兩位作者全然改變了我們對科學與社會的觀點」。因此我們可以說,要理解現代科學,此書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讀物。
作者簡介:
史蒂文‧謝平(Steven Shapin)
為哈佛大學科學史教授,曾出版《真理的社會史》(A Social History of Truth, 1994)、《科學革命》(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1996)等著作。目前興趣為減肥專家的過去與現代、企業科學以及現代學院與工業關係。他並且長期為《倫敦書評》、《紐約客》撰稿。謝平曾獲得貝爾納(J.D.Bernal)科學社會研究獎、弗萊克(Ludwik Fleck)獎、美國社會學學會莫頓(Robert k. Merton)獎、英國科學史協會丁格爾(Herbert Dingle)獎、伊拉斯莫斯(Erasmus )等眾多獎項。
賽門‧夏佛(Simon Schaffer)
為劍橋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教授,專長於物理史、科學社會史。曾共同編撰《實驗之用》(The Uses of Experiment, 1989)、《休厄爾》(William Whewell, 1991)、《啟蒙歐洲的科學》(The sciences in enlightened Europe, 1999)等書。並曾在英國國家廣播公司製作《光之舞》(Light Fantastic)系列紀錄片。
譯者簡介:
蔡佩君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畢業,清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曾任職出版社,學校,廣播媒體。現職媽媽,並為政府英文機關報執筆。譯作有《前衛藝術理論》、《共和危機》、《知識的騙局》、《多瑙河注》、《劍橋流行與搖滾音樂讀本》等。
區立遠
附錄《物理學對話錄》譯者,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畢。德國杜賓根大學古典語文碩士畢(拉丁文與希臘文雙主修),現就讀於該校拉丁文系博士班。
章節試閱
第一章 認識實驗
阿德索:「但怎麼會這樣,」我很崇拜地說:「您從外頭觀看就可以解開圖書館之謎,但在裡頭的時候卻沒辦法?」
貝斯克維爾的威廉:「上帝是如此認識世界的,因為祂在腦中構思,有如從世界之外,在創造之先;吾人不識其法則,正因身居其間,發現世界早已造成。」
艾科(Umberto Eco),《玫瑰的名字》(The Name of the Rose)
本文的主題是實驗。旨在了解實驗實作及其智識產物的性質和地位。我們試圖解答的問題如下:何謂實驗?實驗如何進行?實驗要透過什麼手段才可以說是生產出事實(matters of fact),而實驗事實和具有解釋功能的建構物又有何關係?如何辨認出一個成功的實驗,而實驗的成功和失敗又要如何區分?在這一連串特定的問題背後,猶有一更普遍的問題:為什麼獲得科學真理需要實驗?實驗是達到各方認可之自然知識中的最佳途徑嗎?其他手段可能做到嗎?是什麼促成科學中的實驗方式優於其他選擇?
我們希望取得歷史性的答案。為此目的,所要處理的問題便是:在何種歷史環境中,實驗作為生產自然知識的系統方法而出現?在何種歷史環境中,實驗實作被體制化,而實驗產生的事實變成所謂適當科學知識的基礎?是故,我們從實驗程序的偉大典範開始:羅伯特.波以耳(Robert Boyle)對氣體力學(pneumatics)的研究以及氣泵(air-pump)在該領域的運用。
波以耳的氣泵實驗在科學文本、科學教學以及科學史的學術養成訓練上都具有典律地位。綜觀科學史,這個主題可能最被認為是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可以多談。故事常常被講,大體上也說得不錯。誠然,波以耳的實驗工作及其發生的背景,許多面向都已有充分記載,似乎無法陳添新意:我們受益於前人的歷史書寫部分甚多,無法一一列舉致意。著名的《哈佛實驗科學個案史》(Harvard Case Histories in Experimental Science)中,對於波以耳在一六六○年代之氣體力學實驗所做的傑出記述為該系列的第一則,的確非常恰當。這份花了三十五年做出來的研究,令人佩服,也是本書的出發點;此研究顯示,波以耳的氣泵實驗目的是在對於如何確立真正的科學知識提供(也從此提供了)啟發式的模型。
有意思的是,《哈佛個案史》本身也取得了典律權威的地位:在此學門中如何做研究?何種歷史的問題才是適恰的?何種史料和研究相關?何者又無密切關係?而歷史敘述和解釋的一般形式應該如何等等?該系列都提供了具體的範例。然而,現在是從深植於《哈佛個案史》及其他類似研究中的方法、假說及歷史綱領中走出,繼續前進的時候了。本書想重新觀看氣泵實驗,針對這些素材提出更多問題,更換方式、重新表述傳統的問題。我們開始此一計劃,目的並非批評對波以耳實驗的既有記述。事實上,開始時我們也曾懷疑,對於過往波以耳研究的學術成果,我們還能添加多少東西。但隨著分析的進行,我們漸漸相信,我們希望已有答案的問題,前人並沒有系統性地提出過。為何如此?
一個解答可能在於「成員說法」(member’s account)和「外人說法」(stranger’s account)之間的差別。面對想要去認識的文化,一個全然外在於該文化的外人如何能認識此一文化,確實令人費解。倘若是屬於該文化的成員將會有很大的優勢;不過,成員若無反省能力,尋求理解的工作也會伴隨嚴重的缺點,其中最主要者或可稱為「自明之法」(the self-evidence method)。史家何以未能有系統地、鍥而不捨地追問我們想要提出的關於實驗實作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那是因為他們做出的說明都覆上了內部成員自明之法的色彩。在這方法下,我們自己文化慣例實作的預設,並不會被認為是個需要回答的問題。我們文化的信念和實作,通常涉及的都是明確的自然事實,或者涉及普遍無私的判準,以了解人是如何做事的(或說在「理性狀態下」是如何做事的)。如果問一個我們文化中的非專業成員,為什麼他稱鴕鳥為鳥?他可能會告訴詢問者,鴕鳥就是鳥,或者他會援用林奈氏分類法(Linnaean system)不成疑義的判準,其中鴕鳥就是歸在鳥類的。相比之下,這個非專業成員會針對一個將鴕鳥排除到鳥類之外的文化,想出一系列的解釋。在實驗文化的案例中,自明之法在史家的記述中特別凸顯;其原因頗易看出:因為史家大抵皆同意波以耳是實驗界的奠基者,而今天的科學家正活在這個世界裡,也在其中進行操作。因此,史家假定他們(和現代科學家)與波以耳共享一種文化,由此假說出發、據此處理研究對象:史家和十七世紀的實驗者皆屬成員。實驗文化的歷史發展也可以用來支持此一假說。波以耳綱領戰勝其他替代方案及反對之說,在他自己的國家更是氣勢如虹,主要受到倫敦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 of London)黨同伐異強勢宣揚的大力支持。實驗綱領的成功,通常就被當作是本身的解釋,不言自明。不僅如此,自明之法在歷史實作中呈現的方式,其實通常更為細緻;並非對於實驗的興起、接受以及體制化過程有一套明確主張,而是一種傾向,讓人無法看到:質疑實驗的性質、質疑實驗在我們整體智識地圖上的地位,到底有何重要之處。
成員說法以其相關的自明之法,有很強而直觀的訴求力;保護及維續它們的社會勢力力量強大。在共享的文化中,若有哪個成員不識相地詢問「每個人都知道的事」,就真的可能被認為是在找麻煩或者笨蛋一個。若要讓自己被某個文化排除,最有效的辦法莫過於不斷嚴肅地質問該文化已經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智識架構。於是,扮演外人就變成很困難的差事;但就實驗文化而言,這正是我們該做的事。我們必須扮演外人,而非就是外人,真正的外人是無知的。對於實驗實作及其成果想當然爾式的認知,我們希望在仔細思量後先將之懸置。扮演外人,就是希望脫離不證自明。就像舒茲(Afred Schultz)提議的外人接近陌生社會時一樣,我們希望處理「我們的」實驗文化,「不當它是庇護之所,而是冒險之地;不是當然之事,而是可質疑的研究課題;不是拆解有問題之狀況的工具,而是本身就構成難以通盤理解的問題意識。」若假裝成實驗文化的外人,那麼在解釋特定文化的信念和實作時,便可試圖挪用外人優於成員的一大優勢,亦即:外人有能力知道其他替代的信念和實作方式。知道替代方案的存在,正與解釋計畫的適恰性,兩者並進。
當然,我們不是人類學家而是歷史學家。據稱,我們與過去的某個背景共享實驗文化,而我們研究的主角之一又據稱是該文化的奠基者,如此,歷史學家怎可扮演外人角色?我們可以使用的方法之一,是指認出以往的爭議事件,並加以檢視。我們認為,那些與自然現象或智識實作相關爭議的歷史實例,具有兩項優勢。其一,它們通常牽涉到對於實存物的實在(reality of entities)或實作的適當性(propriety of practices)的意見分歧,而其存在或價值在後來都被視為沒有問題或已經解決。以柯林斯(H. M. Collins)……的隱喻來說,在對自然界的信念體制化之後,就像是一艘瓶中船;而科學爭議的案例能夠提供一個機會,讓我們了解到那船一度是一堆木條和線,而且原本皆在瓶外。研究爭議還有另一項優勢,即歷史行動者經常扮演類似於我們佯裝外人的角色:在爭議過程中,針對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對手所偏好的信念和實作,他們試圖解構其特性,其作法是嘗試呈現出那些信念和實作中,人為而約定成俗的面向。既然狀況如此,爭議各方就提供歷史家扮演外人的資源。當然,歷史學家若僅是挪用單方面的分析於科學爭議之上,並確認其為有效,那將會是一大錯誤,我們不打算這麼做。我們發現,記下爭議雙方所運用的建構和解構策略,是值得一為的。當使用參與者的說法時,不應將之和我們自己的詮釋工作混淆:歷史家為自己發言。
我們要討論的爭議發生在一六六○年代和一六七○年代早期的英格蘭。雙方主角為羅伯特.波以耳(1627-1691)和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在有系統地從事實驗的人當中,波以耳是主要角色,也是大力宣傳實驗實作在自然哲學中之價值的重要人物。霍布斯的角色則是當地反對波以耳最力者,他試圖削弱波以耳的研究所產生的特殊宣稱和詮釋,並發動強有力的論證,說明為什麼實驗綱領無法產生波以耳所舉薦的知識。歷史家在分析霍布斯與波以耳之爭時特別棘手,有諸般原因。其一,因為霍布斯自然哲學家的角色已在很大程度上從文獻中消跡了。卡爾貢(R. H. Kargon)說得對:「霍布斯同笛卡兒和賈松迪(Pierre Gassendi),三人同為十七世紀中葉最重要的機械哲學家。」不乏證據顯示,十七世紀的人們皆認真看待霍布斯的自然哲學觀,特別是那些認為他的觀點有嚴重缺陷的人,但也不只這些人。我們知道,一直到十八世紀早期,霍布斯的自然哲學論文都還是蘇格蘭大學課程中重要的讀本。但到了十八世紀末期,霍布斯大抵已被排除於科學史之外了。一七九七年第三版的《大英百科全書》中關於霍布斯的條目,幾乎未提霍布斯的科學觀,也完全忽略他反對波以耳的論文。《百科全書》一八四二年的〈數學與物理學史……論文〉(Dissertation on the History…of Mathematical and Physical Science)中狀況亦雷同。大家記得霍布斯是一位倫理、政治、心理學及形上哲學家;霍布斯堅持上述層面的關懷和自然哲學是一體的,但這樣的一體性已被分割,科學被排除不論。即便明茲(Samuel Mintz)在《科學傳記詞典》(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中討論霍布斯的條目,也只獨厚他道德、政治以及心理學的著述。幸好,自從布蘭特(Frithiof Brandt)於一九八二年所寫的關於霍布斯機械哲學的專論以來,情形開始有改善。近來討論霍布斯科學的學者,如卡爾貢、瓦金斯(J. W. N. Watkins)、夏比洛(Alan Shapiro)、賴克(Miriam Reik)、斯普雷根斯(Thomas Spragens)等人的著作,使我們受益頗多,由接下來的討論中便可看出。然而,要充分評價霍布斯在十七世紀自然哲學中的真正地位,我們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本書若能刺激更進一步的研究,就等於達成了部分目的。
卡爾貢認為,科學史家忽略霍布斯,原因之一在於他的論點和英雄波以耳相左,也因此被排除在倫敦皇家學會之外。毫無疑問,霍布斯在英格蘭所涉入的爭議,和他不被科學史家所重視有很大關係,時人認為他在每一個爭議主題上都徹底輸了。在「輝格」史學(Whig history)傳統中,敗者為寇,而輝格史學的這種傾向,在古典科學史中最為明顯。本書討論霍布斯的自然哲學爭論,至於他和瓦立思(John Wallis)及沃德(Seth Ward)在數學方面的爭議我們無法做細節處理,這方面的辯論他更是一敗塗地,之後便從史料中完全消失,比他和波以耳的爭辯消失得更徹底。史提芬(Leslie Stephen)在《英國傳記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所撰寫的條目中說,霍布斯的反對者指出他「多方面的荒謬言行」;《大英百科全書》十一版中,羅伯森(Croom Robertson)的相關述記多所擴充,但也呼應了前者的判斷。沒有一位史家提出異議。
歷史學家對於霍布斯與波以耳之爭議的討論,也是類似的情況。寫到這些爭論的並不多,即使少數論及者,也包含若干根本的謬誤。譬如有位作者宣稱,霍布斯反對波以耳的自然哲學,原因在於霍布斯相信亞里斯多德「恐懼真空」(horror vacui)的說法(這錯得離譜),另一位作者更敏感,他認為霍布斯贊同實驗法在自然哲學中的主要地位(本書也會盡力證明這一點是不對的)。這些謬誤,以及普遍對於霍布斯與波以耳之爭的忽視,部分原因可能是在於文獻。至今我們可以確定的,只有兩位史家確知曾翻閱過關鍵的文件,並釐清其中的內容:這份文件就是一六六一年霍布斯的《物理學對話錄》(Dialogus physicus de natura aeris)。霍布斯《對話錄》的拉丁原典的確從未有過譯本,而這或多或少可以解釋它所受到的忽視。(為彌補這狀況,本書提供由夏佛所做的英文翻譯於書後附錄。)除了上述兩位之外,史家們只和勝利的波以耳及同僚站在同一陣線,重複波以耳對霍布斯文章的判斷,而對於他真正想說的卻隻字不提。即使對霍布斯的科學做了十分詳細之研究的布蘭特也拒絕深入《物理學對話錄》及霍氏後來的自然哲學論文。布蘭特也接受了波以耳對霍布斯觀點的評價:
我們不會檢視《論物體》(De Corpore)〔成於一六五五年,比《物理學對話錄》早六年〕之後的作品……這些年間,霍布斯又開始深入擘畫其物理學,不下三次……但保留了與《論物體》之物理學同樣的特色。在霍布斯批評波以耳著名的論文〈關於空氣彈力新實驗〉(New Experiments touching the Spring of the Aire)中,此特色表現得特別鮮明。霍布斯在此又一次顯示他對於實驗的重要性所知有限。儘管真空實驗持續進行,儘管有氣泵的發明,霍布斯仍堅持他世界充滿物質的觀點。霍布斯晚年相當悲慘。他未充分了解英格蘭經驗科學有了偉大的發展,正發生在當時……當皇家學會成員採納實驗的研究方法後……霍布斯就再也跟不上他們了。
在這裡,我們看到處理霍布斯與波以耳之爭的標準史學策略之萌芽,或也可以說,是一般對於被否決之知識的處理方式。我們看到駁斥,對於被否決之知識提出因果解釋的雛形(這暗中合理化了駁斥),也有對被否決之知識及被接受知識兩者不對稱的處理。首先,表明被否決的知識根本算不上是知識,而是謬誤。史家的作法就是向被接受的知識靠攏,拿勝利一方對敵方觀點的因果解釋當做自己的看法。既然勝利者是如此解決掉謬誤,史家未加以處理自然也有正當理由了。因此,莫爾(L. T. More)提到霍布斯對波以耳的「訕笑」是「糊塗不通」,又引述波以耳對霍氏果斷的還擊,而未詳述霍布斯的立場。麥基(Douglas McKie)對爭議的處理,只說到「波以耳非常勝任地解決了霍布斯的論證,更優雅地平息了他動輒爭辯的衝動怒氣。」賴爾德(John Laird)在結語中說:「波以耳〔對霍布斯〕的批評實實在在是公平的,這顯示……對霍布斯特殊的物理學細節多做討論,並不會帶來多大益處……」彼得斯(Richard Peters)主張,霍布斯要發出批評,「最好是批評者本人先做過一些實驗再說」(這不可能是試圖了解關於實驗之有效性和價值的最佳方式),瓊斯(R. F. Jones)也同表贊成。其他史家則進一步廓清歷史記錄,清除實驗綱領的主要反對意見!霍爾(Marie Boas Hall)雖然沒有提到霍布斯的名字,但說「除了忠實的亞里斯多德論者」(霍布斯肯定不是),「沒有人不認為波以耳的論證強而有力,具說服力」。夏碧洛(Barbara Shapiro)對於英格蘭經驗主義和實驗主義做了極佳的說明,結語說「除了一小群揶揄大師的批評者外」(她也沒有指明是誰),「新哲學未遭到重大的反對」。
普遍而言,史家對於霍布斯立場的因果說明或不予理會,一直是以「誤解」的觀念(及其理由)作基礎。《哈佛個案史》中說,霍布斯反對波以耳的論證,「部分是基於對波以耳觀點的誤解。」史度華特(M. A. Stewart)指波以耳的氣體力學使「霍布斯不智地捲入一場對主旨不理解的爭議之中」。史提芬和羅伯森兩人皆指出扭曲霍布斯的判斷以及使他沒有資格評價波以耳綱領之有效性的因素,試圖以此解釋他之所以會產生誤解的原因:他的數理能力不足;他和波以耳發生爭辯的時候已經太老、太死板了;他個性固執而專斷;他在意識型態上別有用心。(就我們所知,沒有一位史家暗示過波以耳可能「誤解」了霍布斯。)
由於我們的處理方式摒除「誤解」範疇以及與之相關的不對稱,此處需說明一下我們的方法。幾乎毋庸贅言,本書的目的不在評價:而在描述與解釋。然而,與評價相關的問題在本書中的確很重要,在許多方面皆然。前面說過,我們會針對實驗的綱領,從佯裝採取「外人角度」開始著手研究;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本研究著眼於歷史性任務,探究實驗實作為何被認為是恰當的,以及何以這樣的實作被認為能產生可靠的知識。基於同樣的運作,我們會採取接近「成員說法」的態度,處理霍布斯的反實驗論。也就是說,我們採取的位置,是要讓反對實驗綱領的意見看起來可信、有理而且合理的立場。套句蓋爾納(Ernest Gellner)的話,是提供對於霍布斯觀點的「寬厚詮釋」(charitable interpretation)。我們的目的不是站在霍布斯那邊,更不是平反他的科學聲譽(雖然我們認為這方面他嚴重被低估了)。而是要去打破環繞在以實驗生產知識之方法的周圍那種不證自明的光環,而為達此目的,對反對實驗主義的觀點採取「寬厚詮釋」是很有價值的作法。當然,我們的抱負不在改寫清楚的歷史判決:霍布斯的觀點在英格蘭自然哲學界所得到的支持很少。但我們想顯示,在產生支持實驗綱領的自然哲學共識脈絡中,這一系列歷史判決並無所謂不證自明或不可避免之處。該哲學社群若面對其他的環境,則霍布斯觀點的收受狀況很有可能不同。他的觀點並未受到廣泛的讚揚或相信,但卻是可相信的;他的觀點不被視為正確,但觀念本身並不妨礙其他不同的評價。(霍布斯的批評確實在有些地方根據不足;但波以耳的立場中有一些方面也可能會被視為欠缺根據,甚至鬆散。如果史家想要以當今的科學程序標準評估行動者的表現,會發現霍布斯和波以耳兩人的觀點都是禁不起攻擊的。)另一方面,本書對於波以耳實驗主義的處理,會強調成規(convention)、實作協定(practical agreement)以及勞力(labour)在實驗知識的創造和正面評價中所擔負的基本功能。我們將試著指出影響知識結論之歷史背景的特徵,在怎樣的背景中,判定某些成規為適當,某些類似的協定為必要的,而涉及實驗知識生產的勞力是相配的,而且優於其他替代選擇。
我們一點也不逃避「真理」、「客觀性」、「適當方法」的問題,這類問題是我們要正面面對的。但是我們的處理方式和某些科學史及大部分的科學哲學不同。「真理」、「適當性」、「客觀性」會被當作是成就、歷史產物、行動者的判斷及範疇來處理。那將是我們所要探討的課題,不會不經反省就當成資源在討論中使用。某些實作和信念如何以及為何會被認為是適當而真確的?在評鑑科學方法時也會採取相同的途徑。就我們而言,方法論不會只當作一組關於如何生產知識的形式陳述來處理,更不是當作智識實作的決定因素。我們會陸陸續續討論到哲學家應如何做才算適當的明白言辭陳述,但也一定會從該方法陳述(method-statement)產生的確切背景、針對陳述者的用意,以及參照當時的科學實作之實際性質,來分析這種方法陳述。對於我們的計劃,更重要的是檢視被解釋為真正實踐活動的方法。譬如,我們會特別注意以下的問題:具有實驗性質的事實,實際上是如何做出的?判斷實驗的成敗,實際判準為何?實驗實際上是如何重製的,重製到什麼程度?是什麼使得重製能夠發生?事實和理論的實驗分界,實際上是如何安排的?有關鍵性的實驗嗎?如果有,是基於什麼理由被視為具有關鍵性?並將進而放寬對於科學方法內涵常見的評價,並察知自然哲學的方法和其他文化領域中或更廣的社會中的實際智識程序如何發生關聯。為此,方法之一便是將科學方法以及關於它的爭議置於社會脈絡之中。
提到「社會脈絡」,一般的理解是指向更廣的社會,而在很大的程度上,我們會注意指出自然哲學社群的行為和英格蘭王政復辟時期(Restoration)之社會整體的關聯。然而,我們用到「社會脈絡」一詞時,也另有所指。我們打算將科學方法作為社會組織的具體化形式(crystallizing form)、作為調節科學社群中之社會互動的方式,加以展現。因此,我們會廣義但非正式地使用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語言遊戲」(language-game)和「生活形式」(form of life)的觀念,旨在將科學方法視為被整合於活動型態(patterns of activity)之中。對維根斯坦而言,「『語言遊戲』一詞,是為了凸顯語言的說(speaking)為活動或生活形式之一部分的這項事實」,我們對科學方法之爭的探討,同樣是將之當作對於不同的作法以及組織人類以達實際目之不同方式的爭論。我們並將指出,知識問題的解決乃鑲嵌在對社會秩序問題的實際解決之中,而對於社會秩序問題的不同實際解決辦法,又包含了截然不同的對於知識問題的實際解法。這正是霍布斯和波以耳之爭的癥結。
讀者應可看得出,本書是一個科學知識社會學的演練。你可以辯論知識社會學的可能性,或者就直接開始動手。我們選擇後者。這來自我們另一項決定:相對上不要援引太多知識社會學的理論文獻,即使那一直是本計劃的主要靈感來源。不過我們確信,本書所採取的實際歷史程序會充分證明我們受惠於該領域之處。方法論方面,我們受惠的來源擴及許多其他方向,深刻而廣泛,無法一一致意。在霍布斯的研究方面,特別受惠於瓦金斯(對於自然哲學和政治哲學之關係的堅持),即使在關於霍布斯對實驗之態度的議題上,我們的看法與他不同;也感謝昆汀.史金納(Quentin Skinner)(在他的史學方面),雖然我們不同意他談到霍布斯和皇家學會關係的部分。在科學史家中,晚近一些人對於實際的實驗實作性質之研究,給予我們不少重要啟發:特別想到的是羅伯特.法蘭克(Robert Frank)和約翰.赫布隆(John Heilbron)。在認識科學實驗的特有取向上,我們認為最可貴的,係得自於英國和法國的科學微觀社會學家,柯林斯、品區(T. J. Pinch)、拉圖(Bruno Latour)、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還有先趨者傅雷克(Ludwik Fleck)。
既然本書受益上述各者之處顯然可見,再提出另外兩項經驗性研究,或許是滿重要的,這兩項研究和本計劃較無直接明顯的關係,但示範了與本研究類似的取向。約翰.齊根(John Keegan)在他的戰爭史研究大作中,開宗明義說道:
我不曾上過戰場;未曾接近、未曾聽聞,也未親炙戰後餘殃……當然,我讀過、談過,也講授過關於戰爭的課……但我從未親臨戰場。我愈來愈覺得,戰爭是什麼樣我幾乎一無所知。
齊根身為桑德赫斯特(Sandhurst)的老師,在自身,也在許多軍事史家身上,看到了一種無知,他自承無知的告白令人動容。若缺乏此種認知,齊根可能就無法寫出這樣一部生動憾人的史書。在我們著手本書之研究時,便自覺所處位置正類似齊根。我們讀了很多關於實驗的資料:當學生的時候甚至做過一些實驗;但對於實驗是什麼,以及實驗如何產生科學知識,卻覺得自己所知猶嫌不足。與齊根關於戰爭的記述相類似之處還更多。齊根指出絕大多數的軍事史,都是所謂「參謀部歷史」(General Staff History),此類歷史起於毛奇元帥(Count von Moltke)。在「參謀部歷史」中,意義最重大者就是將官的角色,其戰略規劃、理性決策以及對戰役最後發展的影響。這類歷史中,徹底被遺漏的是實際戰役的無常和混亂、部隊士兵的角色、實戰現場與將官的計劃之間的關係等。若在參謀部歷史中察見與科學史及科學哲學中「理性重構論」(rational reconstructionist)傾向有家族相似性,應非子虛無有。科學史的「毛奇們」出現了相同的不願涉足實際科學實作的態度,他們偏好理想化和簡化,而非混亂的偶然性;偏好談論本質,勝過指認出約定俗成的事物;偏好參照不具問題性的自然事實及科學方法的超驗判準,勝過真正科學行動者所執行的歷史研究。我們不敢說自己在實驗史方面的小小努力可以比得上齊根對於軍事史的貢獻,但是很高興能夠參與同樣的史學事業。
另外一個出乎意料的模範,在經驗焦點上和本研究的對象比較接近:那是雅培斯《描繪的藝術》(Svetlana Alpers, The Art of Describing)。可惜該書出版的時候,本書已大抵完成,所以未能如我們所欲地加以大幅援引參照。但該書與本研究計劃平行之處甚為重要,故在此簡要說明一番。雅培斯關懷的是十七世紀荷蘭的描繪性繪畫。具體而言,她想要了解的是荷蘭偏好描繪性藝術背後的假設,以及繪製此類畫作時所採用的成規。她說:「那是十七世紀特有的假設,即發現與製作;我們對於世界的發現和對世界的塑作,被假定為一體。」她證明了這樣的預設散播在不同文化領域:世界語的計劃、科學中的實驗綱領,以及繪畫,而在尼德蘭地區和英格蘭,這種情況特別明顯。荷蘭的描繪性繪畫和英格蘭經驗主義科學,都涉及一種感知的(perceptual)知識隱喻:「由此,我指的是一種文化,它假設我們是透過心智對自然的反映,而知道我們所知道的東西。」確信知識的基礎,在於親眼見證到的自然。因此,畫家的手藝和實驗論者的手藝,都是製作出忠實模仿、未經中介之觀看行為的再現物(representations)。
雅培斯的說明對我們而言有兩點特別重要。其一,她在北方(特別是荷蘭)的圖象觀念和義大利繪畫特有的圖象觀念之間,提出對照。後者,繪畫主要被認為是對文本的評註;前者,則因偏好視覺對於自然現實的直接捕捉,圖象的文本意義因而被摒棄了。對照的細節我們無法在此討論,不過雅培斯在結論中說,對圖象構成的不同理論表達了不同的知識構思:文本相對眼睛(text versus eye)。霍布斯和波以耳之爭和背後的知識理論上的衝突,與此間的平行之處一點也不準確;不過,關於實驗方法適當性的衝突方面,我們卻看到極類似的爭辯,即:爭辯眼睛和見證在生產及擔保知識上可信賴度問題。其二,雅培斯對寫實意象的性質採取我們所謂的「外人觀點」來看待。寫實意象對現實的「反映」被當作成規和手藝的產物來處理。「為求栩栩如生,圖畫必須仔細製作。」寫實再現的手藝,取決於事先接受虎克(Robert Hooke)成規:在科學中做成寫實的陳述,係基於「誠實的手」和「忠實的眼」。接受了這項知識成規,又履行了再現的手藝,則製作再現物當中斧鑿的性質消失了,再現物取得現實反映的地位。因此,本研究計劃和雅培斯是一樣的:凸顯出這些成規和手藝面。
下一章,我們將檢視波以耳為實驗哲學所提出的生活形式。指出實驗的事實得以產生、確認,並成為共識基礎所憑藉的技術、書面及社會實作。我們將特別注意氣泵的運作,以及採用這項發明的實驗之所以產生出被認為無懈可擊之知識的手段。我們會討論波以耳建議實驗主義者採行的社會及語言實作;並說明這些實作如何成為製造事實的重要構成要素,以及如何免於某些或可引發不和及紛爭的知識項目,干擾這些事實。我們在此的任務,即是指出生產實驗知識所必須遵循的成規。
在第三章,我們會討論,波以耳《新實驗》(New Experiments)於一六六○年發表之前,霍布斯自然哲學理論的地位和目標。該章主要在閱讀《利維坦》(Leviathan, 1651),並且將之當做是自然哲學和知識論來閱讀。作為政治哲學(civic philosophy)論文的《利維坦》,旨在展示確保國家秩序的實作系統。該秩序可能受到神職知識分子的威脅,他們擅自取用他們沒有資格獲得的公民權威,內戰進行期間正是如此。霍布斯認為,這些僭越動作主要是來自於一個錯誤的本體論和錯誤的知識論。霍布斯努力揭發那設想了無形實體(incorporeal substances)和非物質之靈(immaterial spirits)之本體論的荒謬。因此,他建立了空間普滿的(pleinst)本體論,過程中又樹立唯物主義的知識理論,在其中,知識的基礎就是因(cause)的觀念,而那些因就是物質(matter)和運動(motion)。配稱哲學的事業,本質上是探究因果的。它以幾何學和政治哲學的證明(demonstrative)工作為模型;更重要的是,透過其證明性產生同意(assent)。
波以耳的實驗綱領在王政復辟時期公開時,霍布斯的哲學,在《利維坦》和《論物體》(1655)所提出者已有地位。他馬上對波以耳激進的立論加以回應。霍布斯《物理學對話錄》的分析構成本書第四章的內容。在該篇文章中,霍布斯根據若干理由企圖戳破波以耳的實驗主義:他強調波以耳的氣泵缺乏物理完整性(有漏損),因此,他所推斷的事實根本不是事實;他利用泵浦的漏損,為波以耳的發現提供另一套物理解釋。泵浦總是充滿一部分大氣中的空氣,絕非操作上的真空。以空間普滿論觀點描述泵浦,要比波以耳的說明優越,而霍布斯又批評波以耳是真空論者(vacuist),儘管波以耳聲言對於以往的真空論和普滿論之間的辯論採不可知(nescience)的態度。霍布斯更抨擊了:事實的產生過程、把此種事實變成各方同意之知識基礎的建構過程、波以耳將事實和那些或可解釋這些事實的物理原因加以區分的作法;這三點抨擊在知識論上更具重要性。這些抨擊都等於是斷言:不論波以耳的實驗綱領為何,它都不是哲學。哲學是探討因果的事業,並以此確立一項全面而不可變更的同意,而非波以耳所欲達成的那種部分的同意。霍布斯的抨擊指出了實驗事實本質上是約定俗成的。
第五章中,我們要看波以耳如何回應霍布斯以及一六六○年代的另外兩位對手:耶穌會教士萊納斯(Franciscus Linus)以及劍橋的柏拉圖主義者亨利.摩爾(Henry More)。藉著檢視波以耳所作回應之不同性質和風格,我們發現波以耳最在意保護的東西:以氣泵為介,產生合法的哲學知識,並使規範實驗社群之道德生活的法則健全而完整。波以耳對待霍布斯如同一個失敗的實驗主義者,而不認為他提出的是一種相當不同的建構哲學知識的方法。他利用反駁這三個對手的機會,顯示可以如何操作實驗的爭議,而不會破壞實驗工作本身;實際上,也顯示出可以如何運用爭議,以支撐實驗知識的事實基礎。
第二、四、五章討論氣泵在實驗綱領中的核心作用,以及批評者可能如何利用運作過程的不完整來攻擊實驗本身。第六章則旨在處理兩件事:第一,觀察作為一個實物的泵浦在一六六○年代如何演化,並論證這些改變體現了對於稍早之批評的回應,特別是來自霍布斯的批評。我們揭開在該十年間成功製成的少數泵浦的資料,也指出,雖有波以耳講解作法,卻沒有人可以不看原件而自行製成可以運轉的泵浦。這使得重製的問題比史家先前以為的還有可探討之處。該章第二項任務重點正是重製。第二章中我們強調,事實的構成涉及見證(者)的增衍(multiplication of witnesses),而波以耳自己也竭力鼓勵大家重複他的實驗。然而就在《新實驗》出版後不久,另一位哲學家,荷蘭的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提出一項發現,似乎使得波以耳最重要的一個解釋資源無效(此發現即所謂水滴異常懸浮〔anomalous suspension of water〕)。我們檢視這重要的異例如何被處理,結論是,氣泵運作之成功與否的校準,取決於先前對於此現象能否存在所採取的立場。在本分析中,對於異例的反應呈顯出實驗之生活形式,以及實驗社群用以保護自身不為內部不合諧所破壞的成規。
波以耳的實驗法和霍布斯的證明法,都被提出以作為解決秩序問題的方法。第七章中,我們將對於此一問題的解答放在更廣泛的範圍來討論,即復辟時期關於社會中之同意及秩序的性質和基礎的辯論。該辯論提供了一個脈絡,為了製造和保護秩序所設計的不同綱領得以在此脈絡中加以評估。我們想在此說明自然哲學史與政治思想暨行動史之間交叉互涉的本質。一個解決方式(波以耳的)是整飭自然哲學之家,補救其中的分歧,並從其與政治哲學擾嚷不休的爭辯關係中抽離。如此加以修補之後,自然哲學家的社群就能建立其在復辟文化中的合法性,並更有效地保障社會中的秩序和正確宗教。另一解決方式(霍布斯的)則主張,要確保秩序,只有透過建立一種證明式的哲學,這種哲學讓自然、人類和社會之間都不存在界線,而其中也無異議(dissent)產生。
最後一章將提出本書的研究對於科學史和政治史所隱含的意義。我們強調知識生產和保護的問題是政治中的問題,相反的,政治秩序的問題也總是涉及對知識問題的解答。
第一章 認識實驗阿德索:「但怎麼會這樣,」我很崇拜地說:「您從外頭觀看就可以解開圖書館之謎,但在裡頭的時候卻沒辦法?」貝斯克維爾的威廉:「上帝是如此認識世界的,因為祂在腦中構思,有如從世界之外,在創造之先;吾人不識其法則,正因身居其間,發現世界早已造成。」艾科(Umberto Eco),《玫瑰的名字》(The Name of the Rose)本文的主題是實驗。旨在了解實驗實作及其智識產物的性質和地位。我們試圖解答的問題如下:何謂實驗?實驗如何進行?實驗要透過什麼手段才可以說是生產出事實(matters of fact),而實驗事實和具有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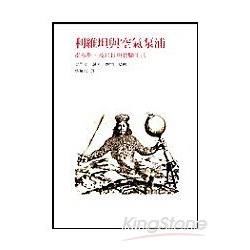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