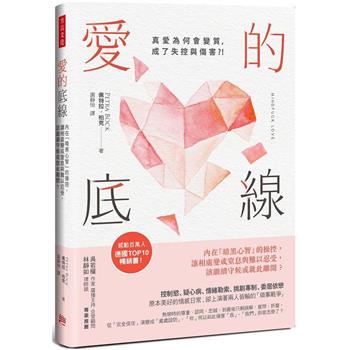◎
神逸
「神」字起源於甲骨文「申」字,象雷電曲折之形,原始符號意指為閃電,
有著上古初民對大自然的敬畏,象徵無上的大能。
感應如飛電馳光,觸發似疾雷奔霆,
何來莫名的感知,竟將自我意識與神揉合成一個想像的世界,
引出萬物,沒有界限。
《易·説卦》:「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這不是應該的名字 ◎阿翁
(一)
睡不著的時候天就暖了,
我就看見你
杉杉屑屑週圍滿是針
一直的事情演化
你就愈來愈兇惡
睡不著的時候天變低
左側右側麻麻的記憶
手撕著肚晾著門口咔擦響著
週圍有人沒人我睡在一絲吊竿上
這些那些事做成飛快的油彩
暈眩裡世界光華 品質飢渴
我輕輕笑出來
(二)
初碰
說不知道這是什麼
一下子便出來了
出來後
天地仍然暗
她說
我願意
氣體慢慢開裂
出現了一絲的感觸
遲來的相遇
本來已經掉頭了
卻在枝葉間輕搖慢瀉
還將你層層包過
包得天地間都淡淡的輕黃
輕黃
如芽地生長
尖尖刺著你
愛麼要麼都不容易
但她總在那兒
但我總看不見
整座山的青氣持續在手中
還播著遠古石上的文字
文字永遠不老
咬著你我相碰的種子
神的臉 ◎孫得欽
試想一張神的臉,大至無垠
一聲巨吼,將你完全包圍
將你的世界完全包圍
你的日常生活就是他的臉
你踩踏他,嚼食他
吹過你皮膚的風是他的呼吸
試著每分每秒都這樣想
忘了,就再想起
窗外忽然傳來的鳥鳴
浸透身體的溫泉水
對面大樓玻璃反射過來的光
你用他的眼淚洗臉
梳頭時梳的是神的毛髮
你的念頭就是他的念頭
痛苦時,歡樂時
你發出神的呻吟
二月 ◎廖人
花樹吵雜
暴力安靜
周身清冷
蛇進入鋼琴
天空是沒法寫生的
少年憂真
憂不真
年輕的君王
在曠野
放牧惡靈
看洪水
高高站在岩壁上
你停止演奏
走回自己的身體
穿過破碎的鏡子
面向
三千個中央
來往的風都被切開
你是音樂
以萬物為懸崖
(收於《2022臺灣詩選》)
小幽靈 ◎邢辰
我死去之後,媽媽把我種在院子裡的李樹下。她一個人從城市跋涉,回到我們遺失了很久的房子。白天,她將樹枝放進爐灶,燃燒的火是她的伴侶。夜晚,房子四周的幽靈織出一塊透明的布,保護她的夢境。
日子在四季輪替中消逝,媽媽的記憶亦是。現在她的生活中只有燒火和睡眠兩件事。燒火的時候,她進入夢境。睡眠的時候,她回到童年。
長在泥土裏,我變得愈來愈稀薄,同時愈來愈寬闊。我長滿了一整個院子。太陽不躲避的時候,媽媽從灶前回頭,她看著李樹投在地上的陰影,像是看到一個小幽靈在玩單腳跳繩。然後她摘了顆李子,又跑到櫻桃樹下擼一把櫻桃,通通把它們放進嘴裏。
夏天是果實成熟的季節,小小的幽靈在整個時空中蕩一隻鞦韆。
夢想中的詩歌節 ◎翁文嫻
2002年 台北《文化快遞》9月號
心被碰到了,動而成詩。詩語言可發出一陣陣的光織網,將死去的人與活著的人,東邊的或西邊的甚麼,無厘頭地連成一片,我們在寬闊呼吸中去到太初以來的的純真無邪──這全部過程又可是極私密的事,某人某刻在斗室或暗角中便完成。但是,如果要變成「詩歌節」,那就好比將一些會發光的字,從天上摘下來,黏到社會群眾的眼前、身上。
詩歌節的宗旨可有二:一、親近那些已出現了的詩的文字;二、抽出那些尚未爆發的、龐大熔岩狀態的,在眾人深藏的詩意。
不是很遠的昔日,還會用毛筆時,詩不時掉在客廳飯桌間,文字的美離我們很近。現代生活改變,則必須換一種方法。詩歌節的項目之一正需要大型的「詩展」,將詩文字與裝置藝術結合,詩可以寫在長裙上、帽沿邊、撐在傘面、寫在內衣褲上,用竹竿吊起來。隨著詩內容的轉變,展出可以是千奇百怪的。有人用麻將方塊刻詩,觀眾看完正版還可自己搓亂重排;有人將詩投在水缸底,透過水的演漾閱讀;有人將幾百行的長詩一句一紙條長長吊著,隨風吹盪,詩名曰「鞦韆」,男女不對焦的愛請語句,起起落落,令人心神錯亂。古人光是吟詠派別就夠繁多,但現在詩可用吉他,也可用搖滾的,雖然若干名詩人已有不少文字譜了曲,但「詩歌節」的意義正是「發生進行中」才可貴,因此,我們要那些未出版的詩文字,請作者本人自徵寫曲的朋友為他譜歌,即席唱出最新鮮的創作。如果有舞蹈就加舞蹈,會演戲的就加演戲,參與演出的事先登記,主辦單位稍微分區排先後,完全的自發,將創作者拉上觀賞者,才情便可瑰麗燃燒。
因為詩的靈魂在於「字」,每一個字需慢慢吟味。主辦單位便必須將參展的詩編成詩刊,預先讓人閱讀,再附記每一首詩的展出方式、時間、區域等,可按圖索驥尋找。詩裡「字」的空間宏大,可有許多解釋,開研討會未免太正經,不若鼓勵一小撮一小撮的人,樹蔭下咖啡旁激辯,吵個面紅。或者可以請作者在一旁,細說從頭,或者喜歡時吟詠一兩下,聽眾必須付費(金錢與詩是平衡的)。而且,前所說的詩之裝置,也可以來個「大黑店」般買賣:作者說喜歡這個人今天子夜可來電溝通,一吻成交,或者有些只要半打啤酒。已前有樁買賣不錯,主人將詩換來一隻波斯貓。喜歡錢的可用錢,喜歡貝殼用貝殼,一切隨主客雙方的意。想到錢還有更有賺頭的,就是用現代詩作成「籤」問卜。大可開放三五個不同的詩社(最好是老、中、青不同年齡層的),各自設計不同的「神」及「儀式」,重點令觀眾念力集中,達成某種氣氛,求問。各年代詩社選出作籤的詩自然不一樣,那才有趣。但現代詩語意的模稜兩可與難解,絕對比古詩過之無不及。因此,解籤的人,權高威重,面相莊嚴,內心過癮,這絕對比大學講壇上的學者表情及靈感多一百倍。令全台北市民大街小巷,公車站旁都可以籤詩問情問財,便達致全民讀詩的運動了。
要開掘群眾的詩感覺,先從識破文字污染開始。詩歌節重頭戲需在月明星高的夜晚,將城市裡說自己尚有夢的人帶到廣場,或點燃火把去一個森林公園,燒。將自己說錯的話,有遺憾的話寫下,將所有不能真誠、沒創意、不對題的公共文字(夠爛的電影譯名、政府文宣、夠疲乏的政治人的話),謊言髒言,嘮叨道理,全部寫出來,如送垃圾時間般拿去,燒,讓他們變成灰,消失在清空裡。
接下來,如果有流觴曲水,可以喝酒;有點點音樂,可以清唱;主要是先認識你身旁的人,然後呢?然後有幾千百種可能的途徑。韓波說,他抱起靴子,輕輕彈弄如六弦琴般的鞋帶;斜坡上,一個大菜籃般倒在臉上,那滿筐深邃悠久的神秘。
言之寺院時間線
這一個特定宇宙,吾等皆存在其間,
是詩的引力將眾星會集,在穹窿拱頂,在言之寺院。
一條條與阿翁聯繫起的因緣,
是連結起諸多星系的虛擬線,
如銀光纖絲晶透交織,
閃亮成不可名狀的星座,
綺麗妖豔。
如天文學家們觀測星象,紀錄當下抵達的光。
夜空興起私密的浩瀚感。
喔,那是西格瑪星,
看哪,地平線右上方的環狀小行星帶,
那是邪惡機甲帝國文明的慰靈地。
如大航海探險船隊,揚帆駛向海平線遠方的火山島。
民族誌學家在海圖上筆繪,標註島上有食人族,
烏面白紋,紅首似火燒頭髮,持弓矛裸奔,喜褻玩獵物。
聽說上個世紀末有考古學家出土了古老的圖騰柱,
尚皮耶說: Génial, c'est peut-être la dernière pièce manquante du puzzle.
這城市的行動詩學運動者常出沒在大黑店喝冰啤酒,
彼此哈囉,一起去「界末」海產店吃生魚片,
他們主張沒有一個人是局外人,
他們會闖入詩答答動物園的猛獸區,
快閃起舞,與獅子四目相對,
他們認為所有通感都是與生俱來,並高舉標語「祝你幸福」。
(大眾也祈願他們幸運)
詩的起源可能來自不一樣的母親。
在詩意的天文奇觀中,
不時有超新星爆炸,新恆星誕生,
持續為生命與美提供了必要的元素。
也必有中子星碰撞。
縱使生活如星塵般紛亂,終將熔融為黃金,
成為重質量的經驗,在個體內心熾熱的地核中藏隱。
只有不可捉摸的靈思如小行星般逸軌飛炸,
才顯化成文字,見光出地表,將既有詮釋更新。
也許只是單純活著,自在隨天體運行。
春夏秋冬看似畫了一個又一個相同的圓,
但在時間維度裡,意識已螺旋成另一個次元,
某個人觀測。紀錄。
確認了某個人存在。
多數人觀測。再疊加上多數人的紀錄,
就是一座時空傳送門的開啟,
無數可能性,一步即跨過去。
當是一個老花的業餘天文愛好者,
手中僅握有一張粗糙、簡陋又片面的星圖,
深信透過多方來源的魔法交相合流,
原本紙張線條斷失的空白處,
將隨時間生成輪廓更華美更不可思議的形貌。
一條拉長放大的時間虛線,
有無量訊息密布在線與線之間,
間隙自有無限宇宙無窮綻開,
一朵金花,忽現。
昨天也是今天。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超維度互動股份有限公司的圖書 |
 |
$ 237 ~ 270 | 言之寺院-天生善人會特刊 :神明
作者:阿翁,高興,林妡芮,張容箏,邢辰,許明涓,黃湘涵,Saint Lemonade(阿閃),李妍慧,王天寬 出版社:超維度互動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3-10-01 語言:繁體書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公司
公司也稱為公司行號,是指依法成立,以營利為目的,由股東投資形成的企業法人,從事生產、貿易或提供服務等。
 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言之寺院-天生善人會特刊 :神明
◎「詩」是「言」與「寺」的結合,是可用來供奉拜拜,高達神明的語言。
◎代理經銷 白象文化
我們在各種廟宇的詩意空間,鍊洗文字。期待有一天,不知道哪一人,新的詩句帶有神力,成為未知領域的「文獻」。猶如朱利安耙疏東西方信仰的傳續,最終出現一個新詞:Incommensurable(不能約比),未出現在任何系統中、不能整合、無以名狀的……
作者簡介:
◎
本書作者群來自2022年成立之「言之寺院天生善人會」成員。
包括詩人阿翁、藝術創作及評論家劉高興、小說家駱以軍,
以及1990至2022年間,分別在文大文藝創作組或成大中文系,曾師習於翁文嫻所教授之詩學,並持續以詩意開拓生活之美,不斷探索意識邊界的眾多詩人們,
如:張寶云、右京、廖人、吳俞萱、孫得欽、王天寬、黃柏軒、張家祥...
章節試閱
◎
神逸
「神」字起源於甲骨文「申」字,象雷電曲折之形,原始符號意指為閃電,
有著上古初民對大自然的敬畏,象徵無上的大能。
感應如飛電馳光,觸發似疾雷奔霆,
何來莫名的感知,竟將自我意識與神揉合成一個想像的世界,
引出萬物,沒有界限。
《易·説卦》:「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這不是應該的名字 ◎阿翁
(一)
睡不著的時候天就暖了,
我就看見你
杉杉屑屑週圍滿是針
一直的事情演化
你就愈來愈兇惡
睡不著的時候天變低
左側右側麻麻的記憶
手撕著肚晾著門口咔擦響著
週圍有人沒人我睡在一絲吊...
神逸
「神」字起源於甲骨文「申」字,象雷電曲折之形,原始符號意指為閃電,
有著上古初民對大自然的敬畏,象徵無上的大能。
感應如飛電馳光,觸發似疾雷奔霆,
何來莫名的感知,竟將自我意識與神揉合成一個想像的世界,
引出萬物,沒有界限。
《易·説卦》:「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這不是應該的名字 ◎阿翁
(一)
睡不著的時候天就暖了,
我就看見你
杉杉屑屑週圍滿是針
一直的事情演化
你就愈來愈兇惡
睡不著的時候天變低
左側右側麻麻的記憶
手撕著肚晾著門口咔擦響著
週圍有人沒人我睡在一絲吊...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遇見神明 ◎阿翁
啊!遇見神就會「明」?會發「光」?以前只認識「誠」則「明」,但現在主體的「誠」很不靠譜,可能愈以為是「誠」,愈弄得一塌糊塗。
小小一片台灣,神明就365天數不完。以前愛過那些像燙滿小圈頭髮的神廟,後來才搞清楚是民間道教。各種佛門聖地也在台灣:佛光、慈濟、法鼓、中台、淨土、靈鷲?講都說不清。另一種更遍佈莊嚴深入民心的,天主基督各派長老,西方的摩西來到幾千年後,從未知道釘十字架故事的華人社會,於是法國漢學哲學家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1951-)將西方《聖經》神學如何演變「現代性」...
啊!遇見神就會「明」?會發「光」?以前只認識「誠」則「明」,但現在主體的「誠」很不靠譜,可能愈以為是「誠」,愈弄得一塌糊塗。
小小一片台灣,神明就365天數不完。以前愛過那些像燙滿小圈頭髮的神廟,後來才搞清楚是民間道教。各種佛門聖地也在台灣:佛光、慈濟、法鼓、中台、淨土、靈鷲?講都說不清。另一種更遍佈莊嚴深入民心的,天主基督各派長老,西方的摩西來到幾千年後,從未知道釘十字架故事的華人社會,於是法國漢學哲學家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1951-)將西方《聖經》神學如何演變「現代性」...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天生善人會神明2023
序言- 遇見神明
神逸
這不是應該的名字
如來
牧羊人記
嫦娥
林默的神秘迴圈
媽祖接過炸彈之後
雲中君 · 二度降臨
道祖
山鬼
大象需要技巧,神不用
她可以表達
菩薩
詩的生產流程──與L 的對話
膜
窗外失神
要不要一起做寶殿裡的大雄
殘響
潛意識第三層之催眠旅行
夏令營比冷氣還凍人的3 分鐘
樓上的地基主
如神
神的臉
藥師佛
觀自在菩薩
月老
更傾芳酒酹花神—記2023 年花朝節
有什麼在那邊經過....... ?
覺- 夜曈繪圖作品
脊系列
神思
緣之空
風中的餘韻
火端的光芒
地底的熔...
序言- 遇見神明
神逸
這不是應該的名字
如來
牧羊人記
嫦娥
林默的神秘迴圈
媽祖接過炸彈之後
雲中君 · 二度降臨
道祖
山鬼
大象需要技巧,神不用
她可以表達
菩薩
詩的生產流程──與L 的對話
膜
窗外失神
要不要一起做寶殿裡的大雄
殘響
潛意識第三層之催眠旅行
夏令營比冷氣還凍人的3 分鐘
樓上的地基主
如神
神的臉
藥師佛
觀自在菩薩
月老
更傾芳酒酹花神—記2023 年花朝節
有什麼在那邊經過....... ?
覺- 夜曈繪圖作品
脊系列
神思
緣之空
風中的餘韻
火端的光芒
地底的熔...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