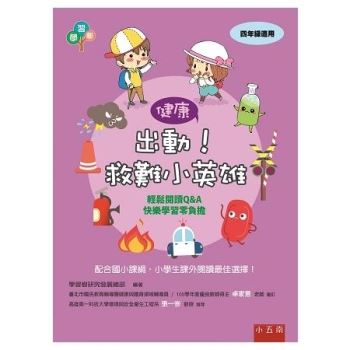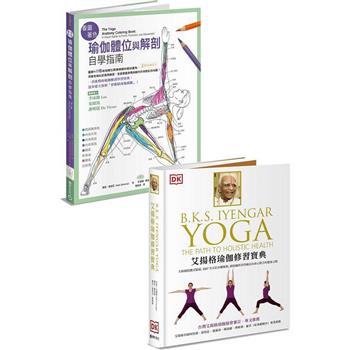國王的新冠:現代性、瘟疫想像、傳統智慧(廖咸浩)
美國小說家傑克倫敦所撰的《荒野的呼喚》(The Call of the Wild)這本充滿生態關懷的小說馳名於世,也建立了他在生態文學的聲譽。然而,他在1910年出版的篇短小說〈史無前例的入侵〉(“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在中文世界雖不甚知名,卻可以讓人對他完全改觀。小說中描述的是,面對中國在二十世紀人口爆增而如瘟疫般往隣國強迫移民,西方以軍事行動干預但毫無效果之後,有人想到以病毒來對付中國,而於1976年在美國的號召下,全球以軍隊船艦在所有的海陸邊界將中國團團圍住,然後再由飛行船在高空施放各種各樣的病毒,讓中國人大量染病死亡,逃至邊界者則一律格殺勿論。幾年後西方再進人中國全面消毒,順便將殘存的中國人徹底滅絕。最後再從全世界的白人國家移民至中國,並從而世界帶來空前的和平與盛世。這是以關注生態及社會主義胸懷知名的傑克倫敦突發的狂想嗎?不,這是他的懸念之一。他曾在1904日俄戰爭期間在中國戰場報導時,寫給《舊金山考察報》的一篇題為〈黃禍〉(yellow peril)的文章中已經使用了不少小說中所採用的內容,甚至語言也極為相似。而在1909他也寫過一篇〈如果日本叫醒了中國〉(If Japan Awakens China)的文章,一樣憂心忡忡的擔心中國崛起、危及西方。尤其最可怕的是,中國人口眾多,不用武力都可以淹沒西方。
於是在這篇小說中,他提出了後來希特勒口中的「最終解決方案」。(Swift) 顯然,26年之後,日本人聽到了。在東北的731部隊已做了不少細菌戰相關的實驗,而且在好幾場中國戰場的戰役都已經小規模使用。32年之後,希特勒也聽到了。只不過猶太人散居歐洲各地,無法採用這個方式。
小說中把中國人想像成如瘟疫般無法阻擋,可謂人類對異己的終極想像。而以細菌或病毒進行種族清洗滅絕也是回應「人形瘟疫」的終極版本:對方是瘟疫的話,我自以瘟疫對付之。這也是當代「生物政治學」的終極想像。
提這篇小說的目的是因為,這個故事幾乎觸及了本文要討論的每一個主題:
瘟疫的想像:它是什麼?來自何處?
此想像之延伸:誰是瘟疫?
瘟疫如何解決?:阻絕於門外,並加以撲滅
如何面對內在的邪惡?:疫病真正源頭(包括真正的或想像的疫病)
在中西的歷史上,對瘟疫都有兩種並存的解釋:一是上天的懲罰,二是邪魔的作祟。
前者指的是上天或上帝對人類不遵守道德規範所施加的懲罰。(Cooke;林富士)如聖經中的埃及瘟疫或希臘神話中底比斯的瘟疫。前者是上帝用以懲罰埃及法老對他的不敬(利未記),後者是奧林帕斯諸神對伊底帕斯的傲慢所予的懲罰。中國對疫病的記載早期比較簡略,但到了漢代以後,除了歸咎於水土環境之外,也會開始反省是否人的行為本身有以致之?也就是說,瘟疫是上天所降的災難,用以警告為政者的施為可能踰矩。(林富士)
而認為疫病來自特定鬼魅的想像,則引發了各種各樣驅邪的企圖。比如古希臘知名的「罰馬剋死」(pharmakos),或聖經中的「代罪羔羊」(scapegoat),中國的儺,以及流傳至今的王船祭,皆有此意。只要把災難趕出去(多半是趕到文明之外的荒野或大海),疫病就會消失,一切就會恢復正常。
所以,一種是經由自省以找回人與世界間恰當的關係,一種是怪罪他人並且以排除想像的代罪羔羊來象徵性「解決」問題,這是人類面對疫病時的兩種不斷辯證、且也常常並存的的態度。很遺憾的是,認為疫病是上天的懲罰的看法,隨著科學與科技的發展逐漸消失之後,關於疫病是來自邪魔的原始恐懼,不但沒有因此消失,甚至隨著科學的控制力增強而與時增長。原因之一也是因為科學科技的哲學本來就是將有害者排除。
西方自古這一個路徑的疫病想像,多半認為疫病起因於陌生人。一開始認為瘟疫是由陌生人所帶來,後來因為恐懼而經由「隱喻式推衍」演變成了陌生人本身就是瘟疫。經此,瘟疫與陌生人逐漸成了孿生兄弟:瘟疫來自陌生人,而陌生人常有如瘟疫。因此,瘟疫期間對外來人口的敵視,其來有自。這次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以後,在歐美的亞洲人遭到歧視固然非常典型,但在台灣內部對於武漢甚至大陸台商毫不保留的歧視,乃至後來對所有海外回國的台灣人的敵意,更是大家親眼看見、甚至親身參與的現象。(這也就是阿岡本說的「神聖之人」(Homo sacer)。)但是對外國人(歐美,或日本)反而很少有敵意,這是為什麼?在這裡我們就看到了撒依德所謂「東方主義」的問題。我們需要追溯一下西方疫病的歷史。
就疫病而言,西方對亞洲如此敏感,也跟黑死病據傳與蒙古軍隊西征有關(當然這也可能是栽贓)。雖然,將疫病與黃種人聯想之前,西方已經率先屠殺了大批的猶太人(因為當時猶太人是歐洲人數最多的「外來人口」,而且猶太人前此已經不止一次被用作「代罪羔羊」),但最終黑死病與黃禍又結上了不解之緣。這個聯想讓西方從此動輒將亞洲人,尤其是黃種人視同瘟疫。這種東方主義式的聯想,其實與當時的社會條件並不符合。當時中國與印度都比西方在各方面都先進許多。(Dussel; Abu-Lughod)
而這種想像也非始自今日。比如說最近非常有名的修西底德斯(Thucydides)在他的傳世之作《伯羅奔尼撒戰史》中,便描述了當時發生於雅典、造成三分之一人口死亡的瘟疫,但他不免說疫病來自伊索匹亞,傳入埃及後再進入雅典。而二十世紀初德國作家湯瑪士.曼所著《威尼斯之死》的主角艾申巴赫最後死於疫病,而文中對此疫病來源的描述就是來自印度恆河那既濕又熱、當然免不了髒亂的遠方。在2010年,紐約時報還報導了最新科學研究認為黑死病起源於「中國或中國附近」。
二十世紀末以來隨著各種全球化而出現大規模人口移動(尤其是難民潮),更強化了西方對於所有外來人口「東方主義式」的敵視。
蒙古西征這個歷史事件,另外還凸顯了一個關於疫病的特質。蒙古跨歐亞大陸的統治所形成的「蒙古安全架構」(Pax Monglica),常被當代學者視為第一個全球化時代的來臨。但關於黑死病來源的傳聞也讓人意識到,瘟疫不請自來,而且勢如破竹,並且在短時間之內橫掃數十、甚至上百個政治體制,幾乎可以說是最早的「另類」全球化力量,只不過是人人恐懼的全球化罷了。
這正是今天西方反全球化主要的理由,但是跟當年傑克倫敦那個時代西方人反移民及反混血的原因並沒有差別:外來人口如「瘟疫」一般,不但會搶走工作機會,更重要的是會污染種族的純粹,乃至造成種族的滅亡。(Young)一個眾所周知的謬論就是,白人和猶太人混血,生出來的還是猶太人。黑人的身份更是立足於「一滴論」(one drop of blood):「有一滴黑人血」,就是黑人。這種東方主義的想像最後更堂而皇之的理由是:這些落後人種(或「人形瘟疫」)也是造成一切問題,包括生態問題,的根源。
看看以下這位美國知名的激進生態學者大衛.福爾曼(David Foreman)的言論,就可以舉一反三:「人類已經變成了一種病,就是『人痘』」。(We humans have become a disease, the Humanpox.)或「我認為人口過剩是今天地球最根本的問題」。關鍵問題當然是:「人口過剩」發生在什麼地方?北美洲或歐洲嗎?當然是第三世界。
這就是為什麼在西方通俗文化中以疫病為主題的作品,竟然至少有兩部談到恐怖份子想要以能讓人不孕的病毒來扼止全球人口膨脹的問題。而更讓人驚恐的是,丹.布朗在《達文西密碼》之後的小說的《地獄》一書中,主角在發現恐怖份子之病毒意在讓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不孕時,竟覺得不必做任何挽回的努力,因為畢竟地球確有「人口過剩」的問題。
然而,疫病的來源雖然往往無法確知,但卻無疑的與人類對大自然的擾動有必然的關係。人類因為各種資源(包括食物)的需求(或「假需求」)不斷的「開拓」自然,應該是疫病一再發生的深層原因。因為這些病毒本來與人類並無接觸,接觸之後才會產生突變形成新的種屬而開始肆虐。因此瑪莉.雪萊(《科學怪人》的作者)的另一部科幻小說《最後一個人類》(The Last Man),就很明智的把疫病、戰爭、氣候暖化這三者並置,特別是強調疫病因暖化而變得更為猖獗。
因此,把疫病的來源歸諸地域或種族是沒有看到人類對大自然長年的侵害,尤其是現代性(也就是資本主義)出現後,以更有效率、更深層的方式傷害自然。醫藥愈來愈發達的當代社會,疫病的頻率與強度卻也史無前例,這次的病毒更出現了許多過去的病毒所沒有的特質。顯然,瘟疫是「天災」,更是「人禍」。人類除了持續用科技來解決科技造成的問題(效果堪疑!)之外,恐怕更需要從人與自然的關係來思考疫病的問題。也就是人類對自然的客體化、資源化、商品化。
但人與自然的關係,要責難的不是「人口(過剩)」,而是「人心(貪欲)」;不是第三世界人口過剩,而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真正對生態進行侵害,並造成病毒四處蔓延的不是陌生人,而是我們自己。病毒在我們的思維裡、在我們的內心中。我們對異己的敵意想像,都來自於想要掩飾自己內在的邪惡。在這次疫情中我們已有不少體會,而且有些國家的領導人甚至日復一日的如此操作。目的就是要透過這種推諉策略(blame game),咬住一隻該死的代罪羔羊。
正如愛倫坡的短篇〈紅色死神之面具〉(The Mask of the Red Death)中所描繪的,公爵以最嚴密的方式把眾人隔離在城堡中,以為疫病已被阻擋在外,而放心的日日在其中狂歡。但死神還是戴著紅色的面具出其不意的現身。原因很簡單:疫病在心裡,不在外面。心與自然的規律衝突了,病必然不請自來,什麼銅牆鐵壁也擋不住。
在傳統中國社會,瘟疫大多被認為是人類全體必須共同「承負」之惡,沒有人是唯一的禍首,也沒有人能獨善其身,而必須共同負起責任,才能消弭災禍。比如,道教就認為,終結疾病的根本之道,是要同時從個人、社會、國家、宇宙的「改善」入手。(林富士)而這裡所謂的改善還是必須回到包括傳統儒釋道皆強調的:人對天(自然)的尊重,天(自然)與人的和諧。看似老生常談,但因為我們遭現代性洗腦而遺忘久矣,如今更迫切的需要重新認知。
最終而言,我必須再次強調,面對病毒時,「不要問鐘聲為誰何響?就是為了你!」。(John Donne)——如果你不明白問題的源頭就是你自己對自然的態度。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趙寬子的圖書 |
 |
$ 198 ~ 360 | 思想 41: 新冠啟示錄
作者:郝志東/陶東風/榮劍/白貴理/子安宣邦/山室信一/藍弘岳/趙寬子/曾金燕/石富元/熊秉真/廖咸浩/周桂田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11-26  共 11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1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新冠啟示錄(思想41)
本期的專輯是「新冠啟示錄:從全球化到人類世」,面對新冠病毒史無前例的衝擊,全球在驚恐之餘,各方都開始思索下一步應如何踏出。而新冠可謂全球化與人類世的合體。從今以後,我們已無法忽視全人類/全地球之間緊密相連、禍福與共的事實。台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在疫情正熾之時,舉辦了論壇,請到醫學、歷史、文學、風險治理、經濟、國際關係等不同角度的學者,反思此次疫病與全球化及人類世的因果、糾結與啟示。本期還有「帝國日本的歷史及其殖民地」專題、「抗疫與生命政治」專題、訪談導演艾曉明女士,以及多篇學術論文。
作者簡介:
編者
思想編輯委員會
作者
郝志東(澳門大學榮休教授)
陶東風(廣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榮 劍(獨立學者)
白貴理(愛爾蘭科克大學教授)
子安宣邦(大阪大學名譽教授)
山室信一(京都人文科學研究所名譽教授)
藍弘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趙寬子(首爾大學日本研究所副教授)
曾金燕(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博士)
石富元(臺大醫院急診醫學部主治醫師)
熊秉真(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教授及台灣研究中心主任)
廖咸浩(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及台灣大學外文系特聘教授)
周桂田(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及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中心主任)
杜震華(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及中國文化大學全球商務學程副教授)
張登及(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及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副院長)
徐先智(安徽安慶師範大學人文學院講師)
章節試閱
國王的新冠:現代性、瘟疫想像、傳統智慧(廖咸浩)
美國小說家傑克倫敦所撰的《荒野的呼喚》(The Call of the Wild)這本充滿生態關懷的小說馳名於世,也建立了他在生態文學的聲譽。然而,他在1910年出版的篇短小說〈史無前例的入侵〉(“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在中文世界雖不甚知名,卻可以讓人對他完全改觀。小說中描述的是,面對中國在二十世紀人口爆增而如瘟疫般往隣國強迫移民,西方以軍事行動干預但毫無效果之後,有人想到以病毒來對付中國,而於1976年在美國的號召下,全球以軍隊船艦在所有的海陸邊界將中國團團圍住,然...
美國小說家傑克倫敦所撰的《荒野的呼喚》(The Call of the Wild)這本充滿生態關懷的小說馳名於世,也建立了他在生態文學的聲譽。然而,他在1910年出版的篇短小說〈史無前例的入侵〉(“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在中文世界雖不甚知名,卻可以讓人對他完全改觀。小說中描述的是,面對中國在二十世紀人口爆增而如瘟疫般往隣國強迫移民,西方以軍事行動干預但毫無效果之後,有人想到以病毒來對付中國,而於1976年在美國的號召下,全球以軍隊船艦在所有的海陸邊界將中國團團圍住,然...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致讀者
新冠肺炎從年初橫掃全球,造成四千多萬人罹病,一百多萬人死亡,經濟、社會方面的損失更難以估計。疫情至今未歇,甚至有再現高潮之勢。這場災難顯然需要正視,我們也希望刊登相關的文章,反思災難所暴露、所帶來的各種問題。但是疫情屬於「非常態」的緊急狀態,一般習慣於「常態」的人文、社會知識未必適用。正如新的疫苗與藥物還在研發、實驗的過程中,目前的相關討論也必須經過摸索與試探的階段,只能看作一種初步的嘗試。
本期的專輯「新冠啟示錄:從全球化到人類世」,是台大高研院一次工作坊的成果。高研院廖咸浩院長邀集了...
新冠肺炎從年初橫掃全球,造成四千多萬人罹病,一百多萬人死亡,經濟、社會方面的損失更難以估計。疫情至今未歇,甚至有再現高潮之勢。這場災難顯然需要正視,我們也希望刊登相關的文章,反思災難所暴露、所帶來的各種問題。但是疫情屬於「非常態」的緊急狀態,一般習慣於「常態」的人文、社會知識未必適用。正如新的疫苗與藥物還在研發、實驗的過程中,目前的相關討論也必須經過摸索與試探的階段,只能看作一種初步的嘗試。
本期的專輯「新冠啟示錄:從全球化到人類世」,是台大高研院一次工作坊的成果。高研院廖咸浩院長邀集了...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三個政治角色:從他們在美國問題上的分裂談起(郝志東)
也談五四激進主義與文革的關係(陶東風)
民族意識濫觴與民族主義歧途(榮 劍)
「公民宗教」與儒學:日本的過去,中國的現在,以及當前的儒學研究(白貴理)
帝國日本的歷史及其殖民地
重思「日本近代化」:於明治維新一百五十年之際(子安宣邦)
日本帝國形成的學知與心性(山室信一)
你的忠臣也是我的英雄:鄭成功、江戶文藝與日本帝國的臺灣統治(藍弘岳)
東亞體制變革與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做為「思想課題」的歷史認識(趙寬子)
思想訪談
紀錄...
也談五四激進主義與文革的關係(陶東風)
民族意識濫觴與民族主義歧途(榮 劍)
「公民宗教」與儒學:日本的過去,中國的現在,以及當前的儒學研究(白貴理)
帝國日本的歷史及其殖民地
重思「日本近代化」:於明治維新一百五十年之際(子安宣邦)
日本帝國形成的學知與心性(山室信一)
你的忠臣也是我的英雄:鄭成功、江戶文藝與日本帝國的臺灣統治(藍弘岳)
東亞體制變革與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做為「思想課題」的歷史認識(趙寬子)
思想訪談
紀錄...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