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到說故事這檔子事,
我講得硬是比別人出色。」
吉蒂.季林不僅故事說得出色,在母親交上討厭的新男友方面──尤其是他們可能成為討厭的新繼父的話──她更是世界級的偉大專家。所以她才被老師派到樓下黑漆漆、無人打擾的失物櫃去跟海倫.強森說話……
《窈窕奶爸》作者安.范恩最傑出的作品,滑稽、感人且帶有她獨特的幽默感和寫實面,是個讀來令人難以抗拒的故事。
如果你沒讀過英國作家安.范恩(Anne Fine)的原著小說《Madame Doubtfire》,一定也看過由羅賓.威廉斯所主演的電影《窈窕奶爸》吧!安.范恩是英國現今當紅的作家,不但作品得獎無數,她也是英國二○○一至二○○三年的兒童文學桂冠作家!甚至還在英國女皇的生日時,獲頒了OEB榮譽呢,那是一種只頒給對英國有特殊貢獻者的獎項。
安.范恩的小說從逗趣到嚴肅的都有,但喜劇性的多半較成功,其中《金魚眼叔叔》可說是頂尖的一部了。在美國,《金魚眼叔叔》也被改編成電影,名叫「我與金魚眼的戰爭」。安.范恩的慧黠幽默,以及她一向所關注的家庭問題及社會公共議題,都在《金魚眼叔叔》這本書中巧妙地融為一爐了。而女主角吉蒂高超的說故事技巧,差點兒讓人忘了,整本書──我們正在閱讀的──竟只不過是她窩在一個昏暗狹小的儲物櫃裡,向同學海倫所述說的一個故事而已呢,多麼了不起的本領!
《金魚眼叔叔》是個贏家:慧黠滑稽、心思纖細、溫暖人心……一本好可愛的書!
──英國衛報
安.范恩這麼優秀的作家太寶貴了,不應單單保留給兒童才是。
──英國獨立報
各界推薦
得獎紀錄:
1990年英國卡內基文學獎;1989年英國衛報兒童小說獎;2001年英國史馬堤斯童書獎6-8歲金牌獎;美國圖書館協會傑出童書;國際閱讀協會青少年首選好書;美國學校圖書館期刊年度好書;德國少年文學獎入圍;誠品「好讀」推薦選書;新聞局優良讀物推薦;「好書大家讀」選書
得獎紀錄:1990年英國卡內基文學獎;1989年英國衛報兒童小說獎;2001年英國史馬堤斯童書獎6-8歲金牌獎;美國圖書館協會傑出童書;國際閱讀協會青少年首選好書;美國學校圖書館期刊年度好書;德國少年文學獎入圍;誠品「好讀」推薦選書;新聞局優良讀物推薦;「好書大家讀」選書
章節試閱
今天海倫來到學校的心情簡直爛透了。她看來好奇怪,而且她的眼睛好紅好腫,又不肯跟任何人說話。如果有人想跟她說話的話,她立刻肩膀一聳,轉身就走。她趴在課桌上,把腦袋埋在兩隻胳膊中間,等待第一堂上課鈴響。
「有什麼不對嗎?」
只聽得悶悶的一聲,「沒有!」
「海倫,你怎麼啦?」
「沒事!」
她抬起頭來說得好憤怒,幾乎噴出了口水。我們覺得有點被嚇到了。平常的她大概是我們班上最溫柔的同學。她想必是出了什麼不得了的大事。
盧老師走進教室的時候,我們看得出她也深有同感。
「海倫,你怎麼啦?發生什麼事了?」
又是一聲悶悶的「沒有!」
她連頭都沒有抬起來,也沒有設法把話說得禮貌一點的意思。
盧老師抬起眼睛,把我們其他的人望了一圈。然而海倫的腦袋仍安安穩穩地趴在課桌上,盧老師臉上現出「有沒有人知道她出什麼事了?」的表情,於是我們全都搖搖頭,聳聳肩膀。
然後,第一堂課的鈴聲響了。
「請大家就座,」盧老師說,「點名。」
點名簿裡夾了一張辦公室送來的名條。我們等著老師把它從信封裡拿出來,她看過之後,扮個小小的鬼臉,然後朝海倫瞄了一眼,這才拿起她的筆。
「報號。」
「一,」安娜.亞契喊道。「二,」蕾拉.艾欣喊著。這是我們點名的方式,也是盧老師節省時間的偉大點子之一。每個人都按照姓名字母順序排列,然後每天我們就輪流從一號喊到三十四號。我是二十二號。
「十八。」「十九。」「二十。」
一片靜默。
(海倫是二十一號。)
通常盧老師不會為此大驚小怪。如果我們因為什麼人還在埋頭猛趕昨天晚上的功課而卡在什麼號碼上的話,她不過抬眼看看人在不在,然後自己報了號碼,我們就繼續往下報號而已。這一回她卻不是如此。
「二十一號?」
每個人都望向海倫。她仍然拚命想要把頭埋在桌面板底下。
「任務控制中心呼叫二十一號,」盧老師說。她目不轉睛地盯著海倫看。「我知道你在那裡,二十一號,請跟我說話。」
還是靜悄悄的,這會兒我們都在看了。海倫.強森的行為舉止怪異成這樣的時候 ,肯定出了什麼天大的事。
盧老師給了她一點時間,然後:
「拜託……?求求你,求求你,拜託……?」
「噢,閉嘴!」令人驚愕莫名的是海倫一躍起身,把椅子往後一推,刮得地板嘎吱響。她抬起桌面板,然後砰的好大聲用力關上,她的筆全給震得飛向四面八方。「看在老天份上,別來煩我!」
然後她匆匆衝過教室,打開教室門,咚咚咚咚衝了出去,只剩下那門旋轉時嘰嘰嘎嘎地響。
每個人都驚訝得瞠目結舌。
「好啊!」盧老師過了一會兒才後悔地說。「我可處理得真好,不是嗎?」
她看來頗為震驚的模樣。
「這不是你的錯,」艾莉絲讓她放心。「她也不肯跟我們任何一個人說話。」
盧老師朝躺在點名簿裡的紙條投以一瞥,然後又若有所思地望著大開的教室門口 ,老遠傳來更多的門一一砰砰打開又關上的聲音。
「我想最好指派一位同學去找她比較好,」她說。「只是陪她待在衣帽間,直到她平靜下來為止。」
她的眼光直直朝我望過來。
「吉蒂。」她說。
我完全沒有料到她會選上我。「為什麼是我?」我嚷嚷道,同時指著教室的另一頭。「你應該讓麗茲去陪她才對。麗茲是她最好的朋友。」
「就是你,」盧老師說。「你才是我特別挑選的人。快,現在就去,免得她衝出學校,給車子撞了。
麗茲想要替我說話,看得出她也覺得盧老師挑錯人了。
「我不能一起去嗎?」
「不行。」盧老師把手指尖湊在一塊兒望了一眼,先看看我,再看看麗茲。
「不是瞧不起你,麗茲,」她說。「不過我想這回吉蒂可能是執行這項任務的最佳人選了。」
(現在你該知道我們為什麼都背著她叫她盧瘋子了。)
我站起來,開始把書收拾到書包裡。
「甭擔心你的書了,」盧老師說。「快去跟在她後面。」
「那我不上課啦?」
盧老師從她的講桌後面跨出來,並且把教室門開得大大的。
「快去!」
我把書包用力摔到課桌底下,然後匆匆衝到門口。
我走過她身邊的時候,她對我敬個禮。
「我們都靠你了,二十二號。」她說。
我還以為她在說什麼笑話。
要猜出她走哪一條路並不困難。那麼許多的門一扇扇打開,又砰砰關上,想必是跑到樓下的衣帽間去了。我把最後一道門輕輕打開。
「海倫,你躲起來了嗎?」
沒有回答。我沒把握她會不會回答,但我很有把握她一定躲在裡面什麼地方。麻煩的是衣帽間實在大到不行——一排排的掛架上掛滿了冬天的厚重大衣和毛呼呼的圍巾。要在裡頭搜索失蹤的人,說不定得花上好幾個小時。
我可不傻。我用的是妹妹茱蒂從多次捕捉脫逃的黃金鼠經驗中練就的絕招。首先我一腳跨進房間,口中大喊一聲:「海倫?海倫?你在這裡面嗎?」緊跟著我帶了點不耐煩地嘆一口氣,然後兩腳在原地快速踩幾下,再把背後的門喀啦一聲穩穩帶上。
接下來就是等待了。
不多久我就聽到了,起先是小小的抓面紙的聲音,接著是長長的吸鼻子聲,最後是超大的擤鼻涕聲。
「找到了吧!」
她像是一隻被燙著的貓似的一躍而起。
「給我滾開!」
她的模樣看來怪恐怖的,不騙你。要是你看見她的話,你會以為她家裡每一個人都給海浪捲走了。她的臉整個腫起來,鼻子流著鼻涕。她對我尖聲咆哮:「不要管我!」
「不行,」我告訴她。「是老師叫我來的。我得坐在這裡,等你平靜下來。我的責任是絕不讓你跑出去給車子壓扁了。」
「給車子壓扁了?」這會兒她除了心煩意亂之外,又多了一臉的困惑。「喔,給車子壓扁了。」
這個消息似乎讓她氣勢減弱了一些,她不再凶巴巴地對我瞪著一雙怒眼,於是我趁著她態度稍稍軟化的機會,趕忙一把拿起對面凳子上的一雙曲棍球靴,這才在兩件濕到不行的外套中間坐下。她似乎已經不在意多出我這麼一個不速之客,也似乎已經接受我有責任坐在這一堆盪來盪去的鞋袋和不成雙的襪子中間,好讓她別給車子壓扁了。在我們學校,所有的老師與大部分的學生家長都有一種深切的恐懼,唯恐有一天會有什麼同學衝出校門的時候不長眼睛,結果不幸葬身於什麼送貨的卡車輪胎下,壓成了稀巴爛。因為我們學校位於小鎮的中心。數學課畫街道圖的時候,我們把想得到的東西全畫了上去,連每個人的父母在我們早上離家上學時說的每個字都寫上去。那真是一幅怪模怪樣的街道圖。艾莉絲說她父母總是告訴她說:「要當乖乖的小豆芽喔。」其他人的父母說的則跟這句話差不多:「過所有的馬路時,都給我當心點!」
現在海倫正往口袋裡掏面紙呢。淚水順著她的臉頰滾下來,她的嘴巴張著,兩片嘴脣看起來像魚似地掀動。我猜她的鼻子塞住了,她無法呼吸。
我實在看不下去,於是跳起來,開始掏每一個口袋,一件一件大衣找著,直到我終於找到一小包面紙為止。
「哪,拿去。」
海倫真是善良,她還沒來得及抽出面紙來擤鼻涕,就已經抬起頭來瞄一眼掛釘上的號碼,並且用顫抖的聲音問話了。
「面紙是誰的?」
「我的老天爺,」我說。「不過是面紙罷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洩露了自己的不耐煩,不過海倫立刻在我眼前崩潰了,而且又開始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我覺得自己真是殘酷又野蠻,不禁暗暗罵起盧老師真沒概念,怎麼不派麗茲來幹這個差事呢?麗茲才知道該怎麼辦啊,她可是海倫的死黨呢。她會用雙臂圈起她的肩膀,給她一個安慰人心的擁抱。
我笨手笨腳地伸出一隻胳膊到她背後,試探性地輕輕捏了她一下。
「手拿開!」她怒聲低吼道。「別碰我!」
「好極了!」我快快跑回對面凳子我的位子坐好。「當然好啦!我再不會靠近你了。我就安安靜靜坐在這裡數大衣好了。」
我坐在那裡安靜地數著大衣,可是海倫那邊的大衣完全沒辦法數,因為這會兒她的模樣看起來實在糟糕透了,糟到我倆都感到好難為情的地步。於是我只有任憑眼珠子四處亂轉,真希望剛才帶了書包下來,那樣的話,至少還有書可以看。我最討厭坐在某個地方但手上沒書可讀的時候。我是那種早餐桌上的玉米片盒子被拿走之後,立刻會大為緊張起來的人,因為沒有東西可以讀了。
再說衣帽間裡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瞧的,畢竟我們都穿同樣的衣服。四百件女生的大衣——好大一片深藍色的衣海。要是你能相信的話,這是一間女子學校。是我媽送我來這裡讀書的。她受夠了每天早上都要為我應該穿什麼衣服上學,和飯盒裡要裝什麼午餐而爭吵的日子,晚上又往往為了我帶回家的每一張爛報告,而大吵一架。
「這個打了分數沒有?」她會這麼問道,滿臉懷疑地盯著任何她發現的東西。「為什麼老師都沒說說你那些恐怖的錯別字?」要是我把功課藏起來的話,就會聽到這樣的話。「你一整天都在幹麼?我敢說你啥事也沒做吧?你也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對不對?學校希望你們長大跟豬一樣啥都不懂嗎?」
這話說得有點刻薄呢,不是嗎?以前我就不得不忍受好多這樣的話。然後有一天 ,我放學回家的時候,犯下一個十分嚴重的錯誤,那就是告訴媽說我需要洗髮精做科學家庭作業。
她眼睛瞪得老大。
「你們科學課在上什麼?」
「頭髮的保養。」
「頭髮的保養?」
她發起火來。你就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事。她氣瘋了。然後她打電話給我住在柏威克的老爸告狀。
「上課教洗頭髮!」她對著電話尖著嗓子罵道(我不得不把分機從耳朵旁邊拿開 )。
「別傻了,蘿絲,」我老爸說。「她一定是在學什麼髮根、毛囊和皮脂腺之類的東西吧。」
老媽一手摀住話筒對著我怒聲哇哇叫說:
「你是在學什麼髮根、毛囊和皮脂腺之類的東西嗎?」
我一手摀住分機話筒,也對著她哇哇叫回去。
「不是。我們只學油性髮質、中性髮質,還有乾性、燙過的和受損的頭髮。」
然後她又重新怒氣沖沖起來。從她大聲嚷嚷的樣子聽來,她壓根就不需要電話,我猜住在柏威克的每一個人,恐怕都可以聽見她的聲音吧。
「再這樣下去,這孩子只會長一顆豬腦袋,什麼都不懂,」她告訴我老爸說。「 學校的功課不過是一些爛爛的報告、彆腳的實驗,還說什麼『錯別字不重要』。我要去找一間像樣的學校,一間真正教人讀書、老師用紅筆認真批改作業,學生都安安靜靜上課的學校。」
「可是吉蒂很喜歡她現在這個學校啊,」我老爸說。「你這樣可能會讓她不高興呢。」
「不高興總比當文盲好吧?」老媽凶巴巴地回嘴,然後又繼續說什麼接受好的教育是一輩子的投資。聽她這麼說得沒完沒了,你會以為我是一筆按生活指數調整的退休金還是什麼的。 之後,老爸便豎起白旗投降了。
「或許你說的對,」他說。「上回她過來跟我住的時候,我提到平赫斯特太太,她還以為我說的是幫我洗衣服的太太咧。」 「你看吧!」老媽得意極了。「你還能指望什麼?她沒有學到半點歷史,除非你把好幾年前做的黑死病報告也算在內的話。」
而他們似乎覺得這樣事情就已經決定了。老媽出門開始看一所又一所的學校,挑選真正教人讀書、老師用紅筆認真批改作業、而且學生都安安靜靜上課的學校。 唯一的問題是,這是一間只收女生的學校。 「我可不能上都是女生的學校。」我哀嚎道。
「為什麼不能?」她說。「你還說你是什麼女性主義者?女生有什麼不對?」
於是我就來上學了。這會兒習慣之後,我還挺喜歡的。等你聽膩老師絮絮叨叨、對你說個沒完的時候,書桌底下有幾本真正的好書可讀,要比讀些爛報告好多了。完全的寂靜也不至於壓得你透不過氣來——你總是可以低聲說幾句悄悄話。偶爾你會在你寫的功課上面,看見紅色墨水寫的一些體貼又激勵人心的話。老媽也更滿意了,現在我每天起床後,都穿上同一件跟別人一模一樣、黯淡又可悲的深藍色制服,午餐盒是不准帶的,而且我已經不再去想學校沒有男生這回事了。
「海倫,不是為了男生吧?」 「才不是!」 我多少也猜到應該不是。海倫比她實際年齡顯得小很多,如果你懂得我的意思的話。偶爾在星期六的早上,我會在超級市場看見她跟在她媽的推車後面買菜。上星期我就看見她跟一個男人走過洗衣粉旁邊,那人和我老爸一樣,頭上已竄出一根根的白髮。他從紙袋裡拿出什麼東西要給她,她卻倔強地別開了臉。或許他們兩人剛剛吵了一架吧。
「那人是你老爸嗎?你是不是剛剛跟他吵過一架?」 「我才沒有!」 她睜了一雙怒眼瞪著我,彷彿我是她這個世上最大的死仇大敵似的。 「喔,對不起。」 「聽著,」她大聲吼道。「我並沒有要求你到這裡來,所以請你少來煩我!」 即使是聖人,也只能忍受這麼多吧。我忍不住發飆了。
「你給我聽著,」我也吼回去。「我也沒有要求錯過我最愛上的美術課,到這個霉味十足的臭地洞裡來,讓你大呼小叫的啊!所以請你說話禮貌一點。」 我從來就不是那種善於安慰別人的人。這會兒,她的眼淚像決堤似地流下她的臉頰,就算是說她剛剛碰上一場雷雨也不為過。
「噢,吉蒂,」她聲音顫抖地說。「對不起。」 就在那個節骨眼,隔著牆壁,我聽見第二堂課的鈴聲響起。我不能讓任何人看見她哭成這副德性。
「快,」我說。「趁大家還沒有趕去上課,趕快躲進櫃子裡。」 我伸手把她拉起來,她還來不及抽手,冷不防瞥見兩排架子中間鏡子裡自己的模樣。她看來實在狼狽透了,那張臉哭成一塊一塊紅紅的,眼睛周圍腫得活像是頭大肥豬,而且裡面佈滿了血絲。乾掉的眼淚讓蒙住臉蛋的頭髮糾結成硬邦邦的一團。
「噢——噢!」 「快啦。」 我用力扯著失物櫃的門把,直到門跳開為止。那是一種滾珠軸承裝置,緊得不得了,因此有些人以為這道門總是上了鎖。櫃子裡有一顆燈泡,因為它其實算不上什麼真正的櫃子,而是一個好小好小的房間,斜斜的屋頂好陡好陡,正好卡在後方的防火梯下面。除非你是個侏儒,否則根本站不起來,於是你不得不坐在一堆堆別人遺失的東西上面。其實坐起來還滿舒服的,不過如果學校的體育老師才剛剛大清倉的話,那裡就只會剩下一隻網線斷裂的舊網球拍,和那隻模樣古怪的靴子了。
我們運氣不錯,裡頭堆滿了東西。我把海倫往一堆看來很柔軟的東西上推,自己就站在門口把風,直到我聽見第一批趕去上課的說話聲音為止。我又等了兩、三次關門聲,之後果然不出我所料,麗茲已經在兩排架子中間輕輕走來走去,同時左顧右盼地,正在找她最要好的朋友。
「海倫在這裡面。」我指著櫃子說。 「她有沒有好一點?」 「沒有。更傷心了。」 麗茲扮了個鬼臉。「也許應該把她送回家才是。」 櫃子裡傳來一聲「不——要!」隨即乍然而止。 「她不想讓人送回家。」我告訴麗茲。 麗茲不安地老是往後瞧。 「我是絕對不該到這裡來的,」她告訴我。「盧瘋子硬是叫我離得遠遠的,還一直說,『這回得靠吉蒂才行。』我想她真是瘋了。」 她看著我的樣子,彷彿若是任何人覺得應該派我而非派她來排難解紛的話,我就該頭一個跳起來同意那人想必是頭殼壞去了。
「也許你該走人了。」我建議道。 「也許吧。」 她又回頭看了一眼,彷彿唯恐盧老師隨時可能會出現在衣帽間的門口似的。後來她傾身向前,橫過我伸出的手臂,朝黑漆漆的櫃子裡喊道:「待會兒見,海倫。」 她轉向我。「我會告訴盧瘋子說你們躲在櫃子裡,」她說。「免得她擔心你們兩個都給車子撞扁了。」 說完她把書包背高了些,這才慢慢走向衣帽間的門口,我還聽見她嘴裡喃喃說著一句話。 「我就是不懂她幹麼找上你……」
我根本懶得回答,因為我實在想不出該說什麼,也不懂自己為什麼被選中。據我所知,吉蒂.季林這個名字在咱們學校的教職員辦公室裡,從來不是以善解人意出名的。尤其自從有一天早上,艾莉絲因為她養的兔子莫力斯年老力衰,再也無法爬進爬出牠的籠子而心情沉重的時候,我竟建議把牠的名字改為「沒力氣」之後。
所以為什麼選上我呢?為什麼是我?可是盧老師想必有她的理由。海倫和我肯定有什麼共通的地方,除了我們老媽都在同一家超級市場買菜,我們老爸頭上都冒出白髮之外……
可是我明明見過海倫的老爸,他頭上可是一根毛也沒有,完完全全是個不折不扣的大光頭。而且她的父母比我老爸、老媽離婚還要更久。
我把櫃子的門用力一把拉開。她還弓著背坐在那裡,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 「我知道了!」我大聲喊道。「我知道你為什麼心情這麼惡劣!我知道你為什麼快把眼睛哭瞎掉!我知道你為什麼不肯讓人送回家了!」 她抬起兩隻憤怒、泛紅的眼睛,那目光從陰暗的櫃子裡射過來,活像是兩塊燒紅的炭。
「你媽打算要嫁給那個灰白頭髮的人!」 她的嘴巴不由地張開,我覺得自己彷彿是春風得意的福爾摩斯。 「而且你覺得他根本就是個大壞蛋!你一直都覺得他是個大壞蛋,但你是乖巧、懂事的海倫,個性溫柔、有教養的你又不願意說難聽話。這會兒你媽卻說什麼你們即將一起過著快樂幸福的日子,你再要解釋自己不喜歡他已經太遲了。」
她拚命把她的手指頭扭得死緊,我真怕會給她扭斷了。 「不喜歡他?」她重複說道,聲音好冷、好低沉。 她的臉色好蒼白,血色盡失。 「海倫?」 我打開櫃子的電燈開關。她很幸運,我還從來沒見過光線這麼昏暗的燈泡。我鑽進櫃子,坐在一堆舊的體育短褲和毛衣上面,然後把門拉上。 「聽著,」我說著身子朝她靠過去。「這種事你不需要告訴我,我可是世界級的專家。海倫.強森,我能告訴你的故事可多嘍。」 她抬起頭。 「那你說啊。」她說,依然是一臉的死灰。
「等你聽完就知道了。」我把一隻挺尖的靴子從我屁股底下推開,再換個比較舒服的姿勢坐好。不用急,沒有人會來打攪我們。好心的盧老師想必已經知道,我得花上好幾個小時還說不完一半的故事。這一年來我寫的每一樣東西——我所有的詩,一篇篇的散文,我那齣兩句兩句押韻的劇本,甚至是我匿名投稿到校刊上的文章,用掉她多少紅墨水洋洋灑灑地批改,怎能叫她白費工夫呢?喔,是的,從我媽開始跟金魚眼叔叔交往以來發生的所有事情,她統統都知道。
我也知道她為什麼指派我下來安慰海倫,而不派麗茲了。
今天海倫來到學校的心情簡直爛透了。她看來好奇怪,而且她的眼睛好紅好腫,又不肯跟任何人說話。如果有人想跟她說話的話,她立刻肩膀一聳,轉身就走。她趴在課桌上,把腦袋埋在兩隻胳膊中間,等待第一堂上課鈴響。 「有什麼不對嗎?」 只聽得悶悶的一聲,「沒有!」 「海倫,你怎麼啦?」 「沒事!」 她抬起頭來說得好憤怒,幾乎噴出了口水。我們覺得有點被嚇到了。平常的她大概是我們班上最溫柔的同學。她想必是出了什麼不得了的大事。 盧老師走進教室的時候,我們看得出她也深有同感。 「海倫,你怎麼啦?發生什麼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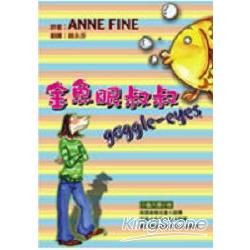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