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佛教擴展的路線──佛教大圓環
商貿歷史上,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主要地區間的接觸,不僅限於貨物往來及商業利益,透過商人的商貿路線,更可以勾勒出文化、宗教習俗以及信仰相互作用的輪廓。如果我們隨著時間與地域的移動,繪製佛教擴展的路線,大致可將其描繪為一個「圓環」(circle),我稱它為佛教的「大圓環」(“¬Great Circle”of Buddhism)。在許多方面,「圓環」可當作環線(rim)的標誌,標示佛教傳統的外圍框線。啟發我將佛教世界想像為一個「圓環」的靈感,源於八世紀韓國僧人慧超(Hyecho)所寫的日記。慧超從韓國出發,沿著中國的海岸,越過「南方」海域的島嶼及沿海港口,抵達印度,之後又穿越內亞,返回中國。值得留意的是,這位韓國僧人知道可以從韓國的海港搭船至印度,他清楚「大圓環」,並隨著環線旅行。慧超的日記可能是由中國西部敦煌洞窟的抄寫員所復刻,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二十世紀初到訪敦煌莫高窟時,在存放各種著名文獻的第十七窟中發現了這個復刻本,並將其公諸於世。由於慧超一直留在中國,未再回到家鄉,所以韓國並不知曉他的事蹟,一直到數世紀後,他的旅行日記才在其曾經旅行過的大圓環遙遠環線上被發現。
透過大圓環的「環線」,可勾勒出佛教發展的外緣地帶,從中可看出,相較於位處環線內的首都、山區的人口中心、朝聖地和修道寺院,「環線」上的佛教發展並沒有獲得相對的重視。事實上,此「環線」提供我們研究佛教如何從印度傳播至中國的大量線索,也幫助我們了解佛教的影響力如何沿著「大圓環」的環線擴張。雖然目前尚未完全掌握「環線」周圍雙向互動的內容,但無論是大環線上穿越沙漠的路徑抑或海岸線的港口,皆告訴人們,若要探究佛教的傳播,不可忽略對於「大圓環」之「環線」的認識。縱然大部分的佛教傳統,都在這一條界定佛教傳播區域的界線內發展,比如重大的佛教事件、團體機構的所在地等,但佛教循著「環線」發展的動向,在佛教史上極其重要。
誠如前述,在佛教傳統歷史和傳播的研究上,商隊路線一直備受關注,歸因於眾人對商隊路線考古發現的青睞,這些發現也為陸上遺址的研究提供了數據資料。相較之下,海上傳播路線的研究資源不易取得,因為船隻航行於港口間,並不會留下任何可供研究的文物,唯有從海床上的零星殘骸,或港口的考古遺址中發掘出的文物,如陶器或金屬物品,讓我們得以一窺早已消失的生活模式。而我們也非常幸運能透過新遙感技術探測深海,發現大量迄今未知的遺蹟。不過,儘管人們對於沉船水下考古日漸感到興趣,但囿於取得困難,其吸引力仍無法與陸上的遺址考古相比。
佛教「大圓環」的「環線」結構(包括寬度),在各區域都有所不同。從內亞通往漢朝中心地帶的這一段「環線」,散布著商隊路線上小型城鎮和修道寺院所形成的「節點」。橫貫內亞的「環線」通常非常「狹窄」,有些地方僅有商隊途經的道路,一路上杳無人煙,唯有少數服務商隊的驛站「節點」。由此可見,對於陸路環線上的城市而言,只依靠當地的貿易,不足以推動城市發展的龐大體系。中亞的商貿和傳播路線無法依靠沿線的活動支撐,而需仰賴由印度西岸港口到漢朝首都長安的大圓環體系的驅動力。這條漫長的陸路蜿蜒穿過中亞的山脈和盆地,在某些情況下啟動的國際貿易,有助於此環線的維持。但中亞這一段「環線」很容易受到商業活動興衰的影響。由於國際貿易依賴遙遠的資源和市場,沒有當地的市場支撐作為後盾,該地區的貿易便十分脆弱,一旦背後較大的貿易世界轉移時,該地區的貿易量即會下滑。可見,在「大圓環」上內亞這條「環線」成長的「城鎮」,通常只是印度和中國之間貿易和商品中繼過渡的支持基地,沒有人和貨物的積極流動,這許多城鎮就失去了支撐力。
以澳大利亞和美國為例,現代化的高速公路和鐵路橫越人口稀疏的廣大區域,而提供燃料、食物和休息的補給點,皆隨著旅人的旅程而蓬勃發展。但旅人並非以在「補給點」上停留為其旅行目的,「補給點」的設立也不是為了給當地稀少的人口提供服務。我們只能將這種發展理解為它是更大的旅行和通訊系統的一部分,而這個系統的目的不是由特定地點來界定。在這些體系存在的地方,變化可以是非常巨大的,中亞的「環線」就像這樣的情況。今天我們沿著這條路線旅行,經過一個又一個廢棄的城市,就能見證這種變化的結果。這通常有幾種解釋,包括缺水的生態災難,以及伊斯蘭商人和文化「入侵」所致,至於經濟基礎對貿易路線和人口增減的影響則較少受到關注。比如塔克拉瑪干盆地(Taklamakan basin)附近的幾個城市,因為擁有足夠的人口和農業生產區,都可以長期維持,繼續運作;而像喀什(Kashgar)這樣的城市,雖然沒有被廢棄,但因為現在已脫離主要的商業活動,與它在古代的歷史風華相比,已顯得十分沒落。
當我們將焦點從商隊陸路轉移到佛教「大圓環」的海路環線時,我們發現,從印度西部穿越東南亞和中國海域數千英里的海岸線系統,同樣受到貿易和傳播網絡的影響。隨著貿易模式的變遷,曾經繁榮的海港也可能衰微,我們可以從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的俄厄港(Óc Eo)看到例證。中國使節在四世紀訪問這座城市時,將之描述為一個充滿生機的國際貿易中心,城市的房屋都建在高腳樓上,以避免每年遭受氾濫之災。這座城市的重要性,足以吸引中國旅人造訪,並留下對它的紀錄。但如今,對於俄厄港往昔千畝壯麗稻田的輝煌景象,我們僅能想像。俄厄港可能是在技術的發展進程中,成為中國和位於蘇門答臘的室利佛逝(Srivijaya)首都巨港(Palembang)之間貿易方式改變的犧牲品。當有更大、更強的船舶可以負荷更長途的公海航行時,例如,往來於蘇門答臘和廣州之間的船隻,便無須在俄厄港等地停泊。因此,即使是附近有大河灌溉可以種植水稻的繁華港市,一旦新的貿易路線變換,也就失去其作為港口存在的理由。也就是說,當它脫離國際貿易體系,就再也無法維持其重要性,最終遭到遺棄。我們發現,昔日在印度有很多類似的港口,它們過往比現今其他的港口活躍得多,但現在也僅能透過考古挖掘來認識它們。雖然在某些情況下,海岸線的淤積和移位也是導致棄城的原因,但海上航線似乎也像陸路商隊路線一樣,容易受到貿易模式的影響。
有關廢棄遺址的研究,過程很複雜,須仰賴數據分析所獲得的結果。例如,根據考古學的數據分析,可知城市基礎設施隨著時間推移而漸趨衰微的模式。這些數據點出了一個基本問題,即:為什麼居住者不再維護那些必要的道路、運河、水壩、水井和農業,以滿足當地社會對這些設施的需求?衰微的歷史面貌通常可以透過各個層位的考古發掘而清楚呈現,但其衰微的原因卻很難從這些出土的文物中得悉。佛教為什麼在特定時間、在「大圓環」的特定區域繁榮發展,而在其他時候卻衰退甚至消失?其原因離不開貿易路線對整體生活的影響。當我們研究佛教的「大圓環」,觀察其受遺棄的歷史時就會知道,內亞與湄公河三角洲沿海地區兩者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然而,這兩個相隔甚遠的地域具有共通性,佛教都曾經在這些地方傳播,並在它們的歷史中占有主導地位。然而,無論是透過海路或陸路傳播,佛教的興衰都與「環線」上「節點」的繁榮與沒落密不可分。畢竟,宗教活動是人類的生活行為,只能存在於人口聚集的地方;如果居住地失去其商業中心的角色而遭廢棄,那麼該地的宗教也將面臨同樣的命運。
在某個層面我們觀察到,「大圓環」具有一種夾雜經濟和文化的活動體系,因此,在人口和商業活動發生重大變化的地區,佛教的消亡不能僅僅歸因於宗教傳統內部的某些弱點。「大圓環」「環線」上的每個區域都匯集多項功能,這些功能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個獨特而連貫的整體,由於這種結構的複雜關連性,系統中任何改變,就會造成結構上的變化。「大圓環」環線上的廢城的戲劇性衰敗,讓人們認知到社會形態的變化歷程。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考量挑戰了中亞廢城是受生態和文化入侵所致的說法,或者至少說明生態變遷或文化入侵並不是判斷該地區衰變的唯一可能性。
這條「環線」所經之處也常是文化交流的重鎮,故而有其重要性。由於「環線」是根據佛教活動和文物出土的「節點」所測繪出來的,它不只是佛教發展的最大範圍界線,也可以視為是與之相鄰的非佛教文化特徵的「邊線」(edges)。佛教與其他宗教可說是共享空間並相互關聯,因此區隔不是那麼絕對。由於「環線」通常是世界性的混合體,在某段時期和某些情況下,佛教並不是主要的宗教,因此,用數據來繪製「大圓環」地圖的這種研究方法,不足以反映出「環線」的真實動態。這引導我們超越地圖上的那些「節點」,進一步看到延伸數百英里沿線上的「節點」。而為了了解這些「節點」的性質,我們必須考察連接「節點」的「邊線」。「邊線」研究是在探索兩個節點之間的活動類型,我們可以製作邊線圖,這些圖提供以下訊息:從一個「節點」到另一個「節點」的商品運輸清單;涉及不只一個「節點」的事件日期或類型;該地區的人口統計數據。在許多方面,我們是沿著大量「邊線」移動的文化活動來研究「大圓環」,透過這種方法,就可以理解構成佛教地圖「環線」體系的動態因素。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路易斯.蘭卡斯特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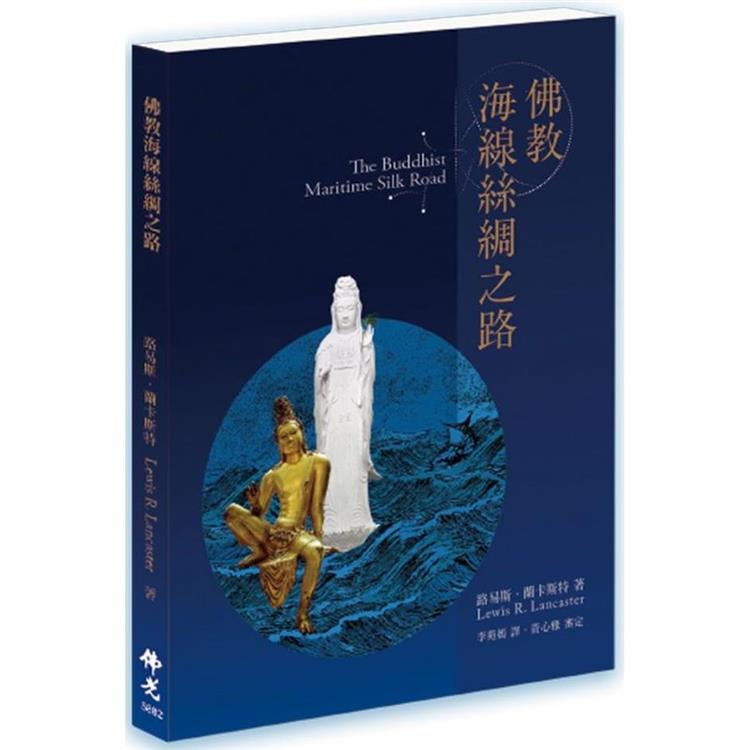 |
$ 284 ~ 335 | 佛教海線絲綢之路【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路易斯.蘭卡斯特 出版社: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06-03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佛教海線絲綢之路
這是一部浩瀚的海上佛教史,其範圍廣闊,令人驚嘆!不僅涉及佛教宗派、著名僧侶和規範行儀,有關海上跨中西文化接觸、南島民族的航海技術和遷徙等各種因緣,都是佛教傳播史的重要環節。
蘭卡斯特教授的分析研究,從靜態的歷史視角轉向歐亞貿易體系各地域間相互往來的動態網絡系統。教授筆下的佛教傳播故事,以公元伊始的歐亞內陸商隊路線及數世紀來日漸蓬勃的海上航行網絡為背景,他將南北兩大環線延展並相接成一個大圓,稱之為「佛教大圓環」,佛教便是隨著這個大圓環上的興盛商貿擴展開來。
本書分成五個章節
• 前言
• 佛教的起源和傳播
• 佛教大圓環的弘傳和發展
• 海上傳播的佛教衍變
• 結語
作者簡介:
路易斯.蘭卡斯特
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終身榮譽教授。佛教經典電子化與數位化開創者、電子文化地圖(ECAI)主席、佛教學術研究的重要國際學者。
2007和2014年各別榮獲由韓國佛教基金會頒發的萬海獎及大韓佛教曹溪宗授予的貢獻獎。曾於2004至2006年擔任美國西來大學校長,協助學校獲得美國西部大學聯盟(WASC)認證。目前為「佛光大辭典英譯計畫」的最高指導顧問;也是2021年5月於佛陀紀念館開展「佛教海線絲綢之路—新媒體藝術特展」的學術策展人;常受邀擔任各大學術會議的主題演講人。
蘭卡斯特教授曾出版及編輯多本佛教書籍,如:Prajnaparamita and Related Systems、The Korean Buddhist Canon、Buddhist Scriptures、Early Ch’an in China and Tibet和Assimilation of Buddhism in Korea。
章節試閱
五、佛教擴展的路線──佛教大圓環
商貿歷史上,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主要地區間的接觸,不僅限於貨物往來及商業利益,透過商人的商貿路線,更可以勾勒出文化、宗教習俗以及信仰相互作用的輪廓。如果我們隨著時間與地域的移動,繪製佛教擴展的路線,大致可將其描繪為一個「圓環」(circle),我稱它為佛教的「大圓環」(“¬Great Circle”of Buddhism)。在許多方面,「圓環」可當作環線(rim)的標誌,標示佛教傳統的外圍框線。啟發我將佛教世界想像為一個「圓環」的靈感,源於八世紀韓國僧人慧超(Hyecho)所寫的日記。慧超從韓國出發,沿著...
商貿歷史上,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主要地區間的接觸,不僅限於貨物往來及商業利益,透過商人的商貿路線,更可以勾勒出文化、宗教習俗以及信仰相互作用的輪廓。如果我們隨著時間與地域的移動,繪製佛教擴展的路線,大致可將其描繪為一個「圓環」(circle),我稱它為佛教的「大圓環」(“¬Great Circle”of Buddhism)。在許多方面,「圓環」可當作環線(rim)的標誌,標示佛教傳統的外圍框線。啟發我將佛教世界想像為一個「圓環」的靈感,源於八世紀韓國僧人慧超(Hyecho)所寫的日記。慧超從韓國出發,沿著...
顯示全部內容
推薦序
推薦序(一)
──Michael K. Buckland
(加州柏克萊大學榮譽教授、「電子文化地圖協會」副主席)
這本書從顛覆過往的視角論述佛教的發展與傳播。本書象徵著教授終其一生奉獻於學術的研究成果,也代表著一種對各領域間合作的熱忱與嚮往。
二十五年前,蘭卡斯特教授邀請了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聚集他家,一同商議可以透過什麼樣的方法,讓人文和社會科學中的時間和地點向度更易於向學習者呈現。這個聚會的討論促成了「電子文化地圖協會」(Electronic Cultural Atlas Initiative,簡稱ECAI)的誕生。ECAI是個有別於過去傳統合作...
──Michael K. Buckland
(加州柏克萊大學榮譽教授、「電子文化地圖協會」副主席)
這本書從顛覆過往的視角論述佛教的發展與傳播。本書象徵著教授終其一生奉獻於學術的研究成果,也代表著一種對各領域間合作的熱忱與嚮往。
二十五年前,蘭卡斯特教授邀請了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聚集他家,一同商議可以透過什麼樣的方法,讓人文和社會科學中的時間和地點向度更易於向學習者呈現。這個聚會的討論促成了「電子文化地圖協會」(Electronic Cultural Atlas Initiative,簡稱ECAI)的誕生。ECAI是個有別於過去傳統合作...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推薦序
自序
第一章 前言
一、歐亞之間的往來
二、貿易歷史的重構
第二章 佛教的起源和傳播
一、佛世時的城市發展與貿易
二、雨季對僧團文化的影響
三、舍利與佛塔信仰
四、佛教跨出印度半島之外
五、佛教擴展的路線—佛教大圓環
第三章 佛教大圓環的弘傳和發展
一、海線商貿與佛教的足跡
二、佛教弘傳借助於海線貿易
三、城鎮和佛教社區的形成
四、佛教大圓環上的傳法與朝聖之旅
第四章 海上傳播的佛教衍變
一、早期佛教
二、大乘佛教
三、密教
四、改革後的上座部
第五章 結語
一、佛教「曼陀羅」式...
自序
第一章 前言
一、歐亞之間的往來
二、貿易歷史的重構
第二章 佛教的起源和傳播
一、佛世時的城市發展與貿易
二、雨季對僧團文化的影響
三、舍利與佛塔信仰
四、佛教跨出印度半島之外
五、佛教擴展的路線—佛教大圓環
第三章 佛教大圓環的弘傳和發展
一、海線商貿與佛教的足跡
二、佛教弘傳借助於海線貿易
三、城鎮和佛教社區的形成
四、佛教大圓環上的傳法與朝聖之旅
第四章 海上傳播的佛教衍變
一、早期佛教
二、大乘佛教
三、密教
四、改革後的上座部
第五章 結語
一、佛教「曼陀羅」式...
顯示全部內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