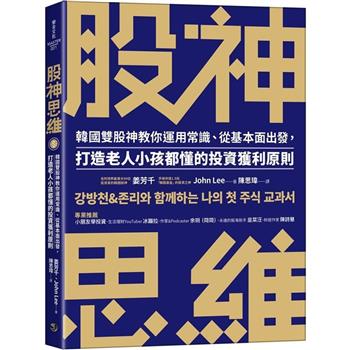墨西哥的聖女貞德,真人實事的迷人傳奇!
媽媽「蜂鳥」生下泰瑞西塔就拋棄她,丟給兇悍貧苦的阿姨撫養。她常常挨打、挨餓,躲在豬舍裡,和大母豬彼此安慰,各自思念失去的小孩與母親……好容易找到生父,成為墨西哥農場大地主的么女,即將擁有美好的人生。誰知道,更悲慘的命運才剛剛拉開序幕……
◎家族傳奇轉化為劇力萬鈞的迷人作品
泰瑞西塔真有其人,是伍瑞阿家族的傳奇人物,也是作者的遠房高祖姑姑。生於1873年,當時墨西哥內戰正熾,執政的狄亞茲將軍採取高壓手段,迫害境內的印第安原住民。泰瑞西塔十六歲遭到強暴致死,停靈數日之後,忽然從棺材中坐了起來,從此擁有療癒能力,吸引成千上萬人前來朝聖、求助,並稱她「卡波拉聖女」。印第安人標榜她是「墨西哥的聖女貞德」,想藉此號召革命。墨西哥政府因此指控她是「墨西哥最危險的女孩」,逼她流亡美國,再也無法返回心愛的故土……
◎重新賦予「魔幻寫實小說」生命力的新經典巨著
墨西哥這個加勒比海邊的高原古國,原居的印第安人孕育了馬雅、印加、阿茲特克等古文明。十六世紀遭西班牙入侵,古帝國瓦解。十九世紀初才獨立,但內戰依舊頻仍。作者結合史實與寫作技巧,讓世人得以重新回味馬奎斯四十年前掀起的文學狂潮與閱讀的喜悅。雖然取材自真實人物,故事的細節、人物的特色卻都出自作者匠心。作者文筆洗鍊,從辛辣到浪漫,野蠻到風趣,無不揮灑自如,讀者可以充分體驗視、聽、嗅、觸等感官的悸動。全書洋溢落日餘暉的豔麗與淒清,既肅殺又抒情。
唯一能夠媲美馬奎斯《百年孤寂》的拉丁美洲魔幻寫實小說!
作者簡介:
路易•艾伯托•伍瑞阿(Luis Alberto Urrea),美國當今最受歡迎的作家,目前在伊利諾大學教授創意寫作。父親是墨西哥人,母親是美國紐約人。著作豐富多樣,曾獲得「桐山環太平洋文學獎」「美國圖書獎」「美國西部州圖書獎」「科羅拉多圖書獎」「蘭納基金會獎」「克里斯多福獎」等多項文學獎項,並躋身「拉丁美洲文學名人堂」。著有《魔鬼公路:真實故事》《鐵絲網的另一邊:墨西哥邊界的生活與艱辛》《睡童湖畔:墨西哥邊界的祕密生活》《無人之子》《浪遊時光》《尋雪》《六種天空》等;詩集《生之熾》《鬼恙》《墨佬》,詩作入選《美國最佳詩選》。目前和老婆、三個小孩、一隻貓和一隻鸚鵡住在芝加哥。
章節試閱
湯瑪士獨自騎馬進到山裡。這時候,他想起他們害怕的哭喊、他們的爭執和叫囂。葳拉跟他爭論,「族人」求他不要去。不過他已經和艾吉瑞及西根多吵了一整夜。他壓制了牛仔們的意願,也辯贏那毀了他睡眠、沒完沒了的爭論。
「看在天主的份上,你這個白癡──你一定帶些武裝騎士一起去!」艾吉瑞叫道。
「不要。」
「這樣做等於自殺呀,老闆,」西根多爭辯。「不要一個人去,至少讓我跟你一起去。」
「不要。」
「他們會殺了你。」艾吉瑞大喊。
「我不認為。」
湯瑪士有種感覺,如果他不帶著雇請的槍手,獨自騎馬到雅基人當中,他們將會尊敬自己的大膽。就算他們沒有受到感動,他也不希望他的人再被殺害。況且,雅基人不騎馬,不像阿帕契人或柯曼契人──他知道自己能騎得過任何可能追殺他的戰士,況且他還佩戴著兩把左輪槍,又在馬鞍兩邊槍套裡各放了獵槍和溫徹斯特槍。如有必要,他可以開槍殺出一條血路,不然他就開槍開到自己沒命為止。
「我是個好天主教徒,」他開玩笑地說。「雅基人會和我一起唸玫瑰經。」
他的離開幾乎是靜悄悄地。湯瑪士帶了一把裝在黃色皮雕槍套的連發來福槍、兩把左輪,還有一把大刀插在腰帶背後。他穿著銀色鑲海貝的黑色長褲、生皮製套褲,還戴頂寬邊帽。馬鞍袋裡有兩袋子的披索金幣,是要付被搶女人的贖金。晨曦出現前他就早早騎馬出了營地。
當天下午到達阿拉莫斯時,他很開心能看到酒吧、餐館和樹木。他拿花生餵一隻站在芙蓉樹的大白鸚鵡。他吃了西班牙辣香腸和蛋、南瓜和木瓜、一碗茄汁燉飯,上頭撒紅洋蔥,喝了咖啡和熱牛奶,吃了三個甜麵包。他到藥房買了一些胃腸藥粉,以免辣香腸讓他拉肚子,他還買了七根雪茄和一聽的菸草──書報上報導過印地安酋長都喜歡菸草。他把馬托付給馬廄,自己就到廣場附近的旅館,要了一間房,花錢洗了個澡。他把自己泡在冒熱氣的熱水中,把身上的牛隻味道刷掉。當他站起身時,洗澡水看起來像是寬口杯裡的豆子湯。
「我真是隻豬呀。」他說。
他從背囊中拿出乾淨的長褲和一件白襯衫穿上,照了照鏡子,把頭髮往後撫平。然後到樓下享用一杯龍舌蘭酒和一顆萊姆,又坐下來玩了一局撲克。他付錢給女歌手,要她唱三首歌,然後到堂兄家裡喝茶、逗弄嬰兒。到了午夜,他回到自己房裡,倒在羽毛床上,睡得像個疲累的天使。黎明時分,他穿戴好了,坐下來吃了一頓有水果、圓麵包、火腿排佐綠辣椒和四個蛋的早餐。他去買了結實的靴子、理了個髮,等電報局開門,給米格爾先生拍了份電報:「卡波拉焚毀!重建中。我與叛徒協議。艾吉瑞和西根多負責牧場。」
他騎馬出鎮時,在烏瑞亞大宅「禮拜堂」稍作停留,往裡面看著華美的裝潢。女僕們十分驚慌,手足無措。他對一個來自諾加雷可愛的十幾歲女孩眨眨眼,說,「我絕對會再看到你的!你叫什麼名字?」
「尤洛索其托。」她回答。
他覺得這真是美妙,於是躍回馬鞍上,馬兒快步奔向荒原。
卡波拉的工人曾告訴他說雅基戰士的村子有十哩遠,不過他這時才想到自己竟然沒問該往哪個方向走。他可以選擇的方向竟然可以形成一道長有千哩的圓弧。他朝百約瑞卡騎去,那裡是座小小的礦城,阿拉莫斯以外唯一的文明中心。至少可以從那裡開始。他向路上看起來像是印地安人的行人打聽。沒有人知道攻擊的是雅基族的哪一支,也不知道他們那個小小部落叫什麼名字。他們告訴他,在百約瑞卡或許可以找到知道消息的人。他說不定還能找到一些突擊者呢,因為雅基人常會在礦場工作,運用他們充沛的體力把礦車從坑道裡拉上來。
騎到那裡要一天的時間,湯瑪士把鋪蓋捲綁在身後。他的補給品有辣椒醃漬的肉乾、一個軟木塞罐裝的豆子、圓麵包、裝滿熟飯的皮囊,用蠟紙包的醃肉條、幾瓶啤酒。他還帶了一個粗麻布袋,裝著壓碎且烘烤過的咖啡豆。馬鞍鞍頭吊了三個水壺。在他後面還叮叮咚咚帶著鍋子、盤子和一個咖啡壺。足夠的子彈。他最愛的棗子。
周遭的世界十分安靜,寧靜又廣闊。身後沒有牲口拖車和牧場工人,他感覺像被鬆開了,像薊草的冠毛般輕飄飄在空中。如果風向對的話,他甚至還可以飛起來呢。他從沒有想過這片土地有多大,而天空卻還要更大。雖然巨大,大地卻像是水果塔上頭薄薄的那層焦糖,而天空隆起,成為高高的一個大圓頂,無窮盡的向外延伸出去。
遠處的烏鴉小得像他香菸上散落的煙灰。他幾乎聽不見牠們的叫聲,牠們的聲音被風聲掩住,聽起來像是牠們被摺起來,塞到天空一角的下頭了。
然後是往上走:泥土路逐漸攀上山麓丘陵。龍舌蘭、蔓仙人掌、墨西哥三齒拉瑞阿樹、牧豆樹。他看到斜倚的俗麗小屋,像是被強風吹歪了。光著身體的白屁股小孩,渾身都是石灰土的塵灰。路邊有三座墓,立著白色十字架,上頭沒有寫字,石頭也漆成白色,彷彿在這個熱天中還下了雪。蒼蠅飛上他的眼睛、他的鼻子。他把花巾罩住臉;四處翻找可用之物的窮人看到他經過時都嚇得躲起來,深信這個高大的土匪發現了他們的罪惡和不檢點,悲慘的時刻終於來臨了,於是他們弓起肩膀,準備挨他的子彈。不過他卻騎著黑種馬「庫奎」過去了,只有達達的馬蹄回聲訴說他的經過,既沒有開槍,也沒說一句話。
路上還駛來山區的大篷車──一排排小驢子馱著帆布下一綑綑過重的機器和工具。趕驢子的有拿著手杖的滿面倦容的小個子男人、有牙齒掉光、皮膚黝黑、光腳走八字路的男人,那雙赤腳像是油炸過的皮革,在土裡呈黃色,還有裂口。他們經過時都跟湯瑪士點點頭,還偷瞄他的武器,又很快把眼光移開。
「很遠嗎?」他問。
「不遠。」一個人回答。
他騎到山頂,望著那雜亂、破敗的百約瑞卡部落。這是座煙和塵灰的城鎮。礦坑廢棄的渣滓、四散在巷弄中像破布一樣的酒鬼、死狗、曬的衣服。這座城很髒。兩哩外他都能聞到它的氣味。
湯瑪士把原本要給蘿芮托夫人的帳篷留下來,於是葳拉和屋裡的工作人員就搬進去住,把他們的毯子鋪在摺疊床上。勞洛先生在破敗的牧場屋旁邊的白楊樹下架起床架。他組合起鐵製床頭板和床腳板,又在床邊擺了一張小桌,桌上還有一盞油燈,然後把一把來福槍靠桌立著,一條槍帶掛在床頭板上,這床頭板真的很像一道黑色鐵圍籬,有鐵條和橫槓,他就在夜裡的微風中平靜地睡了。當他早晨醒來,雞隻都在他頭上的床頭板上站著,咯咯輕啼,還像胖嘟嘟的貓兒一樣發出呼嚕聲。
遭到雅基人攻擊後,卡波拉的工人都逃走了,他們那些在畜欄和後頭的茅屋,以及會嘎嘎作響的小屋就空了下來,辛納魯亞的工人就漫步到這些屋子,隨意挑選。這座村子和他們來時的村子幾乎是一模一樣──不太整齊的兩排簡陋房屋,屋子後面是用薄木板和紙板牆搭成的糞坑,臭氣沖天,後面則是小小的豬圈。這條小小的街道甚至還有同樣的、驢尿形成的泥潭。「族人」依著上個村子同樣的順序一一住進這些小屋。葳拉的助手和騾車車夫提歐法諾先生選了街左邊,是最西邊的一戶。車夫自認是村子的哨兵兼守護神,雖然要把他叫醒,恐怕要在他門外炸完一堆炸藥才行。每家人都謙卑地彎身走進低矮的門口,躺在草蓆睡墊上,接收前屋主的跳蚤。村民很快就把這裡取個和舊日住處相同的名字──波特雷洛。
住不進這條街的人──牛仔和住不進小屋的人──就到沒燒掉的小馬廄棲身,或是睡在篷車底下、裡面或附近。泰瑞西塔跟葳拉一起睡。晚上蠍子就會爬下牆,牠們是從老工人編進屋頂的棕櫚葉和野草中鑽出來的。蜥蜴也會從牆上下來,壁虎和怪異的多彩小生物也來了,這些小東西彼此推擠,然後在憤怒的爭戰中竄過木頭和磚塊。
工程師艾吉瑞已經接掌卡波拉。沒有木材,他們要怎麼重建主屋?泥磚。他們有黏土、有沙土、有泥漿和乾草。有一些椽木和橫樑,雖然被火燒黑了,但是仍然結實。還有人的肌肉和雙手雙腳。
他們把主屋裡的焦炭和破敗的殘留物全清走,艾吉瑞很高興房屋地基很正常。磚頭耐得過火燒,而硬木的支柱和支架也都質地緊密,燒不起來。門廊和樓梯情況良好,壁爐和煙囪也仍然站在那裡。雖然艾吉瑞有半數的手下已經從這個燒掉的屋子裡拿走所有能拿的東西,但是其他人還是用從圍籬撬下的木板和附近穀倉背面的木板,以及兩間拆了的工作間,把一排排泥磚框起來。這些泥磚擺放在地上,像是巧克力蛋糕。泰瑞西塔和其他小孩就會去踩踏大桶裡的黏土和草葉混合物,看泥巴從他們腳趾縫間歪歪扭扭地擠出來。
艾吉瑞在他們拆了的工作間裡發現一堆銅管,於是立刻把他的下午時光用來設計一個系統,可以把風車從牲口那長滿青苔的水槽裡抽送出來的綠色水,送到工人屋中心和主屋附近一帶。等到這些管子終於擺放好位置,彼此交織出格子形狀,孩子們就用它來玩大型的「跳房子」遊戲。水終於穩定地流進工人屋的泥巴巷尾附近的桶子裡,也啪達啪達進到離艾吉瑞床不遠的一個大陶罐,而為他躺在床上看著時──全身塗滿葳拉的金光菊防蚊膏──製造了怡人而且清爽的氣氛。他吹熄油燈後,仰望清朗的夜空、無邊無際的藍白色星星,以及流星劃開天空時那奇特的一道道光。他會點起火柴,查看他那本小小的星圖,找出黃道帶那些神祕的圖形。當月亮升到馬德雷山脈那些嚇人的暗黑齒牙之上時,艾吉瑞就會打開放在床頭桌上的一個長長的皮盒子,拿出一架黃銅望遠鏡,細細望著月亮那有陰影的峽谷、磒石坑和深深的死海。歐洲人總是看到月亮裡有個男人,這是工程師在艾爾巴索得知的。不過他的父母親卻總是在月亮表面看到一隻兔子,他每天晚上看到的也就是這個,這隻用後腿站立的兔子,牠耳朵向後垂下,似乎正在吃著這個鬼魅般衛星的邊緣。
有時候,泰瑞西塔會站在艾吉瑞燈光外很遠的地方,看他看書。
「族人」都認為他相當瘋狂,這樣子睡在室外烏瑞亞的大床上,雞隻高站在頭上方和腳上,營地的狗也開始在他附近聚集,而且一晚多過一晚,再加上他的白色長睡衣和望遠鏡、他的書和他那個咕嚕咕嚕吵一整晚的陶罐泉水。當穀倉的貓也決定愛艾吉瑞勝過所有人,而艾吉瑞也讓這小東西睡在床尾時,他們可被說得難聽極了。不過泰瑞西塔覺得艾吉瑞很迷人。
圍繞著某些人的彩色氛圍也回來了,雖然還是很淡,但是同時卻也看得更清楚了。她也開始會看到一些事情,正如同葳拉說的,但是大多數並沒有什麼神奇──她才大到會注意從前從沒注意的事情而已。比方說,最近她就注意到附近有公牛從母牛後面推擠,然後又看到公馬在推母馬。當她告訴葳拉她看到的事情後,葳拉就把她拉到穀倉後面,告訴她那些動物在做什麼。泰瑞西塔又驚又樂的尖叫起來,然後就像兩個小女孩一樣地笑鬧著。
葳拉也教泰瑞西塔擠牛奶,因為她以前只擠過羊奶,葳拉說,「你沒有奶子,不過以後你會有的。我的呢,哎,我的孩子,我的奶子又鬆又垂,跟母牛的一樣!它們開始的時候很大,到最後就變長了。讚美天主。」老婦人的粗言粗語讓泰瑞西塔吃吃笑著。
泰瑞西塔以前從沒注意牧場工人有多少人有一口爛牙,或是缺牙,或是因為掉了牙而下巴歪扭、嘴也癟了。她沒有看到周遭那些手腳、四肢──傷腿和傷踝、受傷或生病而扭曲的腿。工人屋有三個人手臂受傷,兩隻手臂彎曲得像是歪扭的樹枝,一隻手缺了一半的手指,彎成一根暗黑的爪子。沒眼珠的、慘白眼睛的、飄移的眼神和鬥雞眼。牛仔身上有傷疤,有些人還失去大姆指或食指。她太震驚了。這個世界以她從沒看過的方式受著傷。
狗兒用三條腿奔跑。
這是什麼?
死雞躺在雞籠裡,身體已被蛆蟲分解了。
不論她問誰,不論她問了多少「族人」,甚至是葳拉、甚至是艾吉瑞和看起來無所不能的牛仔們,沒有人能解釋為什麼世界上有受苦、為什麼有痛苦或死亡或傷害。聽到人說受苦生病是「神的旨意」,讓她沮喪得要發瘋。或者牛仔們的人生哲學,說生命就是艱苦,痛苦時你就咬緊牙,不要怨天尤人,如果情形太糟,你就騎馬到鄉間熬過去,就像一頭受傷的土狼或是山獅。這些答案也讓她氣餒。葳拉最糟糕。泰瑞西塔在不斷的震驚中發現,這位老婦並非事事都有答案。的確有些神祕的事太過深奧,老婦人不懂,而她面對這些未知事物時的安祥並不能安撫泰瑞西塔。泰瑞西塔不敢說出來,不過光是燒鼠尾草或香草或杉木是不夠的;跪下去沾聖水到她額頭上,誦唸玫瑰經的神祕或唱起古老的「鹿歌」,或高舉祭品祭拜四方也是不夠的。問著從來也沒有人回答的問題,這不是會把葳拉逼瘋嗎?噢,不過她已經知道葳拉的回答了,她甚至連問都不必問──葳拉會告訴她說,「有些問題你是不用問的。有些問題不是要你得到回答的。」
泰瑞西塔在一陣恍惚的異象中漫步著。在沙地大床上躺著的艾吉瑞,在他那搖擺不定的油燈光團和他那成堆的書中,或許不是卡波拉最令人困惑的事物,也不是索諾拉大門外大片土地上最令人困窘的事物,不過他也夠讓人困惑的了。
一天早晨,艾吉瑞在拂曉時分醒來。他的雞隻在上方站著看他,他已經知道要牠們站在床頭鐵杆上時屁股向外,離開他,所以床頭的地上全是牠們的糞便。五隻狗在床腳附近挨擠著仰身睡覺,四隻腳像喝醉了一樣張開,耳朵往外拍動,像是柔軟的翅膀。牠們身上掛著蝨子,像是肥美的漿果。泰瑞西塔坐在蓆子上,逗弄貓兒。
不知道什麼原因,艾吉瑞突然脫口而出:「什麼?」
「早安。」她說。
他把被單拉到胸口。
「早安。」他結結巴巴地說。
「你晚上看什麼書?」她問。
「最近我重訪吉軻德。」他說。雞隻咯咯叫,狗兒搔著癢,艾吉瑞心想:這是多麼特別的場面。
「我可以看看嗎?」她問。
「書嗎?」他說。
她點點頭。
他坐直了身體,試圖用兩手把頭髮撫平。他梳理了鬍髭,然後拿一個陶杯,喝了點水。他把杯子放下,拿起書來,對著書微笑,彷彿書是個熟朋友,然後他把書遞給她。
書在她手上相當重。封面是柔軟的皮革。她喜歡手指摸著它的感覺。上面的字母是亮金色。
她用手指去摸書名。
「這個?」她說。
「是書名,」他解釋。「《拉曼卻的吉軻德先生》(Don Quixote de La Mancha)。」
她摸著第一個字,那個小小的字。
「這個呢?」
「『先生』(Don)。」他說。
「『先生』。就像『湯瑪士先生』的『先生』?」
「或是『勞洛』先生的『先生』,」他說,希望能提醒她他的地位。這孩子很奇怪地和他很熟,好像根本不很尊敬他的樣子。
「『先生』,」她笑道。「你告訴我它的字母。」
「D-O-N,」他脫口而出,一邊四下張望,看看沒有人正在看這堂荒謬的課。
「D!」她吸了口氣。「O!N!『先生』。」
她笑了。這是她學到的第一個字。她已經學會讀一個字了。
他把書拿回去,在書頁中翻找,停下來。「在這裡,」他說。他把書頁拿給她看。「你看這裡。」他說。他指著一行字。
「它說什麼?」
「烏瑞亞。」
「哪裡?」
他把字母指給她看。
「這是個湯瑪士先生嗎?」她叫道。
「不是,不是。這是好幾百年前的事。不過這是湯瑪士•烏瑞亞先生的祖先。」
「這本書裡有一個烏瑞亞家人?」
「是呀。而吉軻德先生還提到他相當有權力。」
「每本書裡都有烏瑞亞嗎?」
艾吉瑞笑了。
「拜託,不是的!」他說。
「謝謝你,」她說,然後就跳下床。「你該起來啦,勞洛先生。時間不早了。」
她把書放下,揮揮手,在一群吠叫的狗中跑走了。
紅色平原上來了這個看似迷了路的獨行騎士,他那拉長的影子連到那些痛苦歪扭的黑色仙人掌和蔓仙人掌上。寬邊帽在臉孔四周形成一個濃密的楕圓形暗影,垂到脊椎骨末端的刀露出鹿皮刀鞘的部份閃著點點光影。當他遇到運貨隊伍時,他會碰碰帽子示意,而當他接近其他獨自行進的流浪漢或是一小群印地安人時,他就會打開來福槍套,把槍橫放在大腿上。
湯瑪士曾經跟一小群印地安獵人吃過響尾蛇,和他們一起弓背圍著一小團冒著煙氣的火。他們穿著寬鬆的大褲子,頭上綁著紅色方巾。他們的鼻子又大又漂亮,眼睛是瞇瞇眼。蛇皮都用木釘釘住,在太陽下曬,淡紫色和粉紅色的蛇肉則串在棍子上,在大火上轉動著燒烤。他們用刀刃吃肉,也用刀刃對湯瑪士比著,還指向火、又指向他,然後全體大笑。「你們這些混帳!」他說。雖然沒有說出來,但是他們全都知道把他放到火上,看著他的肉也燒得滋滋作響,會是非常有趣的事。阿帕契人互相低聲說笑,揉搓他們的臉,又對這個傻瓜白人搖搖頭。他們喜歡他,他還給他們煮咖啡,這個他們也喜歡。到了分手的時候,他們把一條肥響尾蛇綁在一條皮繩上,再把它掛在他脖子上。他們站在他旁邊,假裝用刀子威脅他,還喀喀的笑,他也拿出來福槍比向他們。每個人都認為這太好笑了。
他離開大路,到一旁過夜,把種馬綁在一棵假紫荊樹上。他聽說過這種樹,但卻從沒有看過。這樹沒有什麼葉子,樹身是綠色,很軟。他用指甲在樹身上刻下姓名縮寫:T、U。他用他那條響尾蛇嚇走任何出現的西貒或土狼。然後他發現在一條乾涸溪谷有一個凹岸,形成一個像洞穴的地方,他就在這個遮蔽處涼爽的沙地上攤開毯子。他把矮樹叢和看起來像是空心木材的枯死仙人掌枝幹拉到一起,還有小窗子在其中。他升了一小團火,又在一個坑裡小便,烤了一隻打到的野兔腰腿,那兩隻大大的後腿看起來真像長長的火雞腿。他把鹽抹在火上烤得嗶剝作響的肉上再吃,雖然中間的肉還沒熟,而且是鮮粉紅色。他煮了咖啡,還在裡面放了大量蘭姆洒。甜點是棗子。
仰望天空,他想要禱告,卻又覺得太虛偽了。
第二天騎馬上路,他經過一座農場的大門,「鴿子」。上頭的招牌寫著:「渥夫根•西伯曼先生財產」。「牲口、龍舌蘭、劍麻、棉花」。他走到路邊高高的橫木下,橫木上釘著一個牛的頭骨。直柱上則排列著馬蹄鐵。湯瑪士聽米格爾先生提過西伯曼這家人──別人背地裡叫渥夫先生「德國佬」。
湯瑪士看到遠處有一群牛仔,聚集在一片亮得刺眼的空曠地上,周圍是些無精打采的馬兒。
他騎向他們。
他們轉身看他。
一共有十個男人,其中六人拿著鏟子。他們中間地上有個新土堆,在它旁邊,一個很深的坑旁邊又有一個土堆。
「日安,」湯瑪士喊道。「我叫湯瑪士•烏瑞亞,是從卡波拉牧場來的。」
這些人看看他,兩手托放在鏟子上。
「湯瑪士先生。」其中一個人說,並且點點頭。
湯瑪士心想,他們陰沈得很奇怪。
「我在找叛徒雅基人。」湯瑪士說。
他們面面相覷。
「雅基人?」為首的人說。「這可真不是件好事。」
「他們燒了我的牧場,」湯瑪士說。「你們可以去警告渥夫先生要小心點。」
「謝謝你的警告,先生。」
他們盯著他。
「不過我們倒是沒有看到任何雅基人就是了。」
湯瑪士往坑裡看。
「還有沒有別的事?」工頭說。
「沒……沒有。」湯瑪士瞇眼看。坑裡有東西在動。「多謝。我就要走了。」
「再見了。」這人回答。
挖土的人重新拿起鏟子,埋頭工作。
「我可不可以問這是什麼工程呀?」湯瑪士問。
「湯瑪士先生,」工頭說。「我們從清晨就在挖了。」他擦了擦額頭。「你也是老闆。你知道事情是怎麼樣的。老闆命令,我們就照做,不會問問題。」
「這態度值得嘉許,」湯瑪士說。「而如果你不介意我問的話,你接到的命令是什麼?」
工頭丟下鏟子,走到他的馬旁邊。他從馬鞍上拿了一個小壺,喝了一口熱水。
「這個嘛,」他說,「是勞工問題,這些問題沒完沒了的。」
「當然,」湯瑪士笑笑說。「工人問題是沒個完了的!」
「是啦,先生。是這樣的……」他揩揩嘴,又喝了一口水,嘆口氣,把水壺塞子塞回去。「渥夫先生很嚴格,對付這些人非得這樣不可。他們沒出息又不能信任,控制鬆,只會出麻煩。」
「沒錯。」一名挖土工人加上一句。他把一鏟子的沙丟進去:坑裡冒出一陣灰沙。
「兩個工人談戀愛,」工人繼續說。他聳聳肩。「這些工人呀,發起情來像動物一樣。可是渥夫先生關心的是牲口──牛呀、馬呀,還有他的工人。所以要結婚的時候,渥夫先生就要找最健康的配對,你知道。挑選伴侶,他的眼光從不會錯。」
「配種!」挖掘工喊道。
泥土落入坑裡。
「這兩個人是不准結婚的。可是,不行,先生。他們還是結婚了。」
湯瑪士感到一股涼意直下背脊。
工頭朝遠一點的土堆指了指。
「那裡是女的。」
「渥夫先生,」挖掘工說,「要男的看到女的先被埋,」
「然後我們再埋男的。」另一個工人說。
然後湯瑪士看到了,泥土倒進坑裡的時候,有一隻腳還在虛弱地踢著。
「你們活埋他們?」他說。
這些人全都停下工作,面無表情地看他。
「是的,先生。」
「女的先進去。男的像狗一樣地反抗,」工人說。「不過我們人多,花了很長的時間。等到女的被埋了,男的就崩潰了。女的埋了以後,要把男的弄進坑裡就容易得多了。」
湯瑪士說,「我可不可以把這個人的契約買下?」
「你要救他?」
「我有錢,我付得起。」
工頭搖搖頭。
「不行,」他說。「不行,我想不行。」
「況且,」挖掘工說,同時朝坑裡看。「他不踢了。我想他已經死了。」
「看到了吧?」工頭說。「來不及了啦,先生。」
湯瑪士轉身,緩緩朝大門騎去。
「這是真愛喲!」挖掘工叫道。「現在他們永遠在一起了!」
鏟子把成磅重的碎石子繼續鏟進這個寂寞的墓中,發出清脆的聲音。
湯瑪士把兩隻手放在來福槍上,然後想想不妥,就抓住韁繩,用馬刺催促他的馬,盡可能快速地騎在慘白的路上,朝著邪惡的雅基山丘而去。
幾天後,當西根多帶領好幾車的木材和十多個騎著馬和騾子的新來人手匡啷匡啷回到牧場時,還沒有任何人聽到湯瑪士的消息。新房子牆底已經用繩子拉出輪廓,曬乾了的磚也有一些放上去了。艾吉瑞已經畫好一幢宏偉的兩層泥磚房屋的平面圖,門口改為一座門廊。西根多抵達時,這位工程師正在一條小溪谷的附近,拿鉛筆和素描簿設計溢洪道和下水道路線。他很肯定這一定要用銅管!
西根多要這些新手去工作──這裡有圍籬要修、有牛隻要照料、有坑洞要挖。湯瑪士之前命令要挖一座新的牲口水池,而雖然西根多絕對不可能拿起鏟子動手,但這些從阿拉莫斯來的孩子倒是隨時準備去挖的。反正他們很多人原本也是礦工,早挖習慣了。
西根多找了艾吉瑞,兩人一起走到工人村外面,直到他們發現一處下斜的地面,可以很方便的挖深而且擴大──它天然的土壁就可以形成一個倒三角形水塘的岸邊。他們同意在這個坑的南端做出一道土堤,把他們的小小山谷變成一座水壩,再做一條溢洪道將它和舊的牲口池相連。艾吉瑞立刻著手計算從風車送過來的可能水流量。在他記事本的邊緣,他寫出一欄欄的數目字──要是他在這個水池裡放鱸魚,或是彩色鱒魚,那會怎麼樣?他們不就可以每個星期五都開心享受鮮魚嗎?
「他的腦袋,」西根多對泰瑞西塔說,後者現在跟著艾吉瑞走,像是他的狗一樣,「很忙哩。」
「D-O-N,」泰瑞西莎,「拼成『先生』。」
「乖乖。」他說,這是他的「真的呀」的說法。他漫步走向穀倉。雖然溫度已經很高,西根多還是打算把靴子脫了、往乾草堆上一躺。他停下步子。「嗨,丫頭。」他說。
「什麼事?」
「去弄清楚『西根多』怎麼拼。」
「我會去問。」
「好。」他說。然後他就走開了。
泰瑞西塔跑向艾吉瑞。
「工程師,」她叫道。「教我一個新字。」
「你想要認識什麼新字呀?」他說,他並沒有從他永遠沒個完了的計算中抬頭。
「我的名字。」
他看著她。這個鍥而不捨的小丫頭。不過這個要求還算合理。
他揮手要她過來。他拿起一根棍子,蹲了下來。「你看這裡,」他說。他在地上畫了一個大大的T字。「T,」他說。她跟著唸。「E。」他們接著這樣寫完也唸完她的名字。
「泰-瑞-西─塔,」她說。「像一首歌一樣。」
「我想是吧。」
「Don Teresita(泰瑞西塔先生)。」
「不是,不是,不是。是Doña Teresita(泰瑞西塔女士)。你明白嗎?」他把這個字寫在地上。「你是女士,不是男士,所以要用Doña。」
這話讓兩人都笑翻了,因為他們都知道泰瑞西塔絕不是什麼有身分地位的優雅女士。
「勞洛先生。」她說,伸出一隻手。
「泰瑞西塔女士。」他回答,握住她的手,鞠了個躬。
葳拉站在他倆後面。
「你們在做什麼?」她問。
不知道什麼原因,這話把艾吉瑞嚇了一跳,他倒退了一大步。
「我──」他說。
「他教我唸字,」泰瑞西塔說。「我還寫了我的名字。」
葳拉跨到地上的字前看著。
「看來像是有幾隻雞走過這裡,」她說,並用腳把名字抹去。「你,」她指著艾吉瑞。「你識字。」
「是的。」
「你可以教人家。」
「我想是吧。但我沒有正式給人上過課──」
「明天是星期天,」葳拉說。「你,勞洛•艾吉瑞,你給我們上教會課。」
「女士,我不是神父!」他抗議。
「你識字──你可以唸神父的書。」
她握住泰瑞西塔的手,把她帶開。
於是這使得共濟會美以美教派的艾吉瑞暫時變成了卡波拉的神父。「族人」坐在長椅和石頭上聚攏,如果沒有坐位,就盤腿坐在地上。艾吉瑞從<詩篇>第二十三首開始唸給大家聽,使他們大感安慰,不過大家要他用牛隻的術語來說,因為他們當中沒幾個人看過羊。艾吉瑞想到自己竟然要纂改聖經經文不免感到有些不安,雖然他並不認為經文是絕對沒有錯誤的歷史文獻。終於,他勇敢地大聲說;「天主是我的牧牛人!」
勞洛先生就是勞洛先生,所以他很快就專心經營起「族人」的神父的角色。他鼓勵成立一個午後沙龍,由他為眾人講述歷史或哲學的事情。每天下午三點,他們就會聚集在他大樹下的床邊,聽他講解「動物磁力」、「黃道十二宮」、狄亞茲政權的政治陰謀等題目。在一堂艾吉瑞稱之為「莫提祖瑪之妹帕潘琴,在天主教徒稱作耶穌基督的偉大建築師的陪伴下,在來世──我們稱做天堂──的真實的奇異冒險」的課中,勞洛先生講到高階的阿茲特克祭司見到世界末日跡象的那些日子。天空中出現流星,街上有哭號的幽靈,真的,他解釋道,可怕的墨西哥鬼魅「羅若納」頭一次在他們的巷道中現出她可怖的身影時,簡直把阿茲特克人嚇死了。他們的日曆已到周期的結束──時代與時代之間、令人害怕的「尼莫提米」,已經開始。海岸來的信差帶來可怕的消息,說海面上有好大的白色海鳥,而這些海鳥身上都是奎薩科托神的爪牙,是從日出之地回來的留鬍子的神。今天,所有人都明白這些大鳥是船,而上頭的神只不過是西班牙人,不過在那段古老的日子裡,「世界中心」特諾提蘭城內有莫大的恐懼。
而國王莫提祖瑪的妹妹帕潘琴病倒在床,發著高燒,身體孱弱,最後就死了。垂死之際,她發現自己在天堂裡。
像往常一樣,泰瑞西塔坐在人群最前面,兩手托著下巴傾聽。
「帕潘琴後來告訴莫提祖瑪她在天堂所見,因為帕潘琴果真死而復生了!噢,是的,帕潘琴帶著一個警告從天堂返回──這個警告是給所有人,讓他們提防不公義統治的復仇!」艾吉瑞清清喉嚨,繼續說:「帕潘琴在死者之地被一個穿白袍子的金髮男人迎接。」「族人」劃起十字。即使間接提到耶穌,他們也都知道。「他帶著她走過山谷,她看到河流和鴿子。」每個人都點頭。「可是主帶著她來到一座陰暗可怕的山谷。山谷裡滿是骨頭。」他們倒抽了一口氣。「骨頭!人骨!頭骨。他說,『看哪,你的族人。』因為啊,主警告帕潘琴,她的人民會因為自己的無知而被毀減。他們的信仰會毀掉他們。於是帕潘琴就在墓中醒來了。」
他們低下頭。
「你們能想像嗎?你們可以設想阿茲特克人在她復甦時的『敬畏』嗎?」
他們說,他在說什麼呀?
「起初,因為怕她是鬼,是惡魔派來要傷害他們的,所以沒有人敢走進墳墓。」
泰瑞西塔兩手貼著臉。
「然後呢?」她脫口而出,可是沒有人回答,因為「族人」全轉身站了起來,一陣馬噴鼻息和馬蹄聲傳來,他們全都跑去看老闆了。
艾吉瑞放下書裡的書說,「乖乖!」
他鬆了一口氣,因為他的朋友回來了,而且看起來完好無恙。不過他的談話被打斷,也讓他有些惱火。而看到湯瑪士後面竟有印地安人跟著進入牧場,更讓他大為驚惶。
湯瑪士騎坐在種馬背上,低頭向他們微笑。他和他的馬都是風塵僕僕。後來「族人」會說他跟離開時比已經變了個人,在他獨自騎馬的那些天裡,他身體裡有些東西變了。
在他身後的印地安人都沈著臉,靜默不語,他們後面是被他們抓去的女人和小孩。當「族人」開心地舞著、跳著到他們面前時,他們就呼天搶地的哭了起來。他們從馬上跳下,飛快跑過人群,像是被驅散的雞隻。他們兩手伸向天,雖然沒有任何事發生,而他們也不認識人群中任何一個人,而且他們的陋室如今已成為陌生人的家了,不過他們回到家了,這才是他們認為最重要的事。牛仔們從平原上騎馬衝過來,狗兒吠叫。艾吉瑞推開歡樂的人群,走到湯瑪士面前握住他的手。
「歡迎回來。」他說。
「看起來不錯,」湯瑪士點點頭,朝四下瞥了一眼。「做得不錯。」
「當然。」艾吉瑞微微點頭,表示認可。
他已經下了一道命令;只見一些男人從一輛篷車上拖下一張床,在靠近艾吉瑞床的那棵大白楊樹下組裝起來。他們在床邊放了滿滿一陶罐風車打上來的清涼水,等到湯瑪士終於在晚上的油燈燈光下躺在床上時,他們已經在小桌上備妥一盤糖蕃薯和仙人掌果凍和水了。
湯瑪士目光越過他們,直視遠處的馬德雷山。他搖搖頭,低頭往下看。
「葳拉。」老闆說。
「先生,」她點點頭。「聽候您差遣哪。」
「還有你。」他對泰瑞西塔說。
她朝他搖了搖手指。
西根多漫步過來,那雙因為騎馬而變成的弓形腿使他看起來像是一艘晃動小船上的水手。
「老闆。」他說。
湯瑪士對他微笑。
「我去到外頭。」他說。
「是的,你去了外頭,」西根多點點頭。他從他臉上看得出。「你很喜歡。」
「噢!」湯瑪士說。
他本來打算告訴他們所有人他的旅行。說到帶領他進到戰士村莊的那個瘋印地安人。說那個頭上綁著鹿角的赤裸跑者怎麼樣倒退著小跑步,又喊又嘰嘰咕咕說話又笑他。說這個跑者如何跑遠、突然停下來、彎下身,掰開兩片屁股放了個最最粗野的屁。說這跑者如何在路上小便,再把兩手按在肚皮上對湯瑪士作出誇張的大笑動作。還有,當他厭倦這陣大笑後,他又是如何像演啞劇般的哭著、用兩個拳頭揉眼睛,然後指著湯瑪士,清清楚楚說著:「尤力」愛哭鬼!
說這跑者如何把他領進村子,村民如何拿著武器對跑者吆喝,而跑者蹦蹦跳跳,咻地就穿過村子到了另一頭,只停下來對湯瑪士擺動屁股,就舞出了視線。
他想要告訴他們,當他騎馬走進那些戰士中間時,他們表情驚異地站在那裡,有些人跑向他,用木棍打他,還用他們的大刀作勢威脅。還有他的種馬是如何在這陣混亂中靜靜站立,然後就地舞著、又來來回回、前前後後轉動,在村子中間走方格子,而戰士們全都後退,對這個瘋狂的「尤力」和他那惡魔般的馬感到又害怕又有趣。還有族裡的老酋長如何走上前,他戴著一個十字架,口操西班牙語。他還想要告訴他們他倆如何談到許多事。
他想要告訴他們星星的事,告訴他們躺在可怕的墳墓中的那對愛人,告訴他們阿帕契和烤毒蛇的事。
湯瑪士突然知道,他不會說這些。他一向想像自己是個不受馴服的人,如今他發現自己只是半隻土狼。在過去幾星期中,他終於體會到不受馴服的真正意思了。那頭土狼註定要生活在他社會地位的籠子裡。湯瑪士無法想像要如何讓自己自由。
湯瑪士獨自騎馬進到山裡。這時候,他想起他們害怕的哭喊、他們的爭執和叫囂。葳拉跟他爭論,「族人」求他不要去。不過他已經和艾吉瑞及西根多吵了一整夜。他壓制了牛仔們的意願,也辯贏那毀了他睡眠、沒完沒了的爭論。「看在天主的份上,你這個白癡──你一定帶些武裝騎士一起去!」艾吉瑞叫道。「不要。」「這樣做等於自殺呀,老闆,」西根多爭辯。「不要一個人去,至少讓我跟你一起去。」「不要。」「他們會殺了你。」艾吉瑞大喊。「我不認為。」湯瑪士有種感覺,如果他不帶著雇請的槍手,獨自騎馬到雅基人當中,他們將會尊敬自己的大膽...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