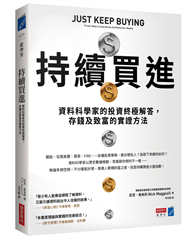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邁克。坦納的圖書 |
 |
$ 190 ~ 381 | 尼采
作者:邁克。坦納 / 譯者:于 洋 出版社:牛津大學 出版日期:2016-07-01 語言:繁體/中文  共 8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8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尼采
內容簡介
尼采在現代西方哲學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性毋庸贅言,但是要對尼采哲學做一個簡明的解說卻是一件難事。坦納的《尼采》就是這樣的一本入門書。作者認為尼采一生的根本關注是痛苦與文化的關係,其立足點不是迴避或消除痛苦,而是為了肯定人生而肯定人生必有的痛苦,據此對文化的價值進行評估和分級,並尋求一種真正能夠肯定痛苦的有內在力量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