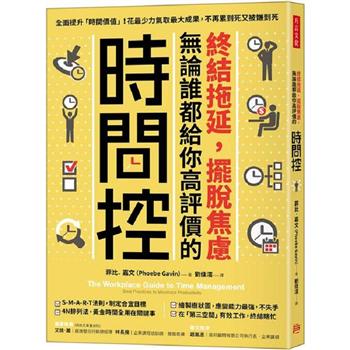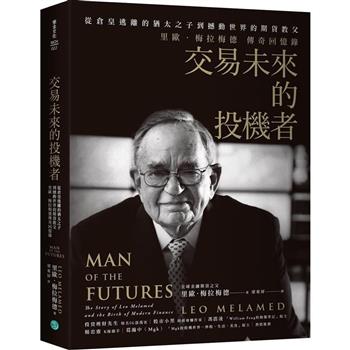第一部分 體自主與社會團結方法論
一、以群體與地方認同為基礎的個體權利與義務
反思資本邏輯主導的城市化、現代社會組織方式與社會關係
Durkheim機械團結與有機團結概念,作為社會學區別前現代社會與現代社會的社群連結機制的理想型。二者皆須仰賴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才能維繫社會團結的向心力,唯前者因社會專業分工程度較低,社群成員間共享著集體的信仰、規範、道德與價值觀,維持著低度社會流動的社會穩定狀態;反之,後者伴隨著技術革新,生產力提升,促進社會朝向更細緻的社會分工,多元異質性群體促使個人意識與集體意識分化,個體已無法藉由自給自足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從而產生更為緊密的社會交換。
因此,分化的個體意識與集體意識,如何進行有效的協調,則成為現代社會是否得以獲取分工之利,同時降低社會失序,導致社會解組的風險。另一方面,西方經濟學個體主義方法論,則延續Adam Smith《國富論》主張個體經濟活動中的自利心傾向,透過市場機制,社會中廣大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皆能在其中各取所需、互蒙其利,最大程度的實現社會整體福利。
Adam Smith雖亦於《道德情操論》以同情心(Sympathy)作為社會成員間彼此得以相互協作的前提,彼此皆共享著普遍的先驗道德,使得互動雙方得以理解對方的處境,做出相應的符合對方期待的回應,進而達成社會共識與社會秩序。
然而,伴隨著社會細緻的專業分工,市場機制運作的範圍擴大、雇傭制度的發展,個體成為受薪單位,由此所衍生的自主意識與權利擴張,產生多元複雜的社會交往,進而創造出陌生人互動的正式規範,細緻的商法、刑法、民法等,藉以建立有序的社會交換環境。正式制度多從消極的層面避免社會衝突,卻不必然得以提升社群休戚與共的意識,達成自發性的社會團結。
社會中頻繁的結社,所創造出的社會信任、社會資本,得以增進社會成員的同情共感,並在互動的過程中,發展出非正式的規範,消極面而言,得以降低監督、司法成本,積極面而言,得以培養公共意識與公德心。
然而,市場經濟社會中,經濟領域的自利心機制與社會領域的結社機制,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金融資本主義的作用下,貧富差距擴大、社會階級向下流動、M型社會、社會福利削減等狀態下,孤立的個體與家庭,成為抵禦各類型社會風險的基本單位,進而提升社會成員間的競爭意識。
在資本邏輯主導下,經濟社會空間朝向高度資本化發展,並決定著市場結構,從而使得強烈的競爭意識,不必然得以提升生產效率、社會創新;反之,資本過度集中,使得其他社會成員僅能仰賴過度競爭,又進一步削弱勞動條件,非正式雇傭契約的產生,則為零和競爭的結果,同時削弱社會信任。
社會成員間的競爭意識,並未如同西方主流經濟學家所斷言,得以帶來高效的生產力、創造力;反之,新自由主義宣稱市場機制具有調節所有資源配置的能力,使得資本邏輯由經濟領域擴張至社會、文化、自然環境領域之中,資本主導的發展邏輯,帶來城市疏離、教育商品化、社會福利削減、房地產價格飆漲等社會困境,進而產生對於「市場機制萬能」學說的挑戰。
西方近代發展延續著,自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等具有世界史意義的歷史轉折,皆從不同的層面,提升個體的自主意識,而其運用至文學、藝術、信仰、科學、政治等領域,則助於提升個體的自覺意識,進而解放創造力,創造精緻豐富的人文世界。
然而,當個體主義應用至工業革命後的經濟領域,其異於前工業社會,小規模群體內部的互惠交換,或者陌生群體間的市場經濟,而是由資本邏輯主導的市場經濟,從而產生迥異生產與社會組織方式。
市場經濟仰賴個體基於精於算計的經濟人、自利心等動機進行運作,並伴隨著社會專業化分工,使得市場邏輯擴張,使得個人的自主意識,大幅度的被經濟人性格所佔據;並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加乘作用下,城市化的發展過程,是以服務於資本邏輯發展為目的。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詮釋下,個體主義並非自由、富涵創造力的象徵,而是自私、貪婪、冷漠、工具理性化。
個體主義至現代經濟領域的發展下,產生了非意圖性後果,進而激勵個體反思現代社會、現代性與個人之間的聯繫,並發展出得以截長補短、利弊均衡的社會哲學,作為後資本主義社會下,個體與社會之間,得以相輔相成的價值體系與社會關係。
資本主義雖以個體主義作為其基本社會哲學,但個體的自主性,以資本持有的多寡作為衡量判准;資本出資比例與動員組織社會的能力存在正相關,並為企業組織與股東所有制建立正當性基礎。
然而,若考察原始資本積累的過程,其中實是充滿著暴力與剝削,但其所確立的不公平競爭條件,卻決定性的成為形塑現代政經體制與社會結構的根源。工業化生產模式,需要大量的雇傭勞工與消費市場,進而得以實現涓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所需的社會條件。
資本主義為持續完成資本積累,不間斷的開發新生產與消費市場,從而帶來大量的結構性失業,而資本主義創造的無產階級工人,其存在低技術化、高取代性等特徵,並在後進國家廉價的勞動優勢下,就業機會轉移。
資本主義將個人主義形塑成為弱肉強食的社會性格,並在金融資本主義加速資本集中的社會語境下,資本邏輯主導的市場結構,逐漸擴張成為決定社會結構與社會關係的來源,進而削弱個體的自主空間。
政治民主化目的在於對抗極權、特權政治,人人平等的投票權,意味著理想中的政治治理,是以社會共識作為前提;另一方面,資本過度集中、貧富差距擴大,帶來經濟與金融霸權,經濟的非民主化發展,使得個人於實質的生活中,喪失自主權。
貧困原先被視為是個人自主選擇、不勤奮、怠惰的結果,而至M型社會、貧困世代、中產階級消亡、階級持續向下流動等現象,則凸顯資本社會的結構性困境。
現代社會於產業發展的過程中,創造非意圖性的社會文化後果;以及自由主義形塑的全球化秩序、人觀,皆受到持續的反思,並由此引發了多元的經濟社會變革行動。而追溯至資本社會根本性的社會哲學、價值預設,則可更為深層的把握建立可持續的經濟社會機制與運行原則。
個體意識到仰賴工具理性、正式制度與規範作為主導的社會結構,孤立的個體,不僅難以與大資本相抗衡;同時,亦削弱個體間的合作意識,僅能被動的服從於資本主導的產業結構、生活方式、價值體系。因此,個人自主性與權利的維護,需透過相應的群體義務,進而創造由下而上的群體共識,實踐非工具理性主導的社會秩序,並形塑非資本主導的經濟結構與產銷模式。
個體權利與自主空間的維繫,使其不為資本邏輯所佔據,仰賴社區與社群為基礎的群體共識與義務,個體與群體之間的聯繫,並非仰賴外部的規則、懲處等社會控制手段,更為強調個人的自主規範,以及社區、社群成員,進行民主式參與,所形成的共識,作為自治的守則與認同基礎。
資本社會強調工具理性助於促進社會持續發展的動力,而其在金融資本壟斷、過度強調私有產權,形成專利權、知識產權的悖論,使其不必然得以激勵創新,反之則可能形成技術壟斷,延緩相關應用性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資本邏輯與工具理性的雙重作用下,產生勞動異化與消費主義式的產銷型態,而其不僅產生負面的社會文化後果,更帶來難以為繼的生態浩劫。
因此,個體生活自主權、非敵對的社會關係、非異化的勞動關係、可持續的產銷模式與生態環境等,則必須仰賴價值理性與非資本邏輯才得以建立。相較於資本社會強調個人、家庭需肩負起所有照護責任,或者慈善、補貼的單向給與,以群體共識為基礎的社會關係,更為強調群體成員間互惠的人際流動網絡。
群體成員存在的共同需求,得以藉由成立共同基金、互助等機制,實踐個體對於群體的承諾,並從中受益。而此異於前工業社會,由傳統規範、約定俗成等權威所構成的共同規範,其具有自發性、自覺性、自治性的特徵,使其得以共同維繫個人自主意識與群體共識,並打破個體與集體二元對立的思維結構。個體作為群體性的動物,個體慾望與群體價值之間並非總是存在張力;反之,以群體成員、民主決策為基礎的共同規範,則成為個人認同與群體歸屬的來源。
然而,自由主義曾被視為實現自法國大革命以來,所宣稱的自由、平等、博愛等普世價值,透過市場經濟與政治民主制度,得以最大程度的實現人類千百來,未曾達到的物質生活水平、免於權威壓迫、符合公平正義原則的自由與平等之境。
至今資本主義由於其強調個體、私有產權,與自由主義具有共同屬性,但卻在其資本邏輯的詮釋下,賦予了資本與權力之間的緊密聯繫,從而使得資本成為實現實質性經濟自由與政治民主的基本前提。
另一方面,面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高度產業競爭與產業風險,個人的生存境遇與世界經濟、國濟關係存在高度依附關係,助長了民粹政治興起,極端的法西斯、納粹政權雖未再度歷史重演,卻也強化個體與個體、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張力,且導致菁英政治、排他性國族主義的興起。
Gustave Le Bon《烏合之眾》對於群體心理的內涵與產生提出深刻的洞見,主張過往人們仰賴各民族歷史、傳統文化等所積蓄而成的價值體系、信念所構成的生活型態,且影響文明持續演進的力量,多數皆由少數貴族、菁英所引領,進而逐步擴散於社會大眾,成為文明演進的主要動力。
因此,在Gustave Le Bon看來群眾的變革力量,在歷史上從未如當代社會中具有影響力,且其主張群眾不是組織化,具有鮮明組織意志的行動主體,僅是由容易受到情緒、政治領袖未經論證的斷言所煽動,最終導致不理性社會文化後果,甚至成為摧毀社會秩序的力量。
換言之,民主政治如何不導致民粹,存在富涵理性討論公共議題能力的個體作為前提,而其在動員社會群體形成公共意見時,才不致淪為政治家獲取個人政治利益的工具。
那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仰賴經濟人邏輯,作為構成當代遍及全球,共通的經濟社會精神氣質,是否足以在面臨各類公共議題時,社會成員間,仍得以創造有效的自治秩序呢?
相較於Gustave Le Bon對於群眾必然現於無知、非理性、盲目的悲觀立場,James Surowiecki《群眾的智慧》則主張若能滿足意見分散、獨立自主決策、專業互補、有效整合,廣大的群眾相較於少數的菁英專家,則能創造出更有效、多元包容性、創造力等的經濟社會樣貌,且能真正的實現平權的經濟社會秩序。
Gillian Tett《穀倉效應》則提出對於以原子化個體作為基本決策單位,並由此做為經濟社會中,各類組織的組織原則,但由此所形塑的專業分工,卻將整體社會變成各自獨立的「穀倉」,導致在實踐經驗中,並未能形成如James Surowiecki樂觀期待的有效整合,反而在各自組織利益的驅使下,導致整體社會各自為政、溝通成本高昂。
然而,個體主義方法論所詮釋的經濟社會,伴隨著不同文化發展下所形塑的民族性格,從而導致個體具有不同程度的理性、公共意識;另一方面,經濟人做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精神,卻又使得工具理性擴張,甚至推翻傳統文化價值體系,而成為指導個體行動的原理原則,進而使得個體與社會之間的張力,擴大成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零和競爭。
換言之,菁英政治/民主政治、計畫經濟/市場經濟此兩項二元對立的範疇,成為現代國家政經體制爭論不休的焦點,且彼此各自擁有不同的理論與實踐經驗中的正當性立場,其有效性則端視不同國情、歷史文化發展條件。
然而,若民主、自由已被視為放諸四海皆準的人類共同價值,那麼何種社會組織方式、社會心理,才得以形塑「群眾的智慧」,而不致淪為「烏合之眾」、「穀倉」?則成為評價各種意識型態,有效性的共同判准。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邱淮璟的圖書 |
 |
$ 288 ~ 304 | 後資本主義社會秩序與經濟思維
作者:邱淮璟 出版社: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02-05 語言:繁體書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後資本主義社會秩序與經濟思維
資本邏輯無所不在,憑藉著經濟全球化所提供的豐富且多元的產品與服務,有效的說服社會大眾,資本主義是邁向經濟繁榮的必要之惡。列寧史達林式共產主義學說破產後,非暴力式的社會改革社群,仍欠缺共同的經濟社會行動綱領,使得反全球化成為空洞的信仰。
空間資本化、文化資本化、社會福利資本化,資本邏輯不僅竭其所能的將整體社會中各類資源資本化,使其成為服務於資本再生產的工具;並分化階級、性別、年齡、族群、國族等,多元社會屬性下的群體利益,加之消費社會以個體為基礎的消費單位,有效的強化原子化的作用。資本邏輯憑藉其多重策略的威脅利誘、合縱連橫,主導著遍及全球範圍的意識型態,甜蜜的外衣,潛藏著社會分崩離析的不穩定因子。
非資本邏輯的市場經濟與社會關係何以可能?傳統文化智慧與價值體系,是否得以再次作為個人認同與引導意義世界的基礎?面對價值傾頹與矛盾的資本社會,個體如何獲得自處與安身立命之道?本書試圖總結出具反思意識的經濟社會觀念與實踐行動,構築出理想的後資本主義社會可能的途徑。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邱淮璟
來自台中的北漂青年。輔仁大學哲學系與經濟學系雙學士、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生。研究領域:經濟哲學、經濟思想、經濟人類學。
章節試閱
第一部分 體自主與社會團結方法論
一、以群體與地方認同為基礎的個體權利與義務
反思資本邏輯主導的城市化、現代社會組織方式與社會關係
Durkheim機械團結與有機團結概念,作為社會學區別前現代社會與現代社會的社群連結機制的理想型。二者皆須仰賴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才能維繫社會團結的向心力,唯前者因社會專業分工程度較低,社群成員間共享著集體的信仰、規範、道德與價值觀,維持著低度社會流動的社會穩定狀態;反之,後者伴隨著技術革新,生產力提升,促進社會朝向更細緻的社會分工,多元異質性群體促使個人意...
一、以群體與地方認同為基礎的個體權利與義務
反思資本邏輯主導的城市化、現代社會組織方式與社會關係
Durkheim機械團結與有機團結概念,作為社會學區別前現代社會與現代社會的社群連結機制的理想型。二者皆須仰賴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才能維繫社會團結的向心力,唯前者因社會專業分工程度較低,社群成員間共享著集體的信仰、規範、道德與價值觀,維持著低度社會流動的社會穩定狀態;反之,後者伴隨著技術革新,生產力提升,促進社會朝向更細緻的社會分工,多元異質性群體促使個人意...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緒論
第一部分 個體自主與社會團結方法論
一、以群體與地方認同為基礎的個體權利與義務
二、社會福利社區化
三、兼具普世價值與多元文化的全球秩序
第二部分 經濟邏輯
一、資源配置
二、經濟創新動力
三、經濟發展觀
第三部分 經濟秩序
一、公共財與私有財邊界的模糊化
二、經濟民主
三、建立生產者與消費者共識
四、穩健的金融秩序
第四部分 重構後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的實踐策略
一、個體自主與社會團結方法論-社會福利社區化與社區產業
二、個人自主與社會團結方法論-再造城市,反空間資本化
三、個體自主與社會團結方法論-社區基...
第一部分 個體自主與社會團結方法論
一、以群體與地方認同為基礎的個體權利與義務
二、社會福利社區化
三、兼具普世價值與多元文化的全球秩序
第二部分 經濟邏輯
一、資源配置
二、經濟創新動力
三、經濟發展觀
第三部分 經濟秩序
一、公共財與私有財邊界的模糊化
二、經濟民主
三、建立生產者與消費者共識
四、穩健的金融秩序
第四部分 重構後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的實踐策略
一、個體自主與社會團結方法論-社會福利社區化與社區產業
二、個人自主與社會團結方法論-再造城市,反空間資本化
三、個體自主與社會團結方法論-社區基...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