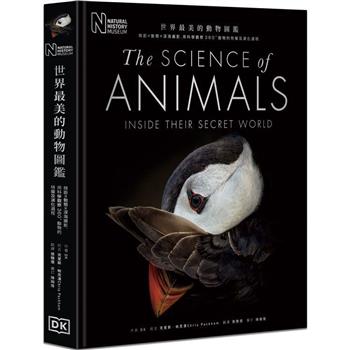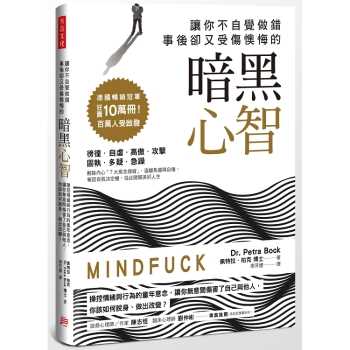游動之間的主體性:臺灣美術史的新思考
臺灣美術史的書寫,雖與近代臺灣的歷史及臺灣史論述緊緊相扣。然而,它卻不僅只是歷史之中的一個樣貌,而應視其為在不同的時空中,藝術家探尋美術主體性的流變軌跡。一九五○年代的王白淵與一九七○年代的謝里法,受到政治史觀的影響,從美術運動史的角度,思索臺灣美術的發展,即是對其所處的臺灣歷史氛圍所做的回應。一九八○年代開始,美術史的研究則著眼於政府與民間的臺灣書畫收藏,試圖以傳世的水墨作品勾勒出臺灣美術的發展面貌。此時的史觀,多以連橫的《臺灣通史》為參照系,而視明清時期流寓臺灣的中國畫家之作品,為臺灣美術史的起點。一九九○年代,周婉窈的《臺灣歷史圖說》,打破此種以漢人為主的臺灣史論述,強調原住民在臺灣歷史中的重要性。之後,有關臺灣美術史的專書陸續出版,其起點則提早並擴大至史前的考古遺址與原住民藝術。
由此可知,臺灣美術史並不固定在漢文化的範疇之內。因為,從史前物質文化的線索可以發現,臺灣美術史的發展已跨出臺灣島的地理範圍,而與「北起臺灣,南至紐西蘭,西達馬達加斯加,東至智利復活節島」的南島語族,產生交流。此時臺灣美術的主體特徵,乃是在南島語族的範疇內逐漸形成,甚至成為南島語族的發源地。十七世紀,隨著大航海時代的興起,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到來,作為東亞轉運站的臺灣,其物質文化的交流,遂在歐亞的航線版圖內移動。爾後,在明鄭與清時期,中國儒家文化傳布到臺灣來,臺灣美術的發展,便在一種新的地緣關係中,形塑出獨有的書畫品味。十九世紀下半葉以後,隨著日本欲「脫亞入歐」與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野心,臺灣美術的發展有了不同於以往的新視野。直到二十世紀中葉,國府來臺後,將臺灣打造成「文化中國」的象徵,臺灣美術的面容,又有了新的變化。
值得注意的是,臺灣的歷史變遷成為臺灣美術發展的一大特色。這個特徵,不在於時空的流變如何影響臺灣美術史的發展;而在於臺灣美術史的樣貌,如何在這個時局的變動之中,開展出某種獨具的「游動之間的主體性」。此論述的關鍵,乃在於不以外部的刺激為影響美術史發展的主要條件;而是著眼於藝術家如何在這個流動的情境之中,探尋作品甚至自我的主體性。
再者,臺灣美術史的內涵,亦非僅是西方藝術史的例證。以希臘羅馬為主流的西方藝術史發展,反映出的是一種受到特定品味人士所推崇的史觀。關於特定品味的討論,西方學者如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一九三○至二○○二)所提出的「秀異」(Distinction)論述,與傅柯(Michel Foucault,一九二六至一九八四)對於權力(power)與知識(knowledge)的批判,皆具有相當的啟發性且發人深思。而我認為,藝術史的發展不應局限在特定品味的界線之內被討論。值得慶幸的是,當我們回顧臺灣美術史的發展時,由於臺灣歷史所具有的多元與融合特徵,我們看到臺灣美術史研究的新契機。因此,舉凡非正統學院出身的畫家與民間的工藝品,亦可視為臺灣美術史的研究對象。此外,七○年代鄉土主義的盛行,也使得素人畫家的作品受到青睞。
再者,當「精緻藝術」與「民間工藝」的界線被打破之後,同時也影響了對於「純粹」與「實用」、「菁英」與「通俗」等概念的價值品評。如此一來,使得創作回歸到一種單純的美的實踐。而這個實踐之後的樣貌,則具有強烈的個人經驗之縮影。然而,個人經驗實與社會的流動與權力的結構有關。因此,如何在這種變動的狀態之間,將個人的經驗轉換為視覺的語言,同時在其中呈現出自我的主體性,亦是美術史發展值得觀察之重點所在。
另外,值得注意是的,除了創作者的身分界線逐漸模糊之外,作品被觀看的方式與意義,也存在著不同觀看者所賦予作品的「複數性」特徵。此現象,在臺灣美術史的發展過程中,屢屢可見。(尤以一九五○年代臺灣畫壇對於「國畫正統」的討論,最為顯著。)
簡言之,本書以「游動之間的主體性」來思考臺灣美術史的發展,一方面是對於以往從「邊緣與中央」、「殖民與帝國」、「自我與他者」等論述的反省;另一方面也是筆者對於現今所處的歷史世界之回應。因為,今天的世界已是一個「平行」交流的世界。因為,今天的世界已是一個可以自由地在「真實」與「虛構」之間移動的世界。而科技的體驗,也使得人類輕易地披覆著他人的文化生活,有如「文化肌膚」(culture skin)一般。因此,如何在時間、空間與文化之間的「游動」中,呈現出對於自我主體的思索,實為今日美術史研究的重要課題。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邱琳婷 著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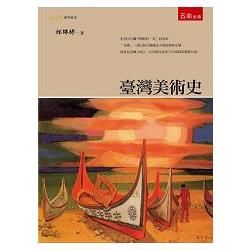 |
$ 411 ~ 494 | 臺灣美術史【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邱琳婷 著 出版社: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09-07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472頁/23*17cm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臺灣美術史
生活中已離不開對於「美」的追求,
「美術」一詞已經不僅僅是小學的課堂名稱,
而是在這塊土地上、在你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臺灣這塊溫暖的土地,孕育了許多豐厚的產物與多元的文化,美術在這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除了早期為人們熟知的陳澄波、石川欽一郎的畫作外,其實更早之前「美術」已經悄悄在這塊土地上誕生並無限繁衍 ......。
本書帶你從美術史的起源,到現代美術家們的精采作品,見識臺灣美術史的發展與進程。
作者簡介:
邱琳婷
台灣大學藝術史博士
曾任暨南國際大學共同科兼任講師
現任東吳大學歷史系兼任助理教授、輔仁大學藝術與文化創意學士學位學程兼任助理教授
曾出版《台灣美術評論全集:謝里法卷》、《圖象台灣:多元文化視野下的台灣》等書。
本書部分篇章,曾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日本長崎大學等校,進行論文發表。
TOP
章節試閱
游動之間的主體性:臺灣美術史的新思考
臺灣美術史的書寫,雖與近代臺灣的歷史及臺灣史論述緊緊相扣。然而,它卻不僅只是歷史之中的一個樣貌,而應視其為在不同的時空中,藝術家探尋美術主體性的流變軌跡。一九五○年代的王白淵與一九七○年代的謝里法,受到政治史觀的影響,從美術運動史的角度,思索臺灣美術的發展,即是對其所處的臺灣歷史氛圍所做的回應。一九八○年代開始,美術史的研究則著眼於政府與民間的臺灣書畫收藏,試圖以傳世的水墨作品勾勒出臺灣美術的發展面貌。此時的史觀,多以連橫的《臺灣通史》為參照系,而視明清時期...
臺灣美術史的書寫,雖與近代臺灣的歷史及臺灣史論述緊緊相扣。然而,它卻不僅只是歷史之中的一個樣貌,而應視其為在不同的時空中,藝術家探尋美術主體性的流變軌跡。一九五○年代的王白淵與一九七○年代的謝里法,受到政治史觀的影響,從美術運動史的角度,思索臺灣美術的發展,即是對其所處的臺灣歷史氛圍所做的回應。一九八○年代開始,美術史的研究則著眼於政府與民間的臺灣書畫收藏,試圖以傳世的水墨作品勾勒出臺灣美術的發展面貌。此時的史觀,多以連橫的《臺灣通史》為參照系,而視明清時期...
»看全部
TOP
目錄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美術」概念的變遷
第一節 「美術」一詞在西方的發展
第二節 「藝術」一詞在中國的概況
第三節 「美術」一詞在東亞的流變
第四節 「美術」一詞在臺灣的形塑
第三章 史前的藝術:人的裝飾
第一節 裝飾藝術中的風格
第二節 史前遺址出土的耳飾玦
第三節 古琉璃珠(玻璃珠)
第四節 文身
第四章 史前考古與原始美術
第一節 萬山岩雕
第二節 青銅刀柄
第三節 木雕
第四節 史前與原始藝術的紋樣特徵
第五章 十七世紀往來於臺灣的物質文化
...
第二章 「美術」概念的變遷
第一節 「美術」一詞在西方的發展
第二節 「藝術」一詞在中國的概況
第三節 「美術」一詞在東亞的流變
第四節 「美術」一詞在臺灣的形塑
第三章 史前的藝術:人的裝飾
第一節 裝飾藝術中的風格
第二節 史前遺址出土的耳飾玦
第三節 古琉璃珠(玻璃珠)
第四節 文身
第四章 史前考古與原始美術
第一節 萬山岩雕
第二節 青銅刀柄
第三節 木雕
第四節 史前與原始藝術的紋樣特徵
第五章 十七世紀往來於臺灣的物質文化
...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邱琳婷
- 出版社: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09-07 ISBN/ISSN:978957117897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72頁 開數:20K
- 類別: 中文書> 藝術> 美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