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那個熠熠閃光的舊世界 駱以軍
這本書非常奇妙地繪下了兩種旅人的眼睛所見:一是在國度之外,他人的祖先之地,像候鳥般暫待一段時光,進入他人的夢境(又不僅是這個安葬了60餘座埃及各代法老陵墓的帝王谷、神廟的浮雕、墓室壁畫、「死者之書」、以及出土的,數千年前建築這些帝王谷墓穴的古代工匠村落遺址,那些陶器碎片上記錄的,那彷彿可見栩栩如生如在眼前的工人們,生活裡的「曾經這般活著」的繪畫);另一是人類學眼睛,鉅細靡遺,不帶成見地進入當地村莊,他們的經濟處境、男女關係、禁忌、笑話,並不如第一眼表面所見的陰陽虛實──譬如這些年台灣已陸續譯介的,像奈波爾、保羅.索魯這些具備了「現代」(大航海、帝國、殖民、貿易,傳教士冒險家與博物學者軍隊的地圖、路徑;文明的侵略或滅絕)全景思維的旅行文學書:旅行不再只是塞萬提斯《唐吉訶德》大冒險那樣魔幻、天真、抒情,一個流動中反溯、見證,幾百年來(由西方)「大旅行」如何由滅絕、踩踏、掠奪、同一化他文明而形成一處處四不像貝塚廢墟,所建構出來的。這個「既在外,又置身其中」的視覺移換,對「旅行」本身提出種種向度的質問:什麼樣的時間耗失,才算進入那個「觀看的風景」裡?如何生活在他方?「我」是誰?在漫長旅途中,我是否被當地人信任、視為朋友,不只是個傻B觀光客?
這個流動中的視覺,恰好目睹(見證了)那一切栩栩如生的古老時光「活化石」,在全球的觀光產業(由旅行社、飯店集團、航空運輸、或作為被「慾望客體」化的這些發明出來的古蹟、海島、沙漠、叢林……「景點」周邊依附寄生的在地導遊、商家、特產紀念品批發、出租車司機、妓女……之網絡),愈來愈不需付出現代旅行之前身「大冒險」之代價:不論時間上、可能遭遇之危險、以及在這旅途中對旅行者內在成見之瓦解、挑戰 ── 旅行愈變成一種至多兩週便可將經驗割取、裝框、消費之的「馴化的風景」。
於是弔詭的,前一代的旅者(冒險家),驚異、獵奇、讚嘆於矗立在他人祖先之地,那些該被保護之考古學遺跡(金字塔、泰姬瑪哈陵、長城、印加神廟),作為這個龐大觀光產業所建構「視覺、或時間感」,旅行的聖物同時快感之高潮(如作者所言,成為「露天秀場」);同時,後一代的旅者,却為了清出這個觀看劇場,造出一個巨大的、拆遷怪手,對「遺跡」周遭(其實也是活生生的「遺跡」)清空的歷史推土機。譬如北京奧運前,將紫禁城周遭整區整區,數百年以上的老胡同(包括裡頭像海底礁岩,各種複雜物種,自給自足的底層庶民生活樣態),悉數遷光,剷平。
本書中間有一段是男主角在睡夢中,會從他軀體中跑出有著和他同樣臉孔、但或鳥身、或黑影、紅影不同層次的「潛意識分裂自我」,「就好像全身各零件湊不太起來。就像『咖』,是我的生命能量;『巴』,是我的靈魂;『舒特』,是我的影子。我正在準備的展覽讓我滿腦子古埃及神話……對古埃及人來說,一定要把這些元素結合起來。」
這一段夢魘中,埃及神話描述的「不同的我」穿越界面跑出的段落,同時在紐約發生了雙子星大廈爆炸攻擊。
這同時,他身邊出現的,是以男色「嫁」給西方觀光客裡「老女人團」而交換房子、電器、貨車、店鋪的當地年輕男人;或是半真半假宣稱自己的畫作被當作十八王朝古董,收藏於羅浮宮的畫家「穆漢梅特」;或同時女主人翁為當地孩子們創作課的美麗布偶,在摩納哥辦了一場「布偶拍賣會」。這糾葛、陷入其中,古蹟,環住於古蹟墓穴旁數百年的遺民、觀光客、因觀光客而改變內在精神與物質時空感的年輕一輩,這一切不再只是「觀看與被觀看」視覺的慾望化想像、建構,這麼單純的問題了。因為他們進駐其中,與當地人犬齒交錯,在文明史的巨人夢境,「夢裡不知身是客」,被扔擲進二十世紀現代的懵懂子裔們;這種消費性觀光浪潮的交涉與逆反對抗:有原創「自我」的召喚,有因應這些文明(經濟)優勢侵入者的偽詐與變貌。這一切都錯織混雜在一塊,一如他的古埃及神話,「好的我」、「壞的我」,不同零件組合的分裂人格在這個旅人的靈魂裡糾葛。
這本書的後半,如同所有在時光洪流中的故事命運──如同物理學家常用的比喻:我們所在的空間如同一張無限大的薄膜,把一只保齡球放在這張薄片上,球四周的「空間薄膜」便會被拉扯變形,在原本「平坦」的場地上形成一個「凹陷」。按廣義相對論,宇宙中的每一顆恆星都在空間薄膜上形成各自的凹陷處──我們跟隨著作者的「既旁觀又進入」、「既預知其命運又無法攔阻」的哀傷,前半書儘可能恬淡、領會古納居民的嘉年華歡會貧窮但笑謔的生活態度,種種「觀看的流動」,然他們亦「惘惘威脅」知道那一切因為「旅遊工業的龐大收益」,所編織交錯的埃及掌權者的貪念、跨國旅行集團將手伸進這些擁有「世界級文明古蹟」的第三世界國家,將原來當地居民「以往總是充滿生命、勞動、創造的地方,但現在卻成了個死寂之地,只剩『文化秀場』:全世界最大的露天博物館」、甚至共犯包括了地方宗教領袖、和譬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這類的外國組織……讀者才意識到,這本「漫畫書」前半部栩栩如生、歷歷如繪的那些旅館怪老大爺、那些美麗臉龐的古納少女和小孩、他們曾經以創造和勞動的布偶展、藝術工作坊,或調情、打屁、虛無地幹譙政府,或嘲笑外國觀光客,那些數千年在沙漠烈日建築蔭涼房屋的工藝……這一切如蠟燭被吹滅前的流光碎燄,竟然是這作者的「哀歌」:追憶、悼亡一個已被全球流動資本主義巨人推倒、踏平,毀滅的村落。
「六十年來,為了保留自己的家與生計,當地居民抵抗國家的開發計畫。建築師和警察(一個靠利誘,一個給威嚇)都沒有辦法驅散他們。開羅的掌權者無暇理會這個位於賽德偏遠處的村莊,古納終於是被遺棄的。」
然如同我們在捷克小說家赫拉巴爾的《過於喧囂的孤獨》,或班雅明的《單向街》已閱讀過的,「文明的塌縮」,那些緩慢悠長時光慢慢形成的充滿靈光的手工製品、人與人悠然互動發展出的關係、櫛次鱗比的小店鋪、這些城市底層的老人、小孩、拾荒者、妓女、酒鬼、雜貨鋪小販、「底層的珠珍」,一個自為的、或許髒亂雜遝的(以那些習慣機場大廳、國際連鎖五星飯店、或免稅名牌店的shopping mall大商城、或所謂「博物館」……的現代觀光客被建構的展廊式空間習性來看),充滿不可測細節、巷弄、黃色笑話、古老神祕觀……那樣一個生機盎然的古老、美好小宇宙,終將被「時代的颶風」碾碎、壓扁。何況古納這樣一個小村落?
「所有的人都成了旅遊工業祭壇上的犧牲品,被驅逐丟棄在荒城的郊區,遠離一切工作的可能。他們甚至付不起孩子們40埃鎊的教育費。
2010年夏天開始,整個古納被幾公里長的混凝土牆圍住。」
漫畫家哀傷地記錄下拉摩斯之墓上方,那些房子被拆毀的過程;被強迫遷村的居民,連他們視為最貼身財物的家畜都不准帶走;全村像被轟炸過一樣;10公里外的「新村」,政府蓋了一排排同一模樣的水泥房,窄小且「夏日像烤箱,冬日像冰櫃」;新屋很快牆壁便裂開、這些居民原來的、幾代下來的生活方式,徹底被斬斷、去脈絡、像科幻片那樣硬生生取消了。而原本的古納,變成居民要循路走回,卻要收門票的,「考古遺址」了。
「古納的繁星之夜不復存在……」
跨國觀光或地產財團、地方政府的巨大利益考量、BOT開發案,所描述、想像的,以全球資本家或觀光產業的剝奪之眼,而非以原本住在其上之居民生存之眼看待土地。而犧牲的通常是弱勢、無能為自己言說、且所依存之地一旦被剝奪,幾乎是被宣判「活著等於哲學意義上的死去」,原本上一代富人不感興趣,才得以在城市地圖邊緣暫棲的立錐之地也被(以法令、警察、國家之名)奪走的「甚麼都沒有的窮人」。
這是坤墉兄在台灣這個紛雜、迷惘,閱讀市場又如此蕭條的時空,猶出版了這樣一本美麗、充滿讓人省思之「視覺書」,讓人可敬可感之處。古納的故事(或這本漫畫最後哀傷的結尾)或並不是孤例,想想這幾年在台灣發生的一件一件規模或不相同,但畫面、場景似曾相識的事件:台東海岸美麗灣開發案、士林王家拒絕都更強制拆遷案、三鶯部落、樂生療養院、華光社區強制拆建案、甚至師大夜市的攤商與居民之對立乃至清除、掃蕩……我們從遙遠的埃及法老王陵墓旁的古納小村,在漫畫家那時光流河、充滿情感的凝視下,終於被消滅、成為煙雲;看到背後類似的巨手:我們其實或也就活在一個更大規模些、更複雜意義,在這個全球化浪潮裡無法逃避那「惘惘的威脅」的古納村。但除了由臉書、或社運團體,此起彼落發生的抗爭、憤怒、以及主流媒體如潮汐、短暫又不留下反省的「變形蟲群聚式」激情,我們有沒有更多的參照系,更抒情的觀看方式,或更持續的思考與辯證;更知道世界其它地方同樣發生著這樣科幻而粗暴的「清除、滅村」?我們可能面對一個新形態的,更複雜而專業操縱公共媒體印象的,變貌的巨獸,它掠奪的或不止是它允諾將變成「大型遊樂場」的美麗新世界的,這些窮人、邊緣人、破爛老社區的小小碎塊土地,而是一個更隱晦而需我們持續辯證,讓它浮現的,「原本比較美好的那個我們裡面的部分」:對時光中他人生活史的尊重;不能棄守的正義價值;美學上抵抗那科幻造景的空洞消費催眠;思慕微微的對那些人們挨擠在一起,有體臭、有體溫,有煙火氣,有笑話,有古老的祝福話語的,熠熠閃光的舊世界,仍懂得珍惜、寶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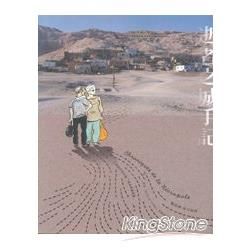

 共
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