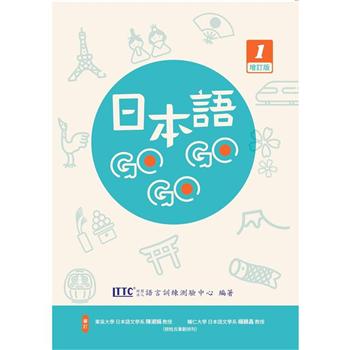郭象《莊子注》一向被視為魏晉注莊的權威,本書作者認為郭注雖然發揚了莊子的思想,同時也扭曲了莊子的思想。因其主觀性太強,對於莊子思想中之某些觀念:或別有用心,而以臆為說;或擅以己見,而強作解人。致使莊周之「莊子」成為郭象之「莊子」。作為莊子哲學之詮釋者,郭注非但無功,或且有過。
郭象的罪過不在他對莊子思想的壟斷,而在他對莊子的詮釋,作者對郭象《莊子注》的檢討即在把握莊子「注文」與「原文」之間的差距,及觀念的相反、義理的相悖。 蓋以「手」指「月」,貴能因「指」得「月」。 愚者見「指」不見「月」, 又復誤「指」以為「月」,是誠可謂不善賞月者矣。
作者簡介
王淮
王淮,字百谷,安徽合肥人(一九三四~二○○九),畢業於師大,執教於中興,早年著有《老子探義》一書,終生服膺老子之道,清靜無為、淡泊自然,尤其對老子所謂:「治人事天莫若嗇」,一義體會深刻,嗇者、收斂精神,拒絕釋放能量,不得已,為了謀生及升等需要,勉力著述,曾獲第五屆菲華中華文化優等著作獎及三次國科會獎助。但皆束諸高閣、未予發表。
因其行事踟躕,顧慮太多,如今匆匆離去,並無交代,而學生故舊,殷切期盼,今特將其早年著作加以搜集分類,整理出四冊定名為「王淮作品集」交由印刻公司出版。以免留下遺憾。
武陵唐亦男 謹誌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