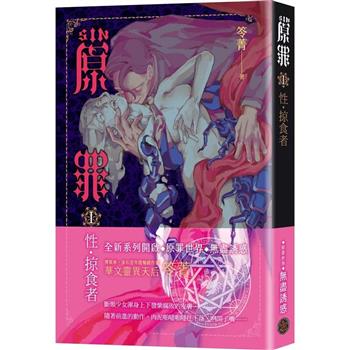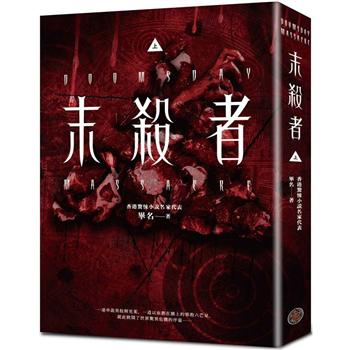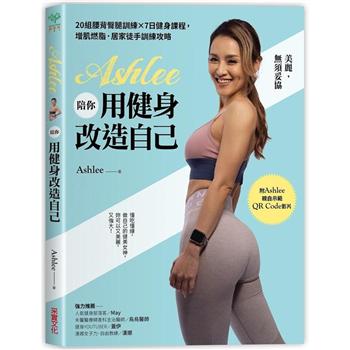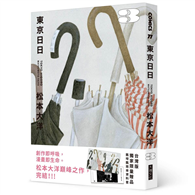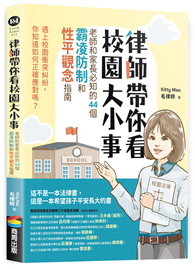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2 項符合
鄭泰昇的圖書 |
 |
$ 425 ~ 475 | 島嶼轉譯:馬祖戰地軍事文化轉譯與空間再生
作者:鄭泰昇/總編輯;龔柏閔/主編.編著 出版社:成大出版社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553 ~ 618 | 島嶼轉譯.文學馬祖
作者:總編:鄭泰昇/編著:黃資婷/主編:黃資婷 出版社:成大出版社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