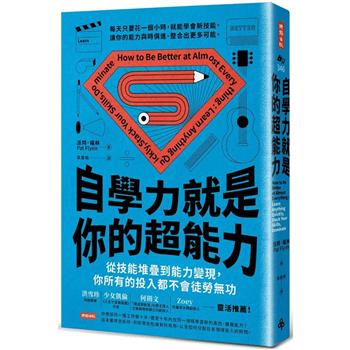推薦序
瘋狂之必要
或許因為我自己是個瘋瘋傻傻的人,所以我對於其他生命充滿熱情的狂人,也特別喜歡。
像我九歲的乾兒子Lawrence,是我認識年紀最小的狂人,他自從會走路開始,就已經會踢足球了。無論走到哪裡,都要隨身帶著一顆足球,不然就好像沒穿衣服似的渾身不自在,即使連跟著大人去喝喜酒也不例外。當然,他也踢得極好,參加兩個足球俱樂部之外,還定期接受每個月遠道從日本來訓練國手的教練指點。
她的媽媽為了想知道小學中年級的兒子是不是真的愛足球成痴,長大後能夠如願到德國或是日本發展,成為職業足球員,所以這學期開始,決定要用跆拳道與空手道試探他看看。
我:「你是要用其他運動來考驗他的定性,就像用美女色誘唐三藏這樣嗎?」
母:「差不多素這樣……」
當媽媽的心機真的好深啊!
可是我一點都不擔心,一個對足球如癡如醉的孩子,就算未來沒有成為職業運動員,也會長成一個很棒的人,因為從小就有運動員精神,一定會潛移默化深植著很好的自律能力,還有極高的道德標準。
那麼旅行者呢?
旅行成癡的人,人生無論走到哪裡,無論做什麼,都是旅程的一部分。我從十六歲背起二十多公斤的行囊,第一次成為背包客開始,這個無形的背包,至今從來沒有卸下我的肩膀,那肩胛骨上的勒痕像是一道光榮的印記,其他人或許看不見,但是另外一個旅行者,卻老遠就能看出來。
這是為什麼,看網名阿Q的香港年輕設計師鍾振翹,存了一年的旅費後辭去工作去新疆旅行,也將我帶回到多年前跟著新疆畫院的老畫家,在絲路旅行的美好時光,從庫爾勒到庫車,阿克蘇到喀什,全都歷歷在目。但這個傢伙比我更瘋狂,他買了一頭瘦小的驢,騎著牠走了七十五天橫越新疆一千四百多里的路程,最後在市集裡把這隻被他取了個帥氣法文名字的Pierre,挑了個應該不會吃驢肉的維吾爾人賣掉,結束這場相依為命的旅途,這故事很難不讓人拍手叫好。
但是更好的是,真正的旅人懂得心存感激、好聚好散,就像阿Q自己說的,這個分手的結局很平淡,沒有濫情哭啼,更沒有歇斯底里,「……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給我一個真實的回憶」。
那些在澳洲、紐西蘭打工度假結束,把陪伴了一年朝夕相處,南征北討的二手車賣掉,靜靜回到家鄉的生活軌道裡繼續生活的台灣年輕人,應該也完全懂得阿Q賣驢的心情。
無論是帶著足球上飯桌的小學生,還是騎著驢子遊新疆的旅行者,表面上做的是一件沒有必要的事情,甚至還會帶給別人困擾也說不定,就像沒有人「必須」去國外打工度假,過著割蘆筍、擠牛奶,在太陽下揮汗如雨的生活,但對於人生充滿熱情、好奇、癡迷、瘋狂,本身就是對生命最真實、也最美好的禮讚,這在我眼中是極其必要的。
因為就像海倫.凱勒說過的:「世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不可目見、亦不可膚觸的,只能用心感受。」感受心臟充滿無可抑遏的、興奮的跳動,是我們為什麼活著的原因,如果什麼熱情都沒有,什麼險都不肯冒,過著心如止水,沒有任何波瀾跟風險的人生,並不見得生命會比別人長-很有可能只是顯得特別漫長罷了。
褚士瑩 國際NGO工作者╱作家
前言
欲求未滿
不要追隨前人的足跡,反而要往未知探索,並留下你的軌跡。──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在同齡的人當中,我的旅遊經驗算是比較豐富,從最大眾化的背包旅行,到現在開始流行起來的單車和搭車旅行,雖然我稱不上是專業的玩家,但都總算涉獵過。然而,旅行的次數愈多,震撼心靈的次數便愈少,當初出發旅行的激動早已經蕩然無存,現在簡直快到心如死水的地步。而且我在單車和搭車旅行期間,都覺得自己只是在走別人走過的路,看別人看過的風景,或許我已經到了旅行的瓶頸。我束手無策,雖然換過不同的旅行方式,但依然無法突破心中那個該死的瓶頸。
老人與海
我知道,只有返回旅途,才可以找到突破瓶頸的方法,重新啟動沉寂的靈魂。我坐著順風車,走過四川、甘肅的一些地方,輾轉之下來到青海湖邊。
中國西部的某些地區人跡罕至,加上當地民風較發達地區純樸,人們彼此之間的猜疑心相對較輕,因此,只要我願意在國道上伸出大拇指,等不了多久,便會有司機邀請我坐上順風車。這些熱心的司機大部分都是孤身上路,因為路途遙遠,很容易在開車的時候打盹,一不小心,甚至會釀成致命的交通意外,所以他們很樂意載上我這樣的過客,閒話家常,打發枯燥乏味的行車時間。
我在這裡搭上一輛開往新疆庫車的大卡車,結識了跟我同樣姓鍾的卡車師傅,我叫他鍾大哥。他喜歡閱讀,在卡車的抽屜裡總會擺上幾本小說。他也熱愛戶外活動,尤其熱衷於釣魚,我們在漫長而沉悶的旅程裡幾乎無所不談。有一次,我無意地問及他自己認為最自豪的一次釣魚經歷,那時候我只想一直跟他聊天,好讓他不至於會開車打盹,反正我心裡早有答案,他無非都是說釣上了一條有多肥多大多稀有的魚而已。
沒料到他很認真地對我說:「我曾經試過只帶上一把小刀、一個帳篷和一個煤油爐子,騎著摩托車到黃河邊,在那兒一共待上十幾天,以漁獲維生。在那段時間裡,有一條大魚上鉤,我看到水中魚影,從來都沒見過那麼肥大的魚上鉤,但我用的是細線細鉤,只能持之以恆地慢慢收竿,絕不能弄痛大魚。只要大魚沒有奮力掙扎,還是有機會成功釣上大魚的,於是我小心翼翼地往回拉,跟大魚搏鬥了一整天,左右手不停地交替接力,雙手幾乎一起麻木了,很可惜最後大魚還是拉斷魚線溜走了。」
這不是海明威筆下《老人與海》裡的情節嗎?鍾大哥一直堅持與大魚角力,雖然最後他沒有戰勝大魚,但換個角度來看,現在鍾大哥卻因為這一段經歷而引以為榮,這何嘗不是另一種勝利?對比之下,我想我是一時之間走火入魔,過分重視旅行中能得到什麼,只為結果,到頭來反而一無所得。旅行的意義有如彩虹一樣難以捉摸,愈刻意去抓緊旅行的感覺,它反而愈會在心中慢慢流走,我們無法闡釋,亦無必要向其他人交代,只能心中領會。
在之後的交談中,鍾大哥無緣無故地說到新疆盛產毛驢,特別在南疆一帶。而我也順便追問一頭毛驢的價格大概是多少,鍾大哥回答說只需掏出一千多塊錢就能買到一頭毛驢,我覺得這樣的價錢非常合理,才初步有一個構思,希望買一頭毛驢幫我馱上行李,由我牽著毛驢徒步在新疆旅行。這一趟順風車,足足走了三日兩夜的路程,才途經庫爾勒。
我想在庫爾勒開始旅行,剛巧鍾大哥也要在庫爾勒卸貨,順便休息一天。於是在晚上,鍾大哥帶我去品嚐新疆有名的□坑肉,淺嚐幾杯啤酒,我就這樣交上鍾大哥這個新朋友。
新疆印象
第一次到新疆是在三年前,為了參加一個回族朋友的婚禮,從成都坐火車出發,兩千多公里的路途,五十多個小時的車程,我就坐在走廊的小凳子上,傍著窗前,呆呆地看著無邊無垠的戈壁灘。感覺自己像一陣風一樣,置身其外,連那淡黃色的沙土都未曾觸摸到手,即抵達烏魯木齊──那被蒙古人稱為「優美牧場」,現今一片喧鬧的繁華城市。參加朋友的婚禮之前,在朋友的安排下,我第一次參加旅行團,像小鴨一樣的跟著領隊的小旗幟,走馬觀花地參觀過吐魯番的一些景點,比如火焰山、交河古城和葡萄溝等。我卻對這些人工化的旅遊景點提不起興趣,我可不敢因為曾經參觀過這些景點,而跟別人說我到過新疆。直到今時今日,不依靠照片輔助喚醒記憶的話,我只能回想起,在達□城附近,那一排排傲然聳立在戈壁灘上,像荷蘭風車一樣的巨型風力發電機而已。
二○一○年一月,我又一次到新疆,這次是因為在乘坐巴基斯坦的夜間火車時被人迷暈,搶去身上財物,接著火車抵達總站──沙塵滾滾的蓋達市(Quetta),那是俾路支省(Balochistan)的首府,這個軍事城市距離阿富汗南部塔利班的根據地大約只有三百多公里。在火車站附近的警察局錄下口供之後,迫不得已要在前往伊朗的路上折返中國,於是又登上了開往首都伊斯蘭堡的列車,回到首都尋求中國大使館的援助。透過一位熱心的巴基斯坦人的介紹,我可以暫時住在一位中國人的家裡,無須擔心吃住問題(即是白吃白住),然後到大使館辦理文件手續,最後就這樣狼狽地拿著大使館發出的旅行文件辦理登機手續,前往烏魯木齊。飛機越過了白茫茫的山脈,從萬尺高空往下看,延綿不斷的山脈就像我們在看地圖顯示的地形一樣,失去了懾人的氣魄,那到底是天山還是崑崙山山脈?我到現在也沒有弄清楚,我只知道我抵抗不了北疆寒冷的天氣,所以老早就訂了翌日的機票,飛回氣候比較溫和的內地。
我總是以一個過客的身分到新疆,除了那天參加朋友婚禮的記憶之外,我努力地回想,也記不起我在新疆遭遇過什麼較為特別的經歷。而這一次我突發奇想,隨心地想到要牽一頭毛驢遊新疆,我知道一定有前人做過這樣的蠢事,雖然我不至於能為別人留下軌跡,但最起碼,我沒有靠著網上的旅遊信息和旅行攻略書籍,刻意地走在別人留下的足跡之上。
驢友感言:機遇
要不是坐上了鍾大哥的順風車,我也許還是會聽聞新疆盛產毛驢,但早一點點或遲一點點聽聞,也許便不會激發我與驢同遊的念頭,Pierre也不會走進我的生命……
如果沒有遇上Pierre,我跟他現在又會怎樣?
致台灣讀者序
遠方的好友
有一天晚上,本應已到睡眠時間,但我還在床上輾轉反側,久久不能入睡。
雙雙似乎發現我失眠,溫柔地問我一句:「你在想什麼了?」
「我在想Pierre……」我深呼吸了一口氣,然後回答說。
在房間裡,只剩下一片沉默,還有在我腦海裡,Pierre那開始模糊的臉。
我用力地回想這位身在遠方的好友,我們曾經一起吃飯、一起拉撒、一起旅行,曾連續七十五天形影不離。旅行的時候,我們總是一前一後地走路,有時他拉著我,有時我牽著他,彼此為大家遮擋炫眼的陽光,雖然如此,但我們的步伐卻是一致的,他從來都不會踩到我的腳後跟。
那時候的陽光總是能令人感到和暖。
記得他很貪吃,喜歡一邊走路,一邊低頭在路上找吃的,無時無刻都在吃,每分每秒都要吃,我知道,他畢生的願望是活在大草原上,躺著都可以吃。他怎樣吃都不夠,像個焚化爐,餓起來的時候連紙皮都要啃,相反,如果在他面前放滿了紅蘿蔔和玉米,他就會挑來吃,剩下一大把乾草,最後來一陣風,將被嫌棄的乾草刮得四處飄零。
那時候的風總是夾雜著乾草的氣味。
他吃得多,故然也拉得多。他拉著我走的時候,經常放屁,又濃又烈,我知道他是故意的,等到我牽著他走的時候,他就會憋著不放。再待他多放幾個屁,我就能從他兩股之間,看到褐色的糞蛋兒咕嚕咕嚕地落下來。他一直都是邊走邊拉,從不為拉屎這件事而停下腳步,像我一樣煞有介事地找個隱蔽的地方解決。我在想,假如有人要追趕我們的身影,只要順著他的糞蛋兒軌跡來找,肯定可以找到我們。
那時候的空氣總是會傳來一股臊臭味。
在他的面前,我才發現自己是多麼的渺小。從前,我總喜歡取笑他瘦小,其他毛驢都比他長得肥壯,但我從沒有以自己來跟他比較。他能輕而易舉地拉著一台載滿貨物的木頭車,走上幾十公里,不哼一聲,但他的一聲驢叫,可以淹沒一切,喚醒方圓十里的人,即便他再瘦小,他的力量亦比我強大得多。在他拿出褲襠間那龐然大物來嚇唬母驢的時候,我更知道自己是何等的卑微,都不好意思在他面前撒尿了。
如今,我已經有大半年沒跟他見面,不知道他耕過多少畝地?吃過多少斤紅蘿蔔?爬過多少頭母驢?我們的生活已經無任何關聯。我只知道,我開始記不清他那惹人發笑的臉,想不起他那高亢興奮的嗚叫。也許會有這麼的一天,我走在喀什街頭,他迎面走來,我也沒記起他就是以前的那個他。
這時,雙雙突然打破了這個空間的沉默,說了一句話:「Pierre總要面對他自己的命運,就讓他走吧。」
我不知道該如何應對,我有一些話想說,但很快又咕咚地把話吞回肚子裡去,只是簡潔地回應一下:「嗯……」
今晚的黑夜異常地清明,像大半年前的夜空一樣,點綴著滿天繁星,我在隱約之間,似乎看到有一顆星星逐漸昏暗下來,最後從黑幕之中退出。
我明白,這一切都沒有永遠。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