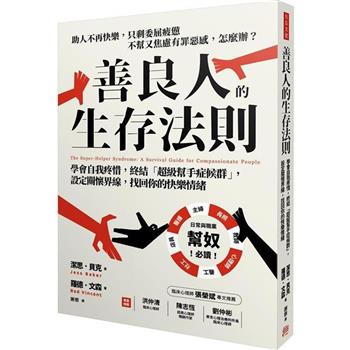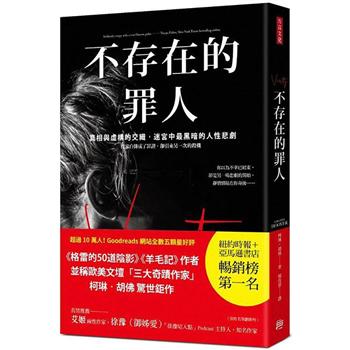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阿涅絲.波西耶的圖書 |
 |
$ 260 ~ 523 | 巴黎左岸1940-1950:法國文藝最璀璨的十年
作者:阿涅絲.波西耶 / 譯者:高霈芬 出版社:創意市集 出版日期:2020-02-08 語言:繁體/中文  共 1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1945年二戰結束後,有一群作家、哲學家、藝術家、作曲家,
在巴黎小小一平方英哩的街區內,創造了歷史,改寫了世界的面貌。
他們辦了新雜誌、提出新哲學思維、改寫繪畫風格、挑戰婚姻與性別、創造電影的新浪潮。
他們是沙特、西蒙.波娃、卡繆、山繆.貝克特、莒哈絲、畢卡索、梅洛-龐蒂、楚浮、莎岡⋯⋯
這群人不僅活躍於巴黎左岸的藝文圈,
也使全世界著迷於他們的生活、思考方式。
對世界充滿熱情的巴黎青年們,
還希望能透過思想與行為改變世界--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間,期望找到「第三條路」;
新一代的畫家,超越了社會寫實主義畫風,轉而投入幾何抽象藝術;
哲學家則開始思索人身為人最終的意義,
並在巴黎咖啡館提出震驚世界的「存在主義」理論。
社會評論家波西耶埋首史料、專書與報章雜誌,並以絕妙的筆法,重述精彩、錯綜複雜的歷史事件,邀請讀者一同見證巴黎那十年的愛恨糾葛、哲學運動、社會改革與藝術創新,一睹巴黎左岸迷人的歷史與傳奇。
【書內人物】(部分)
尚-保羅・沙特
Jean-Paul Sartre
西蒙・波娃
Simone de Beauvoir
阿爾貝・卡繆
Albert Camus
梅洛-龐蒂
Merleau-Ponty
畢卡索
Picasso
法蘭索瓦•楚浮
François Truffaut
山繆・貝克特
Samuel Beckett
瑪格麗特・莒哈絲
Marguerite Duras
法蘭絲瓦・莎岡
Francoise Sagan
碧姬・芭杜
Brigitte Bardot
作者簡介
阿涅絲‧波西耶Agnès Poirier
出生於巴黎,在倫敦受教育。記者、廣播從業員、評論家和作家。波西耶替許多英美主流媒體撰稿,文章散見於《衛報》、《觀察家報》、《倫敦泰晤士報》、《國家》雜誌、英國BBC、美國CNN、Sky News等,她同時也是法國政治週刊《瑪莉安》(Marianne)的英國編輯。波西耶寫了四本介紹英法兩國不同行事風格的書籍,其中包括:《一針見血:一名法國女子對英國的看法》(Touché: A French Woman’s Take on the English)。波西耶任教於巴黎政治學院(Paris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也替坎城影展預選參展之英國片。她巴黎倫敦兩頭住,喜歡騎單車、聽查爾斯・崔尼的音樂。
譯者簡介
高霈芬
傳播學士。翻譯碩士。習舞人士。希望成為文字煉金術士。神是,我不是。
E-mail: kathykurious@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