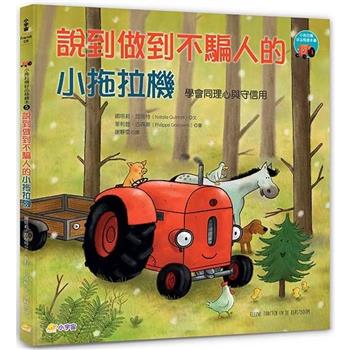一場深入中國的國際尋寶大競賽,
一樁歷史功過蓋棺難定的冒險事蹟
近百張珍貴照片
石窟寺廟、壁畫、經卷手稿、舍利塔……
重現高昌古國的古文明風貌
一八九五年冬天,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歷經千辛萬苦,深入危機四伏的中國南疆塔克拉瑪干沙漠,發現傳說中的古城遺址並帶走大批九百年前的佛教古物。這事件震驚國際考古學界,掀起各國對絲路沿線湮滅已久的佛教文明考古熱潮,一場國際尋寶的大競賽於焉展開。
這場尋寶競賽以德國人斬獲最多。他們在一九O二到一九O四年間共派出四梯遠征隊深入南疆,其中由本書作者勒.寇克所負責帶領的第二和第四梯次遠征隊,成績最為可觀。他從柏孜克里克石窟鋸下九世紀大型壁畫,並將無數文物帶回柏林,卻有陰錯陽差地將垂手可得的敦煌寶藏拱手讓給了英國人。
勒.寇克在書中親筆述說這段尋寶過程,輔之以百張現場拍攝的珍貴照片,生動記述了德國人在絲路沿線冒險犯難的驚險經歷,文中不僅充滿豐富精采的冒險故事,更為南疆的地下文物寶藏記錄了一份珍貴的歷史素描,填補了這段歷史的空缺。
這些掠奪而來的古物寶藏,如今分散在世界至少十三個國家的博物館裡,致使中國學者為之忿忿難平。而當年勒.寇克堅持鋸下帶回柏林國家博物館收藏的壁畫,大多在二次世界大戰毀於砲火……至於勒.寇克的歷史論斷仍眾說紛紜。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