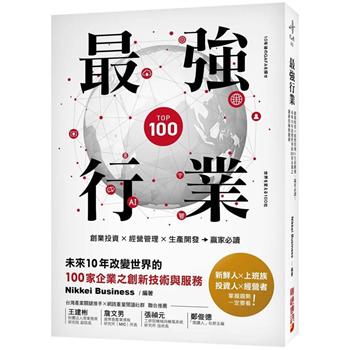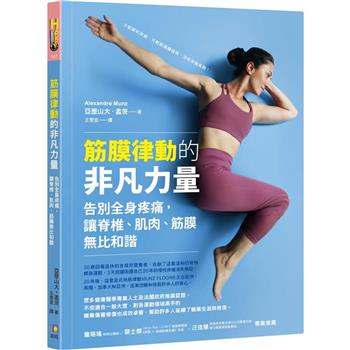穆迪斯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作家之一。
——賈西亞‧馬奎斯
一個嚮往大海卻總被繁務纏身而四處奔波的旅人,
偶然見到一艘老舊不堪的貨船,
那副不得不行旅的堅毅與宿命身影使他著迷。
第二次巧遇,老貨船已像是行將解體,如鬼似影般晃晃蕩蕩。
第三次相遇已非偶然或巧合,那老船似乎即將擱淺沉沒的不安竄上他心頭。
難以理解的夢兆和疑惑驚擾著他,迫使他去找出這艘船的身世謎團。
直到他在一段渡河的航行中,認識了一名旅客伊度里。
伊度里曾經是那艘老貨船的船長。
對漂泊海上的伊度里來說,愛情早已不是他生命中預期的事,
誰知愛情卻百般任性地闖入他的平靜生活。
年過半百的伊度里,愛上一位神秘的年輕美麗女子瓦妲,
為她買下老舊不堪的貨船,成為她的合夥人兼船長,
屬於海上的男人,愛上了一個屬於陸地的女人,
無畏年齡上的差距,或者是命運上的歧異。
伊度里駕船在港口與港口之間移動,瓦妲則一地一地坐著飛機趕去會合。
他們信守在里斯本第一次纏綿時就許下的約定:不去思考後果,也不要承諾未來,
他們經過一個個港口城市,一次次慢慢地、仔細地做愛,
彼此的愛戀更緊密,卻又在等待見面的過程中越來越無法肯定。
他們天生就像是陸地與海洋難以媒合,貨船卻提供了他們相會的機遇。
然而,隨著貨船老舊而不堪航行,命運終究將下判決……
這是哥倫比亞名作家阿爾巴羅‧穆迪斯膾炙人口的系列小說《馬奎洛的奇遇與厄遇》中最精采、且充滿生活哲思的一部,以老貨船的形象與一段注定無望卻又渴望的愛情相依相喻,令人深思不已。系列小說主角馬奎洛在拉美文壇可說是家喻戶曉的形象,他是一個「身上帶著被扔下船的水手氣息」卻又很會賺錢的人,他不怕自己的流浪會遭遇命運最殘酷的磨難,他相信之後總會有個奇妙轉折。
作者簡介:
Alvaro Mutis(阿爾巴羅‧穆迪斯)
哥倫比亞詩人、小說家、評論家,是當代拉丁美洲最偉大的創作者之一。他與賈西亞‧馬奎斯一樣,不僅名遍哥倫比亞,也是世界知名作家。一開始,他是以詩人的身分立足文壇,二十五歲出版第一本詩集,當時,盛行拉美的「魔幻寫實主義」旋風未曾影響他(卻也因此而未若以魔幻寫實創作的小說家受到當時文壇注目),但與他同世代的詩人帕斯(Octavio Paz)則非常讚賞他的詩作。
在他出版第一本詩集將近三十年後,他才開始小說的寫作。彼時,他正在處理詩作“The Snow of the Admiral”譯為法文的事情,突然之間明白,這不是一首詩,而應該成為一部小說,因此,才開始了他以瞭望員馬奎洛(Maqroll el Gaviero)為主角的一系列小說作品。他本來只想完成這一部作品,沒想到卻越寫越多,第一個故事寫完,已經多達三百頁。其後五年之間,他又寫了六本書,都圍繞著馬奎洛的故事發展。最後,七個故事集結成《Empresas y Tribulaciones de Maqroll el Gaviero》,英文版《馬奎洛的奇遇與厄遇》(The Adventures and Misadventures of Maqroll),被選入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經典系列。這個角色,幾乎就是穆迪斯自己的寫照,也成為他創作生涯中最負盛名的作品。
作者得獎紀錄輝煌,曾獲頒美國紐斯塔國際文學獎,該獎項被認為是美洲的諾貝爾文學獎。在他的文學生涯中還曾得過的獎項包括國家文學獎(1974)、國家詩歌獎(1983)、薩維爾‧比亞烏魯蒂亞獎(1988)、阿斯圖里亞斯王子文學獎(1997)、蘇菲亞王后伊比利亞美洲詩歌獎(1997)以及賽萬提斯文學獎(2001)。
章節試閱
船隻開到海港要花上十天以上的時間。途中拖船必須停靠在好幾個地方卸下部分的平底貨船,並收回已經清空的平底貨船,送回該公司位於大港口的倉庫中。其實我們兩個都不急著到達目的地。「我本來可以搭飛機。」伊度里向我說明:「但是我覺得坐船順流而下會更有趣,也更舒服。我一直很希望能像這樣搭船旅行。其實我對河流的認識僅限於某幾處河口三角洲,例如:須耳德河、泰晤士河和勒阿弗爾的塞納河。不是每一條河流都可以通行、都是安全的,不是所有的都這樣的。」我覺得他最後說的話似乎意有所指,但他卻沒辦法把它說出來,好像喉嚨突然變得很乾被什麼東西卡住了,只能隱約發出咕噥聲。接著他沉默了好一陣子,我們才繼續聊另一個話題。
因為有了伏特加梨子果汁的緣故,使得我們每天的旅程都十分愉快。為了紀念我們分享了彼此對巴塞隆納酒吧的忠誠度,尤其是擁有其他店家難以望其項背的調酒技術的波阿達斯和某間位於沙沃伊的酒吧,便決定以加泰隆尼亞語將這飲料命名為vodka amb pera,因為我們在巴塞隆納實在擁有太多相同的經驗了。除此之外,我們曾去過同樣的地方,碰到類似的事情,都特別偏好城市的某些角落,也都喜歡希臘的安普立亞斯港,和在拉艾斯卡拉的航海俱樂部中供應的鮟鱇魚。因為他個性中巴斯克人的特質讓我十分欣賞和敬佩,所以不難想像我們在幾天過後已經開始談論比較私人和內心的話題了。每天晚上喝完第三杯vodka amb pera之後,便會自然而然地說出心裡的話,並且小心翼翼地切入一些比較感傷的話題。我們的態度必須非常小心謹慎,因為不希望變成向別人展示什麼,或是說出一些陳腔濫調;如此不僅對於埋藏在內心深處的不幸過往毫無助益,也只能在幾個屈指可數、不知何時會出現的日子裡才有機會和別人分享。
在一個熱到極點的夜裡,我們坐在椅子上望著在天上緩慢移動的滿月,天空裡幾乎沒有半片雲朵,這在該區算是很少見的情況。看著沐浴在月光中的水面、森林中的空地和河岸,感覺很像走進梅特林克的戲劇場景中。我們很自然地聊到法蘭德斯,包括它的城市、人民以及烹調的風格,最後也無可避免地談到安特衛普。基於許多原因,我非常喜愛這座城市,而且對我來說,它是最有魅力、運作起來最合諧的港口了,因為在須耳德河上的交通是和緩、慢慢進行的,所以當船隻進出港口時,都像遵循著芭蕾舞劇的平衡術一樣。如同前面所說,我們已經對彼此敞開了心扉,而此時伊度里突然提到的一件事也特別引起我的好奇心。
「我在安特衛普,」他對我說:「碰到了讓我的命運產生大逆轉的人。一位是身兼船東和商人身分的黎巴嫩人,和他大部分的同胞一樣的能幹和瀟灑。另一位是船東的合夥人兼好友,我不知他來自何方,只知他常常不遵守道德約束,會在貿易種類繁多的地中海上搶生意。我們三人剛好到同一間印尼餐廳用餐,但是店裡供應的東方菜卻讓人倒盡胃口,完全無法引發食慾。因為我們碰巧在同一時間抱怨該店的服務有問題,最後便決定一起走到一間簡陋的小飯館吃點比較正常、食物種類較多的比利時菜。沒想到這個決定卻讓我的命運產生了無法想像的大逆轉。」
「怎麼會發生大逆轉呢?就貴國的民族性而言,我不覺得您們有哪一個人的身上會發生九十度的大轉變,因為這不符合巴斯克人的民族性。老實說,您們都是反抗者,並不會聽命於人,不過卻常常因為自己的法律而送命,或在自己出生和從年輕起便學習職業技能的村落裡老死。」事實上,看到像伊度里這麼典型的巴斯克人竟然會發生巨大的轉變,讓我覺得有點奇怪。
「您不相信是吧!因為生命中的驚喜總在不知不覺中成長茁壯,也不曉得何時會冒出來,重點是我們根本察覺不到它已經慢慢接近了,所以我們應該隨時做好準備。說真的,像我這樣一個堅持只跑熟悉的航線,避免自己去闖蕩或冒險的人,最後卻變成一艘看來醜的可以、隨時都會沉沒的流動貨船的合夥人和船長。」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便轉而詢問我的朋友,而我充滿好奇的語氣也引起了他的注意:「那艘船原本停在安特衛普,而您就是在那裡開船的嗎?而這些四處闖蕩的貨船在進港時有哪些規定,以及在碼頭靠岸時必須達到哪些標準,想必您應該都十分清楚才是。」
「當然不是,不是在安特衛普,」聽到我發表了有限的航海知識,他的臉上又恢復了笑容,老實說,我知道的也僅止於此。「他們是在亞得里亞海把船交給我的,說得更明確一點是在波拉。我相信您一定看過這艘船,因為它殘破不堪的船身已經變成一種特殊景觀。而且它登記的船名聽起來有點夢幻和誇張,是取自一種出現在神話中、會把鳥巢築在海中央的鳥類的名字。另一個含意則是宣稱自己的婚姻生活比天神宙斯和赫拉還要幸福快樂的夫妻,就看您喜歡哪一個解釋。」
聽到這裡,我的背脊突然感到一陣涼意。當出乎意料之外的巧合發生時,常常讓人覺得無法忍受,因為我們無從得知、也無法用常理去推斷支配它們的是哪些規則。現在的我只能勉強擠出幾個字,而我的聲音也洩露了驚慌失措的情緒:「您的船是『翠鳥號』嗎?」
「是啊!」伊度里極為好奇地看著我。
「我擔心的是,」我說:「到這裡,我心頭的謎團終於能串連成一個圓圈了,它已經占據了我太多的時間,我在醒著的時候幾乎都會一直想著它,甚至連睡覺時也常常會夢到它。」
「我實在聽不懂您在說些什麼?」伊度里像貓一般皺起灰眼珠上方的眉毛,雖然沒有散發出半點威脅感,卻透露出防備心和渴望得到答案的感覺。
我有點倉卒地描述之前和「翠鳥號」相遇的情形、它對我的意義為何,以及最近一次在奧利諾科河河口碰到它時,我突然非常同情起它的遭遇。伊度里聽完沉默了好長一段時間,我也沒有繼續解釋些什麼。我們都必須重新審視才剛剛建立起來的友情,以及出現了這個不可思議的巧合之後不斷浮現在我們腦海中的畫面。在我以為今晚的話題應該就要結束時,卻聽見他低聲地說:「『阿索阿德吉號』。那艘巡邏艇叫做『阿索阿德吉號』。我的天啊!命運實在太難捉摸了!我們居然會天真的以為自己可以任意的控制它,沒想到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到最後的結果也都是一樣的。」雖然他看似屈服於命運的安排,卻表現出和格微度一樣的尊嚴。他的口氣十分自然,似乎想把一切引導至正常的軌道上,好讓自己好過一些。他說:
「也就是說,這艘破破爛爛、好幾年來一直連船名都不完整的流動貨船,竟然曾經和您近距離接觸過,並且讓您如此著迷,這點您跟我是一樣的。不同的是我的生命已經穿過了這條縫隙,並且逃逸得無影無踨了。過去的我很清楚自己想過怎樣的生活,現在卻只剩下一具空殼。並不是因為我失去了所有,而是因為我失去了唯一值得讓我繼續和死神打賭的籌碼。」
聽見他以悲傷的語氣提及自己在很久以前似乎有樣東西被奪走了,我竟天真地說出下面這些無關緊要的話,試圖安慰他:「我想,像我們這樣選擇漂泊度日的人,最後似乎都會落得如此下場。」他又看了我一眼,好像把我當成一個在餐桌上胡亂發言的小孩,因為年紀還小所以不跟我計較。「不,」他糾正我說:「不是這樣的,我指的是某種像船難一樣會讓所有東西都沉入海底、把一切都帶走的大災難。到頭來只剩下回憶繼續吐著細絲,讓我們不停地回想起自己曾經失去的王國。既然您和『翠鳥號』的命運是如此地靠近、如此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那麼告訴您故事接下來的發展也是很自然、很公平的一件事。但是我今天卻做不到,再過幾天吧!我會把所有的故事都說給您聽。我們偶然在拖船上相遇,又因為這件事突然把距離拉近,我得花時間稍微消化一下才行。看來,我們從很久以前就一起旅行了,只不過距離相隔很遠就是了。」我點了點頭,想不出任何可以補充的話,因為他也說中了我心中的想法。我們在控制室上方的甲板休息了一下子,聽見裡面傳來午夜報時的鐘響,又過了很久才各自回房休息。而在互道晚安時,我發現我們說話的語氣已經變得不一樣了,因為在我們流浪漂泊的生活中已經開啟了另一段全新的、不同的旅程,我們之間也因此產生了類似兄弟般的感情。
晚上,我又夢到了流動貨船,而且都是一些快速閃過、毫無時間順序的畫面。這艘陳舊的大船總是帶著難以理解的徵兆出現在我的夢裡,我的心中也慢慢累積了一些模糊的、不安的情緒,以及某種無法形容、說不出來的罪惡感。天亮了,清晨的第一道陽光穿過氣窗上的薄窗簾打在我的臉上,我彷彿看到剛剛漆上亮眼、鮮明顏色的「翠鳥號」出現在我的面前。它的船身是赤紅色的,有點像是乾掉的血跡,甲板則是柔和的米黃色,而在船艙,船員所使用的甲板以及船橋上還多了一些天藍色的條紋。煙囪是米黃色的,上面也漆上了同樣的條紋。「誰會把船漆成這種顏色!實在是太愚蠢了。」在還沒完全清醒,仍處於半熟睡狀態的時候,我的腦海中突然閃過了這句話。而我們的拖船也在這個時候開始往岸邊開去,最後停靠在一個小村莊旁。村莊裡大部分的房子都在屋頂上鋪上稻草,只有少數幾間鋪了薄鋅板,感覺當地似乎籠罩著悲慘的氣氛,也讓人覺得不太舒服。在一間應該是軍營的建築物上掛著一面正有氣無力地飄揚著的三色國旗,更加突顯了天氣的悶熱。兩架塗成灰色的卡達麗娜海軍陸戰隊的飛機被拴在不甚牢固的木質碼頭上。
由於在達卡拉的裝貨工作有點被耽擱,超出原本預期的時間,所以抵達亞速群島時已經是秋天了。他想起瓦妲曾說過想在秋末去參觀俄羅斯東正教的偉大殿堂,例如扎格爾斯克和諾夫哥羅德等地。他真希望在抵達里斯本之前就能見到她,而這個想法也讓他感到很痛苦。他的心中又充滿了睽違已久的情感:一心想要早日得到幸福,卻又在等待的過程中變得越來越無法肯定。這個小型的煉獄讓他睡意全消,神智異常清醒,只好起來工作。他的胃好像被一個要命的重物壓住似的,完全不想吃東西。從亞速群島到葡萄牙首都的旅程變得痛苦萬分,有時候甚至會懷疑自己是不是發燒了。他很無意義的想著,以自己五十歲的年紀,早在許多年前便認為不會再有類似的經驗,現在真的有點害怕會陷入死胡同裡,擔心冒險在裡面橫衝直撞的結果,只會得到一個冷冰冰的拒絕做為獎賞。當船隻進入塔霍河的河口時,他就像任何一個坐在公園板凳上等候情人到來的少年一樣,心跳得飛快。
他沒有收到任何的留言,所以就決定先去拜訪一些客戶,安排將橄欖油和精緻的美酒運去赫爾辛基的相關事宜。秋天在不知不覺中過去了,籠罩在悲傷和昏暗氣氛中的里斯本,十分符合法朵歌曲中所描述的情境,而觀光客去酒館的時候也都會假裝自己很喜歡這些樂曲。當他筋疲力盡地登上一艘接駁船,準備回到貨船上時,他發現自己好像感染了某種回歸線地區的疾病,此刻正在身體裡作怪。他對「翠鳥號」也完全失去了興趣,而遠遠地看到流動貨船停在海灣中央、等著進入碼頭時,它那醜陋的外表也突然讓他大為光火,甚至覺得很厭煩。當他正要步下駁船時,聽到遠方有一個女人在叫他:「鍾!鍾!等等我!」原來是瓦妲正沿著通往港口的街道跑過來。她穿著米黃色的長褲和紅色上衣,手裡不停地揮動著淺咖啡色的毛衣來吸引他的注意力。而他就這樣一動也不動地呆愣在碼頭上,心中頓時洋溢著幸福的感覺。
瓦妲來到他身邊時在他的臉頰上親了一下,看到讓他魂縈夢繫的臉龐,他卻沒來得及輕輕貼上她稍微出汗的臉頰做為回禮。女孩不發一語地勾起船長的手,帶著他往市中心走去。他們穿過七月四日大道,沿著阿烈克靈街往前走,她提到在高地區附近的狹窄巷弄中應該還有營業中的酒吧。「我以為您已經出發去參觀東正教的神聖殿堂,所以不會過來了。」「因為這裡出現了比參觀神殿更重要的事,所以一定要先過來一趟。」她意有所指地看著鍾,而他臉上微窘的表情則讓她覺得很有趣。伊度里跟大部分的巴斯克人一樣,非常不擅長掩飾自己的感情。
「我們在一間酒吧裡坐下來,以嚴肅的態度慢慢地傾訴彼此的感情。我向她坦白說,如果她沒有出現的話,我打算到澳洲去,在那裡從事沿海貿易。」這麼多年過去,我仍記得鍾對我說出這些話時,他的聲音有多麼絕望,也和他正直、嚴謹的個性形成強烈的對比。他已經不太記得談話的內容。瓦妲還是一如往常的平靜、穩健、洋溢著青春氣息,也一樣地散發著抵擋不住的魅力。她提到他身上的某種特質已經盤據了她的心頭,這是她從未有過的經驗,所以她現在只想待在他的身邊,打算把所謂的歐洲教育先丟到一旁。這就是她想要的方式。她認為他們將來不可能在一起,而且她也不在乎,因為她只想要體驗這一切,就像此刻呼吸到的空氣一樣,只想活在當下。鍾結結巴巴地提出他們在年齡、國籍和習俗方面的種種差異。瓦妲則是聳聳肩,以相當肯定且具有遠見的語氣回答道,其實連鍾都不相信自己剛剛說出口的違心之論,所以根本不需要在意。當時是傍晚六點,他們已經喝了好幾瓶的綠酒,吃了好幾盤新鮮度和味道都不怎麼樣的炒魚。
接著,他們裝出很自然的樣子走進位於利伯代德大道的旅館,鍾是以瓦妲丈夫的名義登記的,並且在搭電梯到房間休息的時候刻意緊緊地摟著她,由於他們抱得太緊,電梯裡的服務人員忍不住回頭了好幾次,確認他們是否還在呼吸。他們進門之後便開始脫衣服,任由衣物從門口一路散落到床邊的走道上。「我們慢慢地、仔細地、一次又一次地做愛,就像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一樣。瓦妲已經事先提出明智且正確的見解,她看出我們之間不僅沒有繼續發展的可能性,也充滿了無法克服的阻礙,所以她才會希望好好把握現在的每一刻。而我呢?就如同我在酒吧裡說過的一樣,我也不知道最後會有怎樣的結果。於是,感到絕望的我們也不得不屈服了,只希望能透過對方的身體來尋求一些慰藉。裸著身子的瓦妲渾身上下似乎散發著一種不可思議的光輝,而光環的來源則是她完美比例的身材、吹彈可破、略微溼潤的肌膚、以及她迷人的表情,當我在床上低頭看著她時,甚至覺得她的神情感覺有點像德爾菲的女祭司。這是很難去解釋和形容的一件事。我有時甚至會覺得其實自己從沒看過這樣的表情。
我曾有好幾次試圖尋死,但是只要一想到這個畫面也會因此而隨之消失,就馬上打消了念頭,而這也是唯一能夠阻止我付諸行動的理由。」到此,敘述著過往的伊度里似乎面臨了一道關卡,他正陷入了埋葬著最痛苦的回憶的絕望深淵裡,所以沉默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整整三天,」他接著說:「我們都待在里斯本的旅館裡,沒有踏出房門一步,那裡變成了我們的世界,只輪流做著以下兩件事:幾乎不講話、安安靜靜地做愛,或是互相交換青春時期的秘密或對這個世界的發現。瓦妲十分著迷於水手的生活,但是在我的航海生涯中,實在沒有多少東西可以告訴她。我的工作十分單調,每天做的都是一些乏善可陳的例行公事,除了天氣的變化以及在旅程中不斷更迭的景色之外,不曾發生過任何例外。我現在已經無法重現當時的談話內容了。只記得因為她的個性很好,所以我們談到很多事,氣氛也非常融洽。而在談到一些奇聞軼事和令人驚訝的事情時,也讓我們有機會去檢視、去體會自己對於這個世界和對於民族的看法。如同我之前提到的,瓦妲具有女預言家的特質,她可以行走於現實與夢境之間,就像夢遊者一樣踏出堅定的步伐,這個時候她看起來就跟『天方夜譚』裡的任何一位精靈一樣,是個十足的東方人。」
由於船隻在啟程之前得先處理一些海關方面的事情,所以鍾也必須回到船上。他透過旅館的電話談妥了將貨物運送至赫爾辛基的合約,並且會從那裡接收另一批裝滿紙張而且非常重要的貨物,再運往維拉庫魯茲。在他處理這些事情的時候,瓦妲都陪在他的身邊。因為她一直很謹慎、很好奇地跟著他,並且認為那些程序非常的不可思議,讓伊度里忍不住笑了出來。他們都不願意指出必須分離的時間,而當那一刻來臨的時候,她只能試著以自然的口氣跟他說話,卻沒有成功:「我會在赫爾辛基的碼頭迎接您的到來。」鍾向她解釋說,為了更換馬達的零件,他必須先去漢堡一趟,但是通常修船廠都很忙,所以至少要花上一個月的時間,等他到達赫爾辛基的時候,當地的氣溫可能是零下好幾度。「等您確定哪一天會到的時候就通知我,我會在港口等您。」瓦妲個性中的肯定和毫不猶豫的特質也是吸引鍾的原因之一。以下為套用他的話來形容瓦妲:「她就像我的家鄉愛因歐亞地區的已婚婦女一樣的有智慧,卻擁有愛神芙羅黛蒂的身材。
對一個命運悲慘的男人來說實在是太奢侈了。」當我們進入這一段故事時,他又陷入長時間的沉默狀態,也許是他開始吐露心事的這幾個夜晚以來,停頓最久的一次。
船隻開到海港要花上十天以上的時間。途中拖船必須停靠在好幾個地方卸下部分的平底貨船,並收回已經清空的平底貨船,送回該公司位於大港口的倉庫中。其實我們兩個都不急著到達目的地。「我本來可以搭飛機。」伊度里向我說明:「但是我覺得坐船順流而下會更有趣,也更舒服。我一直很希望能像這樣搭船旅行。其實我對河流的認識僅限於某幾處河口三角洲,例如:須耳德河、泰晤士河和勒阿弗爾的塞納河。不是每一條河流都可以通行、都是安全的,不是所有的都這樣的。」我覺得他最後說的話似乎意有所指,但他卻沒辦法把它說出來,好像喉嚨突然變得...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