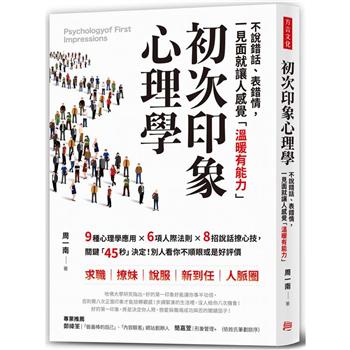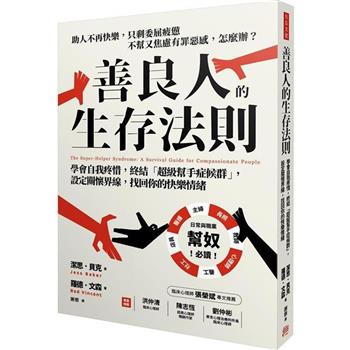文明的進程並不完全是一股邁向更美好事物的統一潮流。如果我們將其用足夠大的刻度描繪出來,它也許具有上述外觀。但這種廣泛的觀點,模糊了許多我們賴以全面理解這一進程的細節。如果放眼幾千年的人類歷史長河,我們就會發現新時代的出現往往相當地突然。寂寂無名的民族忽然取得歷史事件的主流地位;技術的發現改變了人類生活的機制;原始藝術迅速盛開,充分滿足某些審美熱情;偉大的宗教在草創時期,就在各國和各民族之間傳播著天堂的平靜和上帝之劍。
西元十六世紀見證了西方基督教的分崩離析和現代科學的興起。這是一個動亂的時期,儘管許多新領域和新觀念都呈現出來了,然而卻沒有一樣真正確定下來。在科學方面,哥白尼(Copernicus)和維薩里(Vesalius)是代表人物,他們象徵著新的宇宙觀和科學對直接觀察的強調。喬爾丹諾‧布魯諾(Giordano Bruno)則是一個殉道者,儘管他的受難並不是由於科學,而是由於自由想像推測。一六○○年布魯諾的死,迎來了嚴格意義上現代科學的第一個世紀。但是,因為後來的科學思想並不信任他的那種一般推測,所以他受刑的象徵意義並未為人所察覺。宗教改革儘管十分重要,但也只能被認為是歐洲民族間的內部事務。甚至連東方的基督教也以一種毫不關心的態度來看待它。而且,這種分崩離析在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歷史上也不是新鮮事物。當我們將這次偉大革命放置於教會的整個歷史中時,我們不能將之視為給人類生活確立了什麼新的準則。不論好壞,它只是一次偉大的宗教轉型,並不是新宗教的出現。宗教改革本身也這樣認為。改革者們認為他們只是恢復了那些被人遺忘的東西而已。
現代科學的興起卻與此截然不同。在各個方面,它都與當時的宗教運動形成鮮明對比。宗教改革是一場人民起義,曾在一個半世紀裡將歐洲置於血泊之中。而科學運動剛開始時只侷限在一小部分知識精英當中。在目睹了三十年戰爭和記憶猶新的荷蘭阿爾瓦(Alva)事件【1】那段歲月裡,科學家所遭遇的最壞情況便是,伽利略(Galileo)在平靜地死於病榻之前,曾受到體面的拘禁與輕微的申斥。有史以來,人類所遭遇最為密切的變革,就以這種平靜的方式開始了,而伽利略受迫害的方式是這個變革的開幕獻禮。自從一個嬰兒降生在馬廄裡以來【2】,還很難找出有這麼大的一次變革是以這麼小的驚擾開始的。
這一系列演講的主題,說明科學的平靜發展,實際上已經使我們的思想面貌變得豐富多彩,因此,以往被視為特例的思維方式,如今在知識界廣泛傳播開來。這種新的思考方式在歐洲已經緩慢地蔓延了很多年,最終得以在科學的快速發展中迸發,從而也透過這種最顯著的體現,而強化了自身。這種新的思想面貌,甚至比新的科學和新的技術都更為重要。它將我們心中形上學的預設和想像內容改變了,因此,舊刺激能激發出新的回應。也許我關於新的思想面貌的比喻過甚其詞了,我所要說的意思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關於這一點,令人尊敬的天才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一封已經公開的信中有一句話倒是很貼切。當他完成偉大的著作《心理學原理》(Principles of Psychology)之後,他寫了封信給他的兄弟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在信中他寫道:「我必須面對不可化約而又鐵一般的事實,來錘煉我的每一個句子。」
現代思維的特色就是對一般原理與不可化約而又鐵一般的事實之間的關係,發生了強烈的興趣。不分時地,都有一群注重實際的人致力於「不可化約而又鐵一般的事實」;不分時地,也都有一群具有哲學氣質的人,熱衷於構想普遍原理。正是對於詳細事實的強烈興趣,和對於抽象概括地孜孜以求的結合,構成了我們當下社會的新景象。此前,這種現象突然出現,好像是出於偶然。如今這種思想上的平衡兼顧,已然成為有素養的思想所必須接受的一種傳統。這是使生活保持甜蜜的鹽。大學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將這種傳統作為普世的遺產,一代一代傳承下去。
十六、十七世紀讓科學得以在眾多歐洲潮流中出類拔萃的另一個特色,就是它的普及性。現代科學誕生於歐洲,但是整個世界才是它的家。近兩個世紀,西方模式曾持續而混亂地影響了亞洲文明。東方的智者過去和現在都一直困擾著,不知道哪種調節生命的祕密,可以從西方傳到東方,而不至於胡亂破壞他們所珍視的自己的遺產。愈來愈明顯的是,西方能立即給予東方的,便是它的科學和科學觀點。只要是一個理性社會,這類東西都能從一個國家傳播到另外一個國家,從一個民族傳播到另外一個民族。
在這幾次講座中,我將不會討論科學發現的細節。我的主題是現代社會一種思想的繁榮過程,它的普遍化以及它對其他精神力量的影響。閱讀歷史有兩種方式:順推和回溯。在思想史中,這兩種方法都不可偏廢。一位十七世紀的作家說得好:要理解一種思潮,就要考慮它的前因後果。因此,我在這次講座中將會考慮我們現代自然探究的某些前因。
首先,如果沒有一個普遍的本能信念,相信「事物秩序」(Order of Things),尤其是「自然秩序」(Order of Nature),那麼現代科學就不可能存在。我用「本能」這個詞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只要人們的行為被固定的本能所約束,不管人們說什麼都一樣。言語也許最終會損害本能,但是直到這發生之前,言語都不作數。這一點對於科學思想史來說非常重要。因為我們發現自休謨(Hume)時代以來,流行的科學哲學一直在否定科學的合理性。這個結論是建立在休謨哲學的表面理論基礎上的。我們可以以休謨的《人類理解力研究》(I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第四章的一段話為例進行說明:
總之,每個結果都是與它的原因不同的事件。因此,結果是不能從原因中發現出來的,我們對於結果的先驗構想或概念必定是完全任意的。
假如原因本身不能提供任何資訊給結果,以至於概念的產生是完全任意的,那麼我們馬上可以得出結論說,科學是不可能存在的,除非科學的意義就在於建立完全任意的聯繫,而這種聯繫是得不到原因或結果固有本質的保證。休謨哲學的某種版本已經在科學家中廣為流傳。但是,科學信念適時興起,並不聲不響地移走了哲學所造成的這座高山。
鑒於科學思想中這種奇怪的衝突,當看到一個信念與自成體系的理性格格不入的時候,我們首先必須考慮這個信念的前因是什麼。因此,我們必須回溯本能的信念,而這些本能信念相信在每個停留的事件【3】中皆存在自然秩序。
當然,我們都具有這種信念,因而我們相信產生這種信念的原因,是由於我們理解了其中的真理。可是一個普遍觀念的形成—比如自然秩序的理念—以及對其重要性的掌握和許多事例的觀察,卻絕不是該理念的真理所產生的必然結果。熟悉的事物不斷發生,人們並不為此操心。必須要具備不同尋常的心智,才能對非常明顯的事物進行分析。因此,我希望能談談這種分析經過了哪些階段,才逐漸明朗起來,以及最後又如何無可選擇地深入西歐知識分子的心中。
顯然,生活主要場景的重現是極為常見的事,以至於最沒理智的人都不可能不注意到。甚至在理性出現之前,它們就對動物的本能發生作用了。大體上說,某些一般性的自然狀態是重複出現的,而且我們的本性也適應了這種重複,這點是無需討論的。
但與此互補的一個事實同樣真實而明顯:沒有任何事物會把具體細節都一一重複展現出來。任何兩天或兩個冬天都不會完全相同。逝去的,就永遠逝去了。因此,人類的實踐哲學一直在預見大體上的重複事件,而將具體細節視為從高深莫測的事物母體發出的,超越了理性範圍。人們預測著旭日東升,而風卻任意地刮著。
當然,從希臘古典文明以來,一直有一群人,包括許多派的人,都不接受這種終極的非理性的觀點。這些人都力圖將所有現象解釋為事物秩序產出的結果,而這些事物無所不包。諸如亞里斯多德(Aristotle)、阿基米德(Archimedes)和羅吉爾‧培根(Roger Bacon)等天才人物,一定都具有完全的科學精神,他們本能地認為,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支配自然秩序的普遍原理的體現。
但是直到中世紀行將結束,一般的知識分子在這種觀念中,還沒有體會到那種確切的說服力和對於細節的興趣,因此不能持續鼓勵有相當能力和充分時間的人,來共同研究和發現這些假說原理。人們或許懷疑這些原理的存在,或許懷疑是否能找到這些原理,或許沒有興趣思考這些問題,又或許在找到之後無視,它們的實際意義。不管出於何種原因,從一個高度文明的大好時期及其所經歷的漫長時間來看,研究是疲弱的。為什麼十六、十七世紀時,這種步伐突然加快了呢?直到中世紀結束之前,一種新的思潮出現了。發明刺激了思想,思想又加速了對自然界的思索,希臘的手稿也展示了古人的發現。雖然直到一五○○年,歐洲方面所知的還不如西元前二一二年去世的阿基米德那麼多。但是到了一七○○年,牛頓(Newton)的巨著《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Philosophiæ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業以完成,整個世界也就邁入了現代的新紀元了。
在一些偉大的文明中,科學所需要的獨特之心理均衡,只是偶爾出現,產生的效果也微乎其微。譬如,我們對中國的藝術、文學和人生哲學知道得愈多,就愈會欽佩這個文明所企及的高度。千百年來,中國不斷出現聰敏好學之士,畢生致力於研究。考慮到時間的跨度和影響的人口,中國創造了世界上迄今為止最偉大的文明。對中國個人而言,懷疑他們追求科學的稟賦是毫無依據的,然而實際上,中國的科學又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如果任由中國自行發展,我們沒有理由相信中國會在科學研究上取得任何進步,印度也是這樣。還有,如果波斯奴役了希臘,我們就沒有足夠的理由相信科學會在歐洲繁榮起來。
羅馬人在這方面並沒有表現出特別的創造性。即便確實是這樣,希臘人曾經掀起了這場運動,但他們卻沒有用現代歐洲所展現出來的那股熱情來支持它。我並不是暗指大西洋兩岸最近的幾代歐洲人,而是指宗教改革時期小部分的歐洲,當時它們沉浸在戰爭和宗教紛爭之中。再來看看地中海東岸,從西西里島到亞洲西部的這片區域,從阿基米德逝世(西元前二一二年)到韃靼人入侵,這前後一四○○年的時間裡,那裡曾多次發生戰爭、革命和宗教的大變革,但是情況都不會比十六、十七世紀整個歐洲的戰爭情況更糟;也有一個偉大而繁榮的文明,異教徒、基督徒和伊斯蘭教徒都在一起生活。在那個時期,科學上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但總體來看,進展是緩慢而曲折的。除開數學以外的其他領域,文藝復興時期的人們還必須從阿基米德已經達到的高度起步。醫學和天文學方面也有一些進步。但是總體來說,這種進步在十七世紀取得的巨大成就面前,不值一提。比如,我們不妨將伽利略和克卜勒(Kepler)出生前的一五六○年至牛頓鼎盛時的一七○○年之間科學知識之進展,與之前提到的古代作一比較,正好十倍於古代的進步。
然而,希臘終究是歐洲的母體,找尋現代觀念的起源,就必須看看希臘的情形。我們都知道,地中海東岸曾經有一個十分興盛的伊奧尼亞(Ionian)學派,他們對有關自然理論深感興趣。他們的思想經過天才柏拉圖(Plato)和亞里斯多德充實之後,一直流傳至今。但是,這一學派並沒有完全的科學精神,只有亞里斯多德是個極大的例外。從某些方面講,這樣更好。希臘天才是富有哲學性的,他們思維清晰而邏輯性強。這一學派的人物主要提出哲學問題,自然的根基是什麼?是火嗎?是土?是水?還是其中兩種或三種物質的組合?抑或它只是流體,不能化約成某種靜態的物質?他們對數學也非常感興趣。他們創立了數學的一般原理,分析了它的前提條件,通過嚴格遵照演繹推理的方式,在定理方面得出了重要的發現。他們的頭腦裡充滿了對於一般原理的渴望,他們要求清晰的、大膽的觀念,並且從這些觀念出發,進行嚴格的論證。所有的這些都十分高明而富於天才,是一個理想的準備工作。但這並不是我們所理解的科學。那時仔細觀察的耐心還沒有如此突出。他們的天賦並不適於充滿想像的混亂懸疑,而這往往出現在成功的歸納概括之前。他們是頭腦清楚的思想家和大膽的推理家。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阿爾弗雷德•懷德海的圖書 |
 |
$ 338 ~ 428 | 科學與現代世界
作者:阿爾弗雷德•懷德海 / 譯者:黃振威 出版社:五南 出版日期:2020-05-28 語言:繁體/中文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弗雷德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科學與現代世界
對於一般讀者而言最為重要的,關於科學、哲學和已然發生的生活問題之當下關係的重述。 ―約翰•杜威
懷海德的著作裡,我們可以看到在一種思維中思想的不斷修正,這種修正是在不同的經驗領域,在完全新潮理念的作用下進行的,而這達到了一種令人吃驚的程度。 ―愛德蒙•威爾森
本書或許是懷海德讀者最為眾多的哲學著作,主要收錄了1925年他在哈佛大學的八篇洛厄爾演講,主要闡述過去三個世紀中,西方文化在科學發展的影響下所顯示出的某些方面,強調流行的哲學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性。透過本書,我們可以看到思想家不斷的自我修正,敏銳而充滿智慧,表現了當時所處社會的張力。
作者簡介:
阿爾弗雷德•懷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
英國數學家、哲學家、教育學家,先後執教於劍橋大學、倫敦大學與哈佛大學。「歷程哲學」(也稱「機體哲學」)的創始人。他與羅素合著的《數學原理》標誌著人類邏輯思維的空前進步,被稱為永久性的偉大學術著作之一;他創立了龐大的形上學體系,《過程與實在》、《觀念的歷險》等是其哲學代表作,一生著作宏富,影響深遠。
校譯者簡介
俞懿嫻
現職:東海大學哲學系教授
學歷: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藝術與科學研究院哲學博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學士
章節試閱
文明的進程並不完全是一股邁向更美好事物的統一潮流。如果我們將其用足夠大的刻度描繪出來,它也許具有上述外觀。但這種廣泛的觀點,模糊了許多我們賴以全面理解這一進程的細節。如果放眼幾千年的人類歷史長河,我們就會發現新時代的出現往往相當地突然。寂寂無名的民族忽然取得歷史事件的主流地位;技術的發現改變了人類生活的機制;原始藝術迅速盛開,充分滿足某些審美熱情;偉大的宗教在草創時期,就在各國和各民族之間傳播著天堂的平靜和上帝之劍。
西元十六世紀見證了西方基督教的分崩離析和現代科學的興起。這是一個動亂的時期,儘...
西元十六世紀見證了西方基督教的分崩離析和現代科學的興起。這是一個動亂的時期,儘...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前言
本書主要研究過去三個世紀中,西方文化在科學發展的影響下所顯示出的某些方面。本書認為時代思潮源自實際上主導社會知識階層中的世界觀。由於文化部門繁多,觀念體系也可能不止一個。人類的各種興趣活動:科學、美學、倫理學、宗教等都可以提供各種宇宙觀,同時又受到這些宇宙觀的影響。在每一個時期,這些主題都各自提出了不同的世界觀。由於同一群人受到一種以上,或者上述全部興趣活動的影響,他們的實際觀點便會是上述各種來源的綜合產物。但是每一個時期都有其主要考慮;在本書所討論的三個世紀中,從科學中脫胎出來的宇宙...
本書主要研究過去三個世紀中,西方文化在科學發展的影響下所顯示出的某些方面。本書認為時代思潮源自實際上主導社會知識階層中的世界觀。由於文化部門繁多,觀念體系也可能不止一個。人類的各種興趣活動:科學、美學、倫理學、宗教等都可以提供各種宇宙觀,同時又受到這些宇宙觀的影響。在每一個時期,這些主題都各自提出了不同的世界觀。由於同一群人受到一種以上,或者上述全部興趣活動的影響,他們的實際觀點便會是上述各種來源的綜合產物。但是每一個時期都有其主要考慮;在本書所討論的三個世紀中,從科學中脫胎出來的宇宙...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目 次
關於本書
前言
導言
第一章 現代科學的起源
第二章 「數學」之為思想史中的要素
第三章 天才的世紀
第四章 十八世紀
第五章 浪漫主義的反動浪潮
第六章 十九世紀
第七章 相對論
第八章 量子論
第九章 科學與哲學
第十章 抽象
第十一章 上帝
第十二章 宗教與科學
第十三章 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
關於作者
阿爾弗雷德‧懷德海自傳
阿爾弗雷德‧懷德海年表
索引
關於本書
前言
導言
第一章 現代科學的起源
第二章 「數學」之為思想史中的要素
第三章 天才的世紀
第四章 十八世紀
第五章 浪漫主義的反動浪潮
第六章 十九世紀
第七章 相對論
第八章 量子論
第九章 科學與哲學
第十章 抽象
第十一章 上帝
第十二章 宗教與科學
第十三章 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
關於作者
阿爾弗雷德‧懷德海自傳
阿爾弗雷德‧懷德海年表
索引
顯示全部內容
|
 夫雷是法國上法蘭西大區諾爾省的一個市鎮,位於該省中部偏東,屬於杜埃區。該市鎮2009年時的人口為1,375人。
夫雷是法國上法蘭西大區諾爾省的一個市鎮,位於該省中部偏東,屬於杜埃區。該市鎮2009年時的人口為1,37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