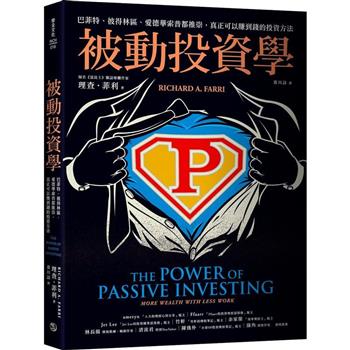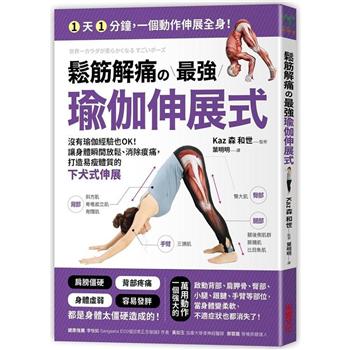第一章 萬壑松濤 2014~2015
一、立春
小米粥和春餅的餘味尚未在唇齒間消散,我已經信步於一排排整齊肅穆的花崗石墓碑間了。
長風陵園職工食堂的伙食味道不提也罷,大小年節裡的食譜安排還是值得稱道的。春餅、餃子、元宵、粽子、月餅、臘八粥、年糕……應景的吃喝從來不落。多數時候,它們是和那些用來祭祀的供品一鍋出的,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對外供應的充足。剩下的——不妨說是留下來的,作為午餐福利來內部消化掉,厲行節約。這是職工食堂順應時代潮流,配合禮儀部日益細化的業務拓展,將環保理念、職工關懷和陵園經營有機結合起來的積極探索,實打實的一舉三得。
正是那些和日曆緊密關聯的食物,讓我這樣一個深居簡出的煢煢孑立之人,依然可以把每一個歲時節令都過得滋味滿滿,像那麼回事。由此,我也便記住了那一段早已離我遠去的俗世煙火,它們平淡,卻不平凡。油鍋撩起的烈焰忽明忽暗,在那三百多個黃昏的顫抖空氣中,輝映著心事重重的灶前人,也一次又一次照亮了我蒙塵的舊憶。
除了那一舉三得,內部消化這些食物還有另一個意義——從側面彰顯了我們的禮祀服務並非流於形式。這些祭品的內在品質有著來自於職工的擔保,簡單直白,世人共睹,日月可鑒。我們服務的根本對象,不只是歸天仙遊的逝者,更是慎終追遠的生者,後者比前者更需要撫慰。
說到服務,長風陵園真正實現了一條龍。從遺體接運到冷藏防腐,從化妝入殮到舉行告別儀式,從遺體火化到骨灰寄存安葬,從墓園管理到代客祭掃,從每年的常規公祭到網上祭奠館的全時對外開放,各個環節無縫銜接,服務覆蓋邊角線面。這一切,得益於殯儀館和墓區一體化的殯葬服務體系。
近些年國家一直在搞殯葬改革,頒布了一系列基於縮減墓穴硬化面積,提高生態安葬率的獎補政策。越來越多的人更新了觀念,擯棄傳統墓穴,採用樹葬、花葬和草坪葬等回歸自然的安葬形式,不築墳頭,不立墓碑,只在一小塊公共區域表以逝者名姓與生卒日,共享有限的土地資源,既環保又經濟。除了這些,還有一種更為形而上的骨灰處置形式——海撒,可謂了化於無形,天地人合一。這些日漸興起的生態葬已經成為趨勢,對長風陵園正在進行的墓區擴建規劃產生了深遠影響。
好在安葬形式再變革,也暫時不會影響到我這個殯葬用品銷售員的職業生涯。更多人還是對安置陰陽氣骨的陰宅素有寄託,我收入的重要來源——骨灰箱盅,也就不會輕易退出商品市場乃至人類死亡文明的歷史舞臺。而且,我們的祭祀文化淵源深厚,「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看得見的祭掃形式比失了形的肉身皮囊更具有存在與延續的意義,這也是我們根本上其實是在為生者服務的原因所在。
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我不會失業,這讓我感到安心。除了可以繼續留在長風陵園這上千畝園林裡,享受得天獨厚的天高地闊與雲淡風清外,我還將繼續接受來自職工食堂「生死同仁」的人文關懷——不管這份關懷的緣起隱含著多少世俗所以為的不堪。
有時候,我們需要的就是某種形式。一張薄餅,一道合菜,一碗清粥,雖然簡單,卻足以擔當起一個承襲了千百年的關於冬去春來的鄭重儀式。在我看來,它們與告別廳裡的白菊、黑紗、挽聯和哀樂沒什麼本質區別。
只是,立春的北京依舊寒冷。
腳下這條青磚甬道位於整個長風陵園的最東緣,沿途雜草叢生,枯葉滿地,因人跡罕至而倍顯蕭瑟。這是從職工食堂到北山墓區的幾條路徑中最不起眼的一條,並且也不算便捷,就算哪位同事飯後想要到那一大片松柏林間散步消食的話,通常也不會選擇這條路。社會人士更是極少出現在這裡,長風陵園比他們在常規情境之所見要大得多。所謂常規情境,無非是指從陵園南大門進入,周旋於業務室、松濤館、告別廳、火化間、骨灰堂和燒紙區之間,以及到北山墓區安葬和掃墓祭奠的這一切活動的行之所至。故而,這條青磚甬道永遠是安靜的,除了我每天午飯後以職工食堂為起點走上一個單程外,鮮有旁人攪擾。
這成了一條專屬於我的路。
甬道盡頭有一座十幾米高的小土丘,是二○○○年陵園擴容墓穴時挖掘出來的土石堆積而成的,它已經存在了十四年。那年初夏我剛來這裡上班,見證了長風陵園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擴建。眼見著一個「墳頭」平地而起,一尺尺升高的同時也被一遍遍地夯實,最終形成的體量,便是那些看不見的地下墓穴空間的總和。
小土丘位處陵園偏隅,並未有礙觀瞻。在得知它將來不會再被移除的確切消息之後,我在上面栽種了一株白玉蘭。
起初我有些擔心,怕它長大後卓然而立,過於突兀,但這份顧慮很快就被打消了。陵園倚山而建,到處都是參天大樹,從遠處看,小土丘與整片山林有機地融為了一體。另外,和那株白玉蘭共同生長起來的,還有野生的灌木和雜草,它們很快就填補了那塊高地上的大片空白,弱化了白玉蘭的存在。只是玉蘭花期較早,每年開春,在爛漫山花尚未綻放之時,那一樹高調的素白以及彌散在乾冷空氣中的段段幽香,還是顯得有些不凡。
這座小土丘為我的陵園生活增添了一項姑且可以被稱為運動的內容。旺盛的雜草被我日復一日踏出了一條深深的「之」字形小路,像斷流後乾涸的蜿蜒河道。溯源而上,行至丘頂,曾經纖細柔弱的樹苗早已壯實得難以撼動了。這不像是源頭,更像是世界盡頭,被終極的清淨永久隔絕著。
玉蘭塚,我這麼稱呼它。沒人關心這株和野生雜草灌木共生的白玉蘭,也沒人洞見它是整個長風陵園裡海拔最高的「墓碑」,更不會有人破譯塚下的秘密。
站在玉蘭塚上,三萬餘座墓碑悉收眼底。與這幅遼遠壯闊的全景畫面相襯的,是一派出奇的靜謐,靜到可以聽見來自玉蘭樹下根須撩動土壤的窸窣聲,猶如觀看無聲老電影時自己發出的喘息。夜晚就大不一樣了,那些層次分明的風聲總是令人浮想聯翩,它們時大時小,時急時緩,帶著抑揚頓挫的韻律,好像有人在說話,從寒暄問候到傾訴宣洩,從嬉笑怒罵到自言自語。總有一些對這個娑婆世界情緣難解,不肯沉睡也不肯消散的魂靈,風是他們的語言,他們和這個世間的我們原本無異。
我瞭望著片片墓園,聆聽著清冷空氣裡若有似無的聲音,這是每一天中我最為清醒的時刻。
在這個行業待久了,早晚有一天要放下唯物主義的大旗。從十四年前剛入行時起,我就隱約感覺自己又生長出了一顆「心」。伴隨著環境裡的經受,這顆「心」越來越大,逐漸超越「本心」,最終撐滿了整個胸膛。我稱它為「敬畏心」。
我敬畏這裡的一切。敬畏之中,時光飛逝。
時光飛逝,卻逃不出輪迴。
那些每年都在我的凝視中生發出來的新芽與花葉,在經歷了一輪又一輪的春生、夏榮與秋枯之後,終將在一個又一個不經意的日子裡,被幾陣夜風吹落,順應天命化作來年的春泥,接下來便是一場註定漫長的冬眠。直到次年,新鮮的嫩芽又會在某一個乍暖還寒的初春之刻被我凝視出來,開始了又一度的輪迴。
我抬頭仰望,此刻枝條空空,比天空還空。
新芽的孕育尚需時日,這個寒冬比往年都要漫長一些。可我虔誠地相信,深埋腳下的根系從今天起就悄然甦醒了,它們已經開始從尚未回暖的土壤中努力地汲取養分,源源不斷地向枝頭輸送開來。
我從棉服外兜掏出一瓶純淨水,對著陽光看了看。昨晚它被放在窗外凍了一夜,經過上午的自然解凍,現在裡面還有一小塊冰沒有化掉,正是我想要的理想狀態。
我淺淺啜了一口,針扎般的刺骨寒涼自上而下佈滿胸腹,浸透周身。這樣的冰點刺激,亦不失為每年立春這一天特有的儀式。
一瓶冰水被我傾灑在了玉蘭樹下,是滌盪,也是潤澤。
阿茹娜,你一定比我更能強烈地感受到來自地面之下的不朽生息。那些根須溫柔地纏繞著你,這方香泥充分地包裹著你,你已經和它們,和這株白玉蘭融為一體了。
以前你比我大七歲,如今我比你大七歲,我會逐漸老去,而你永遠年輕。所以,你應該比我更有理由相信,或遲或早,春天終歸要來。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阿螃的圖書 |
 |
$ 342 | 綠度母【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阿螃 出版社:博客思-蘭臺 出版日期:2023-02-23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綠度母
靈魂始終被一抹絳紅牽扯著!
在裝滿漢白玉骨灰盒的櫃檯前,鐘眠遭遇了明宇的第二次求婚。她無力再拒絕,可又無法真正融入這場婚姻,只因自己的靈魂始終被一抹絳紅牽扯著。
遙遠的雪域高原,莊嚴殊勝的玉沁曲林內,畫僧嘉措對故去之人阿茹娜懷有深重愧疚,發願修習唐卡,以藝侍佛。
身為當年那場慘禍的製造者,鐘眠的贖罪方式則是日日懺悔,月月還貸。然而,十五年後債務的清償並未令她釋懷,只因潛藏心底的違緣尚未遣除。
夕陽下的玉沁曲泛著金光,隨著一個塵封已久的秘密被揭開,鐘眠驀然回首,原來,她一直苦苦求索的解脫之路,就在身後。
作者簡介:
阿螃
女,一九七九年出生,北京人,現定居泰國清邁。
曾混跡於家電營銷、餐飲服務、教育出版、銀行信貸及藏飾文玩等領域,皆一事無成。本書故事提筆於二十年前,其間筆耕常輟,如今付梓,且算成就一事。
E-mail: apangowest@gmail.com
章節試閱
第一章 萬壑松濤 2014~2015
一、立春
小米粥和春餅的餘味尚未在唇齒間消散,我已經信步於一排排整齊肅穆的花崗石墓碑間了。
長風陵園職工食堂的伙食味道不提也罷,大小年節裡的食譜安排還是值得稱道的。春餅、餃子、元宵、粽子、月餅、臘八粥、年糕……應景的吃喝從來不落。多數時候,它們是和那些用來祭祀的供品一鍋出的,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對外供應的充足。剩下的——不妨說是留下來的,作為午餐福利來內部消化掉,厲行節約。這是職工食堂順應時代潮流,配合禮儀部日益細化的業務拓展,將環保理念、職工關懷和陵園經營有機結合起來的...
一、立春
小米粥和春餅的餘味尚未在唇齒間消散,我已經信步於一排排整齊肅穆的花崗石墓碑間了。
長風陵園職工食堂的伙食味道不提也罷,大小年節裡的食譜安排還是值得稱道的。春餅、餃子、元宵、粽子、月餅、臘八粥、年糕……應景的吃喝從來不落。多數時候,它們是和那些用來祭祀的供品一鍋出的,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對外供應的充足。剩下的——不妨說是留下來的,作為午餐福利來內部消化掉,厲行節約。這是職工食堂順應時代潮流,配合禮儀部日益細化的業務拓展,將環保理念、職工關懷和陵園經營有機結合起來的...
顯示全部內容
推薦序
靈魂始終被一抹絳紅牽扯著!
遙遠的雪域高原,莊嚴殊勝的玉沁曲林內,畫僧嘉措對故去之人阿茹娜懷有深重愧疚,發願修習唐卡,以藝侍佛。
夕陽下的玉沁曲泛著金光,隨著一個塵封已久的秘密被揭開,鐘眠驀然回首,原來,耗盡半生的贖罪,她一直苦苦求索的解脫之路,就在身後。
遙遠的雪域高原,莊嚴殊勝的玉沁曲林內,畫僧嘉措對故去之人阿茹娜懷有深重愧疚,發願修習唐卡,以藝侍佛。
夕陽下的玉沁曲泛著金光,隨著一個塵封已久的秘密被揭開,鐘眠驀然回首,原來,耗盡半生的贖罪,她一直苦苦求索的解脫之路,就在身後。
目錄
第一章 萬壑松濤 2014~2015 12
一、立春 12
二、冷境 16
三、絳紅 22
四、蓮盒 28
五、求婚 34
六、謊言 39
七、故地 45
八、夜歸 51
九、家宴 58
十、閃婚 64
十一、無常 70
十二、流轉 76
十三、速度 81
十四、色影 87
十五、告白 93
十六、原點 99
十七、祭奠 105
第二章 鐘眠花舟 1998~1999 112
十八、晨醒 112
十九、玄機 117
二十、嘎烏 122
二十一、舊憶 127
二十二、遲覺 133
二十三、桑田 138
二十四、夜談 145
二十五、突襲 151
二十六、花鑰 156
二十七、島嶼 162
二十八、花舟 168
...
一、立春 12
二、冷境 16
三、絳紅 22
四、蓮盒 28
五、求婚 34
六、謊言 39
七、故地 45
八、夜歸 51
九、家宴 58
十、閃婚 64
十一、無常 70
十二、流轉 76
十三、速度 81
十四、色影 87
十五、告白 93
十六、原點 99
十七、祭奠 105
第二章 鐘眠花舟 1998~1999 112
十八、晨醒 112
十九、玄機 117
二十、嘎烏 122
二十一、舊憶 127
二十二、遲覺 133
二十三、桑田 138
二十四、夜談 145
二十五、突襲 151
二十六、花鑰 156
二十七、島嶼 162
二十八、花舟 168
...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