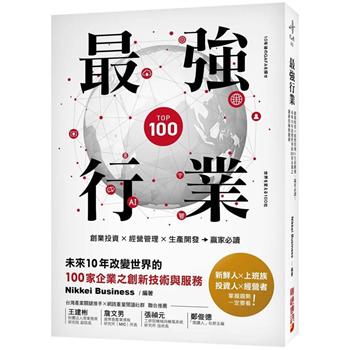推薦序
此曾在
李時雍
曾經我們以為的「媒介物」,是存儲、延伸感覺與記憶,一個個技術的載體,一幀影像,一部電影,纏繞的磁帶,資訊容量滿載的手機,限時動態。然而在妏霜以小說家的凝視裡,「媒」卻成為連結予「靈」而內涵的另一義,魂魅,介面。藏存於物的,總呈現為時間存有的落差與延異,許多時候指向疏遠脆危的人際,有時則使我們聆聽過去如魂魅回返的聲音,細聲說:這將發生,這已發生。如巴特所思,不是揭示「已不存在者」,而是「此曾在者」:碑文,活著的身體,謎樣大象?這部小說深入媒介與時代感覺的描摹,描摹的文字,本身亦即召喚降靈。也許那便是妏霜從愁傷的眼淚,存貨,以至以「語言的齋戒」為名,隱隱暗示施行的一場書寫的此曾在儀式。
復活你自己
葉佳怡
讀這些小說,我想到送葬的歌聲。
西非的吟遊詩人葛里歐在歷史上是個神聖的職業,他們伴隨在君王之側傳遞歷史,而地方的葛里歐也總為村民唱出生活大小故事。妏霜則是為自我一次次送葬的葛里歐,如果他人的敘事是宣判她在某一時空中死去的訃聞,她就是用敘事讓自己再死一次。再死一次是對生的執著,是對虛擬及真實邊界的藝術性重組,是用語言的威力去迎上語言的暴力。
葛里歐什麼都不忘記,葛里歐在每次的葬禮上高歌。這些歌聲有文字,當然也有無以名之的曖昧,以及她進退有據的文學之心。
不發音,但在那裡/幽靈字母列傳
蕭詒徽
我首先想到的是演員功課中的角色自傳:在戲劇發生前,角色從哪一點來到這一點,並且因為從那一點到這一點的連線、形成一道被我們稱為「性格」或「欲望」的向量。許多故事作者嘗試撰寫的,是不同向量被描繪出來之後,「再之後」發生的事:也許互相抵銷,也許是幾何運算後與這個世界之間的新夾角。相比之下,妏霜在這些作品中似乎更專注於描寫那些點、辨識那些點究竟是什麼。而如果真要秤量,在她筆下起點又比終點重要。
比起故事本身,這些作品更像是故事的史前史。我隨後想到的是英文裡的silent letters,不發音的字母,它們是構成單字的必要成分,卻在特定條件下於聲音中隱形。妏霜亟欲描述這些字母為什麼沉默。期待衝突或曲折的讀者會在這些作品中撲空,但那些字母需要被寫下——否則那個單字便是錯的。
莊嚴而沉重的決定
吳曉樂
我一直以為我可以躲在一個默默「喜歡」林妏霜的位置不被發現。責編陳健瑜來找我時,我一度起疑,是不是有誰偷聽到我的默默?好吧,說是默默,並不是完全沒有發出聲音,我的確曾經跟兩位朋友說過,我非常喜歡林妏霜,這裡的喜歡帶著一點絕望的臣服,讀完她的前作《配音》、《滿島光未眠》之後,我曾經陷入很清醒的感傷:再繼續讀她的文字,我可能會失去寫作的信心。林妏霜不僅僅是描述世界,她也描述「描述」本身,兩者她都為我們展現出非常準確(不難想像背後歷經多少黑暗的練習)的技藝,以及,故事肆溢的當代,日益稀薄、罕有的「本真」。我簡直像是得到一把鑰匙,被允許進入一個房間,滿室的角色如同人性標本,有輕輕的搔刮,也有重擊的鑿痕。過去這一年,我對甲骨文萌發興趣,因而得知「我」這個字,造字的本意是一種鋒利、帶齒的戰器,直到更精良的戰器汰除了「我」,「我」才隨著時光流轉,以今日「我」們熟知的第一人稱代詞出現。我並不訝異「我」這個字,最初現身時,這般殺氣騰騰。若我們誠實地面對生活,或許有過那麼幾次痛苦的心領神會,有些事,之所以輸,或被怪罪、被遷怒、被審判,來自「別人的『我』大於我的『我』」。林妏霜的述說,何嘗不是為我們搭建了一個小宇宙,借著形形色色的角色,「你」不妨跟「我」換命,一起歌哭與祝禱;或者什麼也不做,純然看著角色吃痛,內心隨之攣縮。就像滿島光今年出席金馬影展,電影大師課說了一段話,「路上有很多擦身而過的人,可能想哭無法大聲哭、想說話無法大聲說、懷抱痛苦無法展現,我希望用全身來感受他們的喜怒哀樂、代替他們發聲」。
我在她的作品裡,往往是不能自抑地思索起巨量的文學問題(伊塔羅・卡爾維諾《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亦賦予我近似的情境),我幾乎是別無他法地意識到,自己的確是「在進行一個書寫的動作」。也近乎獨自走入山林,你永遠不乏撞見綠與另一抹綠,但有些綠總是更刻骨銘心。以這本《限時動態裡的大象》來說,我的刻骨銘心無非〈枕上的一段夢〉,「影白知道自己,最先渴望的,總是一種較為公平的傾訴,較為公平的傾聽,而非一開始便為那些傷口,因親疏遠近的人情關係,排了階序;對一個人小心謹慎,帶有其意志的敘說,評判了價值的高低。彷彿執行著某些對他人證詞的肯認。而那些現實的語言,也會因此這樣,被壓碎成夢境的語言。四處零散。把身體裡面的某些東西、某些感受,從此交換走了」。
過去這幾年,有時在創作裡「逢劫」,我就會翻出林妏霜的作品,然後,變得更加決定。要形容的話,我會說,她的書寫有一股「全面解構」的魔力,我不禁懷疑我說過的話,遣過的詞,可以嗎?不可以嗎?這裡的懷疑自然攜帶著幾分傷楚跟抵禦機制,像《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貝多芬四重奏的疑問,Muss es sein,非如此不可嗎?然而,又隱約有股確信,答案應該躺在貝多芬於最後一個樂章的標註,Der Schwer gefasste Entschluss,莊嚴而沉重的決定。讀《限時動態裡的大象》,我看到,人的有限性與書寫的無限性之間,可觀的推進。計入附錄共二十一篇,我在這二十一篇裡,老了非常多歲,澈底感受時間流經我,並且將一部分的「我」留在了原地;另外一部分的我,竟仍有所抵達,有所憑依,並在不可見的未來,說服我合成一個信念:有朝一日,現實所凋零的,依舊能在自我的創作裡悄悄地贖還,甚至回春起來。
考慮到林妏霜之於我心裡的特別,在此,我想要以個人前所未有的形式,意即,我放棄過往寫「序」常見的,默契的,因而讓讀者有些懶倦的形式。
我將獻出一個故事。
前些日子,一位讀者提出奇怪的要求「我希望妳在扉頁寫一句,妳母親給妳的建議中,妳覺得最好的」。我一時有點魔怔,忍不住抬眼多看對方一眼,基於過往所累積的一點經驗(或刻板印象),猜想對方的「親情」說不定遭遇了一點麻煩。讓我更加愕意的是,我的右手受到催眠似地,很快地寫下——如果你不能負責,那就別過問。我腦中並不是以「最好的」的格式來儲存這項建議,實際上,更趨近於「最讓我綁手綁腳」的建議。母親認識一個人,基本上,止於對方願意(或不得不)露出的表面,她不對人「多做聯想」。比方說,若社區新搬來一位帶著小孩的女子,有些人可能會在一段時日後,大抵是小小的電梯車廂裡,拋出「先生在別的地方上班嗎」諸如此類的刺探。總之,無非是想要在「女子是/不是單親媽媽」的模糊認知裡,得到一分確信。母親絕不做這種事,她無法為這樣的命運負責。她無法改變女子的婚姻狀態,她沉默。所以她也不在乎,朋友的小孩在哪裡讀書,幾歲了身邊有沒有伴侶之類的。按照母親執行的標準,尋常的人情大致都能篩析成「與我,沒有關係」。八卦沒有容身之處。母親說,沒有所謂「問一問而已」,妳沒看到,多少人際災難就是從「而已」演變的。我一度被母親這樣的規訓弄得很煩,像是限速二十的標示,心思稍稍馳騁,警鈴就響個沒完。三十歲以後,我突然接受了這樣的謹小慎微。我在一次又一次的人際夾纏的事故之間(亦是這本書的「核心」),恍惚明白了,多數時候,「問一問」儼然是光天化日的殘忍。發問本身就是一種階級的確認,終究,一個認為世界對他特別刻薄的人,是不會想去探問別人的命運的,那樣的知情,只會擴大自己的不幸。上述的一切,我以為與林妏霜所云的「複述一次人性底線」有點近。
讀《限時動態裡的大象》,孤身走進一間電影院,銀幕上播映什麼主題,老實說,先別急著分類,因為我們坐在這,想做的、該做的,無非是看見一些人的生活,但又不只是看見。假若我有幸在她的作品裡,有那麼一小塊說話的空間。最末,我想說的是,希臘神話裡,半人半羊的西勒納斯(Silenus)酒後誤闖邁達斯國王(King Midas)的玫瑰園,邁達斯國王好生款待了西勒納斯,並將西勒納斯帶回其輔導、教育的酒神狄奧尼索斯身邊。大喜的酒神實現了邁達斯國王的願望:凡他碰觸之處皆成黃金。邁達斯國王很快地就後悔了,他手上的食物美酒(有一說是他的女兒)都因他的撫摸而成了黃金,失去了本來為世人所識、所接受、進而使用的面貌。後來,在酒神的指示下,邁達斯國王前往帕克托勒斯河,洗去了這項能力。我既醉心於林妏霜創作裡絕美的,亮澄澄的延展質地,但也不禁想問,如果有那樣一位好心的神祇,你是否會允許祂消除妳這「把恐懼或恨意昇華成別的東西」的能力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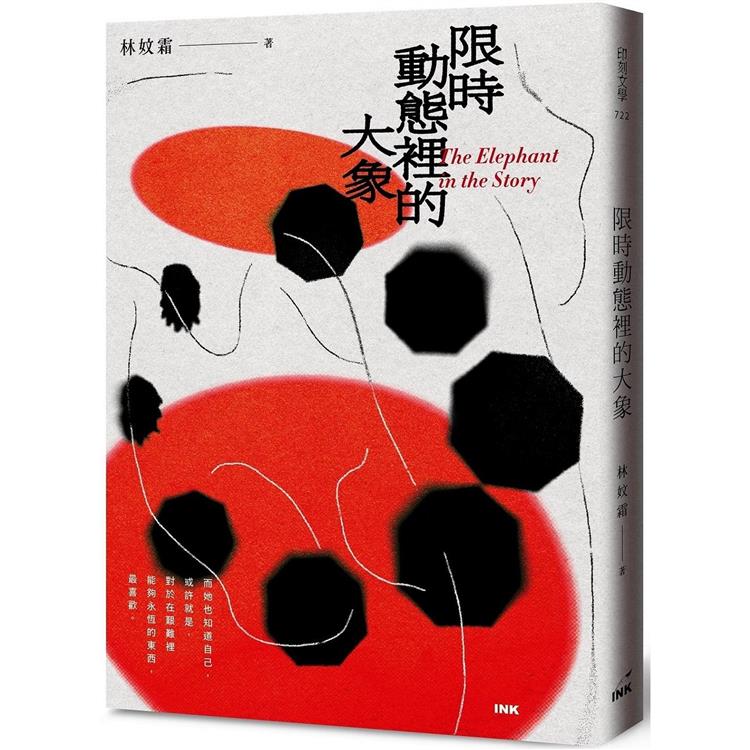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