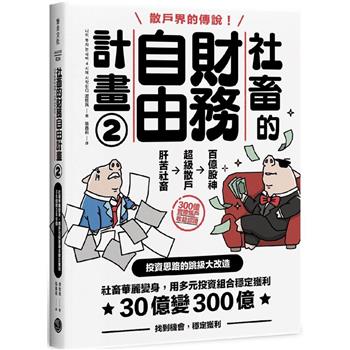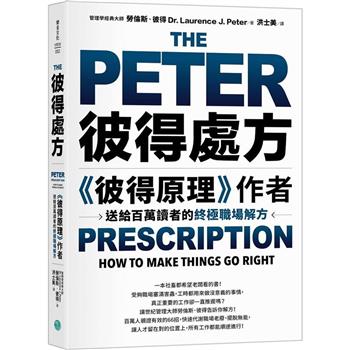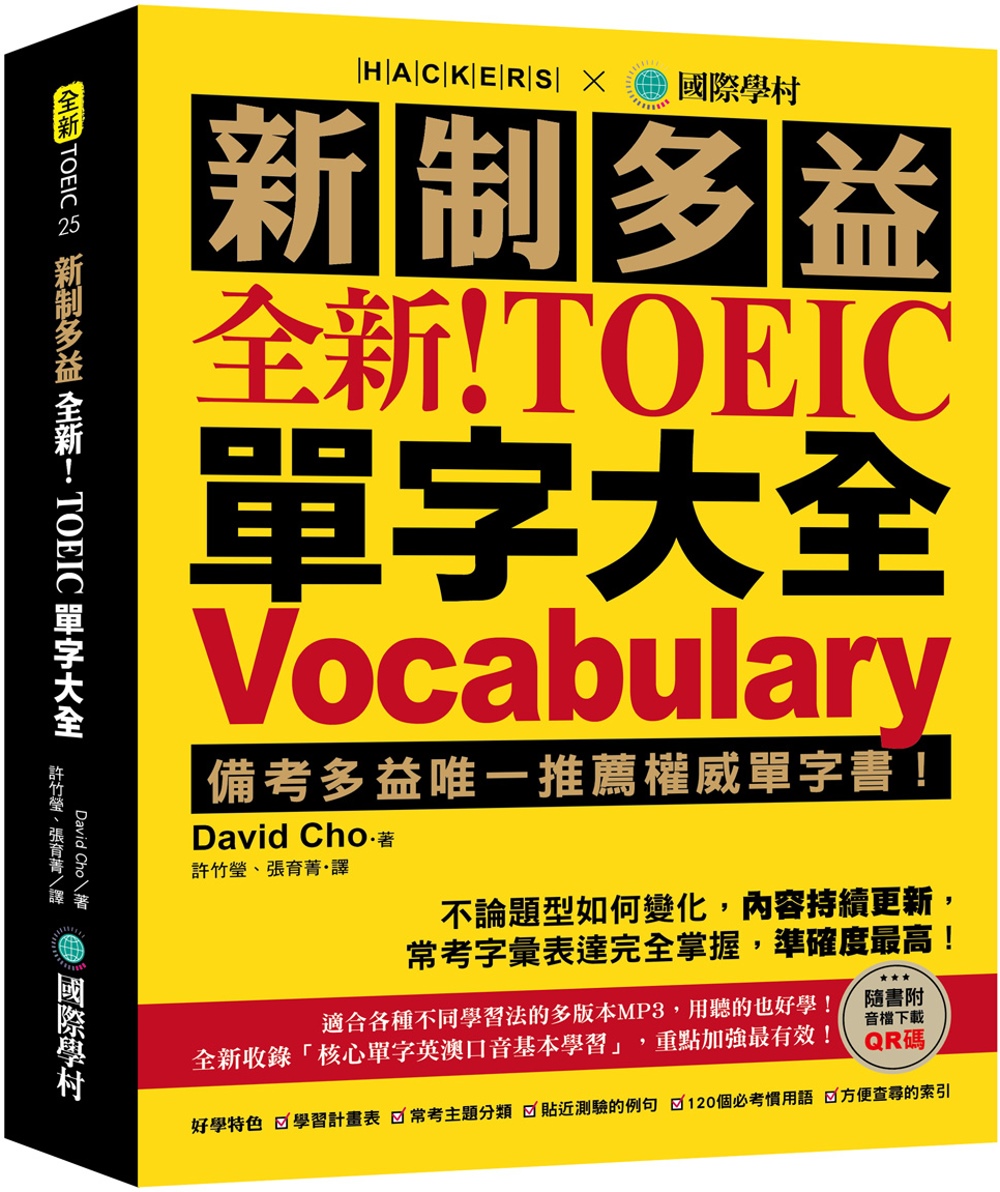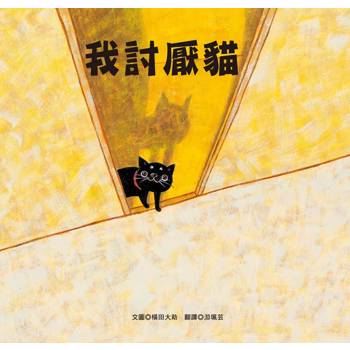所有的愛,
都是有人將自己的靈魂打碎,
再試圖拼成某一種完整。
✦《紐約時報》書評:「這本書,將引發一場史詩級的天候現象。」✦
✦全球多達20種語言版本✦
✦超過30家國際重量級媒體選書推薦✦
✦榮獲誠品選書✦
▍首刷限定.燙印紀念扉.
▍獨家收錄.繁體中文版後記.
風暴的開始總是微小,
一張紙條,一杯熱茶,一次凝視,一份純真──
當兒子亞伯和鎮上那些少年們一樣突然失蹤,賽瑟莉心想,報應果然來了。
她曾以為新的殖民者會讓馬來亞更好,但這份憧憬很快就破滅。日軍三年內殺的人,比英國殖民五十年來殺的人還要多。丈夫日漸頹喪,大女兒小棗變得嚴肅沉默,小女兒茉莉每天都得在地下室待上一天,躲過日本士兵上門「要姑娘」。
這一切都要怪十年前的她,當時她擁有一個女人被認定該有的幸福──一個好丈夫、可愛的孩子、舒適的房子,賽瑟莉卻總幻想著掀翻這一切。直到她遇見了藤原。
那個男人描繪了一個屬於亞洲人的亞洲、一個白人不是唯一勝者的世界。他們不再需要努力表現出文明與教養,卻依舊被視為低下的人種。他說得那麼少,卻讓賽瑟莉如此振奮,改變彷彿就在一波浪潮之外。於是,她開始與藤原「合作」……
如今那波浪潮,卻不斷淹過賽瑟莉的頭頂,殘忍沖刷著她與她的家。眼看又一波惡浪向她的孩子襲來,賽瑟莉知道,她必須把十年前啟動的一切,修正過來──
✦
直到想不起是什麼造就了一切,才終於明白,
原來愛,或者生活,本就是場風暴。
一個過於渴求嶄新的自我,一場沒有盡頭的癡心等候,
一段無法輕易諒解或憎恨的關係,一份禁不起太多慈悲的友誼。
當謊言以最純真的樣貌來到面前,卻只剩懸崖邊緣能夠互相依偎;
當缺角的我們試圖掙扎,卻依然只是易碎的靈魂,
如果終其一生,都得在風暴中前進,請牢記所有失去與失衡──
無論生命多麼破碎,也知道怎麼完整。
✦國際重量級媒體讚譽不斷!
「這本書,將引發一場史詩級的天候現象。」——《紐約時報》書評
「雄心勃勃、波瀾壯闊的處女作。」——《紐約時報》〈一月即將推出十八本新書〉
「充滿活力……陳惠珊成功描繪了一個陷入戰爭恐怖的家庭。」——《出版者週刊》
「有望成為二○二四年的爆紅處女作。」——《君子雜誌》
「這是個錯綜複雜的謎題,作者巧妙地在時間與角色的視角之間移動敘事片段。」——《書單》雜誌
「從第一頁開始就充滿各種陰謀盤算。」——《舊金山紀事報》
「在引人入勝、栩栩如生的歷史背景下,對人性弱點與慾望的代價進行了一場令人不寒而慄的探索。」——《寇克斯評論》
「從其他二戰歷史小說中脫穎而出……這是一部最震撼人心,也最令人心碎的歷史小說。」——《讀者文摘》
「第二次世界大戰可說是歷史小說中最受歡迎的主題,但凡妮莎.陳的處女作打破了許多對於西方戰線的慣有關注以及善惡之間的明確區分。」——《明尼亞波里斯明星論壇報》
「我永遠不會忘記這本書。」——《失格媽媽特訓班》作者|陳濬明
「勇敢、風趣,感人至深。是我讀過最有力、最自信的處女作之一。一個說故事的明星誕生了。」──《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作者|崔西.雪佛蘭
這是本坦率的書,沉浸於道德的複雜性內。喜歡張愛玲的讀者會特別欣賞陳惠珊。」——《Harmless Like You》作者|羅雲.久世.布坎南
「毫不費力地穿越時空,一步一步走向驚心動魄的高潮。」──《Electric Literature》雜誌
「我們在陳惠珊的第一部小說中得以窺見,不平凡的時代是如何降臨在平凡人身上,並令人永誌難忘。」──「Shelf Awareness」網站
「從第一句話開始,你就會被深深吸引……」──「Stylecaster」網站
「這本書具有許多豐富的層次——它的文字之美與萬花筒般的畫面都令我忍不住屏息。陳惠珊寫出了一部傑作,《寂靜風暴》不僅改變了我對戰爭和人性的看法,也改變了我對真正偉大小說的認識。」──《Beautiful Country》作者|王乾
「異常勇敢。令人心碎、美麗動人。注定成為經典。」──《The Mountains Sing》作者|阮潘桂梅
「極其美麗且非凡⋯⋯陳惠珊為這段歷史注入了令人回味的光芒。它會令我思考很長一段時間。」——《Maame》作者|潔西卡.喬治
「陳惠珊筆下的人物在殖民與戰爭的黑暗中面臨到痛苦的選擇,但她卻賦予他們不可磨滅的反抗精神,令你永遠不會忘記光明。這是一個無畏、扣人心弦,又在道德上極為複雜的故事,是個值得關注的作家。」──《The Final Revival of Opal and Nev》作者|達妮.華爾頓
「我愛不忍釋!」──《In Memoriam》作者|愛麗絲.溫恩
✦臺灣名家一致震撼!
作家|許菁芳 專文推薦
作家|李欣倫
作家|凌性傑
作家|郝譽翔
小說家|許俐葳
●按姓名筆畫序排列
我常感覺,啊,眼前的悲劇即將發生,但其遠因卻在手邊早已埋下。因與果都在我的指尖,我是讀故事的人,卻也是見證的全知者。故事本身已經相當精采,而那交織的敘事線,進一步構成超乎文字本身的臨場感。
──作家|許菁芳
作者簡介:
陳惠珊(Vanessa Chan)
馬來西亞作家,現在居住於布魯克林。
長篇小說《寂靜風暴》獲《紐約時報》書評讚譽:「這本書,將引發一場史詩級的天候現象。」並榮登《紐約時報》、《哈潑時尚》、《ELLE》、《讀者文摘》、《週六晚間郵報》、《舊金山紀事報》、《書商》、亞馬遜等逾30家知名國際媒體選書推薦,以多達二十種語言於全球各地出版。
其他作品散見於《Vogue》、《君子》雜誌及其他刊物,另著有短篇小說集《世界上最醜的嬰兒》。
譯者簡介:
劉曉樺
喜歡小說,所以翻譯小說。覺得書籍翻譯工作就像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譯作包括《帕迪多街車站》、《金翅雀》、《階梯之城》三部曲、《流亡者》、《最後的獨角獸》等。
章節試閱
第一章
賽瑟莉
吉隆坡,星鎮
一九四五年二月
日占馬來亞
青少年男孩開始消失不見。
賽瑟莉第一個聽說的是陳家(Chin)的孩子,五名窄額、寬肩的粗壯男孩中的老三。他們分別是文福、文林、文康、文熙、文偉,不過他們母親一律叫他們阿文,男孩自己要知道母親是在叫誰。在英國統治期間,陳家男孩便素來以有錢和殘忍出了名,經常可見他們在陳家那棟華麗又俗氣的金棕色屋子後方圍成一圈,高高站在一名僕人面前,其中一個男孩手裡拿著電閘開關,當開關接觸到僕人肌膚時,所有男孩眼裡都會亮起興奮的光芒。一九四一年的聖誕節前,日軍抵達,男孩們還很抗拒:他們會狠狠瞪著那些巡邏的日本憲兵,對接近的人吐口水。不見的是老三文康,有一天,他就這麼消失了,彷彿從來不曾存在過一樣。就這樣,陳家五兄弟剩下四人。
賽瑟莉的鄰居都在猜那男孩怎麼了。程太太 (Mrs. Tan)推測他只是離家出走;總是陰沉憂鬱的亞茲林女士擔心那孩子是跟人打了架,如今倒在某個下水道內,而這讓大家出門辦事時總忍不住心驚膽戰地往下水道裡偷瞄,不確定自己會看見什麼。其他媽媽則是搖搖頭;這就是霸凌者的下場,她們說,大概有人就是受夠了。賽瑟莉觀察陳家男孩的母親,好奇會看見陳太太守在門邊等消息?還是像個擔心受怕的母親,表現地歇斯底里?但無論是陳太太或其他陳家人都只是沉默。一家人難得出門時,四個男孩會用身軀組成一堵巨大的牆,將面色如土的雙親擋在其中,不讓旁人看見他們。
賽瑟莉只有某天一大早在雜貨店裡碰過陳太太一次。陳太太直勾勾地盯著一包魷魚絲,臉上閃著淚光。那全然的靜默震懾了賽瑟莉,沒有啜泣、沒有顫抖,只有濕亮的雙頰和婆娑的淚眼。
「她已經那樣子五分鐘了。」老闆娘梅姨說,很高興有人能分享她的發現。
幾個星期後,由於再也沒有公開展現的哀慟,也沒其他小道消息可收集,大家便不再將陳家兄弟放在心上。沒多久,鄰居們甚至連是哪個陳家男孩失蹤都忘了。
接著,少年接二連三地失蹤。在墓園當掃地工的瘦小子,賽瑟莉確信他偷了家屬留在墓碑前的花,然後拿去市場賣。雜貨店後的胖男孩,他會用泥巴抹臉,還把褲腳綁起來裝瘸腿,向路人乞討要錢。還有那個眼神陰森的男孩,他曾被逮到躲在女校的廁所外想偷窺。淨是些壞胚子,賽瑟莉與左鄰右舍低聲說,八成是他們活該。
但到了年中,賽瑟莉認識的人的兒子也開始失蹤。賽瑟莉隔壁家夫婦的姪子,那男孩擁有令人欣羨的男中音,學校裡所有演講比賽的冠軍都是他。鎮上醫生的兒子,他是個安靜的男孩,走到哪兒都帶著他的西洋棋盤,只要有人開口,他就會把棋盤擺起來跟對方下。洗衣店老闆娘的兒子,一個勤奮的青少年,所有日本士兵的制服都是他洗的,他母親如今不得不接手這工作,因為日本人沒時間讓人哀悼喪親之痛。
星鎮只有一條將小鎮一分為二的大街、一間藥鋪、一家雜貨店、一間男校、一間女校,小到足以讓擔憂變化成其他樣貌。竊竊私語又開始了,視線投向那些失去男孩的家庭,低聲討論他們的命運。實際上,少年失蹤時完全沒引人注意,彷彿他們是偷偷溜走的,生怕得罪了誰。而這讓賽瑟莉坐立難安,因為青春期的男孩動作時總會發出很大的聲響——老是東碰西撞、走路時腳步踩得用力,就連靜靜站著時都會不自在地動來動去,無法控制自己體格帶來的新力量和四肢的新長度。
「他們餓死我們、毆打我們、搶走我們學校和生活還不夠嗎?現在就連我們的孩子也不放過嗎?」張老伯忿忿不平道;他是張新記雜貨店的老闆,一家位於星鎮中央的在地店舖,從香料、草藥到白米和生皂,每個人都來這兒買用品。他的太太梅姨賞了他一巴掌。這番話太大逆不道了,而且張家自己也有個兒子。
然而情況並非一直都是如此。日本人在三年多前抵達時,賽瑟莉、丈夫以及三名孩子也和其他家庭一樣,在自家屋外排排站好,向軍方的車隊揮手致意。賽瑟莉記得,當她指向遊行隊伍最前方那名矮小結實的光頭日本將軍藤原茂時,她有多麼心花怒放。「他就是馬來亞之虎!」她如此告訴孩子。
藤原將軍在七週內便擊敗了英軍,他精心策畫了一套出人意表的高明戰略,自陸地入侵,命士兵從北方馬來亞與泰國接壤的邊境出發,騎自行車穿過炎熱崎嶇的叢林,而在此同時,英國海軍估計敵方會從海上進攻,因此將槍砲指向南方與東方,瞄準新加坡和南中國海。對賽瑟莉來說,這猶如新世紀的曙光到來,但她希望新殖民者會更好的憧憬很快就破滅了。日軍抵達的幾個月內,學校便開始關閉,士兵現身街道。日本占領者在三年內殺的人,比英國殖民五十年來殺的人還要多。這暴行震驚了平和的馬來亞人民,他們那時已習慣了英國人的拘謹嚴肅與冷漠乏味,只要有達到錫礦和橡膠開採的配額量,他們大多與當地人不相往來。
對於未來的不安,讓賽瑟莉開始每天晚上點起名來,確認三個孩子都有回到家中。「小棗,」她會在準備晚餐的嘈雜聲中大喊,「茉莉!亞伯!」
每晚,他們也都會回答——小棗用不耐煩的語調,表情嚴肅扭曲,那是長子長女特有的神情;茉莉則是開開心心地,兩隻小腳像幼犬般在地上蹦蹦跳跳、跑來跑去。而排行第二、也是最讓她擔心的兒子亞伯則會大聲回答:「媽,我當然在啊!」同時大步跑來,用力給她一個大大的擁抱。
有那麼一陣子,這法子似乎奏效。每天傍晚,當夕陽西下,蚊子開始牠們的夜間大合唱時,她會呼喚她的孩子,而孩子們也會回答。接著一家人聚在傷痕累累的餐桌邊,分享自己今天過得怎樣。每當她聽見亞伯誇張的笑話讓茉莉發出像小豬抽鼻子般的哈哈大笑、看著小棗拉著自己那頭像賽瑟莉一般的短捲髮,在那幾分鐘內,賽瑟莉會忘記他們處境有多嚴苛、戰爭有多可怕、生活有多貧乏。
但後來,在二月十五日亞伯十五歲生日那一天——那個不像姊姊和妹妹,有著一頭淺棕色頭髮的亞伯;因為糧食配給總是吃不飽而飢腸轆轆的亞伯;那個在過去一年內抽高了六吋,現在比全家所有人都還要高的亞伯——卻沒有回應她的呼喊,沒有從店裡回家。當蠟燭融化在亞伯乾掉的生日蛋糕上時,賽瑟莉知道了。壞人有壞報,而她正是那樣的人——壞人。
實情是,過去幾年來,賽瑟莉發現她其實沒有辦法掩飾那份明顯的恐懼,那份掌控著她存在的恐懼;她很清楚,她所做的一切終究會回到自己身上,報應總有一天會到來。這份恐懼顯現在她的焦慮、她擰絞的手指、她瞥向孩子的眼神,以及她對任何不熟的人打招呼時所抱持的那種不信任感上。如今,大難臨頭,她感到體內每根緊繃的神經就這麼垮了。小棗後來告訴她,她發出長長一聲低沉且痛苦的嘶吼,然後就陷進籐椅之中,再也沒有半點聲息。她的表情平靜,身子動也不動。
在她身旁,全家人亂得團團轉。丈夫高登來回踱步,扯著嗓子對自己也可能是對她嚷嚷著說:「說不定他是跑去店裡了;說不定他是困在警方的檢查站了;說不定、說不定、說不定。」茉莉則是緊緊抓著姊姊的大拇指不放,臉上流露一種以一名七歲小孩來說過於堅忍的表情。而向來務實的小棗立刻採取行動。她掙脫茉莉,跑到屋子後方,隔著圍籬對兩側鄰居大喊:「你們有見到我弟弟嗎?你們能幫忙找他嗎?」但那時已過了八點的宵禁時間,即便小棗的哭喊讓他們的心都碎了,還是沒有一個鄰居敢回答。
賽瑟莉一語不發。在罪惡感尚未攫獲她的短短幾分鐘內,眼見內心的恐懼成真,她不由鬆了口氣。終於發生了,這一切都是她的錯。
都是因為她,這所有的一切。
*
亞伯失蹤後的第二天早晨,賽瑟莉的街坊鄰居都動了起來。亞肯塔拉一家素來受人敬重,而這樣一個受人敬重的家庭不該遭遇如此沉重的打擊。男人們組織了幾支白天的搜索隊,舉著牌子四處走動,高喊亞伯的名字。他們查看屋子後方的儲藏間、查看亞伯喜歡去的商店角落、查看運動場和廢棄的工廠。他們看了一下已經改造成日本審訊中心的舊校舍,但沒有進去。他們分成小小的隊伍,一有身穿暗綠色制服的日本憲兵往他們方向看過來,便把頭垂得低低的,但心裡暗自得意,因為他們人多勢眾,而且搜索男孩的行動感覺就像他們自己的一場小革命,一次反抗日本的小型起義。女人家則把這件事當做生死大事來看待,她們帶著無窮無盡的食物和安慰送到亞肯塔拉家,向賽瑟莉保證一切都會好起來——亞伯只是粗心大意,大概在哪兒睡著了,很快就會自己回家;或說亞伯是忘了時間,正和朋友待在一塊兒;又說像亞伯這樣的男孩——這麼英俊、這麼迷人,這麼有前途——不會就這樣消失無蹤。
其他婦人則想,賽瑟莉還真是驚人地不知好歹。送食物上門時她沒有道謝,也沒有備茶給在門口等著受邀進屋的她們,她沒有哭泣,沒有傾訴,沒有以人們能理解的方式崩潰。她只是看起來異樣防備,眼光四處瞟轉,彷彿準備要撲上前。但要撲向什麼?她們不知道。當然了,她們是同情她的,她們交頭接耳,但賽瑟莉有時真的太超過了。記得她以前講給她孩子聽的那些可怕故事嗎?
「男人被迫喝肥皂水那個嗎?喝到他肚子都凸出來,然後日本士兵在他身上放了根木桿,像蹺蹺板一樣在兩頭跳上跳下,直到他爆炸?妳是說那個故事嗎?」蔡太太說。
「哎呀,那故事這麼可怕,妳非得重複一遍嗎?對,就是那個!」程太太說,「害我小孩做了好幾星期的惡夢咧!」
有時候,她們覺得賽瑟莉還真是不懂分寸。大家同為母親,都知道母親該有什麼樣的表現。當一名母親失去兒子時,她應該哭泣,應該崩潰,應該向其他母親尋求安慰。她不該只是拿痛苦當擋箭牌,一副渾身是刺的模樣,讓每個人都怕到不敢靠近。
但是,她們提醒自己,她們還是得當個好鄰居。所以程太太繼續送熱騰騰的湯麵到亞肯塔拉家,而且隔天經過,看見那些湯碗依舊原封不動擱在門外同一個地方時,盡可能告訴自己別生氣。蔡太太主動提說她可以照看小棗和茉莉,讓賽瑟莉休息一下。而愛看熱鬧的亞茲林女士則說起每一個她聽說過的失蹤者的故事,而且就是忍不住在她的版本裡加上一抹恐怖的色彩——說那些人回家時不是缺手缺腳,就是頂著張毀容的臉。
對鄰居來說,起碼賽瑟莉的丈夫高登展現了足夠的感激。他和其他男人一起走遍小鎮,呼喚他的兒子,拍拍其他丈夫的背,感謝大家撥冗幫忙。他現在變得和善多了,鄰居們對彼此這麼說。當然,你不會希望這種事發生在任何人身上,當然不,他們咂了咂嘴,但他們比較喜歡這樣的高登.亞肯塔拉,少了點銳氣、少了他們過去不喜歡的那份驕矜自大。在英國人掌權時代,高登是名行政官員,認為自己比他們所有人都高上一等。
亞伯缺席的日子從幾天變成了幾週。男人每日的搜索開始變得零星,女人也越來越少去他們家。失蹤的男孩越來越多,鄰居們留在家裡,把自己兒子藏起來,躲避日本憲兵銳利的灼灼目光。反抗帶來的短暫喜悅消退了,鄰人再次想起,戰爭時期,自己的家庭是唯一優先的考量。他們不能將時間浪費在其他人的失蹤小孩上。
*
亞伯失蹤一週前,曾抱著一大把看起來像雜草一樣的醜陋野花回家,很顯然是他從路邊摘的。但他是如此自豪,因此賽瑟莉將花插進花瓶裡,假裝那是她這輩子見過最美麗的花。在他失蹤後的幾個星期,那些野花變得又乾又脆,但賽瑟莉還是捨不得扔掉。然後,一天下午,下了場雷雨,就是馬來亞那種出了名的吵得震天價響的熱帶風暴,但她忘了關上臥房窗戶。房內雨霧彌漫,強風把所有東西都吹倒了,裝著亞伯乾枯野花的花瓶也砸碎了。風暴平息後的那晚,高登發現賽瑟莉的手指在流血,因為她試著將花瓶碎片黏回去,想讓殘破的野花站得像男孩一樣高。然而,就像她十年前啟動的一切一樣,不可能修補了。一切已無法挽回。
第一章
賽瑟莉
吉隆坡,星鎮
一九四五年二月
日占馬來亞
青少年男孩開始消失不見。
賽瑟莉第一個聽說的是陳家(Chin)的孩子,五名窄額、寬肩的粗壯男孩中的老三。他們分別是文福、文林、文康、文熙、文偉,不過他們母親一律叫他們阿文,男孩自己要知道母親是在叫誰。在英國統治期間,陳家男孩便素來以有錢和殘忍出了名,經常可見他們在陳家那棟華麗又俗氣的金棕色屋子後方圍成一圈,高高站在一名僕人面前,其中一個男孩手裡拿著電閘開關,當開關接觸到僕人肌膚時,所有男孩眼裡都會亮起興奮的光芒。一九四一年的聖誕節前,日軍...
作者序
親愛的讀者,
在馬來西亞,我們的祖父母是藉由「閉口不談」的方式來愛我們。說得更具體一點,他們絕口不談的是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這段時期的生活,當時,日本皇軍入侵馬來亞(馬來西亞獨立前的名稱),把英國殖民者趕了出去,並讓一個平靜的國家變成了一個自我相殘的國家。
問題是,我們的祖父母對其他事情都滔滔不絕。他們會跟我們說他們小時候的事——以前的鄰居、一起玩的朋友、他們喜歡和討厭的老師、他們害怕的鬼魂。也會說他們成年之後的事——初戀的臉紅、為人父母的恐懼,還有第一次碰觸我們,也就是他們的孫子的臉龐。但有關二次世界大戰的那四年,他們卻鮮少提及,只說那段時間很糟,而他們活下來了。然後就要我們閃邊涼快,別多管閒事。
在寫《寂靜風暴》之前,我用一隻手就數得出我對日本占領時期的認知。我知道日本人騎著自行車巧妙地自北方取道泰國入侵,而英國的大砲卻是對著南方的大海。我知道日軍殘暴,殺人毫不留情。也知道他們在入侵時會投下寫著「亞洲人的亞洲」的紅色宣傳單,那既是警告,也是戰鬥的號召。
做為父親那方的長孫,我和祖父母相處了非常長的時間,問了他們許多問題,而他們都會寵溺地回答我。從小時候這些鍥而不捨的拷問中,我從祖母那兒多得知了一點事實,像是如何避免被空襲炸彈擊中(「平貼在地上,要等飛機完全飛走後再起來,因為它們會是從你的斜前方而非正上方投擲炸彈。」)、如何成為媽媽最喜歡的小孩(「當個像我兄弟一樣英俊的男孩,戰時他被日本人綁架,回來後說什麼也沒發生」)、如何讓丈夫吃醋(「二十五年來每年都收到一封郵寄來的月曆,是一個罕見的、善良的日本男人寄來的,戰爭期間,他曾和我一起在鐵路工作。」)。
隨著我年紀增長,從祖母那裡挖掘她青少年時期在被占領的吉隆坡的生活真相,就像在玩一種口語上的尋寶遊戲。當我問她占領時期的生活是什麼樣的時候,她總是回答:「很普通!就像大家一樣。」
但最終,在這麼多年的時間裡,我從她只談事實的平和口氣中得知了更多——人們苦撐著要養家活口、學校關閉、殘暴的日本秘密警察,也就是憲兵隊把英國官員監禁在新加坡,並鎮壓中國人在叢林裡的叛亂行動。
這些事實被我擱置了許多年。我想我有其他事要做,有其他地方要去。我有工作要做、有錢要賺、有自己的故事要說。直到二○一九年,猶如某種返鄉的歸途,我開始撰寫馬來西亞的故事。
在二○一九年底的一個書寫工作坊上,我寫了篇故事,我當時以為那只是個寫完就丟的作業——關於一名青少女想要在宵禁開始、日本士兵掃蕩街道前趕回家的故事。我還記得指導老師手寫的評語:「把這個珍貴的故事貼身收好,」她寫道,「而且要繼續寫。」
我照做了。我在我的小公寓裡寫作,那段期間,我經歷了一場全球性的疫情,經歷了母親的早逝,經歷了無法回到馬來西亞家鄉的深深孤獨。我寫下由上一代傳承下來的痛苦、寫女性、母親、女兒、姊妹,以及我們所做的選擇會如何迴盪在我們一代又一代的家庭與社群間,而且那方式常常是我們所無法預測的。我寫下我們體內是如何承載著殖民留下來的遺跡、被有毒的男人吸引、寫複雜的友誼、寫破碎的生活、寫當生存面臨威脅時對與錯也變得模糊。而那份寫完即扔的作業現在成了我小說中的第四章。
我希望你們會喜歡《寂靜風暴》,以及賽瑟莉、小棗、亞伯和茉莉是如何在他們的世界裡前進。我希望你們在閱讀時能夠感受到愛、驚奇、悲傷,還有喜悅。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你們能記住他們的故事。
感謝你們的閱讀。
惠珊 謹啟
親愛的讀者,
在馬來西亞,我們的祖父母是藉由「閉口不談」的方式來愛我們。說得更具體一點,他們絕口不談的是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這段時期的生活,當時,日本皇軍入侵馬來亞(馬來西亞獨立前的名稱),把英國殖民者趕了出去,並讓一個平靜的國家變成了一個自我相殘的國家。
問題是,我們的祖父母對其他事情都滔滔不絕。他們會跟我們說他們小時候的事——以前的鄰居、一起玩的朋友、他們喜歡和討厭的老師、他們害怕的鬼魂。也會說他們成年之後的事——初戀的臉紅、為人父母的恐懼,還有第一次碰觸我們,也就是他們的孫子的臉龐。但...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