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我和台南人是這麼接上線的。有一天蔡柏璋找我,問我願不願意幫劇團做採訪。「台南人要三十歲了」,我聽了一驚:這麼年輕的團竟已三十年?
台南人給人的印象一向年輕。觀眾群年輕,劇團近年力推的導演蔡柏璋、廖若涵、黃丞渝、許芃,以及經常合作的編劇許正平、趙啟運等人,個個蓄積青春旺盛的創作熱力。除去編導,盤點近年台灣劇場界火紅的設計師:李育昇、李柏霖、柯智豪、王希文……都在創作或事業初期便和台南人合作,從此跨向更廣遼的舞台世界。
能證明台南人只是長了張娃娃臉的,只有劇團裡另外兩個人——團長兼技術總監李維睦,還有藝術總監呂柏伸。這兩人我在參與這本三十年之書以前都不認識,唯一的印象,是李維睦常在台南人演出謝幕時站上台,請觀眾幫忙口碑宣傳其他巡演場次,勤勤懇懇的語氣,通過他一口比花甲男孩更地道的台南腔,情感和說服力都是百分百。
至於柏伸呢,我全然陌生。只曾耳聞他是個對演員很兇的導演。喔,我還曾在採訪蔡柏璋時親眼偷瞄到他狠罵演員的畫面,算是坐實了傳聞。那是《Re/Turn》某次重演復排。說來有點玄虛或渲染,但如今想來,在那個談重返過去,某個程度也處理「命運」的作品排練場上,我這局外人竟也被時間之神編進了台南人劇團的歷史經緯線裡頭。
蔡柏的意思是,那次採訪他寫成的專訪文章給了他某種溫暖正面的能量。所以想找我參與劇團三十年的紀念書。
我猶豫,但沒猶豫太久。猶豫的理由是,我甚至不是個粉絲。不,我說的不是鐵粉。我其實連台南人的粉絲都說不上。曾為了朋友參演、好奇台語劇、對新銳創作者感興趣而看過幾齣台南人,但次數相較於台南人一年執行的業務量,完全不堪一提。此外,自認是劇場(初)老屁股的我,就說是傲慢吧,有時不免感覺年輕創作者呈現的題材或美學風格,雖然流暢完整且越見嫻熟,對「需要在劇場追求未知陌生體驗」的我來說,卻總有個癢處沒被搔到……
可是這個劇團竟能在台灣這麼畸形的劇場環境中生存三十年耶!這不是件值得驚嘆的事情嗎?環顧周遭,我知道台南人創團那年,其實有不少台灣劇團也成立,但可能漸趨停擺,可能忙於現實。並不是每個團都有餘裕回顧歷史,藉此重新估量當下的。
一九八七年,這一年對我們來說,重要性應該遠遠勝於歐威爾的《一九八四》不是嗎?
也許我能為台灣劇團的歷史記錄做點什麼事……是抱著這樣的心情答應的。我更想知道的,到底是什麼讓台南人能以這麼生鮮猛烈的姿態,踏入劇團營運的第三十個年頭?
*
殊不知,我收到的任務,以及正式展開編採工作後的情況,都和蔡柏起初「帶來溫暖、正面能量」的期待,嗯,這麼說吧,大異其趣。
怎麼呈現這三十年的劇團生態?呂柏伸說,他希望能邀請曾對劇團有所貢獻的人們現身說法,就用三十這個數字,「我們採訪三十位幕前幕後撐起台南人的英雄」。當然,英雄遠不止三十個。我們只能抱著遺憾割捨一些感謝之情同樣不少的劇團成員。
我想,既然是談劇團,又是個喜歡搬演經典劇本的劇團,不如就用經典的「四幕劇」架構來定義劇團不同的發展階段。雖然這麼一來,又只能捨棄後來李維睦提出的有趣觀點——身為創團元老的他,歷經劇團從台南華燈藝術中心樹林街廢工廠友愛街聖波尼法教堂百達文教中心台北七一園區等數次搬家,每次搬家,劇團的人事或創作風格恰巧也隨之變貌,從這個角度來說,台南人的變動毋寧是隨空間動線開展的。
「用四幕戲搬演台南人三十年來事」的架構底定後,事件╱作品和角色╱登場人物依序登場便是。既是一齣戲,演後座談和外部評論自不可少。在討論過程中,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柏伸和蔡柏兩人數次表明:「我們不要歌功頌德的內容,直接、犀利都無妨」。
我不知該「怨懟」這兩人的「預言」,還是四幕劇這註定起伏跌宕的戲劇結構,無論是人物採訪、觀眾和劇場界對台南人的提問,回收到編輯台的許多文章,套句維睦的話,「吃飯吵架沒在客氣」。每個曾是「台南人」、仍是「台南人」的人,對這個曾經彼此滋養、彼此深愛,也因而不可避免互相瞋怨甚至恨仇的所在,都在訪談中坦蕩表露了他們的情感。
有一度,為了書中飽滿洋溢的「愛恨情仇」,我苦惱地撥電話問柏伸:「你確定這是你跟劇團要的嗎?」我大抵還是被華人傳統文化的陳俗定見綁架了,認為一本難得的劇團週年紀念書,即便不歌功頌德,至少得多點,呃,正面能量?
但柏伸不愧是那個「一點都不介意做個讓大家討厭」的人。不只是柏伸,受訪者們也一樣,雖然沒能每場訪談都隨行參與,讀著稿子的我想像,或許藉由事過境遷的訪談,所有人都獲機會重返曾造就愛或傷害的現場,稍稍拉開一個距離回顧那些朝夕相處的光陰,那些把自己交託出去、信任過摧毀過重新開始過的無盡循環,以及,歷練過渡後變得強壯的自己,藉由坦率說出往事,再次溫習在排練場上反覆搭建的信任感。
*
《如此台南人》於是成了一本「人味」濃厚的紀念冊。無論是許瑞芳當家時代一群人認真做戲、認真玩樂,把劇團當社團過的「業餘手作」感,或是呂柏伸掌舵後力求拼搏向上、打磨專業技能,把做戲變成壓力鍋裡熬煮魔力湯,眾人在裡頭也親密、也煎熬……
它確實少了歌功頌德,也不侃侃而談美學技藝,就只是把一群捨不得離開做戲的人如何經驗、怎麼感受給攤在書頁上。愛恨情仇或有假戲真作,底下浮出的謎底,其實也就「鍾情」二字。
既然談到「美學」和「技藝」,就讓我再多說一點。在台南人劇團的脈絡底下談這組詞並不好談——劇評人白斐嵐說了,台南人脈絡難耙梳,甚至讓人誤會「沒有」。這也真是場誤會,一個劇團的創作風格因為「非一人一地一時」而難以總結,並不等於它缺乏脈絡,只是,過去針對團隊談技藝、論美學,我們習慣的是單一藝術家領銜掛牌的團隊,一人等於一團,例如,談雲門美學即是談林懷民美學,談表演工作坊即是談賴聲川與他的集體創作術,談屏風表演班,就是李國修編導演三位一體的創作技藝……
我曾問過柏伸這問題。他反問我,如果是找一組參照的方式來看台南人呢?比如,同樣是提供一群導演創作平台的「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
事實上這種比對仍難以對照出台南人的創作風格。莎妹聚集的導演群全是已積累一定劇場經驗、資歷的中青創作者,但台南人的創作者歷來都是由藝術總監舉薦的劇場新人,作品不多或根本尚未舉行過公開售票演出。他們相當於在台南人「出道」的新人,劇團投入行政、製作資源支持創作發表,倘若彼此工作上氣味相投,就繼續在團內發表創作,從而發展出所謂的個人風格。在這樣的前提下,面對還在「長成中」的多數台南人創作者,來自外部的歸納或許當更審慎,更需要一些耐心等待。
當然,也不是不能在一個群體的前提下談創作傾向。王友輝的評論就為我們提供了難能可貴的長期觀察視角,一路將劇團縱切到近期,他就認為,台南人創作者近年似乎普遍對人的闇黑暴力有所執迷。不過,眼看蔡柏璋即將把創作主題轉往跨文化、跨種族的大題目,廖若涵也把觸角探往兒童劇和幽默喜劇,呂柏伸正考慮重返台語劇……在主題的氛圍調性上,每個人曾經交會,但未來似乎依然是各行其是的局面。
會不會我們需要的,是從一個更全局宏觀的視角來探勘劇團的發展脈絡,而不再只是創作風格的歸納?
台南人扶植新銳編導演,既有主動的意圖,也有不得不然的潛在因素。在國家補助的表演團隊中,台南人秉持模範生精神,從表單報告到業務質量無不力求做好做滿,因此一路從地方劇團到今天金字塔上層的卓越團隊,但光靠單一創作者不可能完成一年七到十個製作、年平均總場次一百場。這是發生在當代台灣一場只能進不能退的劇團生存戰役。
「這是人家的遊戲,你要玩就要遵守規則」,「何況我也不同意團隊一年拿國家三百萬,結果只演一檔戲共四場,這也誇張」,柏伸這麼說。
寫到這裡,我多少覺得在進行一個自打嘴巴的行為。倘若自認在做一本有歷史意義的劇團之書,要是都想到這裡了,為什麼不在這本書這麼做呢?
因素很多,就提最易解釋的:時間不夠。我曾想像如果因緣具足,要做到所謂的歷史,除了全面檢索劇團作品檔案和製作文件資料,還要能隨行觀察、記錄劇團一年度的大小製作。但現實因素一如柏伸書中所說的,演員無法每次排練都到、得在外軋幾部戲維生的困境……就連不做到上述超展開的工作模式,完成這本書的現狀也仍因我得「軋戲」接其他稿子而使進度一再延誤。(柏伸,對不起啦,每次你說演員不肯給你更多時間,我心裡都直冒冷汗。)
*
在和台南人(的歷史、成員與文稿)相處一年後,問我會怎麼看這個劇團?我想到的,是園藝領域盛行的一種名為「嫁接」的技術。
頭一次看到嫁接的樹木時我深感吃驚。忘了是什麼樹在離地約莫二十公分處呈現清楚的斷面,上頭赫然是另一不同種的樹木軀幹。異質拼接,它(們)卻長得欣欣向榮。後來我才知道,這在果樹的栽種和繁殖中極為常見。
方法很簡單,在體質強壯的母樹上削出一口子,把移植的樹幹、枝或芽(但最好和母樹是同科同屬樹種)緊密貼合在斷面,然後把它們「牢牢綁在一起」。待切面傷口癒合,它們會成為一體。嫁接樹的優點,或者是提昇抗菌性,或者強化果實質量,也可能是果實多出原本沒有的風味……
從這類比看來,台南人是棵強壯的樹。它有能耐屢次把異質外來的幼株、他樹都納入原來的身體。縱使外表看來橫斷線鮮明,卻不妨它繼續生長,提供自己和新植入的樹養分。李維睦說希望劇團百年。只要環境給好土壤,好氣候,不染上腐朽菌,百年對一棵樹一點不難。編輯報告最後,就把這比喻送給劇團,作為我的小小祝福。
文/主編 鄒欣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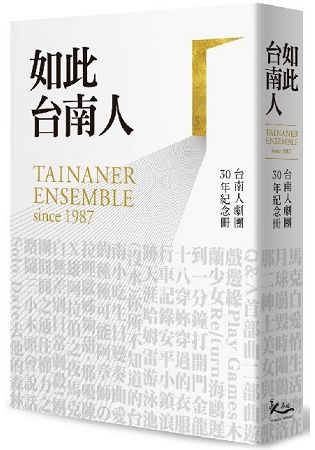
 共
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