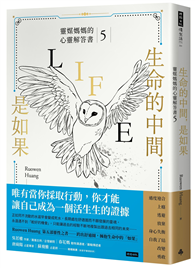圖書名稱:法律有關係
第一本台灣法律與社會研究指南
法律就在我們身邊,從簡單買一杯咖啡的日常交易,到就業、納稅、租房和企業營運等更複雜的事務,都需要有規範及法律支持。在理想情況下,法律為國家提供了政府行使權力進行統治的指導方針,對個人則提供了保障生命財產和公平交易的法律支援。然而,我們還是到處可見非法或法律的無效:滿街的違建,坊間津津樂道逃稅避稅之法。人們走到警察局、來到法院,無不使出渾身解數表演。法律運作經常轉化為制式而瑣碎的流程,即使每個點都合法,還是無法串連出共同的價值。
每到需要溝通的時候,我們經常驚覺不知該與誰對話,如何對話。
台灣政治與社會權力結構的變遷深刻地影響了法律在社會中的角色。解嚴前,法律被用來管制人民,成為統治者的工具;解嚴後,法律轉變成為節制權力濫用的手段,以建構保障個人自由和權利的法治社會,更是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全球化與科技發展也對法律的社會角色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法律鑲嵌於政治、經濟、文化與生活脈絡,以各種方式成為人我社會關係的關鍵部分。如果仔細觀察每個法律現場,我們會發現法律實踐是個體欲望、集體爭論以及權力作用的反映。為了更好地理解生活中的法律,解決糾紛中產生的困惑,朝向理想社會邁進,我們必須不斷探索:要成為怎樣的個體?成就何種集體?個體與集體的關係是什麼?如何藉由個體與集體的相互辯證創建法律?
「法律與社會研究」領域在國外已發展近五十年,起初強調運用社會科學知識來提升法律政策的效能,後來則關注法律和政治權力、組織生活以及日常實踐之間的共構關係,特別是描繪法律的歷史和文化特性。此一領域的研究者採取跨領域的視角,援引了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哲學、人類學等知識,在不同學科的養分下,設定創新的方法論、嶄新的研究議題與多元的分析架構,開啟有別於主流法學的研究方式。在台灣,法律與社會研究受西方的影響,同時也受到社會劇烈變遷的衝擊,因此發展出獨特的學術焦點。
這是一本台灣法律與社會研究的文獻地圖,18章為18個議題,作者就自己研究領域,提供該議題相關的概念、論證與理論,以及近二十年來國內外的知識成果。全書分為三個單元、六個主題,首先「拆解」一般人對法律的認知,意識到法律理念實際上深受經濟發展、全球政治和科技創新的影響,拼湊更完整的法律圖像。接著「理解」法律的內在邏輯,從而掌握當下討論與改變法律的核心議題。最後回到法律的公平正義目標,從社會的主體能動中展現法律改變社會的能量,並具體舉出家庭、性別與各種社會運動的案例,除了讓青年學子與研究者按圖索驥進入學術對話,也讓人文社科讀者從而理解並思考,法律是什麼、怎麼變,如何影響我們生活。
本書從傳統的實證研究延伸出文化、歷史、哲學和人權等更多元的研究視角,更加關注當下的法律權利如何對個體和集體產生影響,以及是否能夠改變根深蒂固的社會不平等模式。
主編簡介
王曉丹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特聘教授,研究領域為法意識/法文化、女性主義法理學、人權法律民族誌、法律動員與社會轉型。
作者簡介
陳維曾
國立新加坡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李柏翰
國立台灣大學全球衛生學程助理教授
劉靜怡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專任教授
王曉丹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特聘教授
莊士倫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博士候選人
林佳和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蔡博方
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副教授
許菁芳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簡士淳
美國克里夫蘭州立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
沈伯洋
國立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副教授
陳韻如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
黃琴唐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
陳柏良
國立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助理教授
郭書琴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容邵武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林志潔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特聘教授
施慧玲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官曉薇
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共 10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0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