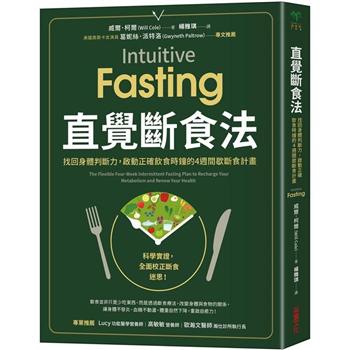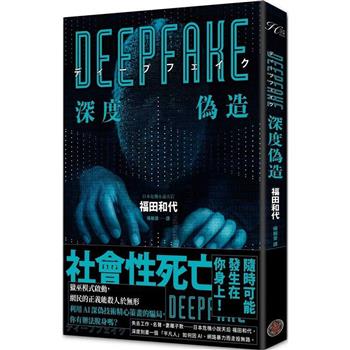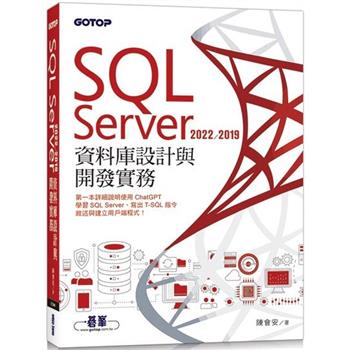大江健三郎的原點
傳說中的名篇復活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的原點
傳說中悲憫之神般的名篇復活
小人物在大環境中掙扎的眾生相
嚴厲控訴,滿懷悲憫,站在理想頂端的文學大師風範
本書共收錄了六篇小說:飼育、死者的招待、他人之足、人羊、不意之啞、今日之戰,為大江健三郎早期的成名作,發表於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受到先前的第二世界大戰影響,主題緊扣強烈的反戰思想,與人性的思索,其中〈飼育〉為第三十九屆芥川賞得獎作品。
死者的招待
管理員領著我與女學生走進地下室,裡面的水池,灌滿黃褐色的液體,死者們的雙眼死死閉著,在水池中時而安靜,時而吵雜地自言自語。而我們的工作,就是將這些死「物」們,搬運到更換新水的水槽中,將沉在下面不堪解剖使用的老舊屍體「處理掉」……
他人之足
未成年病房的我們,是一群身體不能自由移動的安靜小孩,在與世隔絕的病房,我們默默承受著護士對我們的「捉弄」,為的是從中獲得帶點羞恥的小小快樂。一天,一個學生加入我們,他要推翻這小社會的規則,檢討醫院的生活,並討論國際情勢……
飼育
在山裡打獵維生的我們而言,戰爭只是偶爾抬頭從天空飛過的戰機,直到有天,村人們擄獲了一頭穿著軍裝的「獵物」黑鬼,由我負責送飯,我覺得這真是個難以言喻的美好獵物啊,他貪婪的吃相與體臭,讓我的臉頰發燙,閃耀著瘋狂的情緒……
人羊
最後一班開往郊外的巴士,載著即將歸營的外國士兵,士兵們像剝動物皮毛般拔下我的外套,扯下我的褲子,然後拍打我已被凍得沒感覺的屁股,我們是群無助的「羊兒」。其餘坐著的「羊兒們」沒人回應想仗義直言的男教師,沉默地低著頭……
不意之啞
一輛載著外國兵的吉普車由黎明的霧中駛來,難得見到外國兵的村民們或好奇、或忐忑,原本平靜進行著狩獵、耕作、養蜂等的日常工作步調被不知不覺攪亂了。態度比起外國兵來顯得更加蠻橫的隨車日本口譯員,因為一雙遺失的鞋子,小題大作的追究方式,在淳樸的山中村落掀起了一場生死攸關的軒然大波……
今日之戰
那些殺人犯,需要贖罪的羊……我不過是對政治稍微有著像感染熱病般的學院青年,玩笑似與弟弟接下一個暗地裡發送反戰冊子,呼籲士兵逃離戰線的祕密活動。直到一名逃兵真實地出現尋求協助,密告、收留、軍法審判……我們現在做的不是正常人會做的事,如果到死都得保護這個男人的話……
作者簡介
大江健三郎(1935-)
出生於日本四國愛媛縣,東京大學法國文學系畢業。一九五七年〈死者的招待〉入圍芥川賞,翌年(一九五八年)即以〈飼育〉獲第三十九屆芥川賞,一九六七年長篇小說《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獲第三屆谷崎潤一郎賞,一九七三年長篇小說《洪水淹沒我的靈魂》獲第二十六屆野間文藝賞,一九九四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二○○六年時值寫作五十周年、講談社創立一百周年,共同設立「大江健三郎賞」。
出生於戰後的谷崎潤一郎在學生時代已累積相當多的作品,早期作品多涉反戰思想,之後由於個人生活經驗,關注層面更廣,但也因題材殊異、批判性強烈,頗受爭議。除了小說作品外,其隨筆與文學評論也極具重要性。
譯者簡介
林水福
日本國立東北大學文學博士。現任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臺北文化中心主任、國際石川啄木學會臺北分會理事長、國際芥川龍之介臺灣分會理事長。曾任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外語學院院長暨副校長、輔仁大學外語學院院長暨日文系主任及所長、日本國立東北大學客座研究員、梅光女學院大學副教授、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理事長、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理事長。著有《源氏物語的女性》、《日本文學導遊》、《讚歧典侍日記之研究》(日文)、《他山之石》、《日本現代文學掃描》、《中外文學交流》(合著)、《源氏物語是什麼》(合著);譯有谷崎潤一郎的《鍵》、《卍》、《痴人之愛》、《少將滋幹之母》、《夢浮橋》、《細雪》,遠藤周作的《深河》、《醜聞》、《武士》、《沉默》、《海與毒藥──遠藤周作中短篇小說集》、《我.拋棄了的.女人》,井上靖的《蒼狼》,□原登《飛翔的麒麟》(上、下)、《家族寫真》,以及新渡戶稻造《武士道》等書;評論、散文、專欄散見各大報刊、雜誌。
陳諭霖
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畢業,日本廣島大學日本言語文化教育科碩士、文化教育開發科博士。現為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專任助理教授、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日本文學、日本文化、日本語教育。著有博士論文《谷崎潤一郎研究──近代東京□的抵抗》,於中日學術期刊發表多篇有關谷崎潤一郎、芥川龍之芥、台灣文學等學術文章。二○○七獲邀參加興國管理學院年日本研究跨學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谷崎潤一郎「□開日記」□□□戰時生活□戰爭觀》。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