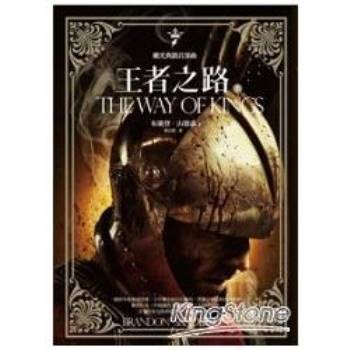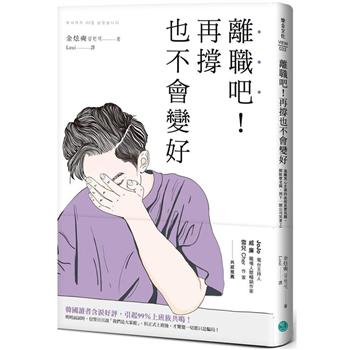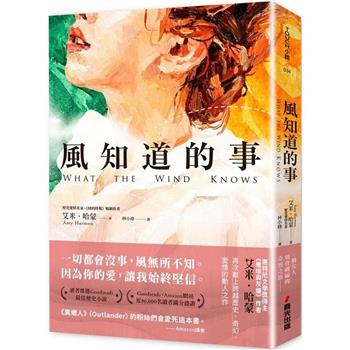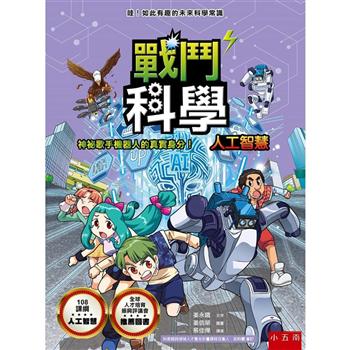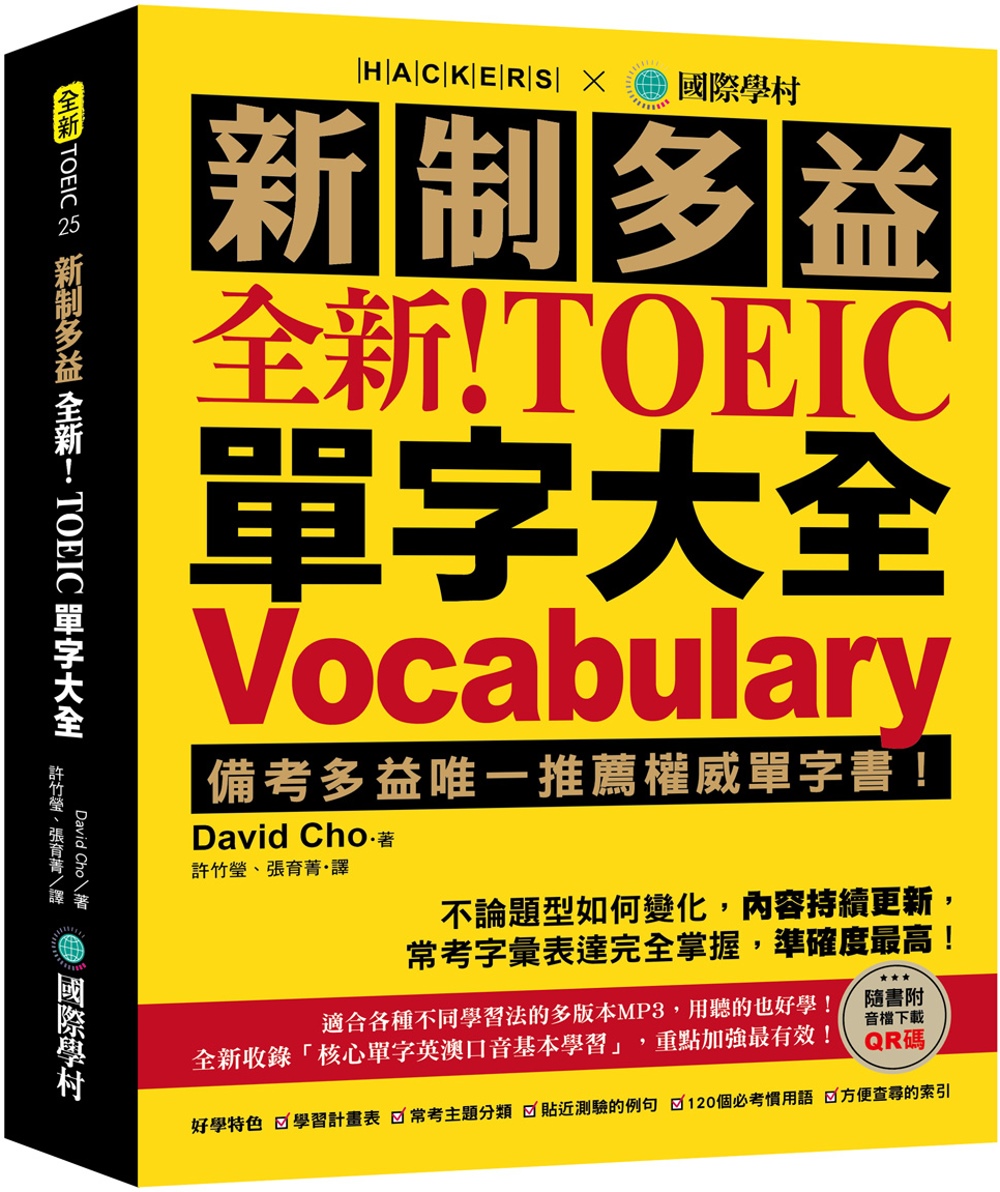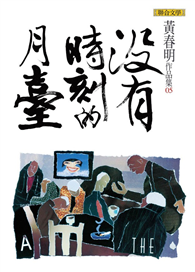中國基督教歷史的研究中,在有意無意間會出現一個斷層,即自1957年至1979年的歷史。筆者從被稱為「中國的耶路撒冷」的溫州教會作為一個縮影,追溯被作為「無宗教區試點」的區域,是在怎樣的背景下經歷無情的逼迫,在被稱為「三無」(無教堂、無教牧、無聖經)的時期中,靈活轉型,引來教會的大復興?
本書向我們展示一個容易被人忽略的城市,如何引來全面的關注,幾十年的「溫州熱」,展現教會中的「溫州模式」。在傳統意義上的政策便利、差會支持、教牧領導、經濟支撐等因素盡失時,溫州教會卻能夠在「無政府主義」的狀態之下進行宗教活動,在無數宗教逼迫中堅守信仰立場,在各教會之間實行聯合派單。同時,溫州教會建立了具有溫州特色的牧區管理體制。藉由本書,幫助我們瞭解今日溫州教會諸多現象的根源。
作者簡介:
陳豐盛
浙江永嘉人,1979年生。先後畢業於華東神學院、伯特利神學院、香港基督教教育研究院、建道神學院,先後獲得學士、基督教教育文憑、教牧學碩士、神學碩士、哲學博士。
在教牧方面,於2013年按立牧師聖職,獲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婚姻家庭諮詢師,並長期從事教牧輔導、婚姻家庭輔導。先後出版《合神心意的婚姻》、《蒙福的婚姻》(合著)、《培育由心——基督教教育的起點》、《傳道者的「神話」》。
在學術方面,於2002年開始研究溫州基督教史、浙江基督教史,先後出版《詩化人生——劉廷芳博士生平逸事》、《溫州基督教編年史》(編著)、《近代溫州基督教史》、《杭州基督教會思澄堂編年史》(編著)。先後在《金陵神學志》、《天風》、《華東神苑》、《浙江神學志》、《甌風》、《中國基督教研究》、《世紀》等刊物發表教牧文章、學術論文超過200篇。
曾任浙江省永嘉縣基督教江北牧區浦西堂傳道、江北牧區教師(副牧師)、浙江神學院專職教師、杭州基督教會崇一堂牧師、思澄堂牧師;《天風》特約撰稿人、特約編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現任義大利華人神學院專任講師、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義務)研究員、杭州葡萄園導師。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導論
引言
溫州教會從第一位傳教士到埠至今已逾 150 周年,其中所經歷的復興是有目共睹的。這也使溫州教會贏得各地教會的好評,甚至得到「中國的耶路撒冷」美譽。在已過的歷史中,溫州教會最為獨特且值得大書特書的,就是在 1957 年至 1979 年
間所經歷 20 多年的逼迫。在全國眾多教會都停止聚會,教堂被關閉的情況下,溫州教會甚至被列為「無宗教區」的試點城市。但溫州基督徒在如此惡劣環境之中不但沒有停止聚會,反而化整為零,在信徒的家中建立聚會點,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使教會得以進入百多年來最大的復興。僅 20 多年間,溫州
基督徒的人數從 10 萬人增加至 30 萬人。這種快速的增長,實在是值得追溯與研究的。
第一節 題目與問題探討
凡是對溫州基督教稍有瞭解的信徒、牧者、學者,都會異口同聲地稱溫州是「中國的耶路撒冷」。其中,有兩本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以「中國的耶路撒冷」來命名,分別是曹南來的
《建設中國的耶路撒冷:基督教與城市現代性變遷》1 和舍禾的
《中國的耶路撒冷:溫州基督教歷史》2 ,鞏固了這個概念。 但我們至今未能找到歷史根據來追溯此「殊榮」的確定時
間,大概只能得出一個大概的時間範圍,3 即在 1980 年左右,或
1 曹南來,《建設中國的耶路撒冷:基督教與城市現代性變遷》(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4)。
2 舍禾,《中國的耶路撒冷:溫州基督教歷史》(臺北:宇宙光全人關懷,2015)。
3 筆者就此訪問十數位牧者、學者,並翻查史料,未能找到一個確切的答案。現任溫州市基督教協會會長吳聖理牧師給出的第一個答案是「魏克利 (Philip Wickeri)」、
「約在 1991 年魏克利來訪溫州,看到溫州教堂多、信徒多、聚會多,後回到香港愛德基金會海外聯絡處,發表文章稱『溫州是中國的耶路撒冷』特別是指教堂多。」這事後來得到溫州市基督教協會原會長張大鵬長老的證實,他說:「美國魏克利博士於 1991 年在香港發表文章稱溫州教會為『中國的耶路撒冷』。」但筆者直接聯繫現任香港聖公會大主教神學及歷史研究顧問魏克利,至今未得到確切的回應。同樣,筆者查找曹南來與舍禾的著作時,都沒有得到確切的答案。曹南來在第一章的註腳中提到:「一位上了年紀的溫州教會領袖聲稱九十年代,他在一篇題為〈溫州:中國的耶路撒冷〉的文章中,第一次使用了這個術語,隨後傳到海外基督教世界。」張敏在〈基督徒身份認同—浙江溫州案例〉中證實這位教會領袖就是鄭大同。後來,鄭大同長老給予肯定的回覆,在其長文〈溫州教會的歷史、現狀與未來展望(一)〉中介紹:「1990 年 3 月 1-4 日,丁光訓的友人美國菲力浦‧魏克利博士率愛德國際訪問團來訪溫州時說到,海外有人因溫州教會的復興,稱溫州為『中國的耶路撒冷』。九十年代初,溫州是中國的耶路撒冷的說法就傳開了。因一位在香港的姐妹,她所在教會的牧師要瞭解溫州教會復興的情況,我已寫過一篇『溫州:中國的耶路撒冷』的文章,在海外廣為流傳⋯⋯後來我不喜歡這個稱呼。」從鄭大同的表述看,他承認自己並非最先提出「中國的耶路撒冷」,他認為自己是致使這一稱呼在「海外廣為流傳」的那位。後來,筆者在 1989 年出版,由魏皓奔主編的《困惑中的思索—社會「熱點」問題紀實》與同年發行的《復印報刊資料:無神論、宗教》第 2 期中找到「中國的耶路撒冷」之提法,且寧波盛足風牧師在 1989 年 2 月第一次到溫州之前就曾多次盼望能去,因「溫州教會素有美名」。再往前追溯,筆者發現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於 1989 年春主辦的《當代宗教研究》創刊號中登載兩篇文章是 1987 年 10 月到溫州對當地宗教與基督教的調查報告,分別是徐鴿的〈改革、開放形勢下的溫州基督教—二訪溫州觀感〉和張樂天的〈改革大潮中的溫州宗教〉,都用「素有『中國教會的耶路撒冷』之稱」,表明該名聲不只是 1987 年 10 月才有的,應該是一種久已流傳的。中國基督教協會原會長曹聖潔曾三次記錄自己以上海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的身份到溫州調研,其原因就是該地被稱為「中國的耶路撒冷」。而第一次去溫州的時間為 1981 年。同樣,海外學者,如:林保德 (Tony Lambert) 在其著作 China’s Christian Millions 的第一章中就以〈序言:復興的種子〉為題講述溫州教會的歷史,宣稱「文化大革命」沒有摧毀溫州,
之前,溫州教會因其人數眾多而被稱為「中國的耶路撒冷」。4但我們的問題是:這樣的外界宣稱與自我認知是否符合實情?溫州教會的獨特點在哪裡?是什麼助力溫州教會的復興?是政治的寬鬆政策、或是經濟的優勢?5 這種普遍的復興從什麼時候開始?相關的探討將在文章進行詳細地探討。
反而原來的「無宗教區」變成聞名全國的「中國的耶路撒冷」。著名傳教士畢范宇 (Frank Wilson Price) 則早在 1948 年就形容溫州在浙江、安徽、江蘇三省的英國循道公會教會信徒占比是最多的。艾克曼 (Divid Aikman) 在 Jesus in Beijing 一書用一章的篇幅來報導溫州教會,追溯「中國的耶路撒冷」的由來,只是沒有陳明「中國的耶路撒冷」名稱的具體時間,而是從歷史的發展來分析溫州教會的復興。相關可參,曹南來,《建設中國的耶路撒冷》,155;張敏,〈基督徒身份認同—浙江溫州案例〉,張靜編,《身份認同研究:觀念態度理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87;鄭大同,〈溫州教會的歷史、現狀與未來展望(一)〉,「溫州基督教文庫彙編」,網址為:http://wzbxcc.blogspot.com/2017/10/blog-post_24.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9 月 4 日);魏皓奔編,《困惑中的思索—社會「熱點」問題紀實》(北京:團結出版社,1989),208、346;蔣志敏、徐祖根,〈面對十字架的思考—中國「基督教熱」透視〉,《復印報刊資料:無神論、宗教》1989 年第 2 期(1989 年): 41;盛足風,《訴說主恩》(自印本,2002),193、194;曹聖潔,〈為研究中國宗教現狀齊心努力〉,上海社會科學院院慶辦公室編,《往事掇英:上海社會科學院五十周年回憶錄》(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236;曹聖潔口述,羅偉虹撰稿,《曹聖潔口述歷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134;曹聖潔,〈向基層教會學習—訪問數地教會有感〉,《天風》第 3 期(1988 年 3 月):2-3;《當代宗教研究》第 1 期(1989 年):3、12;張樂天,〈改革大潮中的溫州宗教〉,《當代宗教研究》第 1 期(1989 年):16;Tony Lambert, China’s Christian Millions (London:
Monarch Books,1999), 18. Frank Wilson Price, The Rural Church in China (New York:
Agricrltural Mission, 1948), 18. Divid Aikman, Jesus in Beijing (Oxford:Monarch Books, 2003), 195-208.
4 因為張樂天肯定溫州教會的發展,將其得到關注追溯到解放之初。他說:「溫州,在歷史上就以宗教興盛而馳名。在這裡,不獨佛、道、基、天四大宗教齊全,且以教徒人數眾多而在全國頗具影響。僅基督教一家,解放之初就已有『全國看浙江,浙江看溫州』之說。據不完全統計,當時的基督教徒約愈七萬,占全國總數的十分之一。更令人矚目的是,在宗教被目為異端邪說,遭到禁止和掃蕩的大躍進及『文革』時代,溫州的宗教非但綿延不絕,甚而出現長足的發展。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隨著宗教政策的落實,溫州宗教更趨發達。迄今,當地的基督教徒已達三十余萬,仍占全國總數的十分之一。」參,張樂天,〈改革大潮中的溫州宗教〉,16。
5 曹南來認為:「溫州的基督教復興發生在這樣的條件下:現代化的國家、寬鬆的地方治理、新興的資本主義消費經濟和個人空間流動性的增強。」參,曹南來,《建設中國的耶路撒冷》,9。
縱觀溫州教會的歷史,我們發現溫州教會自建立之初 (1867-1957),就突顯其在中國教會中特殊的地位,人數眾多,在時勢中脫穎而出,但因民族主義與本色化運動的影響,溫州教會屢次出現教會分裂(自立運動),而教會本身的發展並不理想(不過,在全國來看,算是典型的);在三自革新運動之初陽奉陰違的對策,突顯其在信仰的立場,導致政府更加極端的打壓,從而引來「無宗教區」試點,而教會在此過程中並無發展,反呈下降趨勢。但經歷滅頂之災 (1957-58) 的溫州教會,卻並非完全被消滅,有形教會全面關閉的大潮中,家庭聚會卻如異軍突起 (1958-65),化整為零信仰群體幾乎不受控制,以溫州人靈活與務實的特性,拋開宗派的束縛,形成「小作坊式」的教會。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全國宗教在形式上蕩然無存,但轉型升級 (1966-70) 的溫州教會,拋棄原本宗派的束縛,實現真正的合一。「無教堂、無聖經、無教牧」時代(「三無時代」)的無形教會,使教會實現真正的本色化,即無西方勢力的介入,亦無宗派傳統的束縛,回歸到復原教會的模式。義工傳道全面興起,取代教牧職任的壟斷局面,其生活經營與服侍的模式,帶著溫州特色,成為後來溫州「老闆基督徒」的原型。中美關係破冰之後,溫州基督徒把握時代脈搏而建制復興 (1971-76),牧區制的產生,成為溫州教會特有的管理模式。在
「文化大革命」之後,教會在等待黎明的稍微寬鬆的環境中,教會開始出現不合一的現象,最後在「三自會」復出中使教會因政治立場而重新分道揚鑣 (1977-79)。
縱觀歷史,溫州教會的復興並不是因為經濟發達,不然全中國範圍內比溫州富裕的地區比比皆是,就更有復興的可能,而溫州教會復興過程中較為突出的反而是落後、貧困,特別是信仰的逼迫催生的,其中最集中表現的就是 1957 年開始直到
「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滅教運動」。似乎間接論證了馬克思宗教觀的「鴉片論」。在這個論點的基礎上,我們去思考溫州人因各種運動而陷入信仰的真空狀態,基督徒卻在信仰壓迫中的堅忍,並願意為信仰付出代價,展示信仰的力量。因此,我們幾乎可以肯定,溫州教會的大復興不是在 1980 年之後,而是在此之前。6 在文章的討論中,我們還要述及溫州人「靈巧」
(曹南來:務實主義 7 )的個性在面對不同政治壓力時,其表現亦有不同,更因對信仰的忠貞程度而變得不同。
本書以現溫州市轄各市、區、縣為研究範圍,以溫州基督教(新教)為主要對象,並將時間限定在 1957 至 1979 年。但要給該時期取一個統一的名稱,似乎並不容易。筆者曾用「非常時期」、「特殊時期」來表述,但其實每個時期都有其特殊性,該名稱本身並不特殊。朱宇晶將這一時期稱為「極端社會主義時期」8 ,相較來說是合宜的,但社會主義時期的「極端」時段可能並不只是這一時期,所謂「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傳 1:9),更加極端的事情可能也會發生。正如朱宇晶所斷言,這一時期正是「滅教時期」,9 超過人們想像的是,「滅教」的運動卻催生了溫州基督教的大復興,成為「中國的耶路撒冷」。因此,我們將本書定名為《從「滅教」運動到「中國的耶路撒冷」的誕生》。
6 1980 年之後在人數眾多、教堂眾多、事工增多,卻伴隨著教會世俗化現象的產生,以致教會只是一種表面的復興,反而是另一種衰落。這並非本書涉及的範圍,不作詳細討論。
7 曹南來,《建設中國的耶路撒冷》,145。
8 朱宇晶,《國家統治、地方政治與溫州的基督教》(博士論文,香港中文大學,
2011),5。
9 朱宇晶,《國家統治、地方政治與溫州的基督教》,5。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選題意義
本課題研究是溫州教會史研究的一部分,在溫州教會 150多年歷史中佔有重要的一環,更是今日溫州教會許多現實問題的起點。若想對溫州教會的現狀作出更加客觀的評價,對該時期教會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不管是今日溫州教會所特有的義工為主的服侍團隊、拓展到各地的差傳事工等,或是教會內部各自為政的現象、教牧在教會中缺乏權威、教會鬆散不正規的管理制度、一度勢不兩立的「家庭」教會與「三自」教會的區分等現象,都可以追溯到這一時期的教會。
筆者在近 20 年的溫州教會史研究中,發現目前已有不少人開始重視對溫州教會史,特別是解放前的教會歷史研究,在與不少學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們也挖掘出不少歷史原典。但對於此「滅教時期」(1957-79) 教會歷史的研究尚處於初步階段,特別是該時期的研究成果,也是寥寥無幾。在現有的教會史資料裏,對於該時期的歷史,要不就是避而不談,要不就是一筆帶過。在僅有的一些回憶錄中,也只是一些親歷者主觀的歷史回顧。
因此,筆者認為對影響現時溫州教會極大的時期,需要進行一次較為客觀的研究,作為今日教會情況的一種追溯。
但,為什麼是溫州?這座華東浙南被包圍在眾山之間的城市,有什麼獨特的地方,值得成為海內外學界、教界所關注、研究?筆者同意建道神學院榮譽院長梁家麟博士提出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一種偏差,由於資源有限與史家求速成心切的緣故,在人物研究中都集中在幾位知識份子身上,他們包括趙紫宸、吳雷川、吳耀宗、徐寶謙、謝扶雅、王明道、倪柝聲等。這些人物之所以被優先關注,是因為他們的作品較多,資料掌
第一章
導論
引言
溫州教會從第一位傳教士到埠至今已逾 150 周年,其中所經歷的復興是有目共睹的。這也使溫州教會贏得各地教會的好評,甚至得到「中國的耶路撒冷」美譽。在已過的歷史中,溫州教會最為獨特且值得大書特書的,就是在 1957 年至 1979 年
間所經歷 20 多年的逼迫。在全國眾多教會都停止聚會,教堂被關閉的情況下,溫州教會甚至被列為「無宗教區」的試點城市。但溫州基督徒在如此惡劣環境之中不但沒有停止聚會,反而化整為零,在信徒的家中建立聚會點,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使教會得以進入百多年來最大的復興。僅 20 多年間,...
作者序
【梁序】
作為豐盛的論文指導老師,我理所當然是本書原稿的第一個讀者,在它的形成過程中有相當的參與。但從神碩到哲博,與豐盛同行多年,我很清楚我不是本書創發階段的參與者。豐盛在成為我的學生以前,已是一位歷史的愛好者,積極蒐集溫州教會的歷史材料,做口述訪問,並且已撰寫和出版了好些著述,從數量言不少於許多已拿博士學位的同行。所以,在與他偕行的這些年間,我一直提醒自己不過在做「來料加工」的角色,不是從無到有,毋須引起動機,更不是牽著他的手邁入一個全新領域;卻是幫助他更好掌握學術研究的遊戲規則,涉獵西方世界的研究成果;並強迫他抽離所已熟悉的溫州教會歷史的領域,更寬廣地認識一個宣教歷史乃至基督教會史的世界,在大圖畫裡尋定自己所站位置的座標。而我更知道,豐盛的研究所依據的,並非僅是他一人所曾做過的努力,更是有許多同行者,或說是一個流動的信仰和學術群體,所曾建立的一個尚在塑型的「道統/學統」。
從上世紀八、九○年代中國基督教的高速發展以來,溫州教會的種種突出表現,吸引了全球的中國觀察者和福音關懷者的注意,好些過去因不知內情而推定的歷史解說給推翻了。舉例說,即或政權壓迫兇猛,信徒得付出高昂的信仰成本,中國從未進入「無宗教時期」;在文革中後期的溫州,且曾經歷過數度教會的復興!這些給揭曉的事實刷新了我們的認知,讓我們不斷修訂既有的史本。海外的觀察者棄舊揚新,為他們所看到的新事實冠以新名稱,這便是本書的書名:「從滅教到中國的耶路撒冷」的來由。
不過,海外觀察者對中國的認知總不免有地理乃至文化距離的阻隔,並且跟觀察者的關懷甚或個人利益難以分割,他們下的結論常常是過於倉猝、籠統甚至偏頗。譬如說,在不到十年前,海外不少論者尚在高談中國教會將成為全球宣教最主要的力量、中國將成為下世紀的基督教王國;但在拆十字架事件發生,大量外來事工參與者被迫離華後,海外輿情便來個大翻轉,變得徹底悲觀、絕望,宣稱嚴冬已屆、文革重臨。這些論斷當然不乏事實佐證,但更多其實是論者對所參與的在華事工的命運的描述,過於對中國教會的命運的審斷。至少在筆者所接觸的國內牧者群體裡,他們雖有悲觀情緒,卻遠較海外觀察者積極。可以確定,中國教會仍在艱苦奮進中。
正是由於海外觀察者難以全面掌握真相,一些在溫州教會成長的本土信徒便毅然站出來,承擔考察風俗、採集傳說的田野史學工作者的職任,持定不虛美、不掩惡的治史立場,努力復原這個遺佚了的時代篇章,將眾多零碎的口述故事拼貼成較完整的文字記述。而更重要的是,這些立志治史者都是溫州教會的成員,甚多是認信者 (confessors) 的後代,也因此是這個仍然在延繼發展的活的傳統 (living tradition) 的部分;他們得以從局內者的角度,剔除神話,鑒定事實;重建現場,重尋初心;為溫州基督教會做名乎其實的「歷史沿革」。這不僅是對歷史真相的復原,不僅是對傳統的梳理俾能繼往開來,也是對上帝的心意和作為的神學詮釋。畢竟,作為信者,我們都認定中國基督教會的保存和復興是二十世紀上帝在人類歷史的一大神蹟作為。
豐盛是這個本土的「信者」和「學者」群體的其中一員,其他成員要非他的前輩便是朋輩,他在書中序言已有提到這些名字。他們沒有正式組織或緊密的關係,卻是流動的信仰(強調信仰是必須的)和學術群體。筆者認識他們中間泰半成員,對他們除了欽佩還是欽佩,期待他們以溫州教會為切入點,為我們揭開這個「從外來宗教到本土宗教」的激烈轉化的一頁歷史。在其中,「復原主義」(Restorationism) 與「還原主義」(Reductionism) 這兩個筆者在討論本色化的課題時常用的詞彙,變得不再是高談闊論的虛詞,而是有血有肉的呈現。當然,要全面復原中國當代基督教的面貌,除了溫州外,還得對河南、安徽、福建??等地進行相同規模的考察和採集。任重道遠,豐盛與各位年輕的治史者,要走的路仍長。
我自己也是以「信者」和「學者」這雙重身分,與豐盛偕行。這兩個身分肯定是互相補益的,但間中不免有抵觸處。無論如何,指導研究生於我不單是一個學術活動,更是信心行動和信仰實踐。因此,目睹豐盛的論文付梓,見證他一步步顯露德、才、學、識;我得盡力壓抑心中難禁的驕傲自豪,懇摯地表達對上帝的敬畏和尊奉。祂不僅在現場塑造歷史,也在所興起的年輕治史者中豁現祂的「天命」(providence)。
梁家麟 敬序
香港建道神學院榮休院長,義大利華人神學院院長
2023年3月10日
【劉序】
陳豐盛牧師新著《從「滅教」運動到「中國的耶路撒冷」的誕生》論述溫州教會在「滅教」時期(1957-1979年),教會如何從「地上」走到「地下」,其後信徒人數從十萬增加到三十多萬!
陳牧師把溫州教會被稱為「中國的耶路撒冷」的源起上溯到1957至1979年「滅教」時期,即溫州以至中國教會被認為處於「斷層」的時期,溫州更被作為「無宗教信仰地區」試點。表面上看,基督教在溫州彷彿已經被「滅掉」了。然而,作者以大量史料和訪談記錄鏗鏘有力地指出:溫州教會不但沒有被消滅,而相反地持續成長。溫州教會「化整為零」,信徒持續敬拜上帝和舉行團契等。聚會地點從教堂轉到巷子下和郊野、荒嶺等僻靜隱密處,並且逐漸發展出家庭聚會。其間,儘管「無教堂、無教牧、無聖經」,溫州信徒卻在宗教逼迫中堅守信仰立場。年青人和婦女等平信徒在富牧養經驗的教牧幫助下,既保存了教會、散播福音種子,而且薪火相傳、教會興旺!
「文革」時溫州教會「以義工為領袖、教牧專注牧養」方式演變出「以義工為主、教牧為輔」的管理模式。「老闆基督徒」人數逐漸增加,終而發展出「僱工式教牧」形態—教會乃產生特有溫州管理模式的「牧區制」。
「滅教運動催生溫州基督教大復興,成為『中國的耶路撒冷』。」教會走過「死蔭的幽谷」,信徒在幽谷中尋找到生存途徑。1979年國家走出「十年浩劫文革」深淵再度迎來「改革開放」,溫州教會從「地下」回返到「地面」,其時信徒人數竟已然倍增。誠如作者所言:「溫州教會不是在政策便利、差會資助、經濟騰飛的背景下復興;而是在『滅教』運動的極端環境中所催生」。
1957至1979年「滅教」時期的溫州教會經歷,印證了陳韋安牧師一次培靈信息的主題:「教會就是你們??否則甚麼也不是」。陳牧師指出:「基督是教會不可動搖的根基,無論面對多少內憂外患,教會亦不會沒落。教會是建基於基督之上,上帝是教會的『不變數』(constant),教會的本質是上帝的恩典。」主耶穌基督是教會(弟兄姊妹聚集而成)的根基所在!他鼓勵弟兄姊妹在困厄時候「可以先聚集在一起,維持教會的存在;因為『你們就是神的殿;這殿就是你們。』(林前3:16)」。他勸勉信徒:「只要你肯繼續存在,教會就有未來。」陳牧師強調:「教會是恩典誕生的地方,教會的本質是上帝的恩典。」他呼籲年輕信徒和心境年輕的弟兄姊妹要注目於未來的教會—「教會是一個未來的概念」。
陳豐盛牧師長期從事浙江溫州教會歷史研究。他一面牧會、一面教授神學和著述,敬業樂業;並已先後有《詩化人生—劉廷芳博士生平逸事》、《溫州基督教編年史》和《近代溫州基督教史(上、下)》等多種專書問世。本書建立在堅實歷史文獻材料包括政府檔案、會議記錄、期刊、報章和回憶錄等,加上從採訪近百位「滅教」時期親歷者的口述訪談記錄。陳牧師致力於拓寬學術視野,把握機會和國際學者對話、交流。要旨出眾:他從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及其發展史的角度和觀點出發,為教會和學界能深入、全面認識中國教會歷史作出了獨特貢獻。
2009年筆者和陳豐盛牧師初識於建道神學院,當時在何義思臺憑欄交談良久。其後在建道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有更多機會交流,我們談到陳牧師的牧會、學術研究等等。迄2021年前後十二年間牧師先後完成教牧學碩士、神學碩士和哲學博士三個學位課程。他在攻讀神碩和哲博期間和畢業後來香港時我們都會見面(最近一次在2023年3月),每次都有美好的交通。感謝神!
本書作者勉勵大家:「宗教政策再度左轉的今天,基督徒無需過分憂慮、疑惑,反而要從十架神學的角度去面對即將(或已經)到來的壓力、逼迫,並學效前人的堅韌信仰立場,靈活轉型,迎接下輪教會的復興。」「中國耶路撒冷」之所以促使筆者想起使徒保羅寫給羅馬信徒書信中的話:「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迫害嗎?是飢餓嗎?是赤身露體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如經上所記:『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我們已經得勝有餘了。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權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深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們與上帝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裏的。」(羅8:35-39)其中原因乃是溫州教會在中國大陸「滅教」時期的處境和保羅的話先後呼應。誠然,沒有任何人、事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靠著神的愛,我們將會得勝有餘!
陳豐盛牧師是一位學人牧者。他牧養教會同時以紮實厚積的研究心得和學術才華,撰述中國特別是其家鄉浙江省溫州市教會歷史。二十多年孜孜不倦,筆耕不輟。祝福牧師在牧養兼著述侍奉路上繼續蒙神使用、不斷經歷神的厚恩!阿們!
劉義章 敬撰
於香港 沙田
主曆2023年4月29日
【梁序】
作為豐盛的論文指導老師,我理所當然是本書原稿的第一個讀者,在它的形成過程中有相當的參與。但從神碩到哲博,與豐盛同行多年,我很清楚我不是本書創發階段的參與者。豐盛在成為我的學生以前,已是一位歷史的愛好者,積極蒐集溫州教會的歷史材料,做口述訪問,並且已撰寫和出版了好些著述,從數量言不少於許多已拿博士學位的同行。所以,在與他偕行的這些年間,我一直提醒自己不過在做「來料加工」的角色,不是從無到有,毋須引起動機,更不是牽著他的手邁入一個全新領域;卻是幫助他更好掌握學術研究的遊戲規則,涉獵西方...
目錄
總序 v
梁序 xi
劉序 xv
吳序 xix
第一章 導論 1
引言 1
第一節 題目與問題探討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選題意義 6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概念界定 9
第四節 研究綜述 14
第五節 研究進路與限制 19
第六節 各章簡介 19
第二章 歷史緣起:溫州基督教的起源與發展 (1867-1957) 23
第一節 福音傳入與溫州傳統文化的交匯 (1867-1910) 26
一、溫州地域特徵與人文精神 26
二、福音初入溫州—「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
第二節 民族主義意識與自立運動的發展 (1911-1949) 37
一、溫州教會的自立思想與嘗試 38
二、溫州教會的三次分裂事件 43
第三節 三自革新運動與溫州教會路向的選擇 (1950-1957) 51
一、溫州教會在中外交接過程中徘徊前行 52
二、「慢半拍」的溫州基督教三自革新運動 56
三、循道公會主導的三自革新運動 65
四、三自革新運動中突起的教會領袖 70
五、 始終不被政府肯定的溫州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 80
第四節 本章小結 87
第三章 滅頂之災:社會主義改造策動的聯合禮拜與「滅教」運動 91
第一節 「無宗教區試點」與聯合禮拜 92
一、誰提出「無宗教區」的概念? 92
二、無宗教區與反右運動、聯合禮拜、大躍進的關係 96
三、聯合禮拜是教會發展中的創舉嗎? 97
四、為什麼是溫州?為什麼是平陽? 98
第二節 反右運動及中共宗教政策的曲折發展 100
第三節 「無宗教區」的前奏:反右運動、大躍進 113
一、溫州教會在反右運動中 113
二、「大躍進」催生的聯合禮拜 119
第四節 「無宗教區」試點的具體實施 128
一、在平陽和瑞安實行的三次「鬥爭試點」 128
二、宗教工作現場會議 134
三、全面「滅教」的實例:永嘉縣宗教界整風學習 142
第五節 在「無宗教區」的教會 150
一、教牧人員的遭遇 150
二、 三自的名存實亡—「滅教」趨勢下的「餘種」 157
三、黑暗中的光—家庭秘密聚會的萌芽 165
第六節 本章小結 178
第四章 轉型升級:「文革」前期家庭聚會 (1966-1971) 185
第一節 「文革」前期中共的宗教政策與中國基督教狀況 187
一、「文革」前期中共的宗教政策 187
二、中國基督教狀況 193
第二節 「文革」中溫州教牧與「三自會」的遭遇 200
一、「三無」時期「三自會」的消亡 201
二、「頑固份子」的培靈與「門徒」訓練 208
第三節 「無政府主義」下的教會生活 222
一、「無政府主義」下的相對自由 222
二、家庭聚會的隱密活動 226
三、「三無」時期的勇士—義工模式的發展 245
第四節 本章小結 255
第五章 建制復興:「文革」後期的聯合與復興 (1971-1976) 263
第一節 中美關係背景下的中國基督教 265
一、從中美對話至林彪、「四人幫」垮臺 266
二、三自領袖的復出 269
三、家庭聚會的復興 272
第二節 溫州教會牧區與縣總會的雛形 276
一、聯合禮拜 276
二、禮儀統一 278
三、聯合派單 279
四、縣總會雛形 281
第三節 溫州地區總會的建立 284
一、溫州地區交通會第一次會議 284
二、溫州區「大議會」的情況 287
三、遊走傳道人的遭遇 289
第四節 靈恩運動與神蹟奇事 293
一、三自運動中被打壓的「神蹟奇事」 293
二、教會中廣為流傳的信仰見證 295
三、溫州各地興起的靈恩現象 299
四、溫州教牧對靈恩與神蹟的解讀 302
第五節 教派分歧與神學爭論 306
一、與聚會處蒙頭的紛爭 307
二、與安息日(會)相關的紛爭 311
三、關於得救問題的爭辯 315
第六節 文字事工的興起 318
一、「謄寫」印刷工序 319
二、幾位「謄寫」印刷的傳道人 320
三、一本特殊的讚美詩集 323
第七節 外展事工的開展 324
第八節 本章小結 327
第六章 分道揚鑣:黎明前的等待與路向選擇 331
第一節 後毛時代宗教政策的轉向與中國教會復蘇前兆 332
一、宗教政策的轉向 332
二、中國基督教領袖的動向 338
第二節 溫州家庭聚會的規模與建制 340
一、規模與建制 340
二、逼迫與等待 345
第三節 溫州教會的領袖與派系 348
第四節 「三自會」復出的前兆與路向 355
第五節 本章小結 361
第七章 結論:「中國的耶路撒冷」 365
第一節 溫州教會歷史上的「三變」 366
一、在政治變局中「應變」 366
二、在信仰逼迫中「裂變」 368
三、在時代夾縫中「蛻變」 369
第二節 溫州教會中的「十多」現象 370
一、教牧人員多 371
二、義工領袖多 371
三、婦女領袖多 371
四、青年傳道多 372
五、信仰逼迫多 372
六、家庭聚會多 373
七、合一見證多 373
八、神蹟奇事多 374
九、信徒人數多 374
十、福音拓展多 375
第三節 教會「溫州模式」中的「四挑戰」 376
一、 權威挑戰:義工領袖興起與教牧權威危機的負面影響 376
二、 制度張力:牧區制度與三自體制的制衡 378
三、 信任危機:「文革」中的教牧領袖與三自領袖間的異同 381
四、 發展局限:「各自為政」現象造成「小作坊」式的教會現象 383
致謝 387
參考書目 391
總序 v
梁序 xi
劉序 xv
吳序 xix
第一章 導論 1
引言 1
第一節 題目與問題探討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選題意義 6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概念界定 9
第四節 研究綜述 14
第五節 研究進路與限制 19
第六節 各章簡介 19
第二章 歷史緣起:溫州基督教的起源與發展 (1867-1957) 23
第一節 福音傳入與溫州傳統文化的交匯 (1867-1910) 26
一、溫州地域特徵與人文精神 26
二、福音初入溫州—「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
第二節 民族主義意識與自立運動的發展 (1911-1949) 37
一、溫州教會的自立思想與嘗試 38
二、溫州教會的三次分裂事件 4...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