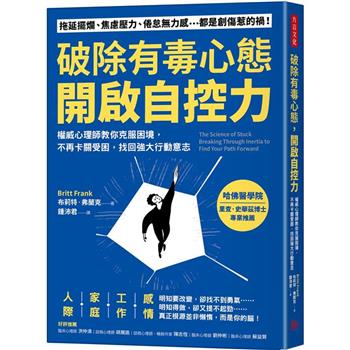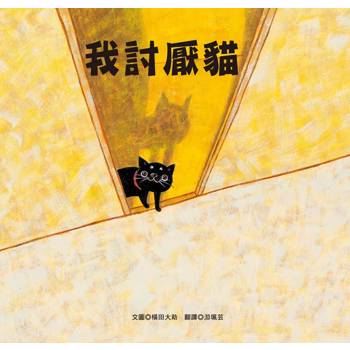新冠肺炎:一個疾病、科技與社會共同生產的故事
陳嘉新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自2019年末出現。行文此時,這個全球流行病的確診數已經超過兩億人,死亡人數達到437萬人。疫情對於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活動的影響,更是難以估計。台灣5月19日因為本土案例增加而提升為三級警戒,在7月27日因為疫情穩定,又調降警戒層級到第二級,目前累積的感染人數也接近16,000人。整體來說,台灣仍是國際各國防疫相對成功的範例;但是作為世界村的一員,也難自外於疫情下的鉅變,而必須採用特殊經濟刺激,例如三倍券乃至於五倍券。
本文試圖描繪與定位台灣在過去這一年餘,面對COVID-19所產生的社會意識轉變,並且將這個轉變連結到因應感染而生的科學知識與防疫技術,以深化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長久以來堅定宣稱的論點,也就是「科技與社會的共同生產」。這個論點主張當代社會與科學技術之間有著相互穿透、相互構成,因而共同演化的關係。
這個概念的重要推手是哈佛大學的嘉森諾夫教授。她編輯的論文集States of Knowledge則是陳述這個概念的重要論著。嘉森諾夫教授於該書她自撰的章節〈給知識一個秩序,給社會一個秩序〉裡面,提到2001年美國紐約遭逢的911恐怖攻擊給予世人(尤其是美國人)的重大心理打擊。她在這個事件中看到了全球化或者工業社會的異質組成與歧異路線,看到了權力與政治的動力關係無法自外於科技化的潮流,也看到了一個現象:科學也好、技術也罷,在當下的社會中都成為了政治的作用者。
嘉森諾夫將近二十年前的宣示如今看來可能並不那麼令人意外,畢竟我們不能否認某些科技物的確深遠地影響了社會的組成與秩序,例如:網際網路既可能串連起恐怖分子的活動,也可能激發起茉莉花革命的火種。影像辨識系統在治安案件的發生時,讓警方得以憑藉影像紀錄追查犯罪人;但同樣的影像辨識系統也可能挪用成為社會監控的體制,讓個人隱私無所遁形。在醫療方面,基因檢測容許某些人得以計算自身的未來罹病風險,因而得以及早預防或者介入處理;但是基因檢測也可能模糊了合理治療的定義與空間,產生保險給付範圍的爭議以及病人身分的界定困難。
當前社會中,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創新科技挑戰了社會組成與秩序的認知,衝擊了道德標準與倫理原則的概念,也顛覆了公民身分與國際政治的架構。但同時我們也注意到特定政體運用資通科技如顏面辨識與社會信用作為治理工具,商業巨擘對於個人隱私的蒐集、利用與商品化,或者是民眾挪用或者轉用既有的科技實踐他們心目中的理想民主,並打造一個值得期待的生活環境。當科技改變了社會與政治面貌的同時,社會與民眾也努力地讓科技為其所用,並引領著科技的發展方向與應用可能。
然而在新冠肺炎來臨且肆虐全球之後,我們看到了更為複雜的科技與社會的互動現象,因為在這兩個面向之上,還加上了疾病這個因子。一個人類史上前所未見的病毒,產生一連串國際的疾病傳染鏈,急速累積的病患數量迅速崩解了反應不及、容量不夠的醫療體系,導致因此感染或者其他疾病死亡的人數大量增加的慘狀。這個病毒引發的不僅是醫療衛生體系的危機,同時也突顯了世界村裡面各國貧富不均、資源分布不對稱、科技發展程度不一致的現實阻礙。這個阻礙不僅是種比喻,也是事實。以防疫與安全為名,各國實施了或強或弱的國境封鎖,但這些舉措卻實際地阻止了人群的跨地移動,也連帶地阻礙(雖然並未終止)了許多社會互動的面向。
要說我們因為這個疫病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很多人都會同意;但要說這個「新的時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恐怕表示同意的人也很難具體說明。不過,要辨識這個新常態有著明顯的科技刻痕,應該對所有局中人都不困難。當下全世界正熱烈施打與爭議的疫苗,不正是一個被認為即將改變社會秩序的科技產品?而這個科技產品不也正是過去一年多不同國家、科學家與藥廠聯手打造的疫情解決之道?解決疫情並不表示恢復社會原有秩序,毋寧是建立了一個更新的經濟、政治、文化、道德的全球體制;而且疫苗作為解方,也同時生產了新的問題:疫苗的健康不良反應、產量不足、分配不均、審查程序有爭議等等。新的科技與新的社會,此時正在眾人眼前成形。所謂科技與社會的共同生產,不正是這個意思嗎?
一、由口罩到疫苗:外來與內生的防禦措施
本文不擬使用深奧的學術語言或者理論鋪陳,而是希望用淺顯易懂的語言與實際可見的現象說明,讓讀者能夠進入這個共同生產論點的具體呈現。
首先要提出的是由口罩到疫苗的這個轉變。
2020年1月,新冠肺炎開始傳入台灣。由於過往SARS的經驗,台灣人很迅速地搶購口罩。一時間,口罩就缺貨了。政府迅速地中止口罩出口,並且成立所謂的「口罩國家隊」,極力提高醫療用口罩的生產量,以滿足國人所需。一開始口罩仍需維持數量管制,但是隨著邊境管制奏效,本土感染也獲得控制之後,公私部門合作生產而追上來的口罩數量就開始過剩。口罩價格大幅下降,各通路如藥局、賣場的盒裝口罩則是立成一垛垛地等人購買,之前上架隨即搶購一空甚至需要限制購買的情景已不復見。
相對應的,則是對於疫苗的關注逐漸上升。隨著媒體的推波助瀾,疫苗的議題逐漸升溫:台灣會取得疫苗嗎?台灣做得出自己的疫苗嗎?台灣會有哪種疫苗可以打?打了以後就可以減少居家檢疫的時間嗎?打了以後,台灣就可以恢復原先出入國境的規定嗎?要多少比例的民眾打才能夠恢復這樣的秩序?疫苗安全嗎?疫苗有實際的保護力嗎?疫苗有不可預知的副作用嗎?疫苗的利弊得失要怎麼分析呢?或者是更貼近自身的問題:我該打疫苗嗎?我甚麼時候應該/可以打?
這些問題以不同的方式與語氣在中央疫情中心的記者會與街頭巷尾的民眾閒聊中出現。如果說2020年的防疫焦點在口罩,2021年的防疫焦點顯然已經轉移到疫苗。
如果我們思考這個由口罩到疫苗的防疫重心轉折,我們可以看見一些個人化措施與集體性作為,是如何重複著這種由外部防禦到內部抵抗的變遷。口罩配戴在個人身體之外,用物理性、非特定性的方式阻斷病原體進入人體,除了減少新冠肺炎感染,也可以減少其他飛沫傳染。這是去年(2020)流行性感冒個案數大幅減少的一大原因。
同樣的,在集體人群的層次上面,台灣也採取了類似口罩原理的防堵措施,也就是有效的邊境管制,即針對入境旅客進行入境限制或密切管理等措施。隨著檢驗技術與量能的改善,這些入境者也同時加上了密集的檢驗,以期將所有可能的感染個案都阻絕於外,就像是口罩內外多層的防護措施。隨著科技的更新與檢測量能的提升,這種非特定式的阻絕防疫措施也可以發展成為較為細膩的、具有內部差別性的管制作為(例如區隔出不同風險層級的國家或者不同職業別如機師而為的防疫規範)。
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苗的研發與分配成為一場全世界的競爭賽。人類有史以來,從來沒有在這麼短的時間研發出一個病原體的疫苗。過往的疫苗開發往往是以年甚至是十年作為計算的基期;但是新冠肺炎疫苗的開發與生產,卻是以月作為計算單位的。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擠出Moderna、Pfizer-BNT、Janssen、AstraZeneca(AZ)等等好幾種疫苗產品,其實是生物科技相關的既有基礎建設加上全球科學、國家與產業社群集體合作的結果。疫情之初,對於這個新型冠狀病毒的遺傳結構就開始在網路的病毒遺傳碼分享平台流傳。過去禽流感時期偶而會出現的病毒主權(viral sovereignty)宣稱,也就是國家宣稱病毒基因碼屬於「該國的」,因而禁止跟其他國家分享;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則沒有這種情況。整體而言,我們看到的更多是病毒科學家群策群力,分享資訊。在網路與資料庫做為基礎建設的前提下,大家分享訊息因而變得簡單方便許多,也更容易比對不同病毒株在基因序列的親疏遠近關係,藉此判斷感染途徑與變異類型。在此同時,醞釀超過十年的mRNA疫苗科技,也首次得以在新冠肺炎這個RNA病毒感染上施展身手。
生技產業的全力研發、國家經費的大膽挹注、甚至是群眾自發性的參與疫苗臨床試驗,都使得這些產品能夠盡快地完成臨床試驗資料,以符合各國食品藥物管理署(或者相當機關)的審查所需。然後是政府體制的流程配合,得以允許疫苗的緊急使用授權(EUA)。當疫苗生產之後,則有多個國際組織合作組成的「新冠肺炎疫苗全球取得計畫」(COVAX)協助疫苗在不同國家之間的分配,促使這項難得的生技產品與防疫利器得以合宜地配送到不同國家,以符合全球正義公平的救濟原則。尤其是那些低資源的貧窮國家,更需要這種國際組織的協調分配以確保自身不會在這場全球浩劫中受傷更深。至於疫苗配送過程當中的冷鍊設置、配送條件與數量的確保,這些則考驗了各國的技術能力與行政效率。
回到防疫意義來看,疫苗跟前述的口罩顯然不同。相較於口罩的非特定性保護功能,疫苗則是特定針對某種病原體的防護機制:水痘疫苗不會讓我們對麻疹免疫,B型肝炎疫苗也無法防範A型肝炎感染。而且疫苗激發的是自身產生的抗體與細胞免疫,所謂防疫力乃是一種源於自己體內的基本生理力量,而非外加於身體的盾牌保護。這種特定性與內源性的特質,使得疫苗的防疫機制大異於口罩非特定性與外加性的特色。
換言之,注射新冠肺炎疫苗,在防疫上的意義在於讓抗拒病原的基本作戰單位回歸個人,但此處所謂的「個人」也蘊含了集體性。因為夠多的「個人」接受疫苗注射後,理想上就會達成「群體」免疫,傳染途徑將因為較多具有免疫力量的個體而產生傳播鏈上的斷點,容易停止在群體中散布。也就是個人接種疫苗這件事本身,就是促成免疫整體的手段。
總結來看,由2020年的口罩熱潮到2021年當下的疫苗關注,我們看到的是防疫焦點的轉變。在起初的低技術性、非特定性、外加式的阻隔手法外,又加上了高技術性、專一特定性、內源性的抵抗力。防疫焦點的轉變,不僅改變了民眾對於防疫措施關心的焦點,也提示了科技與社會兩者密切的彼此糾結對於個人與群體在心態與行為上的深遠影響。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陶逸駿的圖書 |
 |
$ 198 ~ 360 | 思想 44: 記疫共同體
作者:李尚仁/劉紹華/李建良/王長江/姚新勇/鄭家棟/陶逸駿/陳純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01-27  共 8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8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記疫共同體(思想44)
本期的專輯是「記疫共同體」,收錄7篇論文,2019「COVID-19」的出現,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這個給全世界人類帶來巨大且深刻影響的瘟疫,隨著疫情從中國大陸傳到歐洲、美洲乃至全世界,徹底改變了人們的集體與個人的生命樣態,從政治、經濟、社會、法律、文化、教育、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乃至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互動,無一不受影響。所帶來的衝擊深刻而全面,已遠遠超過醫學或公共衛生等領域。本期還有數篇獨立論文,探討政治視域下的中國知識分子問題、抽象的歷史反思與失焦的現實批判等。
作者簡介:
編者
思想編輯委員會
本書作者
王長江(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資深研究員)
忽思慧(史學工作者,哈紮爾學會編輯,撰稿人)
李舵(博士生)
鄭家棟(多倫多大學訪問教授、「亞洲神學」中心研究員)
汪宏倫(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林文源(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李尚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劉紹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
陳嘉新(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李建良(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林宗弘(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陶逸駿(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姚新勇(廣州華商學院教授)
陳純(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博士)
章節試閱
新冠肺炎:一個疾病、科技與社會共同生產的故事
陳嘉新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自2019年末出現。行文此時,這個全球流行病的確診數已經超過兩億人,死亡人數達到437萬人。疫情對於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活動的影響,更是難以估計。台灣5月19日因為本土案例增加而提升為三級警戒,在7月27日因為疫情穩定,又調降警戒層級到第二級,目前累積的感染人數也接近16,000人。整體來說,台灣仍是國際各國防疫相對成功的範例;但是作為世界村的一員,也難自外於疫情下的鉅變,而必須採用特殊經濟刺激,例如三倍券乃至於五倍券。
本文試圖描繪與定位台灣...
陳嘉新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自2019年末出現。行文此時,這個全球流行病的確診數已經超過兩億人,死亡人數達到437萬人。疫情對於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活動的影響,更是難以估計。台灣5月19日因為本土案例增加而提升為三級警戒,在7月27日因為疫情穩定,又調降警戒層級到第二級,目前累積的感染人數也接近16,000人。整體來說,台灣仍是國際各國防疫相對成功的範例;但是作為世界村的一員,也難自外於疫情下的鉅變,而必須採用特殊經濟刺激,例如三倍券乃至於五倍券。
本文試圖描繪與定位台灣...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致讀者
本期《思想》出刊之時,全世界陷在新冠病毒的籠罩之下已經滿兩年。疫情對各個社會的衝擊方式以及幅度不一,但是其影響是全面的,並且很可能相當持久,即使疫情有消退之日,人類的生活與互動方式也將不同於以往。
本刊在前年曾經發表台灣大學高等研究院組織的一次論壇集稿,作為41期《新冠啟示錄》的專輯,對疫情的整體意義從不同學科進行了探討。隨著疫情進入第二年,清華大學社會所林文源教授主持的「記疫」網站上積累的資料與文獻更形可觀,經本刊編委汪宏倫教授倡議,邀請參與網站「對話」活動的幾位學者撰稿,再次針對covid-...
本期《思想》出刊之時,全世界陷在新冠病毒的籠罩之下已經滿兩年。疫情對各個社會的衝擊方式以及幅度不一,但是其影響是全面的,並且很可能相當持久,即使疫情有消退之日,人類的生活與互動方式也將不同於以往。
本刊在前年曾經發表台灣大學高等研究院組織的一次論壇集稿,作為41期《新冠啟示錄》的專輯,對疫情的整體意義從不同學科進行了探討。隨著疫情進入第二年,清華大學社會所林文源教授主持的「記疫」網站上積累的資料與文獻更形可觀,經本刊編委汪宏倫教授倡議,邀請參與網站「對話」活動的幾位學者撰稿,再次針對covid-...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政治視域下的中國知識分子問題(王長江)
中國社會主義與「清真」飲食(忽思慧、李舵)
牟宗三.海德格爾.傳統儒家(鄭家棟)
記疫共同體
記疫共同體:解題(汪宏倫)
「記疫」:朝向公共化的在地認識論(林文源)
疫情的個人書寫:事件、時間與歷史(李尚仁)
記錄歷史的伏流:網路時代中的疫情見證與反思(劉紹華)
新冠肺炎:一個疾病、科技與社會共同生產的故事(陳嘉新)
疫情社會的民主、法治與人權:若干反思性批判(李建良)
台灣新冠肺炎疫情的風險治理初探:歷史機遇、暴露度、脆弱度與韌性(林宗弘)
思想評論
新...
中國社會主義與「清真」飲食(忽思慧、李舵)
牟宗三.海德格爾.傳統儒家(鄭家棟)
記疫共同體
記疫共同體:解題(汪宏倫)
「記疫」:朝向公共化的在地認識論(林文源)
疫情的個人書寫:事件、時間與歷史(李尚仁)
記錄歷史的伏流:網路時代中的疫情見證與反思(劉紹華)
新冠肺炎:一個疾病、科技與社會共同生產的故事(陳嘉新)
疫情社會的民主、法治與人權:若干反思性批判(李建良)
台灣新冠肺炎疫情的風險治理初探:歷史機遇、暴露度、脆弱度與韌性(林宗弘)
思想評論
新...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