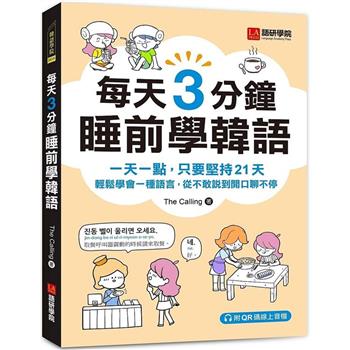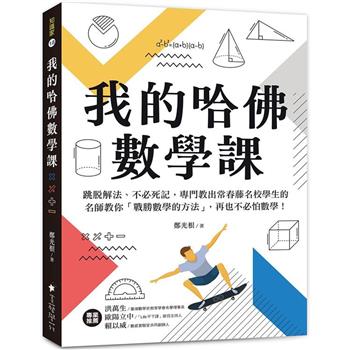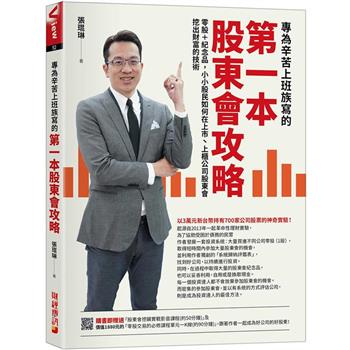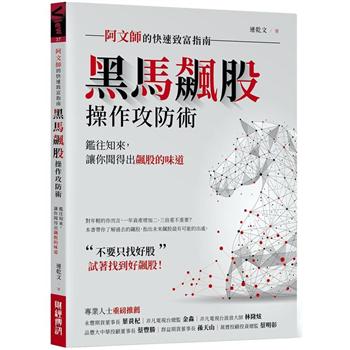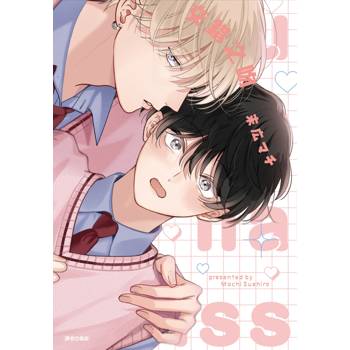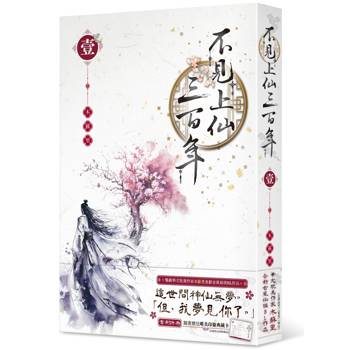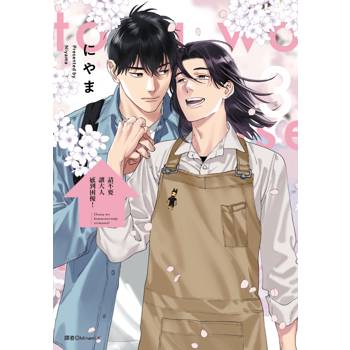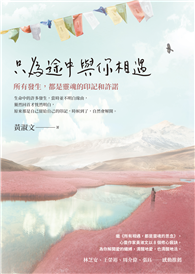《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作者 磨礪十八年又一力作
繼《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之後,陸鍵東先生從1998年構思本著開始,查閱大量稀見文獻,訪談眾多親歷者,長年積累,蘊藉深厚,以十八年之磨礪,使本書成為又一部反映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扛鼎之作。
董每戡(1907—1980),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戲劇研究的著名學者,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1978年「摘帽」,1980年去世。
本書展現了1956年至1980年董先生最後二十四年的浮沉。董先生淪為右派後沉淪底層二十年,卻仍埋頭著述,創造了豐富的學術財富,成為那個年代一個罕見的例子。董先生的際遇,折射了1957年後一代士人,他們對民族的忠誠與高尚的人格。
本書不僅是董先生的傳記,而且還以他個人經歷為主線,帶出了一個與其息息相關的知識分子群體,反映出這一群人的分化、以及三十年間中國社會裂變的內在脈絡。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