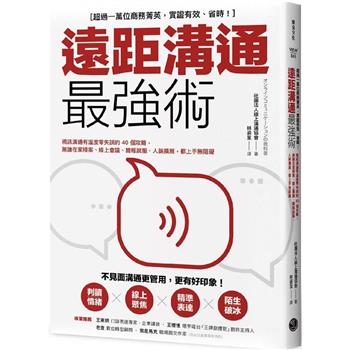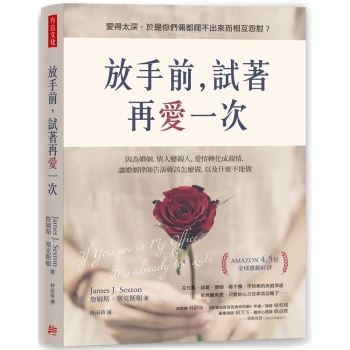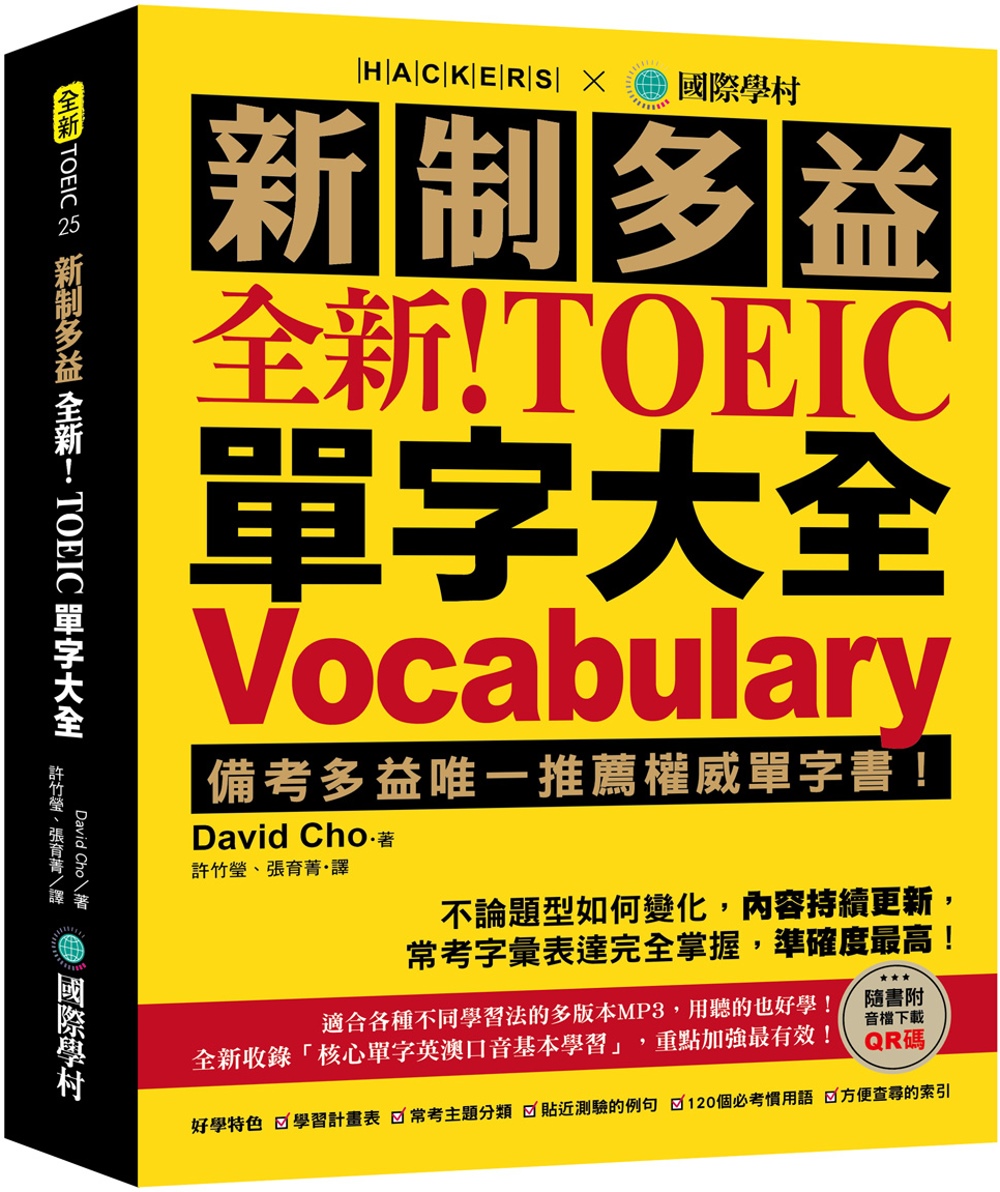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2 項符合
雨果.威爾肯的圖書 |
 |
$ 840 ~ 1008 | 聆聽歲月之聲(三冊套書):大衛.鮑伊+披頭四+麥可.傑克森【隨書附贈3款巨星票卡貼】
作者:雨果.威爾肯(Hugo Wilcken,Steve Matteo,Susan Fast) / 譯者:楊久穎 出版社:潮浪文化 出版日期:2025-01-08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720頁 / 12.8 x 19 x 4.8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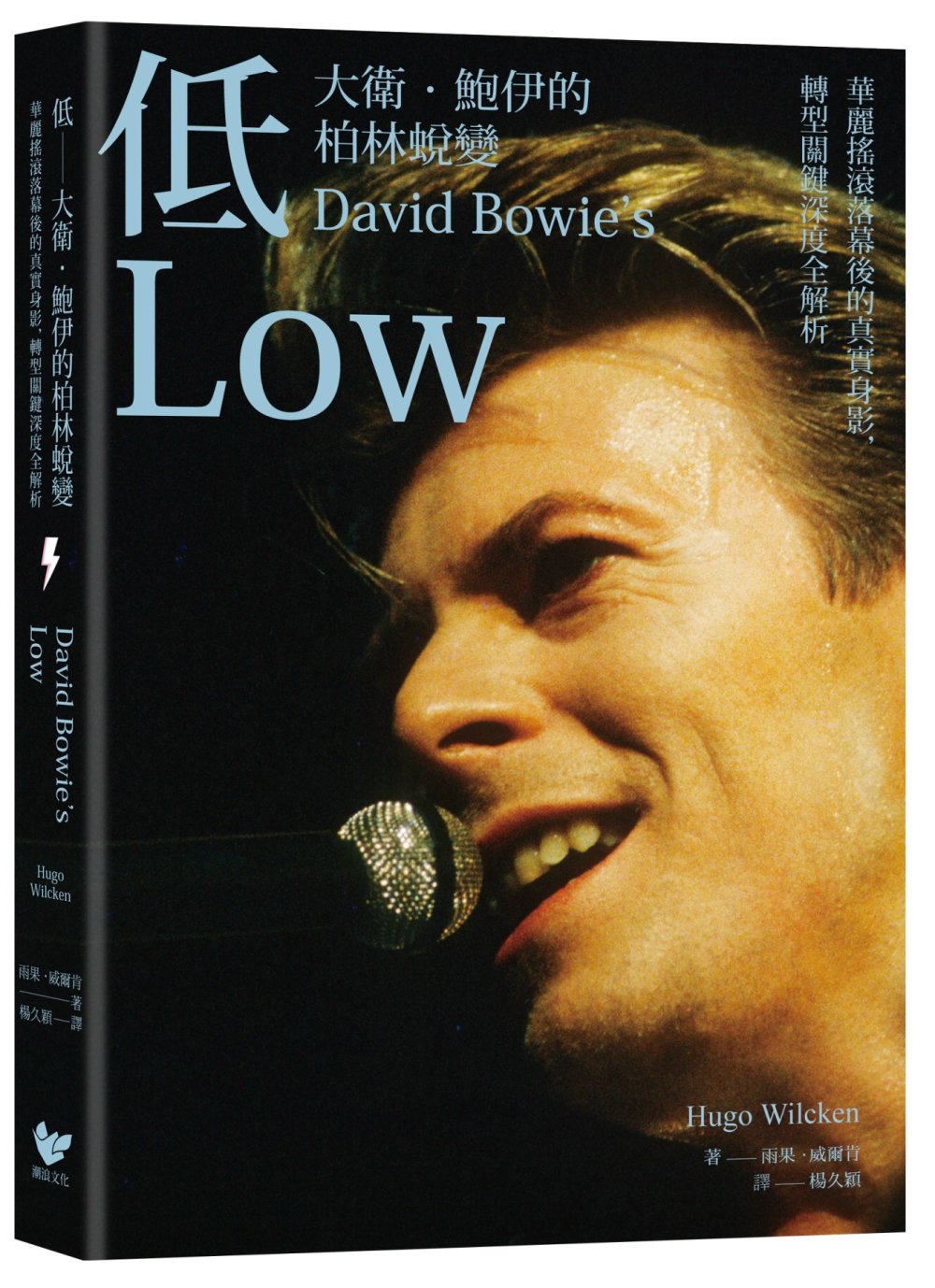 |
$ 210 ~ 324 | 低——大衛.鮑伊的柏林蛻變:華麗搖滾落幕後的真實身影,轉型關鍵時期深度全解析(台灣版獨家收錄大衛.鮑伊柏林時期珍貴剪影)
作者:雨果.威爾肯(Hugo Wilcken) / 譯者:楊久穎 出版社:潮浪文化 出版日期:2022-09-07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40頁 / 12.8 x 19 x 1.6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9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9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威爾
|
 小威廉·詹姆斯·亞當斯,藝名威廉,是一名美國饒舌歌手、歌手、詞曲作家、音樂製作人及演員。美國嘻哈音樂團體黑眼豆豆的創辦者之一,也是該團體現任成員。
小威廉·詹姆斯·亞當斯,藝名威廉,是一名美國饒舌歌手、歌手、詞曲作家、音樂製作人及演員。美國嘻哈音樂團體黑眼豆豆的創辦者之一,也是該團體現任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