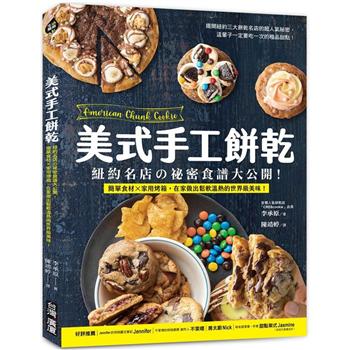導論:西藏的神鬼
西藏神鬼的系統、定位龐雜紊亂,佛教各派說法不一,尤其佛教和本教更是針鋒相對。在某種文獻的說法,可能被某一教派承認,卻又被另一教派否認,更何況各地方的神靈譜系也不盡一致。因此,我在此僅僅是以一個普通西藏人的視角,介紹我自己從生活中所認識或理解的西藏神鬼系統。由於源自個人親身的鄉土生活體驗,談不上權威,甚至我的認知內容不一定有文字依據。但至少期望我的敘述有助於對西藏文化陌生的中文讀者瞭解西藏神鬼的脈絡。
(1)
一般而言,西藏人祈求神靈保佑的時候,除了佛法僧三寶、還會有本尊﹙ཡི་དམ།﹚、護法神﹙ཆོས་སྐྱོང་།﹚、保護神﹙སྲུང་མ།﹚、地方神﹙ཡུལ་ལྷ།﹚、山神﹙གཞི་བདག﹚等不同的神靈。其中本尊和護法神是佛教特有的神靈,其他則是西藏本土神靈。佛教徒認為這些西藏本土的神靈已經被高僧大德降伏而成了佛教的護法神;本教徒則不認同這種說法。因此,同一個神靈,佛、本都信,但各有不同的解釋。
西藏傳統的信仰現通稱為本教。和其他宗教一樣,對世界的認知也是天上、地面、地下的三界觀,神靈也相應地分為拉(ལྷ)、贊(བཙན)、念(གཉན)、魯(ཀླུ)等體系。
其中,「拉」就是藏語中「神」的意思,在三界觀的系譜中,其位置一直都是在天上,拉,即天神,天神似乎是統治階層專屬的神靈,常出現在王室介紹或封誥石碑中,西藏歷史上的贊普就被認為是天神(ལྷ)下凡為人主。一般尋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天神屬於遠在天邊,難於企及的神靈。此外,「拉」也是所有神靈的泛稱,如對「念神」、「贊神」稱為「念拉」、「贊拉」等。
「贊」(བཙན།)神,屬於一種在天地間飄浮不定的神鬼,很多贊神後來都成為西藏的戰神或護法神。如寧瑪派的主要護法神孜烏瑪波,就是一種贊神。此外,傳說認為兇死者的魂魄也會轉生為贊。這類贊的特點是一直都會四處遊蕩,一旦被人觸犯就會加害於人。如色拉寺的孜瑪護法,據說是一位被強盜殺害的康巴朝聖者所轉生的贊神;而紅岩贊神,也是被土匪殺害之僧侶所轉生,後成為亞東的一個本教護法,甚至有著名高僧轉生為本教護法的傳說 。總之,贊神即可能是戰神或護法神,也可能是令人恐懼的害人神鬼,西藏人對贊神可謂是敬畏交織。
「念」(གཉན།)神,構成了西藏各地域的保護神,比如有名的「念欽唐拉」(གཉན་ཆེན་ཐང་ལྷ།),其中「念欽」(གཉན་ཆེན།)是「大念神」的意思;「唐拉」(ཐང་ལྷ།)是神名。在西藏,冠有「念欽」的保護神並不少見,如康區的「念欽卡瓦嘎博」(梅里雪山)也是。因為念神常常居住在雪山上,因此中文稱為山神 。這些神有很多的分類,如「創世九神」(སྲིད་པའི་ལྷ་དགུ།)、「贊普歌詠之十三神」(རྗེའི་མགུར་ལྷ་བཅུ་གསུམ།)、「永寧地母十二尊」(བསྟན་མ་བཅུ་གཉིས།)等,大都屬於念神系統,他們屬於廣大區域的保護神,分佈區域囊括了所有藏人居住的地區,他們主宰著雪域西藏的天地順逆、興衰安危等,他們是西藏的保護神,與西藏人的關係最為密切,是西藏人一再祈請或讚頌的對象。如西藏人常唸誦的《祈請護持西藏之保護神》開篇就是:「諾 !一切因殊勝福報和祈願力而守護觀世音教化之清涼雪域西藏、並一直留居西藏的諸地方神,尤其是五長壽女(ཚེ་རིང་མཆེད་ལྔ།)和諸永寧地母,以及創世九神和讚普歌詠之神等護持西藏的諸守護神、厲神屬眾,我在此急切地呼喚著你們,請你們前來入席享受我們所供養的……」。其中的五長壽女和十二位永寧地母等據說都是被蓮花生調伏後立誓永遠保護西藏的地祇女神。除了這些廣大地域的保護神,西藏各地還有無數屬於某個小區域、部落或村莊的保護神,一般稱為山神﹙གཞི་བདག﹚,只有當地人知道,有些則歸類為贊,但更多的是說不清屬性的神魔鬼類,廣布於山林湖泊或聖地石壘間。
「魯」神世界(ཀླུ་ཡི་འཇིག་རྟེན)指的就是地下的世界,動物中蛇、蛙等被歸類為「魯」。魯神似乎不是那種關心人的命運或行為的神鬼,與人類是相安無事,只是由於人類活動範圍的擴張,無意中冒犯了魯神,才會引發報復而將疾病傳給人類 。傳統上認為痲瘋病、瘡疥腫脹和傳染病等疾病與魯神有關。人們對魯神,主要是出於恐懼而避免觸怒,甚少祈請其保護。後世作品中將魯神描繪為一種人首人身蛇尾的形象,其原型顯然是佛教典籍中八部神鬼之水棲畜牲那珈 。在本教後期的經典中,魯神的形象被描述為牛馬狐豬等動物的頭,人的身,魚或蛇的下身或尾巴。本教有專門針對魯神的儀式。有些中文將「魯」中譯為「龍」,雖然音譯相近,但實則不同,在西藏人的觀念中,龍並不完全屬於魯神,因為龍是在天上行走,打雷就是龍的呼嘯 。如遇到冰雪水災,人們一般會認為是山神所為,而少歸咎於魯神,只有乾旱才會被歸類為魯神的懲罰。 除了魯神,西藏人需要避免觸怒的還有天上的星宿 (གཟའ།),觸犯到牠就會造成腦溢血、中風、天花、瘟疫、半身不遂、癲癇等疾病。
以上只是大體而言,西藏人對這些神鬼是又敬又怕,不論祈求保護或免被傷害,煙供都是最基本的供養或祈求的方式。針對不同的神靈,祭品和獻祭的時間也不一樣,比如上午煙供是針對念神,中午煙供是針對魯神,日落時煙供則是針對贊神。
對一個傳統的西藏人而言,與他相關的神有出生地的地方神(山神或土地神,關乎你的性命ཡུལ་ལྷ་སྟེ་འཚོ་བྱེད་ཀྱི་ལྷ།),屬於自己個人的有戰神(སྐྱབས་བྱེད་ཀྱི་དགྲ་ལྷ།)、男神和體神(སྲོག་ལྷ་སྟེ་སྲུང་བྱེད་ཀྱི་ལྷ།)。戰神關係到戰鬥或競爭中能否戰勝敵人或對手;男神是陽剛之神,決定你在人群中的形象,即眾人對你是敬畏或是蔑視;體神則關乎身體的健康、敏捷程度及生命等(ལུས་ལྷ་ཐོ་ལྷ་སྟེ་མགོན་བྱེད་ཀྱི་ལྷ།);還有幫助你的女性母族神(གྲོགས་བྱེད་ཀྱི་མ་ལྷ།),這些神少有具體形象,位於身體的某個部位。如果是女性,家庭的家神或福(གཡང་།)會依附在妳的身上 ,家神或福氣關乎著家庭的興衰和暖冷,而讓女性富貴亮麗是招家神或福央的方式之一。
由於神靈與人類現世的禍福興衰有如此密切的關聯,因此,為敬神除障而產生的儀式與習俗就成為西藏人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比如源自供養的煨桑煙供、風馬旗等,而避免觸怒神靈的禁忌則更多,如不隨意砍伐樹木以免觸怒山神,不跨越火堆以免觸怒火神、不污染水源以免觸怒魯神或水神等。
當然還有更專業的本教師(或辛師) 主持的各種獻供、祭奠或攘除的儀式。據西藏史料的記載,歷史上本教師或辛師的職能分工中就包括: (1)尋求神靈保佑的供奉儀式;(2)招攬財富的儀式;(3) 安撫遊蕩神鬼以避免災禍的供養儀式;(4)安撫和超渡亡靈的儀式;(5)詛咒;(6)以醫術治療疾病;(7)以沐浴、煙燻等儀式潔淨身上的保護神;(8)對「魯」神的供養;(9)乘「泥鹿」行空;(10)以曆算卜卦確定未來或取捨;(11)通過咒語與神鬼溝通;(12)神變的能力。
與佛教不同的是,西藏傳統信仰關注的只有現世安危,除了為今生祈福禳災,缺乏對來世或生命終極的關懷。
佛教傳入西藏時,蓮花生大士通過降妖伏魔的神通,將這些著名神鬼一一調伏並收編為佛教的護法神,其後,隨著佛教傳播的深入,這些昔日雪域西藏至高無上的神靈,在佛教經典中的地位和形象卻是每況愈下,最後定格在被佛教高僧所役使的守衛者(或守門者)的位置。即使如此,西藏人對他們的熱情、崇拜、供奉和頌揚仍然以佛教信仰的形式傳承下來,並延續至今。
雖然也有大慈大悲、像慈母一樣照護生老病死的救度母,以及降妖除魔神通廣大的蓮花生大士等佛教的出世間護法神滿足西藏人對現世的需求,但相對於倡導「眾生為母」之普世大愛或「涅槃寂靜」為終極目標的佛教,在涉及現實慾求、恩怨情仇或排他利己等世間利害衝突而需要神靈襄助時,西藏人似乎總是本能地轉向傳承自遠古祖先的雪域諸保護神或家鄉的戰神發出祈求。
(2)
西藏人相信世界有無數個――就像恆河之沙一樣多;同樣也相信我們生存的這個世界有無數的生靈存在,除了我們人類能夠感知的動物,還有我們的五官所無法感知的生靈。那些我們無法感知的生靈就被統稱為神鬼。在佛教的六道輪迴中 ,大概歸屬於天界和非人的世界。
如果以現實世界的動物來比較,鳥類具有人類所沒有的飛翔能力,馬匹具有人類所不具有的遠行負重能力,魚類具有人類所沒有的水行能力,這些動物都具有超人的能力,但這種與生俱有的能力並不是神力,而且也不是為了人類而產生。但如果人類馴服了這些動物,就可以為我所用,如馴服馬以後可以乘騎,馴服牛以後可以喝牛奶等。
同樣地,那些我們的五官所無法感知的生靈或神鬼也大都具有人類所缺乏的某種特性或能力,這些特性和能力不是為了人類而產生,而是祂們本身與生俱有的。人類也只有通過各種供養、娛神或獻祭等方式,希冀能夠借助這些神鬼的超人能力為我所用,或得到其保護,或避免被其傷害。
更進一步地,就像人類馴化和役使動物一樣,人類也希冀通過宗教的神秘力量來調伏和役使這些神鬼。
但由於世間神鬼普遍具有唯我獨尊、排斥異類、強烈的妒忌心以及暴力等特性,因此又被通稱為傲慢之神。除非你有超高的修行力可以調伏或役使牠們,否則,一般觀念認為最好的應對方式還是敬而遠之。人類一旦與牠們發生連結,就要注意不要觸怒牠們;如果誤將這些世間神視為皈依處或貪圖現世蠅頭小利而向世間神獻上忠誠,就可能要從一而終、小心翼翼地敬奉牠,因為任何小事都可能會觸動世間神極強的妒忌心,從而引發其暴怒;更主要的是,人死後,很可能會變成世間神鬼(或非人)的眷屬僕從,在輪迴中漫無止境地轉生下去:這些世間神鬼雖然也是六道輪迴的眾生,但其壽命卻可能長達幾千年,當然也就會從此斷了佛緣。
因此,西藏人與這些世間神鬼的交流,一般情況下僅限於試圖藉助其能力謀取世間利益,或是避免受其傷害,僅止於戰神或世間保護者的角色,而生命的終極皈依和來世等則獻給了佛陀的教法。而且,隨著對佛法越來越虔誠的信仰,這些原來由念神或贊神等所組成的西藏保護神,就逐漸地轉化成帶有佛性的神靈,或被佛教的護法神所取代。
猶記得我家鄉山神的變化過程,據說家鄉的山神是一個從外地流浪而來的贊類神靈,因為本身是流浪者,故而對外來人特別好。文革後宗教復興時,我們男孩去拜山神,掛上去供奉山神的旗子多是沒有文字或圖案的五色旗 ,只有拋撒到天空的風馬旗紙上印有風馬和虎、獅、琼鳥、龍四種動物以及少量咒語。我們到山上一邊高喊著「頗拉達」「札拉達」「魯拉達」「格格索索拉嘉洛」 ,一邊拋撒那些風馬旗。我們被長輩告誡不要做跪拜的動作,因為對世間神只能請求其幫忙,而不得作為皈依處,而跪拜的對象只能是佛法僧三寶皈依所。幾年後,五色旗都印上了風馬圖案和佛教咒語,已經很少看到沒有文字和圖案的五色旗;十幾年後延續至今,現在的風馬旗已經很少看到風馬,風馬和其他動物的位置被佛像所取代,而且印滿經文,雖稱風馬旗而實為佛教經幡,早已不是供奉山神或世間神的風馬旗。
而在佛教的護法神殿中,包括密宗經典中的本尊 ,以及譯師從印度引進的出世間神等,這些都被視為修行與解脫途中最為重要的助緣,也可作為皈依處。由蓮花生調伏或其他因緣產生的西藏原生神靈,基本上都屬於世間神的範疇,一般都是外圍保護者的形象,也不能作為皈依的對象。當然也有一些被信眾以「視師如佛」的原理奉為出世間神者,但也僅限於特定信奉者。
(3)
西藏人以本尊和印度引進之佛教護法神為出世間神、以西藏本土神鬼或護法神為世間神的信仰,如此延續千餘年後,「兇天」的出現開始顛覆這些格局。
最早將兇天奉為神靈的是薩迦派,那時候薩迦的高僧們將其稱為「朵結」 ,當這個被稱為鬼或非人的神鬼跑到薩迦寺時,因為據說神通力強又兇悍,薩迦派的人不願得罪牠,就為其修地祇壘 供了起來,並撰寫祈請文,算是將祂列入世間神的範圍內,從而產生了連結。其後,薩迦派的高僧對「朵結」的評價和讚美稍有提高,甚至還將其身世追溯到西藏贊普時期。但畢竟不是被蓮花生調伏的神鬼,也不是後來由得道高僧以伏藏等形式產生的世間神,而是自己冒出來並自稱為「格魯派怨鬼」的神鬼類,充其量也不過是傳統神譜中類似「贊」之形象,或更低階的地祇神鬼----燒施朵瑪之對象。總之,熱鬧了一陣以後,「朵結」在薩迦派中慢慢沉寂下來,雖然還不是消失無蹤,卻也是被邊緣化的角色。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朵結」改稱「兇天」 進入到格魯派中。一些僧侶開始將其作為世間神來供奉,其目的依然是希望借助其神通和超人能力。其實就是西藏傳統的供奉山神或保護神的信仰以佛教的形式在延續。包括僧侶在內的西藏人,對具神通力或很靈驗的神鬼傳說依然會怦然心動,充滿嚮往,不同的是僧侶們懂得將其包裝成佛教的護法神,從而避免與自己的正統信仰發生衝突,這種現象在西藏佛教中並不罕見。對此,就像本書闡述的那樣,雖然會遭到正統佛教僧侶的強烈反對,但由於本質上還是作為世間神鬼來供奉,與佛教的正統信仰尚無根本的衝突。
事情發生本質的變化是在第十三世達賴喇嘛時期。當時西藏著名的佛教學者帕旺卡對兇天情有獨鍾,約在1920年他專程前往朵曲彌地方,據說在當地找到了「朵結的臂膀」,並藉著給「臂膀」舉行儀式之機撰寫酬補薈供的經文和儀軌等內容,從而將傳說中的神鬼變成實實在在的存在。兩年後帕旺卡又撰寫了「對兇天依命立誓」的儀軌,把以前只配享受朵瑪供施的非人神鬼兇天抬高到了格魯派殊勝護法神的地位。當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聞訊後以「依止世間傲慢鬼神,有違佛教皈依法」為由下令禁止時,帕旺卡亦曾信誓旦旦地向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做了保證。但等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帕旺卡不僅故態復萌,還變本加厲地利用達普仁波切礙於情面難於拒絕的處境,將帕旺卡自己編寫的「對兇天依命立誓」儀軌改頭換面為「淨相」傳承,開始在康巴地區傳播。
記得西藏著名學者更敦群培曾說過:上師執著己見而宣說之,弟子懵懂盲從而傳播之,後輩視為教條而堅持之。
帕旺卡的弟子赤江仁波切在流亡印度後,以達賴喇嘛副經師的身分,不僅繼續傳播兇天信仰,甚至更進一步以文字再造了兇天的歷史,將兇天與五世達賴喇嘛時期的上府邸喇嘛札巴堅贊相連結,宣稱是札巴堅贊遭到謀殺後轉生為厲鬼。毫不顧慮其行為可能會置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於難堪之處境。
如上所述,西藏歷史上的確有修行者或朝聖者被強盜殺害後其靈變成贊神並成為護法的故事,但這些贊神即使變成護法神也僅僅是世間神,根本不具有成為皈依處或對其獻出忠誠的資格。因此,就算札巴堅贊真的是被殺害後成為厲鬼,充其量也不過是贊神類的世間神鬼。佛教反對拜鬼神,但不反對通過宗教力量調伏和役使這些神鬼,並將這類神鬼的神通或超人能力做為自己修行的順緣和助力,但也僅限於此而已。而且也都是世間神鬼獻出自己的生命之根並立誓護教護民,從未允許信眾向傲慢世間神奉獻皈依或以生命立誓。
常聽達賴喇嘛尊者講:「信徒太虔誠了,可能會造出假上師」。
千百年來,西藏正是仰賴無數高僧大德和譯師的恩德,才有了現今仍舊璀璨的宗教和文化;西藏民族每逢危難之時,佛教領袖總是挺身而出;而西藏民族對信仰的虔誠也讓他們忠誠地團結在佛教領袖身邊,從而展現出了強韌的生命力。但事情總是有其兩面性,輝煌的另一面是陰暗,尤其是如果陰暗是由上師所帶來或倡導,則弟子對上師的虔誠信仰反而會強化和推升這種陰暗。兇天信仰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我常常感到疑惑――那些被西藏信眾願意以生命維護和信賴的上師們,當他們向信眾傳播兇天信仰,要求信眾以生命立誓的時候,他們難道不知道這不符合佛教皈依法嗎?不知道這必然會引來正統佛教信眾的抵制和反對?不知道會產生紛爭嗎?他們當然知道!既然如此,對那些一片癡心的弟子或信眾,他們為何竟沒有絲毫的慈悲和憐憫,仍然將他們引向或置於這樣的處境當中呢?
而更令人唏噓的是,現在的兇天團體,幾乎已淪為了與西藏佛教和西藏民族為敵、殘害西藏人民之中共政權的爪牙和打手。那些惡意攻擊達賴喇嘛尊者、背叛西藏民族的卑劣分子,也常常會以兇天信徒的面目出現並混淆視聽,從而為他們甘為侵略者鷹犬的惡劣行徑披上宗教的外衣。而一些兇天追隨者本就愚盲,此時更不乏聞雞起舞者,結果卻是將自己從信奉世間神的單純行為墜入與西藏民族為敵的黑暗深淵。
(4)
過去十餘年間,達賴喇嘛尊者基於西藏宗教領袖的責任,延續第五世達賴喇嘛和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的作法,對於將世間惡神兇天奉為格魯派護法神或皈依處的做法表達了堅決反對的立場。由此也引發了許多的討論或關注,而許多信仰藏傳佛教的華人信徒也希望對此議題有更深入及全面的瞭解,希望本會介紹一本內容全面、文字通俗易懂的中文書籍。
有鑒於此,雪域智庫同仁們查尋了相關藏文書籍,最後從諸多藏文書籍中,選擇了藏人行政中央宗教部所屬「兇天研究小組」撰寫的《朵結或兇天研究•公正歡喜之雲供》、民間社團「多麥兇天研究小組」撰寫的《朵結研究•除污明鏡》以及西藏佛教格魯派總會編寫的《兇天問題真相•辨別善惡真假之教理金鑰》三本書。
審閱時發覺三本書中的內容多有重複,而且,《朵結或兇天研究•公正歡喜之雲供》之前曾由次仁旺久先生翻譯,以《供養朵傑雄登護法神的得失》的書名由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於2000年印製發行;《朵結研究•除污明鏡》之前也由臺灣雪域出版社以《護法神Vs厲鬼》的書名出版。而《兇天問題真相》一書,以相當篇幅探討深奧的教理問題,並不適合一般信眾或讀者閱讀。
綜合考量後,雪域智庫決定重新編譯,將《朵結研究•除污明鏡》和《兇天問題真相•辨別善惡真假之教理金鑰》兩本書的內容,刪除重複或與主題無直接關聯處,重新編纂成《西藏的神鬼與護法神――兇天如何拱成護法神》一書,並力求名詞統一,文字內容簡明易懂。全書以《朵結研究》的架構為主,將《兇天問題真相》的內容以註釋或新增章節的方式增補進去,並詳加註釋。而宗教部的《朵結或兇天研究•公正歡喜之雲供》則以單獨章節的方式呈現,至於其他相關的內容則以附錄的方式收錄。希望這樣的改編有助於中文讀者克服對西藏歷史文化的陌生,並能了解西藏神鬼世界及西藏佛教護法神的時空背景和脈絡。
本書敘述的是過去的三百年間,一個西藏本土的世間怨鬼之方方面面,包括:怨鬼如何產生、怨鬼與佛教的連接、怨鬼如何轉化為護法神、怨鬼最終被拱上需要以生命起誓的皈依對象等。同時也敘明正統佛教陣營對此的反應以及雙方的矛盾,也深入記載雙方在西藏流亡中的激化、現代政治介入所造成的深遠影響等。但在論述脈絡上,受限於上述兩本原著的敘事框架,依然是從第五世達賴喇嘛時期哲蚌寺上、下府邸、札巴堅贊的歷史以及第五世達賴喇嘛的火焚儀式作為鋪陳,接著敘述西藏薩迦派和格魯派對兇天的立場,最後是帕旺卡、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赤江仁波切、澤美和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等的立場互動,看似給人以一以貫之的感覺。其實,在不同歷史階段,兇天議題的癥結點或關注焦點並不一致;在第五世達賴喇嘛時期,兇天(當時稱「朵結」,意思是「朵地方的非人」)的問題僅僅是雅魯藏布江流域「朵」地區一個叫「曲彌」的地方出現了一個神通廣大的害人鬼魅,需要通過火焚儀軌去鎮壓滅除,僅此而已。接著,在沉寂了六十餘年後,兇天又再次出現,並被薩迦派所接受,還首次被奉為護法神――但仍然是世間神的身分地位,故而其依存處(或者說被供奉的地方)只能是荒郊野外的「小神殿」或石垛堆(神垛)中。當兇天信仰從薩迦派傳到格魯派後,在格魯派中引發供奉與反對的爭議時,爭執的焦點依然不脫「僧人供奉世間神是否適宜」的問題,並沒有人質疑兇天的世間神身分;最後,到了帕旺卡和第十三世達賴喇嘛時期,帕旺卡將兇天稱為「格魯派與眾不同的護法神」,後又推升到「依命立誓」的地步,這時,爭執的焦點才開始發生質變,變成兇天信仰「是否違背佛教皈依法」的大是大非問題。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也是基於這一點而堅決反對供奉兇天的。
然而,對於並不怎麼了解西藏佛教或文化的中文讀者而言,從諸多敘事中去挖掘或把握這些精神,實在是有點勉為其難。即使如此,我們還是期望通過本書,讓中文讀者對西藏佛教或護法神等議題至少具有比較粗淺的認知。
最後,雖然幾經校正,但錯誤一定還是難免,望有識者指正,容我們在再版時予以改進。
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
董事長 跋熱•達瓦才仁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日於台北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雪域智庫暨見悲青增格西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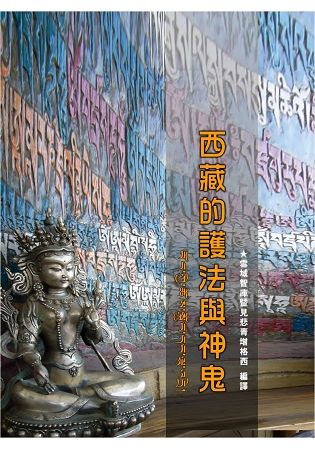 |
$ 237 ~ 270 | 西藏的護法與神鬼
作者:雪域智庫暨見悲青增格西/編譯 出版社:雪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8-10  共 9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9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格西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西藏的護法與神鬼
歷史上,西藏傳統的神鬼崇拜與佛教護法神的信仰通過調伏神鬼的方式,以世間神和出世間神(或本尊)的形式做了調和。但這種調和並沒有完全消解彼此的歧異,有時甚至還會對信仰體系與現實社會激盪出更大的衝擊。本書敘述的就是這樣一個案例:三百多年前,西藏中部出現了一個自稱「怨鬼」的神靈,最初他以世間神鬼的身分成為佛教的護法,幾百年後,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這個歷來褒貶不一的神鬼竟然被拱上了本尊護法的聖壇,需要信眾以生命起誓的皈依對象,由此引發了正統佛教的反擊,彼此的矛盾在流亡中繼續演化、以及現實政治的介入等……
作者簡介:
雪域智庫
一群關心西藏未來的臺灣人、華人與西藏人。
TOP
作者序
導論:西藏的神鬼
西藏神鬼的系統、定位龐雜紊亂,佛教各派說法不一,尤其佛教和本教更是針鋒相對。在某種文獻的說法,可能被某一教派承認,卻又被另一教派否認,更何況各地方的神靈譜系也不盡一致。因此,我在此僅僅是以一個普通西藏人的視角,介紹我自己從生活中所認識或理解的西藏神鬼系統。由於源自個人親身的鄉土生活體驗,談不上權威,甚至我的認知內容不一定有文字依據。但至少期望我的敘述有助於對西藏文化陌生的中文讀者瞭解西藏神鬼的脈絡。
(1)
一般而言,西藏人祈求神靈保佑的時候,除了佛法僧三寶、還會有本尊﹙ཡི་དམ།﹚、...
西藏神鬼的系統、定位龐雜紊亂,佛教各派說法不一,尤其佛教和本教更是針鋒相對。在某種文獻的說法,可能被某一教派承認,卻又被另一教派否認,更何況各地方的神靈譜系也不盡一致。因此,我在此僅僅是以一個普通西藏人的視角,介紹我自己從生活中所認識或理解的西藏神鬼系統。由於源自個人親身的鄉土生活體驗,談不上權威,甚至我的認知內容不一定有文字依據。但至少期望我的敘述有助於對西藏文化陌生的中文讀者瞭解西藏神鬼的脈絡。
(1)
一般而言,西藏人祈求神靈保佑的時候,除了佛法僧三寶、還會有本尊﹙ཡི་དམ།﹚、...
»看全部
TOP
目錄
導論: 西藏的神鬼
第一章 兇天的來歷
第二章 第五世達賴喇嘛調伏非人兇天
第三章 高僧大德制止供奉兇天
第四章 帕旺卡對兇天的造神活動
第五章 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管制兇天信仰
第六章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制止供奉兇天
第七章 達賴喇嘛有關兇天的講話
第八章 佛法與進入佛法之理
第九章 佛教與護法神
《兇天問題研究・公正歡喜之雲供》
一、 西藏最早期的各護法神
二、 轉世者札巴堅贊的簡歷
三、 轉世者札巴堅贊與第司・索朗拉登的關係
四、 轉世者札巴堅贊是怎樣轉生成厲鬼的
五、 對兇天的供奉方式及其變化
六、 有關兇天...
第一章 兇天的來歷
第二章 第五世達賴喇嘛調伏非人兇天
第三章 高僧大德制止供奉兇天
第四章 帕旺卡對兇天的造神活動
第五章 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管制兇天信仰
第六章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制止供奉兇天
第七章 達賴喇嘛有關兇天的講話
第八章 佛法與進入佛法之理
第九章 佛教與護法神
《兇天問題研究・公正歡喜之雲供》
一、 西藏最早期的各護法神
二、 轉世者札巴堅贊的簡歷
三、 轉世者札巴堅贊與第司・索朗拉登的關係
四、 轉世者札巴堅贊是怎樣轉生成厲鬼的
五、 對兇天的供奉方式及其變化
六、 有關兇天...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雪域智庫暨見悲青增格西編譯
- 出版社: 雪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8-10 ISBN/ISSN:978986961933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85頁 開數:18
- 類別: 中文書> 哲學宗教> 佛教
|
 格西,漢語意譯為善知識、善友,是善知識的略稱,為藏傳佛教格魯派僧侶經過長期的修學而獲得的一種宗教學位。
格西,漢語意譯為善知識、善友,是善知識的略稱,為藏傳佛教格魯派僧侶經過長期的修學而獲得的一種宗教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