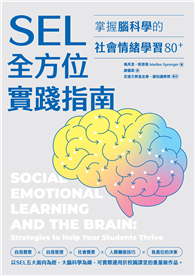名人推薦:
開啟兩性生殖議題的新視角
王家瑋婦產科院長/王家瑋博士
身為一個研究生殖醫學不孕症的資深婦產科醫師,當我收到這本書稿時,映入眼簾的是「Guynecology」這個字,從一開始以為是婦科學「Gynecology」的誤字,之後才看出Guynecology原來是自創的研究男性生殖與健康的一門科學,尤其著重於男性與生殖的關係,也因此類比而稱之為「父產科」。不論東西方文化,自古以來男性在生育方面的角色單純就是精蟲提供者,一旦生育方面有了困難,基本上大多歸咎於就是女性的問題,由女性負起絕大部分的責任,可是實情真的是如此嗎?
夫妻想說什麼,和我們聽到什麼,生殖醫學中的性別議題
女性在孕育生命上擁有特有的經歷,讓生育這件事情,不論是在醫師的觀點、訓練以致於醫學研究等,多圍繞在女性的身上,生殖醫學的訓練路徑也多為婦產科的延伸。但當多數醫師把眼光投注在卵巢功能、女性年齡、卵子品質等議題時,男性生育健康卻在療程中逐漸縮小為只是精子提供者,而無法關注在精子數量品質減低的背後,我們還可以提供些什麼照護和關心。
提供一個小故事讓大家理解男性在生殖醫學療程中的處境,這個案例看似荒謬與無奈,卻是現今男性看不孕症最常發生的場景:
我有精索靜脈曲張,最開始發現時其實是我在走路的時候有一邊的蛋蛋(睪丸)會不時有點抽痛,有時也會在射精前後出現,後來是因為太太堅持要我去做生育檢查,我才走進了一家網路上很有名的泌尿科診所。你知道男生走進泌尿科診所是多尷尬的情境嗎?身邊都是老人家,看著我這個年輕人以為要來做性病檢查,護理師也在大庭廣眾下問我:什麼問題要看醫生?我心理想:如果我有勃起障礙也要在櫃檯跟妳說嗎?覺得很羞恥。我只說了我要精液檢查,根本不敢說我蛋蛋會痛。泌尿科診所裡沒有一個醫師看起來是真的專攻生育的,告知我有精索靜脈曲張後,又請我來找婦產科醫師看一下怎麼讓太太懷孕。我覺得整個就是浪費我的時間。現在療程需要做睪丸切片,我竟然又要回到泌尿科,拜託真的給我一個可以看生育問題的泌尿科醫師。
如本書中所言,醫學這幾百年來的進步,近幾年終於有比較多的人開始正視男性的生殖醫學。男性在生育的過程中絕不只是精子的提供者而已,生育健康也不該跟男性雄風畫上連結,關注自己影響生育健康的因素,改善會影響生育健康的習慣,適時定期執行生殖系統檢查,適時使用冷凍精子保存自己的生殖力都是重要的觀念。
我很高興有這麼一本書,開啟將女性生殖議題轉向探討兩性生殖議題,翻轉學術視角,從社會學、心理學、文化研究與醫學各方面開始補足東西方自古以來所欠缺或者忽視的「男性在生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非常值得大家深入去了解與探究。
媒體推薦:
第一章 父產科何去何從?
力爭尊嚴,結果失利
被嘲笑的不僅是名稱(生殖泌尿或男科),也包括這門專科打算治療的器官與部位。位於紐約的協會有意為長期以來與性病、不道德、庸醫等聯想在一塊的身體部位力爭尊嚴。這些聯想在那篇《美國醫學會期刊》社論裡顯而易見,文章指出「男性疾病一直是庸醫與江湖郎中荷包豐收的領域。」該文強調「整個這行」必須催生「專門研究男科的協會」,文末得出樂觀的結論,稱「等到另立門戶的專科與命名像今天的婦科一樣廣被看重時,時機就出現了。」但是事與願違,這個新協會面臨的文化阻力實在太大了。
十九世紀末的男子氣概與種族
在醫學領域之外,大家對於十九世紀末(白人)男子的陽剛氣概式微,普遍感到憂心。那些曾經在自家農場刻苦勞動的人,現在整天軟趴趴地坐在辦公桌前(如果他們能順利就業的話):工業化浪潮導致許多人失業,就業前景黯淡。一些中產階級男子甚至被診斷患有神經衰弱,這是一種神經系統疾病,因為當代生活型態,導致身心極度疲憊。為了對抗久坐導致的各種疾病,倡議健康與養生的專家伯納爾.麥克費登(BernarrMacFadden)在流行雜誌以及暢銷書裡倡議「身體文化」的重要性。他寫道:
有數以千計甚至多達數百萬計的男孩、青壯男、乃至老男人,他們的智力、體力與性能力都在迅速下降……每個成年男子的首要職責是成為男子漢,所有其他要求都應該排在這點之後。如果沒有地基,房子是蓋不起來的;男子氣概是地基,教育和文明生活薰陶栽培出來的所有結果必須置於這個基礎之上……如果你不是男子漢,你不過只是輕如鴻毛的存在!
新教領導人倡議「肌肉健碩基督教運動」(muscular Christianity),該運動背後傳達類似的觀點,均強調競技運動與體能教育對男人的重要性,特別是考慮到一波又一波天主教移民湧入美國。
由於「白男」是常規,意味文章裡討論的某類男性身體時,並不會次次都詳述是那種類型,但是陽剛氣概從來都不只是二元的性別觀。在同一時期,新崛起的性學與當時的「種族學」有諸多重疊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學者,他們仰賴科學手法剖析以下兩類男性,這兩類男性與體弱的異性戀白男形成鮮明對比。一、娘娘腔的白人男同志;二、性慾旺盛猶如「野獸」的黑人男性,據信有性侵白人婦女的傾向,唯有透過去勢或私刑(或兩者皆用)才能控制。正如梅麗莎.史坦(Melissa Stein)所指,體弱的白人男性讓人擔憂,這種心情與唯恐喪失種族支配地位的心情息息相關。蓬勃發展的女權運動,主要由白人女性組成,倡議女性有權接受高等教育以及擁有投票權,結果進一步加劇社會對白人男性地位式微的憂慮程度。
就是在這樣更廣泛的背景下,包括艾伯特.莫羅親王在內的醫師對性病傳播提出警告。儘管鮮少衛生部門彙整統計數據,但莫羅等醫師估計,在一九○一年,紐約市多達百分之八十男性曾得過淋病,以及可能多達百分之十八罹患梅毒。雖然一般認為,淋病不比普通感冒來得嚴重,但是梅毒這性病可要嚴重得多。此外,性行為傳染疾病被認為會進一步威脅男性身體。但是這類疾病不僅有害男性,也會禍及無辜。公共衛生報告指責男性犯了道德差池,導致發生婚外性行為,把性病傳染給了「無辜」的妻子與孩子,這正是易卜生戲劇《群鬼》探討的核心課題。雖然生殖泌尿外科醫師在會議記錄或日誌裡,鮮少直接提及種族或移民,但疾病與衛生、優生學與先天論(nativism)交織出現在研究裡,等於間接透露,生殖泌尿外科醫師在思考男性身體時,難免與種族、移民產生聯想。
拱手讓「庸醫」治療男性疾病
性病與道德淪喪被劃上連結不僅讓大家以有色眼光看待感染性病的男性,也對治療這類疾病的人打上問號。事實上,治療「男性特有」疾病的人,長期以來一直被專業「正規」醫師嘲弄,認為他們不僅業餘,而且眼裡只有錢。在十九世紀,醫學界努力鞏固其專業權威,為了剷除各種形式的競爭,把「庸醫」這個標籤貼在助產士、順勢療法師(homeopaths)、以及擅長醫治男性疾病的人士身上。因為這貶義的標籤不一定有科學證據作後盾,也無科學證據質疑這類人士的照護品質與療效,所以接下來提及庸醫這一詞時,都要加引號。
正規醫師與庸醫的一大區別是,正規醫師不太可能像庸醫一樣,保證醫好病患,有些甚至勉為其難地承認,他們實際上拿不出更有效的療法。此外,庸醫比較可能大打廣告,這是正規醫師不屑做的。事實上,為了讓協會的正規醫師與庸醫有所區隔,美國生殖泌尿外科醫師協會禁止會員在名片上列出專科別,儘管美國醫學協會允許這麼做。此外,生殖泌尿外科醫師協會標榜自己「成立目的是為了互相促進科學前進」以及「聚集工作人員的誠實組織。」
顧及這麼多男性患有性傳染病,以及其他影響其生殖器官的難啟齒疾病,他們向庸醫求助,也是情有可原。雖然很難確認十九世紀男性中,有多大比例會到所謂「男性專科診所」找庸醫求助,但蘇珊娜.費雪(Suzanne Fischer)將這類診所定義「曾經無所不在的醫療機構」。107有些有店面,「限男性進入」,有些是巡迴診所,只要有病人排隊,就會停下車提供服務。他們承諾能治療生殖泌尿專科醫師宣稱歸他們領域的疾病:梅毒、淋病、陽痿、遺精、男性不育症等。追蹤其中一個這類機構的命運後,費雪發現,海德堡醫學機構(Heidelberg Medical Institute)在一八九○年代至一九一○年代期間,在中西部開了三十多家男科診所。海德堡醫學機構由出自聖保羅的萊因哈特兄弟(Reinhardt brothers)創辦,其中兩位兄弟擁有名校的醫學學位。圖一是海德堡醫學機構的一則廣告。
這類醫療事業體面臨正規醫界的嚴厲抨擊。例如,撰寫生殖泌尿系統教科書的作者,往往一開頭就先致歉,抱歉撰寫這麼不光彩的科別,但隨後強調,正規醫師必須正視這些生殖泌尿系統疾病,以免有人被庸醫所騙。詹姆士.喬治.比尼(James George Beaney)在《生殖系統》的序言裡寫道,他對這個「科別的本質」感到「尷尬」,但是大家對「生殖器官」的「知識不足」,促使他寫了這本書。「男女的性系統」因為大家「故作有教養」而被漠視,結果讓「江湖騙子」乘虛而入。法國醫學教授克勞德-佛朗索瓦.拉曼德(Claude-Francois Lallemand)在其探討遺精症的知名論文裡寫得更直接,稱醫學界對這類疾病一無所知,並且「一致同意」忽視這些「絕對讓有教養人士反感」的科別。影響所及,「病患發現自己被正規醫護人員漠視,因此只要發現哪兒有丁點的機會,就會急於到那兒尋找慰藉;沒有本事又貪婪的庸醫大打廣告,銷售有害的配方(仙丹),快速從中牟利。」不僅是個別的醫師抱怨庸醫,在二十世紀初的數十年裡,美國醫學協會與一些報紙紛紛揭露男性專科診所不實的廣告與說法。
為什麼這麼多男子向備受冷嘲熱諷的庸醫求診?那些能夠負擔得起找正規醫師(甚至生殖泌尿專科醫師)治療的病患,可能不願意透露自己感染了難以啟齒的性病。男性器官染病往往被視為道德有污點,毫無疑問,這讓男性覺得非常丟臉,影響所及,他們可能偏好像萊因哈特兄弟經營的診所,因為能讓他們匿名以及幫他們保密。至於那些經濟條件較差的男性,例如城裡的工人階級男性,男科專科診所提供了可負擔和易於獲得的治療,有時甚至提供多種語言服務,讓新來乍到的移民也能安心治療。至於在偏遠、醫師嚴重不足的郊區,城裡的診所提供函授遠端診斷,並承諾回函時會謹慎包裝信封,寄件人地址也會刻意變造。
但是就算男性的生殖器官出了毛病完全和非法性行為無關,醫師們還是發現,病患仍遲遲不肯就醫。例如,上個世紀中葉,兩位撰寫睪丸教科書的作者納入了幾個實例,稱睪丸病患在上門求診前,往往忍受了數月之久的煎熬,儘管只是半夜不小心撞到抽屜,導致睪丸受傷;或是騎馬時睪丸撞到了馬鞍翹起的鞍頭,這可是「導致睪丸受傷最常見的暴行」。一如柯林在教科書裡寫道「心智很容易被生殖器外觀上的瑕疵所干擾。」他和庫伯發現,病患若失去睪丸或睪丸畸形,會嚴重打擊男人的男性氣概,甚至會走上自殺絕路或殺人犯罪。
覺得丟臉、見不得光,導致這些男人很容易成為庸醫的獵物,但這也給了基斯、莫羅等人一線希望,亦即寄望男科不久後可獲得和「婦科一樣崇高的地位」。但是儘管他們努力讓自己有別於庸醫,也努力讓男科得到社會的肯定與尊重,可惜事與願違,終究還是失敗了。
去掉生殖兩字,改稱泌尿科
事實上,類似的情況在數年後再次出現,當時「新潮」的泌尿科醫師倡議了一場成功的運動,把生殖泌尿外科的生殖兩字去掉,只關注不那麼被抹黑的尿道疾病。全盤分析這些發展已超出本書的範圍,有待學術進一步關注,畢竟除了在二十世紀初有泌尿科醫師寫了幾本小冊子之外,似乎找不到完整而全面的泌尿外科史。簡而言之,美國泌尿外科協會(AUA)成立於一九○二年,當時紐約生殖-泌尿協會表決決定解散組織,並另取一個新名。值得注意的是,泌尿科醫師特別擔心自己被誤認為是「淋病醫師」(clap doctors)而招來「異樣眼光」。
有了新名稱之後,醫師刻意將重點放在非性病以及非生殖系統的問題上。拉蒙.吉特拉斯(Ramon Guiteras)是「美國泌尿外科協會」的創辦人,也是第一任主席,這位哈佛醫學院畢業的醫師在《美國泌尿外科期刊》第一期中解釋,「刪掉了大部分泌尿生殖疾病中有關生殖器官的部分……性病(尿道感染與損傷除外)被排除在外,而生殖器疾病,除了會影響泌尿器官的疾病,也不在考慮之列。」他繼續寫道,有些人想知道新的泌尿外科協會是否會成為美國生殖泌尿外科協會的「對手」,但「其實不會」,因為「診治範圍」「非常不同」。事實上,只醫治性病的執業醫師不得加入美國泌尿外科協會,而協會的學術會議也不會接受聚焦性病的論文。儘管生殖泌尿協會與泌尿外科協會都設在紐約,但是創始會員中,沒有任何一位重複。
基斯有關生殖泌尿科的教科書也點出輕生殖重泌尿科的趨勢。一九○六年的版本是他和兒子合寫,他兒子也是泌尿科醫師,在序言中,他們呼籲關注性傳染疾病,因為和之前版本相比,大家對性病的關注力下降。美國生殖泌尿外科醫師協會至今都還存在,事實上,該協會舉辦基斯獎,頒發獎章給「對泌尿外科有傑出貢獻的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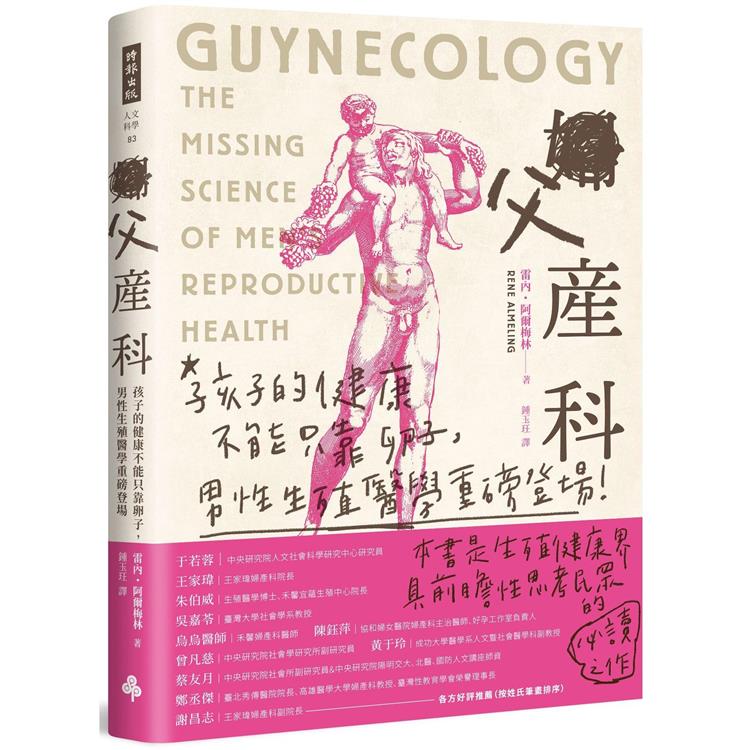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