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更改主題」代表的意涵是:哲學家理論之更替,其實基於他們不斷改變思想及討論的主題,亦即不斷在尋找,對人而言重要的問題,應如何去問的方法。哲學家並不會對問題提供直接的答案,反而,他們會因身處的時代世界,不斷更改追問、反思的因由與方向。
驟眼來看,本書似乎是芸芸西方哲學史文集其中之一,但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教授諾伊豪瑟(F. Neuhouser)的書評認為,本書有很多超乎尋常之處。作者蓋斯(R. Geuss)挑選了古今十二位哲學家作導讀分析,這名單所包括的部分作者(例如盧克萊修、蒙田等),在英美派的西方哲學史中,只佔次要邊緣位置。諾伊豪瑟指出,於此這可看出,本書所側重,乃是實踐哲學(倫理、政治、社會)的面向。作者在介紹哲學家思想之同時,更不斷反思討論極重要的問題:「什麼是(西方)哲學?」作者認為,直到目前,哲學家還是重複地虛幻妄想,認為從古至今哲學只投入在一個(本質地)「相同的」活動:哲學的目的,就是解釋及維護一套正確思想及行動的規則。他極度反對這種迷思,寫這本書,就是要論證:哲學最特別的性質,就是它總是與某個時刻扣連,而這個時刻,就是正值恆常的軌跡改變之際,所有準則正在崩潰、改變或已改變的時期。
本書特色
★ 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英國劍橋大學哲學系榮休教授雷蒙德.蓋斯原著,從蘇格拉底到阿多諾,一次導讀西方哲學大師的思想精華。
★ 每個哲學理論的產生,都在呼應當下所有準則改變之時刻;時代主題的不斷遞嬗更迭,便是哲學思想不斷尋找如何提問的過程。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雷蒙德·蓋斯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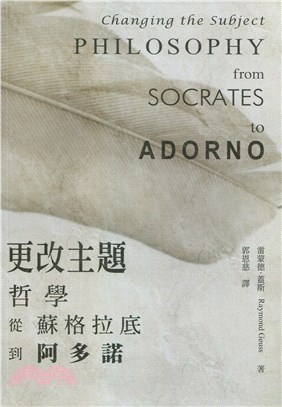 |
$ 450 | 更改主題:哲學從蘇格拉底到阿多諾
作者:雷蒙德·蓋斯 出版社:Denzel & Witt Creation 出版日期:2022-12-02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更改主題:哲學從蘇格拉底到阿多諾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雷蒙德.蓋斯 Raymond Geuss
英國劍橋大學哲學系榮休教授,19世紀、20世紀的歐洲哲學、政治哲學專家。著作包括美學、尼采研究、脈絡主義、現象學、知識思想史、文化及古代哲學。近期著作:A Philosopher Looks at Work (2021)、Not Thinking like a Liberal (2022)
譯者簡介
郭恩慈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畢業後,於法國巴黎第三大學比較及普遍文學系獲取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
後取得香港大學佛學研究碩士學位。曾於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教授設計史及理論。現居台灣,從事法、英語哲學文學翻譯工作。
雷蒙德.蓋斯 Raymond Geuss
英國劍橋大學哲學系榮休教授,19世紀、20世紀的歐洲哲學、政治哲學專家。著作包括美學、尼采研究、脈絡主義、現象學、知識思想史、文化及古代哲學。近期著作:A Philosopher Looks at Work (2021)、Not Thinking like a Liberal (2022)
譯者簡介
郭恩慈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畢業後,於法國巴黎第三大學比較及普遍文學系獲取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
後取得香港大學佛學研究碩士學位。曾於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教授設計史及理論。現居台灣,從事法、英語哲學文學翻譯工作。
目錄
序言
參考資料說明
譯者說明
導論
第1章 蘇格拉底
第2章 柏拉圖
第3章 盧克萊修
第4章 奧古斯丁
第5章 蒙田
第6章 霍布斯
第7章 黑格爾
第8章 尼采
第9章 盧卡奇
第10章 海德格
第11章 維根斯坦
第12章 阿多諾
結論
原文註釋
延伸閱讀參考資料
附表 本書各章節介紹之哲學家生卒年份及國籍
參考資料說明
譯者說明
導論
第1章 蘇格拉底
第2章 柏拉圖
第3章 盧克萊修
第4章 奧古斯丁
第5章 蒙田
第6章 霍布斯
第7章 黑格爾
第8章 尼采
第9章 盧卡奇
第10章 海德格
第11章 維根斯坦
第12章 阿多諾
結論
原文註釋
延伸閱讀參考資料
附表 本書各章節介紹之哲學家生卒年份及國籍
序
序言
在所有文獻著作中,包括所有哲學文獻,最令人震撼的影像,可說是在柏拉圖的《理想國》的第七卷中所描述的一幕:在一個地底的洞穴,被囚禁的人群被鐵鍊鎖著,他們背後有一光源。眾人自出生開始便被囚禁,一生也是這樣,每天就是觀望在他們眼前顯現的,投影在牆上的幢幢影子中度過。這些影子漸現形狀,搖曳不停,又不時重疊,消溶不見,(有時)又會重現,還時不時會合成有規則的圖案,又有時隨機地一個圖案接著另一個圖案出現,但在其他時間它們好像會展示某種的規則秩序。有部分囚徒漸漸學習適應了那些影子出沒的序列,對其做出描畫,即在有限範圍內,掌握影子的出現與隱沒的規律性─稱為「常識」的,就是囚徒們在學習影子出沒的規則過程中,所發展出來的「技巧」。
柏拉圖提議:假設有人讓幾個囚徒獲得自由,讓他們轉身,迫他們從背向而轉身面對光源,同時讓他們看見那些投射了影子在牆上的東西─他們花了一生人只觀看到影子的那些東西。柏拉圖說,這些(被釋放的)囚徒很可能會感到目眩、盲目及感到沮喪。這樣迫他們轉身去看,釀成了痛苦與失去方向,毀滅了他們不斷辛勞地學習而獲得的常識,但是,如要真正理解他們生活在其中的世界,這毀滅是啟蒙過程中必然附隨之事。到了最後─這「最後」可能是指涉頗長的時段─那些被解放的囚徒所學習到對影子變化(的規律)的理解,可能比起那些從來未被解放的囚徒所學的更佳,因為他們有可能掌握到一些有關真實的東西(即那些將影子投射在牆壁上的東西)本來的知識。如果他們持續嚴肅地研究那些影子,他們會視其為其他的事情發生之後的效果,而不是某些實存之東西,因其自身而衍生的重要的及依因果而生的效應─然而影子之充滿迷惑的閃爍,仍然影響到那些未被解放的囚徒,他們持續地受制於信念主張或言論的某些形式。
就以我們的政治生活作為例子吧。那所謂「影子」可以比喻現代有關「權利」的論述。在1980年代薩達姆‧海珊 使用毒氣殺害他本國的國民,美國卻從後鼓勵支援他,給他武器,宣稱薩達姆‧海珊是(美國的)重要盟友。但突然在1990年代,薩達姆‧海珊卻將自己變成了一個討厭鬼,同時,人們又「發現」他破壞了自己國民的人權,因此,他的國家於是被侵略。伊拉克被國際認為是一個「主權」國家,並且是不同的國際組織的被承認的成員國,而這次侵略乃是不顧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反對而進行的。於第二次侵略之後,負責占領伊拉克的軍事行動的美國指揮官嚴肅地警告伊朗不要違反國際法律─即不要干預伊拉克的「內政」,因為伊拉克是一個有主權的國家。在這脈絡中,那些訴諸人權的人,將「人權」表象為一套有強大力量並且有嚴謹組織的原則的體系,並且可管制在發生的事。然而,如果我們只是簡單地去探究一下「人權」如何在真實的政治脈絡中運作,我們就會感到迷惘而不知何去何從;在上述在此情況中,進行「人權」的分析,嘗試找尋任何有持續性、可信賴的協調,或企圖在其中掌握理性、一致性或實則性,很清楚,是完全徒勞無果的。有一些人會認為在這幢幢黑影,背後屹立著的是法律內合乎規範的真實,或者理想的人權的預算,並且,哲學家的任務就是去把它們揭示出來。就讓我祝福有此種想法的人好運吧,就算他們沒有見過(所謂影子背後的情況),他們確實相信如此。另外一些人就認為,去改變影像、哲學家所奠定的自然定律,或者人權,可說是影子的影子而已─即是說這些事物皆不是堅實確切的真實,反而只是某些人因花了過多時間去觀望影子的變化而產生的幻覺。那麼「理解」,如果它不是百分百「真實」,就得到別處去找尋。依所上述的兩類人的論點而言,沒有人會覺得「理解」,是可以從簡單地透過培育我們學習將這些影子的分類及繪製而獲得。無論所接納的是那兩論點的哪一邊,我們都要改變主題才可以有所進展。我們要麼就需要一套有關人權/自然律例等等的理想論述,要麼就是或需要另外一套有關人們如何行動及說話的理論,而這套理論不會完全只在表面意義上去了解人們的純粹表述。我們可能不是很清楚,所提議的新的勾畫繪製,哪一種最值得去慎重考慮,但所有提議,皆以自己的方法,去嘗試建構某些對立於(前述的)常識的進路:這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下,每一項提議都在正更改主題─或者,這就正是,或,無論如何,哲學到目前為止經歷的情況。
這一本書之所以得以面世,乃是源於兩件性質很不相同的事的偶然契合。第一件事,就是在2010年,位於英國劍橋的海弗斯書店(Heffers)其中一位經理,詢問了在劍橋大學任教的不同學科學者,邀請他們各自提交十本書的書單。選取這十本書的準則,首先是學者們會覺得它們在其學科內是最有趣的,但這不是說這十本書是在歷史上最有影響力,或在目前最為普及,也不是受到最頂級的研究專家最推崇,或達到了文筆最精煉的巨著,或在教學方面是最有用的教學材料。這十本書的揀選原則,很簡單,就是它們向所屬學科貢獻了最佳的嚴肅的研究,因為它們談及了有關這學科本質上的要點。我作為海弗斯書店書局的常客,書局經理於是邀請我為「哲學」這門學科提交那十本書的書單。書局方面另加一項要求,那就是所提議的每個作者,只能揀選她/他一本著作,這條件十分有助於我這項工作─如此就防止了我直接地簡單提交五至六個柏拉圖的對話錄就了事。再者,將提交的書單限制在十本書以內的這個要求,果然在很多方面對智性訓練都是有用的:我草擬書單的最初幾次都不滿意,全失敗了,我到最後才恍然悟到原因─縱使書局已提醒我,在選擇那十本書時要避免的各項條件,但我還是讓自己受到這些條件的影響。我還是考慮到所要揀選的書籍的作者普遍的聲譽、其在歷史性的影響,或在現時在哲學學科內,它是否占中心位置,或甚至在一般教學課程是否中重要的參考。確實是經過了好幾次來來回回的挑選,我才終於從這等考慮中釋放出來─這些考慮如在其他範圍內作為挑選要求,可以是完全適切的,但是,在當今二十一世紀初期,面向廣大的容易旁騖的讀者,如果要決定哪個作品是有力量的、引人入勝的、啟蒙的,並且讓該等讀者認為值得去注目的,上述的揀選書作的條件,可說確實是離題不相關的。
下筆書寫這本書的第二個源起是,我於法語書寫能力方面,實在愧慚,總是屢屢犯錯,造句及詞彙方面又欠缺變化多樣性,滿是贅字冗詞,但我又好像沒有空餘時間去認真地改善這些缺點。當我於2014年1月退休,我便去了劍橋的法國文化協會,商討安排了學習的計畫。我實行了以下的(學習)時間表:每個星期我會寫兩三篇八百至一千字的法語文章,並請法國文化協會的名師和我討論及修改這些習作。我很幸運得到三位法語教師(Anne-Laure Brevet, Isabelle Geisler, Aline Guillermet)的教導。經過了一年多的時間的學習,我認真地覺得我在法語書寫上有了些微進步。但於此同時,一個問題出現了:我已經寫了過百份短文,即是說我需要更多資料,亦即更多的作文題目,去繼續書寫。我開始去翻閱我人生所積累的個人收藏回憶:暗地裡詆毀某些我相識的人的小故事、捏造出來的敘述、夢境、政治評論,假想的書信來往,或翻譯希臘拉丁或德文的短篇文章,又或者我所喜愛的文學作品的短評……,但我感到我已開始重複自己了。我需要一些新鮮的想法和主題,最理想就是一些要求非常不同及比較複雜的句式及字彙的寫作,但也不要讓我本身有限的想像力過度地負擔。在2015年夏天,正當我在清理一些舊檔案時,那一份(在2010年)我替海弗斯書店草擬推薦的哲學書單,竟出現在眼前。自從那時之後,我再也沒有理會過它─我真覺得我找到我所需要的東西。這真是一份甚有價值的書單,我可以開始寫一些跟一直在寫的法語文章很不同的東西:替這十本著作的每一本寫五千至七千字的導讀介紹文章─以每一份習作寫一千字的進度實行。如果這樣安排,再加上另外用我一向的資料來草擬題目而寫的文章,照如此的方法去寫,我可以有足夠最少一年的材料去寫作。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工作的Ian Malcolm,乃是負責我的出版事宜的優秀編輯,他非常有雅量地向我提議,我其實可以用英語(而不是法語)去寫這些哲學著作的導讀,如儲起來就是能夠出版的稿子了。我放棄了海弗斯書店最初定下的選書規則與限制─外在限制很多時都會很有用的,但也無須固執地推崇為不可修正的規矩。將預想介紹的著作從十本增加至十二本,然後到最後添上導論作為第一章,再加一個簡單的結論,如此安排我可由原本設定的範圍稍作擴充。
當我寫這本書之際,我湊巧拿起保羅‧維恩 的自傳來讀,他在書中描述,1950年代的法國高等師範學院所有的學生都熱烈地討論,有關應該成為寫科學論文式的學者、抑或寫散文式評論的作者兩者之間的選擇(a)。我得到的結論就是「散文式評論」的處理正是去書寫這本書的進路─這未必是唯一的方法,但是,如考慮到哲學的本質從過去二千年到現在如何被普遍地理解的脈絡,這個處理的方法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哲學史是一門備受尊重以及重要的研讀的科目,我們一定要具備文獻學的準確標準、對歷史的嚴謹、詮釋學的技能,以及分析性的敏銳,才能有資格去研究撰寫。然而,這一本書的目的並不是打算作為一項對哲學史(或任何其他附屬學科的)研究的貢獻。這本書企圖面對的讀者群,並不是學術界專家學者,反之,這本書的內容,乃是一系列我有興趣的課題,而我所採取的,乃是在學術上比較輕鬆的,散文式導論的寫作風格。在本書中我會對某些歷史文獻做出討論。這本書的理想讀者,應該是有一定學識,但卻沒有特別接受過學院式哲學訓練的諸君,他們會認為,哲學家會不時提出一些有趣的問題,故此希望嘗試清楚了解,是否真是如此有趣,同時,讀者們可能會想知道,這些問題可能會是甚麼模樣,也有興趣更進一步去思考它們。
雖然這本書並不假設讀者有任何哲學知識,同時在每一章節我都嘗試盡力做最清楚及簡潔的展述,然而這一本書也確實有一個循序漸進的累積性的結構。因此之故,如果讀者能從頭開始,並且順序地一個跟一個章節地讀下去,應該會覺得較為有效地吸收;反之,如果視各個章節為個別獨立的散文文章而隨意選讀,那可能會較難理解。
我一定要說明,這一類型的著作,尤其是歷史方面或詮釋方面的錯誤,是難以避免的。當然,我會儘量對所有參考的文本做正確的閱讀─如果不是這樣,有甚麼理由書寫此書呢?─但是,我真正的關注是在於,不管所揀選的文本是否在歷史過程中不斷地被錯誤詮釋,它們如何能保持我期望它們所擁有的價值。在研讀文獻之時,也同時會出現某些扭曲,原因正是我企圖集中注意力於參考文獻內,我認為最應該要再三深究的部分;換句話說,這等文獻中有其他部分,是我覺得較沒有興趣的,我可能會對它們疏於處理或完全忽略。很明顯,「值得深究」並不等如「真」的意思。我也察覺到,很可能會有很多讀者覺得,對於書中論及的參考資料所含藏的重要思想向度,我這種進路的態度未免太輕鬆了,對這些讀者諸君而言,一定會找到很多適合的口味的(其他)的著作。對某些讀者來說,本書的某部分課題可能不是太熟識,有關這個問題我會借用十九世紀初作家讓‧保羅 ,談及其作品《美學初階》(Vorschule der Ästhetik)的一段話回答:
Es wird doch jeder mehr als eine-meine-Ästhetik in der Studierstube haben. Gut, was also in meiner fehlt, das ergänz’ er sich aus der ersten besten; warum soll ich eine erste beste schreiben, da sie ohnehin schon oft genug da ist.(b)
任何閱讀這本書的讀者,都通常會(除我所著這本以外)有至少一本有關「美學」的書籍在他的書架上。因此這位讀者如果發現在拙著中缺失了甚麼,很容易在其他(美學上的)「標準處理」著作中找到補充;既然已經有那麼多標準處理的著作,我又為何再多寫一本同樣的書呢?
因為我的企圖是儘量將這文本保持在簡明及基礎程度上,也可能因為我的記憶力也漸漸不大靈光,我知道我可能從別人那裡借用了一些要點─有時從他們的對話,有時從他們的寫作,有時從他們的出版著作等─但沒有以附註去標明出處。我毫不保留地請求有關人士多多見諒。
我由衷地感激Alex Englander, Lorna Finlayson, Peter Garnsey, Gérald Garutti, Alexis Papazoglu, Richard Raatzsch, Tom Stern, and Eva von Raedecker 各位,在過去五至六年,和我討論在本書內處理的各個題目。我也很感激哈佛大學出版社的兩位閱讀/校稿人員,他們所寫的報告讓我在最後一稿中避免了或修正了一系列的錯誤、引起誤會的陳述、不貼切的詞句。請讓我對Hilary Gaskin表達最大的謝意,她的評語讓我改善了所寫的每一頁。同時,在任何情況之下,她是讓本書得以完成不可或缺的人。
在所有文獻著作中,包括所有哲學文獻,最令人震撼的影像,可說是在柏拉圖的《理想國》的第七卷中所描述的一幕:在一個地底的洞穴,被囚禁的人群被鐵鍊鎖著,他們背後有一光源。眾人自出生開始便被囚禁,一生也是這樣,每天就是觀望在他們眼前顯現的,投影在牆上的幢幢影子中度過。這些影子漸現形狀,搖曳不停,又不時重疊,消溶不見,(有時)又會重現,還時不時會合成有規則的圖案,又有時隨機地一個圖案接著另一個圖案出現,但在其他時間它們好像會展示某種的規則秩序。有部分囚徒漸漸學習適應了那些影子出沒的序列,對其做出描畫,即在有限範圍內,掌握影子的出現與隱沒的規律性─稱為「常識」的,就是囚徒們在學習影子出沒的規則過程中,所發展出來的「技巧」。
柏拉圖提議:假設有人讓幾個囚徒獲得自由,讓他們轉身,迫他們從背向而轉身面對光源,同時讓他們看見那些投射了影子在牆上的東西─他們花了一生人只觀看到影子的那些東西。柏拉圖說,這些(被釋放的)囚徒很可能會感到目眩、盲目及感到沮喪。這樣迫他們轉身去看,釀成了痛苦與失去方向,毀滅了他們不斷辛勞地學習而獲得的常識,但是,如要真正理解他們生活在其中的世界,這毀滅是啟蒙過程中必然附隨之事。到了最後─這「最後」可能是指涉頗長的時段─那些被解放的囚徒所學習到對影子變化(的規律)的理解,可能比起那些從來未被解放的囚徒所學的更佳,因為他們有可能掌握到一些有關真實的東西(即那些將影子投射在牆壁上的東西)本來的知識。如果他們持續嚴肅地研究那些影子,他們會視其為其他的事情發生之後的效果,而不是某些實存之東西,因其自身而衍生的重要的及依因果而生的效應─然而影子之充滿迷惑的閃爍,仍然影響到那些未被解放的囚徒,他們持續地受制於信念主張或言論的某些形式。
就以我們的政治生活作為例子吧。那所謂「影子」可以比喻現代有關「權利」的論述。在1980年代薩達姆‧海珊 使用毒氣殺害他本國的國民,美國卻從後鼓勵支援他,給他武器,宣稱薩達姆‧海珊是(美國的)重要盟友。但突然在1990年代,薩達姆‧海珊卻將自己變成了一個討厭鬼,同時,人們又「發現」他破壞了自己國民的人權,因此,他的國家於是被侵略。伊拉克被國際認為是一個「主權」國家,並且是不同的國際組織的被承認的成員國,而這次侵略乃是不顧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反對而進行的。於第二次侵略之後,負責占領伊拉克的軍事行動的美國指揮官嚴肅地警告伊朗不要違反國際法律─即不要干預伊拉克的「內政」,因為伊拉克是一個有主權的國家。在這脈絡中,那些訴諸人權的人,將「人權」表象為一套有強大力量並且有嚴謹組織的原則的體系,並且可管制在發生的事。然而,如果我們只是簡單地去探究一下「人權」如何在真實的政治脈絡中運作,我們就會感到迷惘而不知何去何從;在上述在此情況中,進行「人權」的分析,嘗試找尋任何有持續性、可信賴的協調,或企圖在其中掌握理性、一致性或實則性,很清楚,是完全徒勞無果的。有一些人會認為在這幢幢黑影,背後屹立著的是法律內合乎規範的真實,或者理想的人權的預算,並且,哲學家的任務就是去把它們揭示出來。就讓我祝福有此種想法的人好運吧,就算他們沒有見過(所謂影子背後的情況),他們確實相信如此。另外一些人就認為,去改變影像、哲學家所奠定的自然定律,或者人權,可說是影子的影子而已─即是說這些事物皆不是堅實確切的真實,反而只是某些人因花了過多時間去觀望影子的變化而產生的幻覺。那麼「理解」,如果它不是百分百「真實」,就得到別處去找尋。依所上述的兩類人的論點而言,沒有人會覺得「理解」,是可以從簡單地透過培育我們學習將這些影子的分類及繪製而獲得。無論所接納的是那兩論點的哪一邊,我們都要改變主題才可以有所進展。我們要麼就需要一套有關人權/自然律例等等的理想論述,要麼就是或需要另外一套有關人們如何行動及說話的理論,而這套理論不會完全只在表面意義上去了解人們的純粹表述。我們可能不是很清楚,所提議的新的勾畫繪製,哪一種最值得去慎重考慮,但所有提議,皆以自己的方法,去嘗試建構某些對立於(前述的)常識的進路:這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下,每一項提議都在正更改主題─或者,這就正是,或,無論如何,哲學到目前為止經歷的情況。
這一本書之所以得以面世,乃是源於兩件性質很不相同的事的偶然契合。第一件事,就是在2010年,位於英國劍橋的海弗斯書店(Heffers)其中一位經理,詢問了在劍橋大學任教的不同學科學者,邀請他們各自提交十本書的書單。選取這十本書的準則,首先是學者們會覺得它們在其學科內是最有趣的,但這不是說這十本書是在歷史上最有影響力,或在目前最為普及,也不是受到最頂級的研究專家最推崇,或達到了文筆最精煉的巨著,或在教學方面是最有用的教學材料。這十本書的揀選原則,很簡單,就是它們向所屬學科貢獻了最佳的嚴肅的研究,因為它們談及了有關這學科本質上的要點。我作為海弗斯書店書局的常客,書局經理於是邀請我為「哲學」這門學科提交那十本書的書單。書局方面另加一項要求,那就是所提議的每個作者,只能揀選她/他一本著作,這條件十分有助於我這項工作─如此就防止了我直接地簡單提交五至六個柏拉圖的對話錄就了事。再者,將提交的書單限制在十本書以內的這個要求,果然在很多方面對智性訓練都是有用的:我草擬書單的最初幾次都不滿意,全失敗了,我到最後才恍然悟到原因─縱使書局已提醒我,在選擇那十本書時要避免的各項條件,但我還是讓自己受到這些條件的影響。我還是考慮到所要揀選的書籍的作者普遍的聲譽、其在歷史性的影響,或在現時在哲學學科內,它是否占中心位置,或甚至在一般教學課程是否中重要的參考。確實是經過了好幾次來來回回的挑選,我才終於從這等考慮中釋放出來─這些考慮如在其他範圍內作為挑選要求,可以是完全適切的,但是,在當今二十一世紀初期,面向廣大的容易旁騖的讀者,如果要決定哪個作品是有力量的、引人入勝的、啟蒙的,並且讓該等讀者認為值得去注目的,上述的揀選書作的條件,可說確實是離題不相關的。
下筆書寫這本書的第二個源起是,我於法語書寫能力方面,實在愧慚,總是屢屢犯錯,造句及詞彙方面又欠缺變化多樣性,滿是贅字冗詞,但我又好像沒有空餘時間去認真地改善這些缺點。當我於2014年1月退休,我便去了劍橋的法國文化協會,商討安排了學習的計畫。我實行了以下的(學習)時間表:每個星期我會寫兩三篇八百至一千字的法語文章,並請法國文化協會的名師和我討論及修改這些習作。我很幸運得到三位法語教師(Anne-Laure Brevet, Isabelle Geisler, Aline Guillermet)的教導。經過了一年多的時間的學習,我認真地覺得我在法語書寫上有了些微進步。但於此同時,一個問題出現了:我已經寫了過百份短文,即是說我需要更多資料,亦即更多的作文題目,去繼續書寫。我開始去翻閱我人生所積累的個人收藏回憶:暗地裡詆毀某些我相識的人的小故事、捏造出來的敘述、夢境、政治評論,假想的書信來往,或翻譯希臘拉丁或德文的短篇文章,又或者我所喜愛的文學作品的短評……,但我感到我已開始重複自己了。我需要一些新鮮的想法和主題,最理想就是一些要求非常不同及比較複雜的句式及字彙的寫作,但也不要讓我本身有限的想像力過度地負擔。在2015年夏天,正當我在清理一些舊檔案時,那一份(在2010年)我替海弗斯書店草擬推薦的哲學書單,竟出現在眼前。自從那時之後,我再也沒有理會過它─我真覺得我找到我所需要的東西。這真是一份甚有價值的書單,我可以開始寫一些跟一直在寫的法語文章很不同的東西:替這十本著作的每一本寫五千至七千字的導讀介紹文章─以每一份習作寫一千字的進度實行。如果這樣安排,再加上另外用我一向的資料來草擬題目而寫的文章,照如此的方法去寫,我可以有足夠最少一年的材料去寫作。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工作的Ian Malcolm,乃是負責我的出版事宜的優秀編輯,他非常有雅量地向我提議,我其實可以用英語(而不是法語)去寫這些哲學著作的導讀,如儲起來就是能夠出版的稿子了。我放棄了海弗斯書店最初定下的選書規則與限制─外在限制很多時都會很有用的,但也無須固執地推崇為不可修正的規矩。將預想介紹的著作從十本增加至十二本,然後到最後添上導論作為第一章,再加一個簡單的結論,如此安排我可由原本設定的範圍稍作擴充。
當我寫這本書之際,我湊巧拿起保羅‧維恩 的自傳來讀,他在書中描述,1950年代的法國高等師範學院所有的學生都熱烈地討論,有關應該成為寫科學論文式的學者、抑或寫散文式評論的作者兩者之間的選擇(a)。我得到的結論就是「散文式評論」的處理正是去書寫這本書的進路─這未必是唯一的方法,但是,如考慮到哲學的本質從過去二千年到現在如何被普遍地理解的脈絡,這個處理的方法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哲學史是一門備受尊重以及重要的研讀的科目,我們一定要具備文獻學的準確標準、對歷史的嚴謹、詮釋學的技能,以及分析性的敏銳,才能有資格去研究撰寫。然而,這一本書的目的並不是打算作為一項對哲學史(或任何其他附屬學科的)研究的貢獻。這本書企圖面對的讀者群,並不是學術界專家學者,反之,這本書的內容,乃是一系列我有興趣的課題,而我所採取的,乃是在學術上比較輕鬆的,散文式導論的寫作風格。在本書中我會對某些歷史文獻做出討論。這本書的理想讀者,應該是有一定學識,但卻沒有特別接受過學院式哲學訓練的諸君,他們會認為,哲學家會不時提出一些有趣的問題,故此希望嘗試清楚了解,是否真是如此有趣,同時,讀者們可能會想知道,這些問題可能會是甚麼模樣,也有興趣更進一步去思考它們。
雖然這本書並不假設讀者有任何哲學知識,同時在每一章節我都嘗試盡力做最清楚及簡潔的展述,然而這一本書也確實有一個循序漸進的累積性的結構。因此之故,如果讀者能從頭開始,並且順序地一個跟一個章節地讀下去,應該會覺得較為有效地吸收;反之,如果視各個章節為個別獨立的散文文章而隨意選讀,那可能會較難理解。
我一定要說明,這一類型的著作,尤其是歷史方面或詮釋方面的錯誤,是難以避免的。當然,我會儘量對所有參考的文本做正確的閱讀─如果不是這樣,有甚麼理由書寫此書呢?─但是,我真正的關注是在於,不管所揀選的文本是否在歷史過程中不斷地被錯誤詮釋,它們如何能保持我期望它們所擁有的價值。在研讀文獻之時,也同時會出現某些扭曲,原因正是我企圖集中注意力於參考文獻內,我認為最應該要再三深究的部分;換句話說,這等文獻中有其他部分,是我覺得較沒有興趣的,我可能會對它們疏於處理或完全忽略。很明顯,「值得深究」並不等如「真」的意思。我也察覺到,很可能會有很多讀者覺得,對於書中論及的參考資料所含藏的重要思想向度,我這種進路的態度未免太輕鬆了,對這些讀者諸君而言,一定會找到很多適合的口味的(其他)的著作。對某些讀者來說,本書的某部分課題可能不是太熟識,有關這個問題我會借用十九世紀初作家讓‧保羅 ,談及其作品《美學初階》(Vorschule der Ästhetik)的一段話回答:
Es wird doch jeder mehr als eine-meine-Ästhetik in der Studierstube haben. Gut, was also in meiner fehlt, das ergänz’ er sich aus der ersten besten; warum soll ich eine erste beste schreiben, da sie ohnehin schon oft genug da ist.(b)
任何閱讀這本書的讀者,都通常會(除我所著這本以外)有至少一本有關「美學」的書籍在他的書架上。因此這位讀者如果發現在拙著中缺失了甚麼,很容易在其他(美學上的)「標準處理」著作中找到補充;既然已經有那麼多標準處理的著作,我又為何再多寫一本同樣的書呢?
因為我的企圖是儘量將這文本保持在簡明及基礎程度上,也可能因為我的記憶力也漸漸不大靈光,我知道我可能從別人那裡借用了一些要點─有時從他們的對話,有時從他們的寫作,有時從他們的出版著作等─但沒有以附註去標明出處。我毫不保留地請求有關人士多多見諒。
我由衷地感激Alex Englander, Lorna Finlayson, Peter Garnsey, Gérald Garutti, Alexis Papazoglu, Richard Raatzsch, Tom Stern, and Eva von Raedecker 各位,在過去五至六年,和我討論在本書內處理的各個題目。我也很感激哈佛大學出版社的兩位閱讀/校稿人員,他們所寫的報告讓我在最後一稿中避免了或修正了一系列的錯誤、引起誤會的陳述、不貼切的詞句。請讓我對Hilary Gaskin表達最大的謝意,她的評語讓我改善了所寫的每一頁。同時,在任何情況之下,她是讓本書得以完成不可或缺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