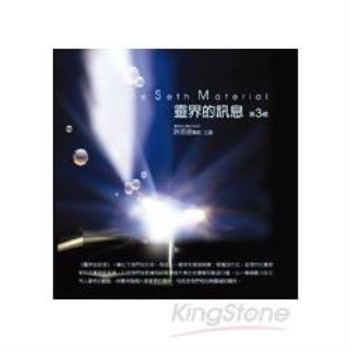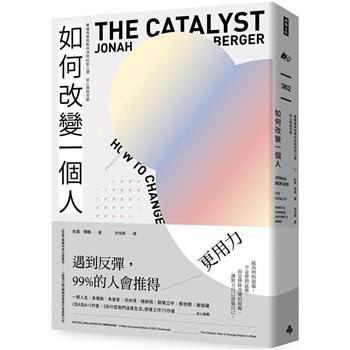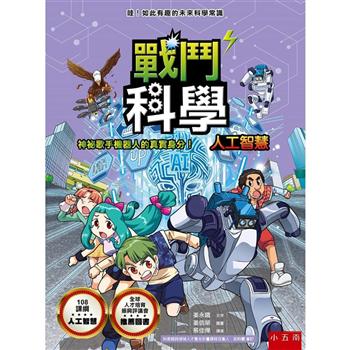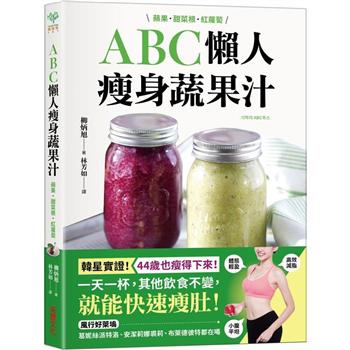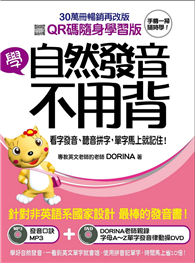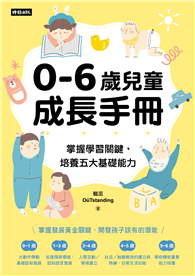【美的邀請】
美不介意回答問題,而且她喜愛謎語。任何有勇氣邀請她的人,美都將與之共舞。
就像水一樣,美既是尋常而必要的,又不同凡俗,撼動人心。
美如水一般,以許多形式呈現,無所不在。美也是同樣地流轉、積聚、傾注。觀看並傾聽雨如何改變世界,徒步或在飛機上凭窗尋溯河流的軌跡,在海洋邊緣談話,在瀑布底下游泳,這些經驗都如此美好。
我們在許多經驗的交會、邊緣和核心發現美。雖然我們不斷試著談論內在或外在的美,所用的語言卻過於靜滯,試圖將美固定於單一的位址。美是能量,而非形象,那種能量可以到任何地方;那種能量展現為某種形象、某種形式、許多形象、許多形式。
身為視覺藝術家,我經常從視覺的角度思考美,雖然我很少刻意製作美麗的藝術品。藝術創作是一種觀看的過程,當我們看得更深入,便會在意外之處發現美。當一個藝術家,讓我以特殊的方式練習拓展視覺,並運用感官的知能;我的雙手知道如何創造秩序,如何將一塊石頭擺在另一塊旁邊,彷彿那是一種語言。藝術創作是我理解世界、看待自身經驗的方式之一。我開始畫一些心中有葉片的人,然後驚異地發現,這些葉人愈看愈像天使。一種形狀變成其他形狀。葉片變成火焰變成翅膀。
美的研究其實是許多層次的搜尋。我渴望掙脫習慣的模式,向外觀看各種不同的文化。在這些文化中,「神秘」仍然活著,人們將更多時間投注於慶祝、交換禮物、舞蹈、演奏音樂。有幾次最重要的旅行,是以藝術家與詩人的身分造訪學校。一名青少年寫道:「美不喝沛綠雅礦泉水。美不吃迷你三明治配下午茶。美不穿蕾絲睡袍。因為美忙著照料中國的稻田。」
我研究美的目的不在證明某項學術論點;我心中並沒有單一的看法或理論。我所做的是探索和頌揚美,感覺美既珍貴又尋常──它太少出現於我們的文化和日常生活中,但只要稍加留意,它又隨處可得。
還記得荷柏特(Anne Herbert)「隨緣行善,無需理由地表現美」的說法剛出現不久,便成為大家傳誦的名言。人們喜愛這句話,因為它將美與善牽繫在一起,使美超越美學的領域,回歸心靈。美讓我們在一成不變的軌道上停下腳步,將我們抽離自我,同時又帶我們進入本心。我們活在如此遠離生命本質的時空中,如何能知曉真正的甘美為何物?
心理學家希爾曼(James Hillman)的陳述:美是「諸神碰觸我們的感官、感動人心、並吸引我們投入生命」的方式。希爾曼的定義並未說明美是什麼,卻暗示了美如何讓人融入世界。美並非偶然、瑣碎、無足輕重;相反地,它位居核心,攪動我們的心靈和敏感的身體,以它的直接和愉悅吸引我們投入生命。
在我們所生活的時代,處處可見已被證實的危機──環境危機、教育危機、社會危機;錯誤、醜陋、失衡的事物經常令人不知所措,麻木不仁。無論就個人或文化而言,我們所需要的治療,不能只來自於實際的解決辦法和處方,也必須來自於許多對於完整和神聖的憧憬、對於美的憧憬。我們必須從容而耐心地發現,對每個人來說,什麼是美的,其美好的程度足以讓我們願意保護並珍惜它,改變我們的生活;那是一種內在固有的美,使萬物井然有序,賦予世界意義和目的。
這本書邀請你擴展並深化你對於美的感受。它尊崇美──這種性質不僅是實質的,也是精神上的,存在於我們之內、我們之間、我們之中。我們體驗不到美的原因之一,是我們移動得太快,以至於無法敞開胸襟、盡情感受周遭的事物。美需要時間展現,當我們不斷超前自己時,便錯失了許多美的體驗。
《關於美之必要》(Notes on the Need for Beauty)這個書名體現了本書的精髓,它告訴讀者,書中充滿環繞著美這種性質的想法、故事、反省,以及情感豐富的探索。「筆記」的英文notes亦有音符之意,令人聯想到音樂的語言。強調對於美的需求,則是因為人們已經忘卻美如何賦予生命意義和目的。美使我們回歸平凡、質樸、塵俗中的神聖;它滋養、更新、攪擾、安撫、並喚醒我們。美透過關注而展現;藉由注意細節,我們發現美以千變萬化的型態閃耀在生活中,以超脫凡俗的方式深植於靈魂內。
《關於美之必要》是從我與許多人的交談中發展出來的:園藝家和建築師、舞者和教師、美容師、治療師,還有科學家。傾聽人們的故事──關於刺青與錶、楓樹與化妝、最喜愛的衣服與旅行、美容祕方與愛情故事──我聽到美如何融入日常生活、人性與環境。美展現在交談的精神中,我們的交談往返迴旋,暫停,輕吟,引發更深入的交談。
【鏡與窗】
我想起自己最喜愛的一個問題:鏡子和窗子有何不同?我們為了看見自己而注視鏡中;為了看見世界而望向窗外。鏡子將事物反轉;倘若我們取法於鏡,也許能注視鏡中而看見世界,望向窗外而發現自己。
嚴格說來,窗與鏡的差異在於,窗子傳送光,鏡子則反射光。我們的眼睛是鏡子也是窗,會反射、聚集、傳送光。我們是鏡子,懷著興趣與關注向彼此展現自己;我們是窗,在彼此熟悉的世界向陌生的風景開啟。我們從眼睛之窗的背後往外看。於是,內在的光遇見並招呼外在的光。鏡與窗成為另一種談論洞見(insight)和看法(outlook)──也就是「看見」(seeing)的雙重性質──的方式。
鏡:反映認同,展現靈魂
我們的鏡像,就像影子、照片一般,具有神秘難解的性質──彷彿有一部分的我們,活在那兩度空間的化身之中。古代的埃及人和中國人以鏡子陪葬,相信它們是靈魂邁向來世的必要工具。在哀悼死者的過程中,東歐人和正統猶太教徒會遮蓋屋裡的鏡子,以便專注於內心,避免讓塵俗的事物分散注意力。對海地人來說,鏡子代表神明的水域,人死後,靈魂會在那裡居住一年。西藏人在脖子上戴著銀鏡。東印度有一項風俗:新娘第一次注視夫婿時,應該是透過她手上的鏡面戒指。
從有鏡子以來,它不僅被當成實用的物體,也被用做通往永恆的管道。鏡子通常令人聯想到外觀的世界、室內裝飾、裝飾本身、幻象與虛榮。然而,鏡子也告訴我們邁向自我了解的歷程,引導我們培養愈漸準確的感知和真正的洞見。
中國和西藏的佛教徒,發展出滌洗、淨化並照亮心靈的儀式,方法是擦亮一面鏡子,鏡中反映出佛的形象。中國的鏡子是一種有形體的隱喻,象徵智慧:鏡子接受光而反映真理。早期的中國鏡子是備受重視的護身符,被尊為宇宙的象徵,並且在特殊節日、婚禮和國家場合中被當成禮物贈與。
生活中有更多鏡子,是否使我們更加了解自己?我不知道。也許這只讓我們變得更忸怩不安,更挑剔自己。我們對自己的外貌意見很多,卻不知自己真正的模樣。我們很少好好看自己,卻多方設想別人怎麼看我們。
人際關係之鏡
我最喜歡的一條字典定義,將鏡子描述為「任何忠實反映或如實呈現另一事物的東西。」我們也是彼此的鏡子。我們渴望被看見;我們急切地想被呈現、被反映、被了解。藉由看彼此的臉,我們開始認識彼此;對於眼中所見的情緒和相貌,我們時而受到吸引,時而退避。生氣蓬勃或脆弱、乖戾或溫柔──我們在別人臉上遇見自己,發現令人害怕或愉悅的模樣和表情。身為鏡子,我們為彼此提供多重的印象。我注視著你,為的是要發現你和發現我自己,重新發現你和重新發現我自己。
我們預期在窗外發現世界,在鏡中發現自己。
通往美的窗
鏡子變成了一扇窗:我們是彼此的鏡子,而突然間,我們發現自己也是窗,各自開向各種不同的世界;缺少了彼此,我們便無法認識這些世界。
我生命中的窗子總是不斷邀請我去探索,讓心靈旅行,甚至當我必須待在原地時也不例外。窗子提醒我,在這個讓我花太多時間坐在電腦前的小書房之外,還有一個美妙的世界。記得在我租住多年的屋裡,小臥室的平開窗朝東面向柏克萊丘陵,就像我在佛羅倫斯當學生時,住在大小如衣櫃的房間,窗子面向托斯卡尼山城菲耶索萊(Fiesole)。我最愛在一大早推開窗戶,跟清晨打招呼,深吸一口氣,眺望藍綠色的丘陵。
藝術:鏡與窗
觀賞藝術的必要,以及它為心靈帶來的滋養,可能就像打開一扇窗、或透過鏡中回望自己的眼睛來檢視靈魂。藝術提供了一扇向自我與他者開啟的窗。而是一個開口,讓我們望向自己之外,也望進自己之中。藝術反映並傳送光亮與黑暗、精神與靈魂、體悟、以及新視野所帶來鼓舞人心又振奮精神的挑戰。
藝術幫助我們越過自己,望進另一個人的心智與時間。同一幅藝術作品朝著多種方向旅行,將我們帶到各種目的地,沿途提供許多駐足之處。。藝術家把她的視覺和想像給了我們,將它轉化為形狀與色彩、質地與線條;我們收受這份禮物,並不是透過疏離的分析,而是透過自己的視覺、自己的想像。承載生命的藝術滋養了心靈的眼睛。
【記得身體的歌】
當我們把身體當成機器看待,或是以機器來象徵身體時,會出現什麼狀況?許多故事暗示,當人以機器為典範,試圖仿效機器時,機器將採取報復行動,轉而攻擊人類。然而,所謂的報復,也許只是人為了機械化的生活而犧牲身體。當我們不再體會豐富而微妙的感官層次時,感官就會變得遲鈍。我們追求更極端的感覺,以便覺得自己還活著;我們用更多藥物來刺激或緩和情緒。
思考身體如何不同於機器,促使我與自己的身體建立更密切的關係。我體驗到更細膩的情感紋理與微妙的生理知覺,注意到自己的各種節奏:動作與情緒、休息與復原。
身體不是機器。身體感覺愉悅、狂喜和疲憊的能力教人驚奇。我們需要休息,我們需要親密。我們會遲到,會愛上無法與自己相處的人。就像需要食物一般,我們需要美,無論我們是在藝術、音樂、古董、動物、山巒或彼此身上找到它。美滋養精神,餵飽靈魂。
世界透過身體的感官進入我們的生命,我們品嚐自己的生命。體驗身體的韻律有如行走在美之中,帶著不確定的感覺前行,在生命中體認死亡。
探究身體如何不同於機器,使我們領悟到自己的本質、生命力的美,以及賦予我們生氣的光和精神。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見並讚美生命的神聖之處。
廣告說:身體是一門生意。
企業廣告可能是人類所從事最大的心理活動,但西方心理學卻一直忽視它的影響:「我們認為在美國社會中,有一種在觀念上特別適合消費主義的自戀心態,而大規模的廣告,便是創造並維持這種自戀心態的主要因素之一。」
廣告媒體不斷在我們耳邊低語,說我們的人生有所缺憾。我們如何開始了解什麼能滋養我們的生命?──在廣告的巧妙說服之下,我們已深信自己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的東西。我們被灌輸了這麼多別人的形象與夢想,如何能再關注自己的形象和夢想?
批評消費主義的揮霍無度和廣告的陰險狡詐,並不等於禁止人享受新毛衣、美味鬆餅、優質乳霜或滑雪假期所帶來的愉悅。感覺細膩的靈魂會享受物質世界,但享受物質世界並不等於購買享受。
現代生活的速度、過度工作的壓力,以及與自然世界的疏離,都損害了我們的健康和幸福,削弱我們體會自己生活中的美的能力。身體需要並喜歡休息、美食、與親友相處和動手創作的時間。失去了能夠享受單純愉悅的時間,我們變得更容易受行銷文化左右。培養友誼需要時間;體驗生活的向度與質感也需要時間。如果總是匆匆忙忙,就沒有時間在生活的核心感受自己。
花一個星期觀看媒體給予心智、身體和靈魂的訊息。這些形象(關於身體是什麼、身體看起來像什麼、身體應該做什麼)阻絕了身體自己的經驗,直到我們擁有的只剩關於形象的形象。
【結語】
美,尤其是自然界的美,喚醒我們,使我們體驗到活潑的靜定,感受到驚奇與敬畏。它放鬆我們的下顎、腹部和憂慮的前額,安撫我們的心。卡森(Rachel Carson)寫道:「那些居住在大地之美與神秘中的人,無論是科學家或外行人,從來不會單獨無依,或厭倦生命。不管他們的個人生活中有什麼煩惱或憂慮,他們的思想總能找到途徑,通往內在的滿足,重新感到活著的興奮。那些思索大地之美的人,會發現力量的泉源,終生取之不竭。在候鳥的遷徙中,在潮起潮落中,在迎春待放的蓓蕾中,不僅存在著象徵的美,也存在著實際的美。在大自然重複吟唱的歌聲中──它保證黎明將在黑夜之後到來,春天將於寒冬之後降臨──蘊含著無限的療癒力量。」
美將我們連結到神聖的事物。在「祝福禮典」(那一直是一本充滿美的書)中,我們讚美感官,我們讚美靈魂,是感官在讚美感官,是靈魂在讚美靈魂。
美活在祖傳的蘋果樹裡,在種子裡,在柔軟奢華的喀什米爾羊毛裡,在許多我不常想到的事物中──摩托車經銷商和廢物堆積場、醫院走廊、動過手術者虛弱而猶疑的腳步、從飛機上鳥瞰的河流線條和森林原野的拼貼圖案、山頂與最低層的浮雲彼此交換的雪。
我們是旅人,是過客。我們屬於此時此地。在追尋自我的成長過程中,我們遇見彼此。天使墜入愛河,墜入生命之中。我們在花園和森林中找到美。讓我們開始頌揚世界的美。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露絲.詹德勒的圖書 |
 |
$ 110 ~ 264 | 關於美之必要-LIGHT 011
作者:露絲.詹德勒 出版社:天下雜誌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關於美之必要
美搭起橋樑,連結感官與靈魂、沈思與表達,以及我們自己與世界
書寫美,感覺有如掬飲清泉。泉水甘甜可口;清新而純淨得令人驚奇。長久以來,我一直喝著平淡的水,忘了水的滋味可以如此甘美。就像水一樣,美既是尋常而必要又不同凡俗,撼動人心。美如水一般,以許多形式呈現,無所不在。
在這本內容豐富而感受深刻的書中,詹德勒(J. Ruth Gendler)邀請我們重新擁有經常被誤解的性質──美,體認它是生命中最深刻的力量之一。詹德勒根據她對於藝術、自然、當代文化與個人經驗的觀察,探討這個主題最豐富的含意──它不僅是表面與形象的反映,也是通往完整、真誠、連貫與愛的途徑。
詹德勒認為,「我們體驗不到美的原因之一,是我們移動得太快,以至於無法敞開胸襟、盡情感受周遭的事物。美需要時間展現,當我們不斷超前自己時,便錯失了許多美的體驗。」
本書以好奇、勇氣、敏銳的眼光與富含詩意的感性寫成,配上動人的插畫,展現強烈的個人風格,這是一部值得品味和分享的作品。
章節試閱
【美的邀請】 美不介意回答問題,而且她喜愛謎語。任何有勇氣邀請她的人,美都將與之共舞。就像水一樣,美既是尋常而必要的,又不同凡俗,撼動人心。 美如水一般,以許多形式呈現,無所不在。美也是同樣地流轉、積聚、傾注。觀看並傾聽雨如何改變世界,徒步或在飛機上凭窗尋溯河流的軌跡,在海洋邊緣談話,在瀑布底下游泳,這些經驗都如此美好。我們在許多經驗的交會、邊緣和核心發現美。雖然我們不斷試著談論內在或外在的美,所用的語言卻過於靜滯,試圖將美固定於單一的位址。美是能量,而非形象,那種能量可以到任何地方;那種...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露絲.詹德勒 譯者: 楊雅婷
- 出版社: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8-12-30 ISBN/ISSN:978986658270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2頁
- 類別: 中文書> 藝術> 藝術總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