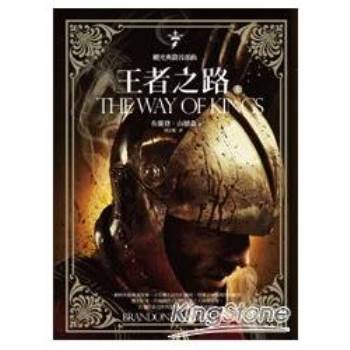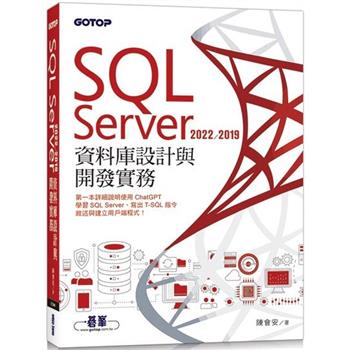◎ 第一部全面探討東亞康德哲學的專著。
◎ 完整呈現康德哲學傳東亞的過程,以及各國康德研究的意義與課題。
◎ 本書由臺、中、日、韓學者共同合作,並以中、日、韓文出版,為東亞學術交流史上一大成就。
在西方哲學的發展當中,十八世紀的德國哲學家康德無疑是最受矚目的一位,他集西方傳統哲學之大成,也是現代西方哲學的共同源頭,具有承先啟後之關鍵地位。康德哲學於十九世紀中葉逐步傳入中國與日本、二十世紀初傳入韓國,迄今已超過一百多年,對現代東亞文化具有難以估計的影響。
本書是第一部全面探討東亞學界如何接受與吸收康德哲學的專門論著,書中從接受史的角度闡述康德哲學傳入臺灣、中國、日本與韓國的過程;並從跨文化的視野,深入分析在此過程中涉及的哲學問題。誠如前輩康德專家鄭昕所言:「超過康德,可能有新哲學,掠過康德,只能有壞哲學。」東亞各國對康德哲學的受容,並非只是被動吸收,而是反應各國學界所面臨的不同課題,呈現出多元化的樣貌。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韓慈卿的圖書 |
 |
$ 220 ~ 270 | 康德哲學在東亞
作者:李明輝/編,李秋零,牧野英二,白琮鉉,韓慈卿/著 / 譯者:廖欽彬,朴敬淑,鄭宗模 出版社: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16-08-18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精裝 / 352頁 / 15 x 21 x 3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康德哲學在東亞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編者簡介
李明輝
德國波昂(Bonn)大學哲學博士。曾任廣州中山大學長江講座教授。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合聘教授、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合聘教授。主要著作有《儒家與康德》、《儒學與現代意識》、《康德倫理學與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當代儒學之自我轉化》、《孟子重探》、《四端與七情──關於道德情感的比較哲學探討》、《儒家視野下的政治思想》、《康德倫理學發展中的道德情感問題》(德文)、《儒家思想在現代中國》(德文)、《儒家人文主義──跨文化脈絡》(德文)。譯作有康德的《通靈者之夢》、《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康德歷史哲學論文集》、《未來形上學之序論》及《道德底形上學》等。
李明輝
德國波昂(Bonn)大學哲學博士。曾任廣州中山大學長江講座教授。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合聘教授、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合聘教授。主要著作有《儒家與康德》、《儒學與現代意識》、《康德倫理學與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當代儒學之自我轉化》、《孟子重探》、《四端與七情──關於道德情感的比較哲學探討》、《儒家視野下的政治思想》、《康德倫理學發展中的道德情感問題》(德文)、《儒家思想在現代中國》(德文)、《儒家人文主義──跨文化脈絡》(德文)。譯作有康德的《通靈者之夢》、《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康德歷史哲學論文集》、《未來形上學之序論》及《道德底形上學》等。
目錄
總 序 黃俊傑
序 言 李明輝
康德哲學在現代中國──李明輝
一、康德哲學開始傳入中國
二、蔡元培、張君勱與康德哲學
三、牟宗三與康德哲學
四、中國馬克思主義與康德哲學
五、中國自由主義與康德哲學
六、結語
中國大陸1949年之後的康德研究──李秋零
一、自1949年至1978年的康德研究
二、1978年以降的康德研究
戰後臺灣的康德研究──李明輝
一、臺灣康德研究的主要推手︰牟宗三
二、牟宗三影響下的康德研究
三、黃振華的康德研究
四、康德哲學的闡述與翻譯
五、康德哲學在臺灣的發展
日本的康德研究史與今日的課題(1863-1945)──牧野英二
一、前言:本文的目的及考察範圍
二、到明治時代前半(1863-1886年)為止的康德接受史
三、明治時代後半(1888-1912年)康德研究的主要動向
四、大正時代(1912-1926年)康德研究的興盛
五、從昭和時代(1926-1945年)的譯語論爭看康德解釋史的一個片段
六、結論:往後的展開之概觀
日本康德研究的意義與課題(1946-2013)──牧野英二
一、前言:本文的目標
二、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民主主義的時代
三、日本康德協會的成立與《日本康德研究》創刊以後
四、後現代主義與英美哲學的影響
五、康德逝世兩百周年以後的展開
六、結語:概觀今後的發展
韓國康德研究的緣由與開展──白琮鉉
一、韓國康德哲學研究的緣由
二、韓國對康德哲學的接受及其研究過程
三、康德哲學在韓國的再生產應用之可能性
參考文獻
康德與東方哲學的比較研究︰以韓國為例──韓慈卿
一、引言
二、康德與東方思想比較的視域
三、佛教與康德哲學之比較
四、康德與儒教
五、結語──期望「格義西方哲學」
附錄一:王國維與康德哲學──李明輝
一、王國維研究康德哲學的歷程
二、王國維關於康德的著作
三、借用康德的哲學概念詮釋中國哲學
附錄二:日本康德研究文獻目錄(1896-2012)──牧野英二
一、明治時代(1868-1912:明治元年―明治45年)
二、大正時代(1912-1926:大正元年―大正15年)
三、昭和時代(1926-1988:昭和元年―昭和63年)
四、平成時代(1989-2012:平成元年―平成24年)
作者與譯者簡介
西文人名索引
中日韓文人名索引
序 言 李明輝
康德哲學在現代中國──李明輝
一、康德哲學開始傳入中國
二、蔡元培、張君勱與康德哲學
三、牟宗三與康德哲學
四、中國馬克思主義與康德哲學
五、中國自由主義與康德哲學
六、結語
中國大陸1949年之後的康德研究──李秋零
一、自1949年至1978年的康德研究
二、1978年以降的康德研究
戰後臺灣的康德研究──李明輝
一、臺灣康德研究的主要推手︰牟宗三
二、牟宗三影響下的康德研究
三、黃振華的康德研究
四、康德哲學的闡述與翻譯
五、康德哲學在臺灣的發展
日本的康德研究史與今日的課題(1863-1945)──牧野英二
一、前言:本文的目的及考察範圍
二、到明治時代前半(1863-1886年)為止的康德接受史
三、明治時代後半(1888-1912年)康德研究的主要動向
四、大正時代(1912-1926年)康德研究的興盛
五、從昭和時代(1926-1945年)的譯語論爭看康德解釋史的一個片段
六、結論:往後的展開之概觀
日本康德研究的意義與課題(1946-2013)──牧野英二
一、前言:本文的目標
二、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民主主義的時代
三、日本康德協會的成立與《日本康德研究》創刊以後
四、後現代主義與英美哲學的影響
五、康德逝世兩百周年以後的展開
六、結語:概觀今後的發展
韓國康德研究的緣由與開展──白琮鉉
一、韓國康德哲學研究的緣由
二、韓國對康德哲學的接受及其研究過程
三、康德哲學在韓國的再生產應用之可能性
參考文獻
康德與東方哲學的比較研究︰以韓國為例──韓慈卿
一、引言
二、康德與東方思想比較的視域
三、佛教與康德哲學之比較
四、康德與儒教
五、結語──期望「格義西方哲學」
附錄一:王國維與康德哲學──李明輝
一、王國維研究康德哲學的歷程
二、王國維關於康德的著作
三、借用康德的哲學概念詮釋中國哲學
附錄二:日本康德研究文獻目錄(1896-2012)──牧野英二
一、明治時代(1868-1912:明治元年―明治45年)
二、大正時代(1912-1926:大正元年―大正15年)
三、昭和時代(1926-1988:昭和元年―昭和63年)
四、平成時代(1989-2012:平成元年―平成24年)
作者與譯者簡介
西文人名索引
中日韓文人名索引
序
序言
李明輝
2013年5月31日,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辦了一場小型而精緻的「中國與韓國的康德研究」研討會。會中邀請了韓國梨花女子大學哲學系的韓慈卿教授報告〈以比較哲學為中心檢討韓國的康德研究〉,韓國首爾國立大學哲學系的白琮鉉教授報告〈韓國康德研究的緣由與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的李秋零教授報告〈中國大陸1949年之後的康德研究〉,筆者報告〈戰後臺灣的康德研究〉。最後還有一場圓桌論壇,由東吳大學哲學系的陳瑤華教授主持,由韓慈卿、白琮鉉、李秋零、李明輝四位學者擔任引言人。
白琮鉉教授曾將多部康德著作翻譯成韓文,包括《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道德底形上學》、《單在理性界限內的宗教》、《未來形上學之序論》及《永久和平論》。李秋零教授則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版九卷本《康德著作全集》的編譯者。筆者也曾將康德的《通靈者之夢》、《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未來形上學之序論》、《康德歷史哲學論文集》及《道德底形上學》譯成中文,均由聯經出版公司出版。因此,這次發表論文的學者都是東亞最有代表性的康德研究者。
這場研討會還有更廣泛的背景與進一步的發展。在這場研討會之前,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邀請日本法政大學文學部哲學科的牧野英二教授於4月29日至5月4日擔任特約訪問學人。牧野教授曾擔任日本康德協會的會長,目前為日本狄爾泰協會的會長,也是日本岩波書店版《康德全集》與法政大學出版局版《狄爾泰全集》的企畫編輯委員,以及弘文堂版《康德事典》的編輯委員。他自己也翻譯了康德的《判斷力批判》(東京:岩波書店,1999/2000)及狄爾泰的《精神科學序説I》(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2006)。在訪問期間,牧野教授發表了兩篇演講︰一篇是〈日本的康德研究史(1863-1945)與今日的課題〉,一篇是〈康德理性批判的兩個功能──後現代主義以後批判哲學的可能性〉。當他聽到筆者正在籌辦這場「中國與韓國的康德研究」研討會時,表示強烈的興趣,甚至表達出席的意願。但由於時間太倉促,我們無法安排。筆者於會後將論文集寄給他。
由這兩次的學術交流活動,筆者產生了一個構想,即編輯一本《康德哲學在東亞》,分別以中文、日文、韓文三種文字出版,並分別由筆者、牧野教授與白琮鉉教授擔任主編。當筆者向牧野教授與白琮鉉教授提起這個構想時,他們都非常贊同。牧野教授尤其興奮,他認為這將是東亞學術交流的一件盛事。為了落實這個計畫,牧野教授還特地於2013年11月及2014年8月兩度從東京飛來臺北,與筆者當面商議進一步的合作細節。此外,由於其〈日本的康德研究史與今日的課題(1863-1945)〉一文僅寫到1945年,他於2014年3月7日再度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發表演講〈日本康德研究的意義與課題(1946-2013年)〉。此一出版計畫也得到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黃俊傑院長的大力支持。韓文版已於2014年8月由首爾ACANET出版社出版,日文版也於2015年3月由日本法政大學出版局出版。如今中文版的出版完成了這個合作出版計畫的最後一步,對東亞學術交流來說,洵為值得慶賀之事。
本書之出版要特別感謝黃俊傑院長的大力支持。此外,編輯過程中,我還要感謝我的助理劉育兆先生的排版與編輯索引,並感謝我的同事張文朝先生與陳瑋芬女士在日文翻譯與校對方面的協助。
李明輝
2013年5月31日,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辦了一場小型而精緻的「中國與韓國的康德研究」研討會。會中邀請了韓國梨花女子大學哲學系的韓慈卿教授報告〈以比較哲學為中心檢討韓國的康德研究〉,韓國首爾國立大學哲學系的白琮鉉教授報告〈韓國康德研究的緣由與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的李秋零教授報告〈中國大陸1949年之後的康德研究〉,筆者報告〈戰後臺灣的康德研究〉。最後還有一場圓桌論壇,由東吳大學哲學系的陳瑤華教授主持,由韓慈卿、白琮鉉、李秋零、李明輝四位學者擔任引言人。
白琮鉉教授曾將多部康德著作翻譯成韓文,包括《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道德底形上學》、《單在理性界限內的宗教》、《未來形上學之序論》及《永久和平論》。李秋零教授則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版九卷本《康德著作全集》的編譯者。筆者也曾將康德的《通靈者之夢》、《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未來形上學之序論》、《康德歷史哲學論文集》及《道德底形上學》譯成中文,均由聯經出版公司出版。因此,這次發表論文的學者都是東亞最有代表性的康德研究者。
這場研討會還有更廣泛的背景與進一步的發展。在這場研討會之前,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邀請日本法政大學文學部哲學科的牧野英二教授於4月29日至5月4日擔任特約訪問學人。牧野教授曾擔任日本康德協會的會長,目前為日本狄爾泰協會的會長,也是日本岩波書店版《康德全集》與法政大學出版局版《狄爾泰全集》的企畫編輯委員,以及弘文堂版《康德事典》的編輯委員。他自己也翻譯了康德的《判斷力批判》(東京:岩波書店,1999/2000)及狄爾泰的《精神科學序説I》(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2006)。在訪問期間,牧野教授發表了兩篇演講︰一篇是〈日本的康德研究史(1863-1945)與今日的課題〉,一篇是〈康德理性批判的兩個功能──後現代主義以後批判哲學的可能性〉。當他聽到筆者正在籌辦這場「中國與韓國的康德研究」研討會時,表示強烈的興趣,甚至表達出席的意願。但由於時間太倉促,我們無法安排。筆者於會後將論文集寄給他。
由這兩次的學術交流活動,筆者產生了一個構想,即編輯一本《康德哲學在東亞》,分別以中文、日文、韓文三種文字出版,並分別由筆者、牧野教授與白琮鉉教授擔任主編。當筆者向牧野教授與白琮鉉教授提起這個構想時,他們都非常贊同。牧野教授尤其興奮,他認為這將是東亞學術交流的一件盛事。為了落實這個計畫,牧野教授還特地於2013年11月及2014年8月兩度從東京飛來臺北,與筆者當面商議進一步的合作細節。此外,由於其〈日本的康德研究史與今日的課題(1863-1945)〉一文僅寫到1945年,他於2014年3月7日再度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發表演講〈日本康德研究的意義與課題(1946-2013年)〉。此一出版計畫也得到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黃俊傑院長的大力支持。韓文版已於2014年8月由首爾ACANET出版社出版,日文版也於2015年3月由日本法政大學出版局出版。如今中文版的出版完成了這個合作出版計畫的最後一步,對東亞學術交流來說,洵為值得慶賀之事。
本書之出版要特別感謝黃俊傑院長的大力支持。此外,編輯過程中,我還要感謝我的助理劉育兆先生的排版與編輯索引,並感謝我的同事張文朝先生與陳瑋芬女士在日文翻譯與校對方面的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