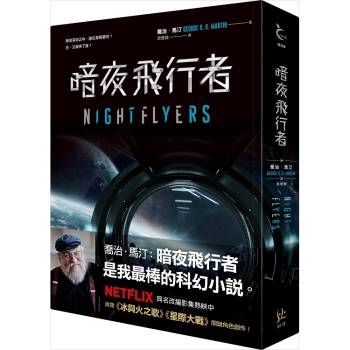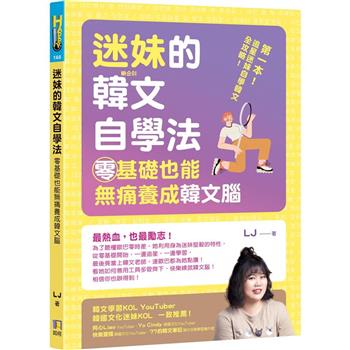開拓「慧」的文學
──東方白精短篇語錄(代序)
◎東方白
我一生慣於追求長而遠的大目標──五年的博士論文、十年的《浪淘沙》、十年的《真與美》……,前年(2001)《真與美》出版後,突然十分空虛徬徨,發表了〈古早〉、〈我〉、〈空〉、〈殼〉……之後,終於形成了「精短篇」的形式,乃決定此後五年做為自己的目標,專寫這種獨創一格的文章,別小看這小小文章,如果寫上三、四十篇,力量就不可忽視了,絕不遜于一篇大河小說(《莊子》就是最好的例子)。為此我花了整整一年,重讀芥川、莫泊桑、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回臺灣前又讀了《101 Modern Short Fictions》,在臺灣又買了卡夫卡、海明威、高爾基的短篇傑作選,更買了三冊褚威格的心理小說選。我花了三個月將三十五本notebook記載的上百篇題材整理出來,列在筆記本,讓它自然醞釀,打算一篇又一篇,精工製作,逐篇把它們寫下來,我對此用心良苦,不遜《浪淘沙》。(2003.1.6)
文學大致可分為兩種──「情」的文學與「慧」的文學。「情」的文學汗牛充棟,「慧」的文學鳳毛麟角(莊子的所有寓言、陶潛之〈桃花源記〉、列子之〈愚公移山〉、芥川之〈羅生門〉、〈竹藪中〉、〈鼻〉,卡謬之《異鄉人》,海明威之《老人與海》……皆屬此類),因為我酷愛「幾何之美」的文學,所以也就寫出「東方白」式的短篇小說!(這可能是「東方白」與臺灣一般作家最不同的特點!)(2003.1.30)
我天生喜愛「哲學性」、「思想性」的抽象文學(寓言、神話,深具人生意義的短篇小說)──莊子的〈夢蝶〉、列子的〈愚公移山〉、陶潛〈桃花源記〉;莫泊桑的〈項鍊〉、契訶夫的〈打賭〉、芥川龍之介的〈蜘蛛之絲〉是我的六個最愛,五十年來此情不變,由此可以說明我為什麼要寫寓言小說?為什麼會如此孤獨?(2003.9.11)
一個純粹的作家(像東方白),沒有外在的「誘因」(像「名」、「利」或什麼……)可以誘使他去創作,卻有一股內在如火山的爆發力逼使他去寫作,將岩漿噴出之後,才能獲得短暫的安靜,不多久,火山又蠢蠢欲動了……說好聽是「才」,說不好聽是「病」,這「病」逼他「不得不」繼續創作,否則會因不寫而無聊而憂鬱而發瘋。我不能像一般退休的人,整日看電視、搓麻將、旅行、吃喝……便了,這種生活我過不下去,我非得在我眼前擺上一年以上的「長期」工作計劃不可,否則就會無以為生而開始憂鬱,因此《浪淘沙》後有《真與美》的十年計劃,《真與美》之後有至少五年以上的《精短篇100》長期計劃……計劃到時能不能完成不在考慮之下,但沒有計劃便立刻倒地而死,概無疑問。(2003.11.3)
六月底之前,會將《真美的百合》完成,積極投入《精100》的計劃中,此書又是五年至十年的長期抗戰,不一定能完成100篇,但目標無妨大一點遠一點,給自己鼓勵,這100篇中若能出現五篇類似〈莊周夢蝶〉(48字)的佳作(而且我有預感可以寫得出),此生無憾矣!我這人慣於眼前有個長遠的大計劃,否則活不下去,可憐不?(2004.6.1)
我把應做的事都做了,又是「無事一身輕!」,開始動腦筋構思擱置快兩年的〈頭〉,接下去便是期待已久的《精100》,大可揮灑自如,大刀闊斧地寫下去了。(2004.8.29)
其實此大工程已計劃并進行了兩年,當初下此決心後,我就花了好幾個月重讀手邊讀過的短篇小說,并從中精心細挑了三十四篇﹝百讀不厭的世界短篇傑作﹞(其中中國的僅選了三篇──〈莊周夢蝶〉、〈愚公移山〉與〈桃花源記〉,由此可見一斑!),決定每日勤讀,再讀,精研其吸引人之妙處與美處,然後綜合塑成自己「精短篇」的格式與長度……到目前已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2005.3.2)
我目前從資料中挑了五篇──〈網〉、〈命〉、〈醫〉、〈眉〉、〈貓〉,已花了幾個禮拜同時醞釀,等果熟蒂落,自然一氣呵成,五篇魚貫推出。以後寫作,也照此方式,直到100篇全部完成為止。(2005.3.2)
人間的「名」「利」與「東方白」無涉,他只想過平淡的生活──每天晨起靜坐,彈蕭邦美曲,白溪散步,傍晚澆花,禮拜日剪草……每晚沉思《精百系列》,看有一天能否寫出一篇五十字的〈東方夢〉(多〈莊周夢蝶〉二字!!)而已。(2005.6.2)
「精百系列」之靈感起於2003.2.14,那時右眼先開了白內障,在等待開左眼的一個月當中(不能看書),乃突發奇想,何不計劃十年,集中精力,創新寫作自己設計的精短篇?學《十日談》,以100篇做指標,可以形成有力的文學集合體,稱「大河精短」也可以,由於集滴成河,仍然會有大河之氣魄,何樂而不為?(2005.6.30)
「精百系列」已進行了兩年,也看盡了(複習)所有過去讀過的短篇小說,相信打好地基,可以緩起高樓了。現手邊已選出六十篇可寫的素材,待細細咀嚼,醞釀,期待發酵成酒,然後一一裝瓶出售。(其餘四十篇也不難水到渠成,自動湧來……)(2005.6.30)
這期《文學台灣》已寄出兩篇:〈網〉、〈命〉。下期的,近日已成〈鸚〉一篇,〈醫〉就要下筆,另一篇〈眉〉在構思中……,就像下下月二十二日的北歐旅行,「精百系列」的旅程已計劃完成,而且也買票上車,就等每天的美景在車窗展現!(2005.6.30)
文人不必自我清高,以為作品有什麼奧秘無可言傳,根據毛姆的說法,所有「小說」不過是為了引人「興趣」給人「快樂」的,如果達不到此二目的,「小說」再好再妙,干卿底事?與讀者無涉!我所敬仰的Chekhov、Maupassant與芥川,他們的作品,一看就叫人著魔,不必再詮釋,也不必再說明,作品自我介紹,一見鍾情,雙雙墜入愛河。(2005.7.28)
為了「精」字,不惜代價「精百系列」暫停兩期,之後再來不慢。你放心好了,寫了〈殼〉、〈網〉、〈色〉、〈絕〉之後,我已發展出「東方白」特殊的精篇形式,故事內容乃我所長,假我十年,完成百篇,將有一番景象。(2005.10.28)
──以上摘自《東方文學兩地書》東方白致歐宗智函,《台灣文學評論》季刊連載。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