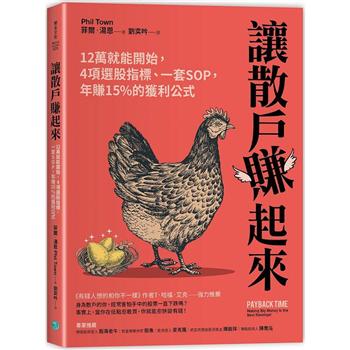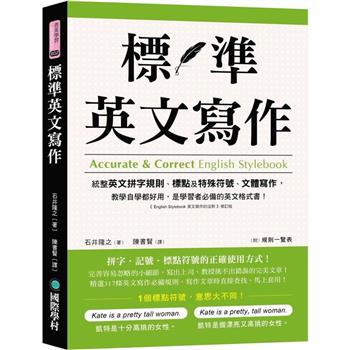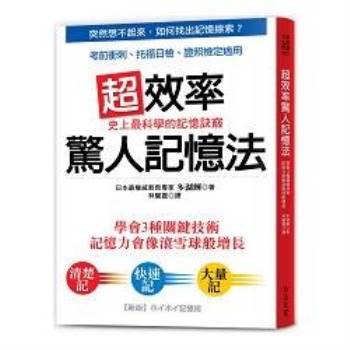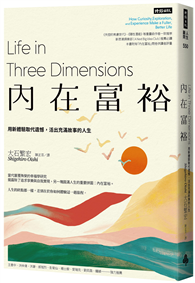《大陸期刊文學獎獲獎作品選集》選錄中國大陸知名文學期刊《人民文學》、《江南》、《作品》、《當代》、《詩刊》所舉辦的文學獎得獎作品,包含詩、散文與小說三類。文學獎得主為青壯世代的作家群,他們的創作主題,流露出深刻的個人情感與觀察,飽含對當代文學現況、文化視野、社會環境的關懷。
文學期刊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幕後推手,設置文學獎項,鼓勵有志者投入創作,在網路數位化的時代堅守文字的力量,為讀者帶來豐富的文學饗宴。
作者簡介:
共收錄11位作家的得獎作品:
高鵬程,1974年生於寧夏。詩文見於《人民文學》、《詩刊》、《天涯》等刊物,曾獲浙江青年文學之星、2014年鄞州‧人民文學詩歌新人獎、第四屆紅高粱詩歌獎、兩屆浙江省優秀文學作品獎等。著有詩集《海邊書》、《風暴眼》、《退潮》等。
沈魚,本名沈俊美,1976年生於福建省詔安縣。1998年開始寫詩,曾獲2015年陳子昂詩歌獎青年詩歌獎。著有詩集《荒廢帖》、《左眼明媚,右眼憂傷》。
張二棍,本名張常春,1982年生於山西忻州。為山西文學院簽約作家,寫詩多年,曾獲2015年陳子昂詩歌獎青年詩歌獎。著有詩集《曠野》。
顏梅玖,筆名玉上煙。作品見於《人民文學》、《詩刊》、《十月》等多家刊物,詩入選多種選集和年度選本。曾獲《現代青年》讀者最喜歡的十大當代詩人、大連「三個十」最佳作品獎、大連第十二屆金蘋果優秀創作獎、2015年茅台盃文學獎詩歌獎、首屆新現實主義詩歌獎等。著有詩集《玉上煙詩選》、《大海一再後退》。
胡竹峰,1984年生於安徽岳西。曾獲2015年紫金‧人民文學之星散文新人獎、書城盃散文大賽一等獎等。著有散文集《空杯集》、《墨團花冊:胡竹峰散文自選集》、《衣飯書》等十餘種。多篇散文入選年度散文和隨筆排行榜,部分作品被翻譯成英、法、日、義語。
謝有順,1972年生於福建長汀。現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心主任,以及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廣東省文藝批評家協會常務副主席。曾獲馮牧文學獎、莊重文文學獎、廣東省魯迅文藝獎等。著有《文學的常道》、《被忽視的精神》、《消夏集》等十多部作品。
徐海蛟,1980年生。迄今在《讀者》、《青年文摘》、《散文選刊》等報刊發表作品一百五十多萬字。曾獲「天一講堂•我要上講堂」優勝獎、2016年鄞州‧人民文學散文新人獎。著有散文集《紙上的故園》、長篇小說《別嫌我們長得慢》、詩集《樹的口袋裡藏著春天》等七部作品。
朱山坡,本名龍琨,1973年生。現任廣西作家協會專職副主席、江蘇省作家協會合同制作家。早年主要寫詩,2005年開始發表小說,近年來在《收穫》、《花城》、《鍾山》等刊物發表。曾獲得首屆郁達夫小說獎等。著有長篇小說《我的精神,病了》、《懦夫傳》、《風暴預警期》等多部作品。小說被翻譯成俄、美、英、日、越語,也改編為影視作品。
東君,本名鄭曉泉,1974年生於浙江溫州。以小說創作為主,兼及詩與隨筆。若干作品曾在《人民文學》、《花城》、《大家》等刊物發表。曾獲第九屆《十月》文學獎、人民文學短篇小說獎、2010年郁達夫小說獎短篇小說獎等,作品多次入選年度選本。著有小說集《恍兮惚兮》、《東甌小史》,長篇小說《樹巢》、《浮世三記》。
楊怡芬,1971年生於浙江舟山。2002年開始小說創作,為浙江省作家協會簽約作家。已在《人民文學》、《十月》、《花城》等雜誌發表中短篇小說七十餘萬字。曾獲《作品》雜誌社「魯迅文學院高研班學員作品徵文」小說獎、2010年度浙江省青年文學之星獎,部分作品選入各類年選年鑑。著有中短篇小說集《披肩》、《追魚》。
艾瑪,本名楊群芳,1970年生。法學博士,現為山東省簽約作家。2007年開始小說創作,曾獲首屆茅台盃《小說選刊》年度排行榜獎、山東省第二屆泰山文藝獎、第三屆蒲松齡短篇小說獎、第六屆中國作家鄂爾多斯文學獎等,有多篇小說被各類選刊、年選轉載。著有小說集《白日夢》、《浮生記》。
鄭小驢,本名鄭朋,1986年生於湖南隆回。北京市作協簽約制作家,現任《天涯》雜誌編輯,《深圳特區報》、《方圓》等報紙雜誌專欄作家。曾獲第26屆湖南青年文學獎、第五屆毛澤東文學獎、首屆希望盃‧中國文學創作新人獎、上海文學新人佳作獎、2014年紫金‧人民文學短篇小說大獎等。著有小說集《一九二一年的童謠》、《癢》、《少兒不宜》,長篇小說《西洲曲》。
彤子,本名蔡玉燕,1979年生。於《作品》、《花城》、《作家》等刊物發表小說,入選多種年度選本。曾獲2012、2014年廣東省《作品》新銳獎。著有小說集《高不過一棵莊稼》、《平底鍋的愛情》,長篇小說《南洋紅頭巾》、《南方建築詞條》、《陳家祠》。
章節試閱
陪夜的女人
◎朱山坡
女人搭乘烏篷船來到鳳莊。 這是一條很特別的船。除了特別扁小外,尖細而稍向上翹的船頭,古香古色的船板和塗抹了厚厚一層桐油的船篷,還有斷斷續續引人發笑的馬達聲都引起了圍觀者的好奇。鳳莊早就沒有這種船了。其實,由於航道淤塞,又由於無魚可打,不說輪船,連漁船都已經很少見到。烏篷船從下游逆流而上,力氣快用完了,速度越來越慢,宛若一個苟延殘喘的人。
在人們的擔心中,船總算在廢棄了的碼頭靠了岸。船頭擺滿了炊具和其他日常生活用的物品,亂得像開雜貨店。女人從船上跳下來,笨拙地拴好船,撣撣身上的暮氣,然後神色鎮靜地往村子裡張望。船裡還鑽出一個竹竿一樣的男人,病懨懨的,吃力地扛著一件東西。後來才知道他是女人的丈夫,那東西是一張彈簧折疊床。男人把東西放在碼頭的石塊上,跟女人嘀咕幾句,轉身便開船離開。他的腳下,便是慧江,寬闊浩瀚,水流平緩,黃昏的江面像大海一樣孤寂。那條船,很快便看不見,似乎已經沉入深不可測的江底。
迎接女人的是一群吱吱喳喳的孩子。女人異常高大,皮膚黝黑,渾身胖乎乎的,頭髮很短,但手臂很長,而且粗壯,本來需要肩扛的折疊床她只是用手夾在肋中,另一隻手還抓著一張薄薄的棉被。
「我要去方正德家。」女人說,「你們前面帶路。」
孩子們迅速分成兩半,一半在前面熱情地引路,一半在女人的身後暗中取笑她的大屁股。通往村莊的石板路還殘留著夏天洪水浸泡過的痕跡,蕭瑟的田野像江面一樣空蕩。女人的到來給村子增添了新的氣氛,像來了一位遠客,引起了一些騷動。踩著幾聲狗吠,從屋裡走出一些老人和一個腆著肚皮的婦女。
「來啦?」她們笑臉相問。
女人回答得很乾脆,來了。
她們如釋重負地鬆了口氣。她們也許覺得女人話不多的時候,女人的話卻意外地多了起來:「早上接到了兩個電話,一個是金灣鎮的,也是個女人,說我煩死了你一定得過來,但我還是答應來鳳莊,方厚生跟我家的侄子在廣州是工友,熟人嘛,總得優先照顧。」
腆著肚皮的女人是厚生的老婆,快生了吧,不是萬不得已連石階也不願爬了,一來累,二來怕摔。厚生家有兩處房子,一處在石階下面,是三年前建的新房子,一層的平頂樓房;另一處在石階的頂頭,是祖屋,破舊得看看就忍不住要動手拆掉,厚生要父親搬,但老人住那裡已經上百年,慣了,不願挪,他說房子倒塌就倒塌順便把他埋了最好。這座陡峭的石階也是他家祖輩砌的,別人很少去爬。爬上高高的石階,孩子們把女人引到老人的房間門外便一哄而散。為表明比其他孩子更勇敢一點,厚生九歲的兒子至善把女人帶到了老人的窗前。窗是老式活動窗,能關上,關上後外面就看不到裡面。至善踮起腳,顫巍巍地拉開窗櫺,女人把臉貼著窗戶往屋子裡探望,裡面只有一團難以打破的黑暗,但女人還是看到了一張有深藍色蚊帳的床並聞到了迎面撞來的臭氣。
「我阿公就在床上。」至善率真地說,「他就習慣這樣,白天睡覺,晚上擾人。」
估計正德老人快睡醒了,睡醒就要吃飯。平常,飯是厚生家的給他送到床邊,手一摸,就能碰到不鏽鋼飯碗,飯菜都在裡面。老人像一個壯勞動力一樣,每頓總得吃滿滿的一大碗飯,一直到死都是,因此他每喊叫一聲都有很足的底氣,誰也聽不出他是一個行將要死的人。 「我還沒有死,你們進來吧,陪我一會。」老人在裡面說。他醒了,也就是說,鳳莊漫長而煩人的夜晚開始了。 女人輕輕推開門進去,點亮了煤油燈。燈光首先照亮了自己,看上去女人有一張還算端莊的臉,樣子很熱情、虔誠、豁達,她四處張望空蕩蕩的房子,像出了趟遠門的主人回到家裡看看是否少了什麼東西。
老人說,來啦?
女人說,來了。
老人說話的時候省氣力,聲若纖蚊,還有些沙啞。屋子很寬闊,沒有什麼顯眼的擺設,地面黑得發藍,凹陷不平。女人先是瞧了瞧老人的床。是一張清朝老式木床,差不多有她家那條船大。老人蓋著被子,枕著一隻高高的光滑的木枕頭,只露出被擰乾水了的瘦癟的臉,鬍子比颱風後的荒草還亂。女人說被子該洗了,臭味熏得蚊子也不願來了。老人斷然拒絕說,不洗,洗什麼,人死後統統都要燒了,連床都要燒掉的。女人還是堅持要洗,明早,我幫你洗了再走。但老人死活不肯,緊緊地揪住被子,生怕一放鬆女人便要搶走。
「被子又不是你的卵,你揪那麼緊幹什麼!」女人笑著說。至善覺得女人挺幽默、樂觀的,也嘿嘿地跟著笑。
厚生家的腆著高高的肚皮送飯進來。她住在台階下面的新房子,老人住的是祖屋,厚生家的對女人說,飯你不用管,他自己還能吃,屎尿平時就拉在床上,他也不讓清理,像牛欄,我習慣了,都聞不到臭味。
女人說,你丈夫跟我說了,我什麼都不用管,我只是來陪夜的——你知道陪夜吧,大多數病人都是在半夜裡斷氣的,陪夜就是讓他們斷氣的時候身邊總算有個伴,不至於死得太寂寞。陪夜不是陪護,陪護得幹很多髒活,我做不了陪護,看到別人的屎尿我也噁心,如果不是這樣,我早到廣州醫院做陪護去了,幹一天能賺七八十塊,遇上大方一點的雇主能賺上百塊,比在這陪夜強多了。 厚生家的把飯碗放在老人的床邊,老人也不側身,伸手抓起就吃,狼吞虎嚥的樣子讓人覺得他是一條從煎鍋跳到水裡的魚。女人說,你慢點,不要白白撐死,我還沒賺夠你們一天的錢呢。
老人說,我早想死了,就是死不了——到了我這個年紀,活著就是等死。
女人嗔怪道,胡說。
厚生家的對女人說,老傢伙一過世,我就要去廣州,連孩子我也要在廣州生……煩死了。 老人邊吃邊咕嘟,快了,說不定今晚就死。這句話厚生家的聽多了,並不以為然,也不想跟老人說話,轉身走了。
女人告訴老人,從此以後,每天晚上我都坐船過來陪你。
老人沉吟說,其實我不怕黑夜,連死都不怕,我還怕黑麼!
女人把自己的床打開,擺在窗口下,離老人的床有三四米遠。她試坐自己的床上,鐵支架床發出尖銳的支支聲。
老人說,我沒有病,我跟我的祖輩一樣,都是老死,自然死亡,像一棵老樹,朽木,風不吹,自己也要倒——我的大限到了,我自己知道,厚生也知道的。
女人說,你的兒子還算孝順,雖然沒有回來服侍你,但捨得花錢。
老人突然來氣,呸!我快死了,他還在廣州幹什麼!
女人說,厚生他忙,你躺在這裡不知道打工的難處,要拚命幹活,還要看老闆的眼色——現在城裡到處都是人,找一份工作不容易……
老人被飯嗆了一下,不斷地咳嗽,突然一把將飯碗摔在地上。女人站起來撿碗,你不要動怒氣,很多老人就是動怒死的,到了這年紀,你還跟誰嘔氣!
老人咳停,猛喘粗氣。女人責備說,我給不少老頭陪過夜,從沒見過火氣像你這麼大的。老人的眼睛瞪得賊亮,突然張嘴大喊一聲:李文娟…… 女人想不到這個連說話的力氣都湊不足的老頭呼喊起來竟像船的汽笛那麼洪亮、尖銳,底氣十足,爆發力強,有振聾發聵之功。有兩三個月了吧,老人每天晚上就是這樣不知疲倦地呼喊著李文娟,差不多每隔一分鐘便叫一次,把鳳莊喊得雞犬不寧,沒有人能睡上一個好覺。厚生家的膽小,夜裡不敢進老人的房間,甚至聽到老人的呼喊心裡也一顫一顫的。厚生回來過兩三次,問老人,你嚷什麼呀?我在廣州都聽到你嚷嚷,把人嚷煩了。老人說,我喊你媽——我快死了,身邊沒有一個人陪。厚生陪了他兩個晚上,他便不叫,厚生一走,他又嚷了,嚷得理直氣壯,像一個委屈的孩子呼喊他的母親。女人覺得這個聲音刺痛了她的耳,使她渾身不舒服。
「你嚷什麼呀,厚生不是雇我來陪你了嗎?」
老人又是呸一聲,接著是更激烈的咳嗽,咳嗽的間隙大聲嚷著:「李文娟……」
厚生告訴過女人,李文娟是他母親的名字。厚生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她的真名,反正有懸疑的問題還有很多,比如老人的年齡,有的說一百零一,有的說才九十九,厚生也說不準,父親六十歲才結婚,母親四十六歲那年生下他後便去向不明。厚生的母親是跟隨一艘運乾魚的貨輪來到鳳莊,嫁給老人的,第二年便生下了厚生。那年四川客商從南海販運一船乾魚到重慶,途經鳳莊時作了短暫的停留,停留的結果是,給鳳莊留下了一個女人。那個女人到鳳莊裡去找生薑治暈船,當找到生薑趕到碼頭的時候,船已經開走了。這個四十五歲的女人剛剛死了丈夫,要到重慶投靠親戚,如果船上載的不是乾魚,太腥臊,她是不會暈船的,不暈船的話她就不會跑進鳳莊要生薑,就不會留在這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有人說她是被船家故意甩掉的,因為他們擔心一個剛剛死了丈夫的女人會給船帶來晦氣。那天,她就在碼頭上哭,鳳莊的人知道她剛剛死了丈夫,不願收留她,甚至不願給她一口飯。是方正德,不僅把家裡最好的一塊生薑慷慨地送給了她,後來還乘著夜色把她帶回了家裡,再後來就成了厚生的母親。那時的人勸他說,正德,現在兵匪猖狂,你怎麼能帶一個來路不明的女人回家?鳳莊的人擔心她給鳳莊帶來不祥和危險,處處防著她,甚至有人悄悄報了官。其實,厚生的母親是一個很好的女人,人長得好看,皮膚細嫩,唇紅齒白,不像四十多歲的人。一聽口音便知道是外地人,她說老家在陝西,鳳莊從沒有人到過陝西,因此不知道陝西離鳳莊到底有多遠。沒幾天,人們便發現厚生的母親不是簡單的女人,處事老練,說話得體,對誰都笑臉相迎,恭恭敬敬,大家明白她是見過世面歷過風雨的人。而且,她還比鳳莊所有的女人都勤懇,家裡家外收拾得整整齊齊,把一個死氣沉沉的家盤活了,對厚生的父親也好,連重活都不讓他做。在鳳莊,只有厚生的父親不用幹重活,都讓厚生母親搶著幹了。厚生母親說,她沒給前夫生下孩子,要給正德生一窩。第二年春,果然生下了厚生。四十六歲了,還能生孩子,簡直嚇壞了鳳莊的女人。但厚生父親高興呀,他逢人便說,他要生十個兒子,要成為鳳莊生兒育女最多的人。厚生的母親跟鳳莊的女人不一樣,她有長遠打算,能謀劃,她跟厚生的父親說,明年春天她要在地裡種上一大片生薑,到了秋天把生薑販賣到重慶去,然後從重慶販回藥材,賣給城裡的藥鋪……厚生父親為娶到一個精明、賢惠的女人而對上天感恩戴德,那是上天賞賜給他的女人,他這一輩子呀,除了對自己的女人好,就是要對上天好,不能罵天。厚生父親一輩子都沒罵過厚生的母親,也沒罵過天。厚生母親曾對厚生父親說,正德呀,你六十歲才娶妻,你得活到一百歲,否則你對不起我。厚生的父親說一定要活到一百歲,跟厚生母親過一輩子,對她好一輩子。但厚生還沒滿月,差兩天吧,他母親竟突然跑了,從此銷聲匿跡,杳無音訊。四十多年了吧,厚生的腦子裡早已經沒有母親的概念了,老人也很少提起她,甚至在他呼喊「李文娟」的時候,人們好久才想起,厚生的母親就叫這個名字。 老人說,我眼睛一閉上,她就出現在面前,說明呀,她要帶我走了。
女人說,那是幻覺,是人都會產生幻覺,有時候我也會。
「我活了上百歲了,也對得起她啦。」老人說。
女人說,她不該離開你,女人哪能隨隨便便離開自己的男人?
「你知道當年她為什麼要離開鳳莊?」老人自問自答,「她生厚生得了重病,她不想連累我——你想想,四十六歲了才第一次生孩子……」
女人說,危險,不容易。
老人一個人感慨萬端。女人解開褲頭,坐在屋角的尿缸上要撒尿的時候才發現窗戶沒有關上,揪著褲子尷尬地跑過來關窗。至善懂得害臊了,走下第五級台階,還能聽到嘩啦啦的水聲和女人埋怨尿臭的謾罵。
至善厭惡地捏住鼻子,誇張地對他母親說,這女人,撒尿的聲音比牛還響!
無論如何,這是鳳莊多少天以來最寧靜的一個夜晚,靜得能聽到遠處江水流淌的聲音。這天晚上,鳳莊所有的人都聽不到老人令人心煩的呼喊聲,睡了一個安穩的好覺。第二天,有人小心翼翼地問,老人是不是駕鶴西去?厚生家的滿懷歉意地說,還得等,還得多等幾天——一盞殘燈即使油料耗盡也不會馬上熄滅。人們才知道,老人能還給鳳莊寧靜的夜晚,全是女人的功勞。 鳳莊早起的人們看到女人天一亮就走了,頭髮也不梳理,臉還來不及洗呢。她說她男人和船在碼頭邊等她,她得回去幹活。女人家在江浦,離鳳莊有二三十公里的路程吧,那邊是姓齊人家,女人的男人也應該姓齊。女人說她家種了十幾畝芭蕉,要除草、施肥,還得防颱風,用柱子撐著芭蕉樹,但颱風來了一千根柱子也不頂用。女人埋怨,去年要不是一場颱風把好端端的一地芭蕉毀了,我也不用給一個快要死的老人陪夜,陪自己男人不更好?
女人的男人果然已經在碼頭等待。他站在船頭抽菸,高高瘦瘦的,腰有點彎,很孱弱的樣子,對女人很殷勤。女人跳上船,男人遞給她一條毛巾,女人澆澆江水洗臉,臉才洗好,船便開了。晨曦中船開得特別快,像是換了一條船似的,一會便到了江中,眨眼間消失在寬闊而沉靜的江面上。 女人是個守時的人。黃昏,最遲也用不著到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結束,她便會如期出現在台階前,朝厚生家的房間裡說一聲,我來啦,便拾級而上,推開房門,高聲地跟老人說話,把孤寂和恐懼驅散。每次進了老人的房間,女人都要往尿缸裡撒尿,好像這泡尿憋了一整天了就等著到這裡放掉的。白天幹活累了,女人撒完尿便要睡覺。老人睡不著,要跟她說話。女人要早休息,因為明天還得回去幹很多的活。老人說,厚生是請你來陪我說話的,不是請你陪我睡覺的,你得說話。女人說,你說唄,我聽就是了。老人說,你真要聽。女人說,我用心聽著呢。老人便說話。他成了鳳莊唯一在深夜裡說話的人。女人開始是真的用心聽,偶爾還回上一兩句,後來注意力不集中了,估計是想著家裡雞零狗碎的事情吧,最後乾脆不知不覺睡著了。老人也不知道女人是不是真聽他說話,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睡著了,反正說話,把每一個夜晚都當作是自己生命最後的一宿,每天夜裡都要說很多的話,要把所有的話一口氣說完,彷彿不說明天就沒機會說了。 女人剛來的時候,老人對她說,我呀,死過很多次了。女人說,大難不死,有後福唄。老人說不是這個意思,他是怕,年輕時對死很怕。厚生十歲的時候,老人轟轟烈烈地死過一次。那時候在鳳凰嶺上修水渠,老人負責放炮炸石頭。他都幹了一天了,幾個放炮的人都累爬了,等他撤下來,他就是不撤。別人問他累不累,他說不累。其實他累得快不成了,他還要炸一口,再炸一口水渠就跟另一頭接上來了,他硬是要多炸一口。結果炮響了,水渠兩頭連了起來,他卻跑不及被泥石掩埋,大夥好不容易才把他扒出來,還沒送到村衛生所便斷了氣。大隊裡緊急開會討論,追認他為修水渠功臣,獎勵他三十分工分。家裡都為他準備後事啦,響器班把嗩吶、牛角、簫笛吹得淒愴而熱鬧,抬棺材的人都要將他入殮啦,厚生的姑姑們哭得天昏地暗,厚生沒有哭,厚生這小子不會哭,別人看不過眼,對厚生說,父親死了,你裝模作樣也得哭幾聲呀。厚生就是不哭,彷彿他知道我還沒有真死。「就這個時候,我醒過來了,把所有人都嚇了一跳。」老人自豪地說,那時候,這是一個天大的新聞,因為好多年沒看到過有人死而復生了。小時候,我就曾看到方必富的祖父捕魚失足跌落江底,被漁網纏住,從早上一直到中午才被人撈起來,身體冰冷,臉色死灰,大家以為肯定死了,但用破棉被一蓋,準備第二天扛到山上埋了,但想不到半夜裡他自己竟醒過來,到自家的廚房裡找吃,把他的老婆嚇得魂飛魄散。這叫做假死,過去有人被埋葬了才活過來,但醒得太遲啦,自己爬不出來,活活悶死在棺材裡。那時候,我就做了一個長長的夢,夢見各種各樣的人,夢見很多陌生的地方,夢見自己走了很遠很遠的路,後來聽到文娟罵我,她說,正德,厚生還小,你死什麼呀,還輪不到你呢,你答應過我要活到一百歲的,你快回去……因此,我就回來。
女人笑了笑。女人知道,老人口口聲聲地說自己不懼怕死亡,事實上,不怕死的人是不存在的,黑夜來臨,會使老人戰慄,他在夜裡呼喊「李文娟」就是對死神召喚的害怕。她的到來,像一盤冷水澆滅了他內心的恐懼。
老人說,他們已經五次把我背到堂屋,但每次我都沒有斷氣,他們又得把我背回來——周而復始,他們都煩透我了。
習俗是,人之將死,最後要躺的地方必是堂屋,死在堂屋,死在列祖列宗牌位面前,才死得安心,才死得不寂寞,死後才容易找到早逝的親人。老人三番五次地瀕危,三番五次地躺在堂屋的左側(女人躺的是右側),平靜地等待生命最後一秒的來臨,親人和背他到那裡的人也屏氣凝神地在等待老人嚥下最後一口氣。然而,不再需要奇蹟的時候,奇蹟卻三番五次地降臨,老人的氣艱難地又緩回來了,死人般的臉色由蒼白、僵硬變成暗淡、溫潤,最後竟然恢復成肉色,像熬過了寒冬臘月的枯樹又有了生命復甦的痕跡,頑強而故意地嘲諷著大地的一切。他們的臉上沒有驚喜,全是一番徒勞後無奈的苦笑。厚生一次又一次從廣州連夜趕回,想一勞永逸地送別老人,但一次又一次地緊急召回派去向親戚報喪的人,一次又一次歉疚地跟已經準備就緒的響器班和抬棺佬悔約,成了別人的笑柄。厚生終於失去了耐心,叮囑自己的女人,大真死了,你才給我電話!這些日子來,他的女人好幾次拿起了電話又放下來,她害怕說錯了又要厚生白白跑一趟。 鳳莊的婦孺最厭煩的不是老人從堂屋的地上一次又一次復甦過來,而是在夜裡老人聲嘶力竭的呼喊。聲音不是野獸,困不住。鳳莊人不多,但怨聲載道起來卻到處都能聽見。開始的時候,小孩聽不慣老人的呼喊,被驚嚇得渾身發抖。後來不怕了,還沒到深夜,還不睡覺的時候,他們有時在老人的窗口外往裡尖叫或吹口哨,像挑逗一個失去法力的妖怪;老人被背到堂屋,他們還敢在門外探頭往屋裡張望、聆聽,向大人報告老人是否還一息尚存。苟延殘喘的老人也知道自己已經被鳳莊所拋棄,招人嫌了,但他偏偏不願嘴軟,把好心好意來勸慰他的人都看作了惡意:你們把我活埋算了——你們,你們也有死的一天。後面那句話多歹毒呀。誰也不想被將死的人罵,那是不吉利的,所以沒有人願意跟老人說話,甚至對他產生了厭惡。他就在深夜裡獨自呼喊,讓所有的人都聽到像從墳墓裡傳出來的聲音,都體會到深夜的寂靜和黑暗的漫長。 有幾個老漢實在忍不住驚擾,站在老人的窗外責怪道,你嚷什麼呀,沒有人像你,存心要整個村莊的人都睡不了覺!面對指責,老人既不生氣,也不爭辯,仍然用冰冷的呼喊回應一切。老頭們找不到更好的辦法,只能用三個字發洩對正德老人的無奈和不滿:老不死。老人如此,厚生的女人便有壓力,她不堪重負,便把壓力轉嫁到遠在廣州的厚生身上。厚生也想不明白老人為什麼會這樣。媳婦說,他要陪唄。厚生陪不了,他在那家韓國人開的電子廠裡幹得正有起色,照此下去年底便能加薪升職了,但韓國人管得死,稍不小心便要被炒掉。厚生是一個兢兢業業的人,到底是珍惜來之不易的飯碗,輕易不請假。留在村裡的男人越來越少,能出去的人都出去賺錢了,出去的女人也越來越多。老人瀕危快不成了,只有一次是厚生背到堂屋,另外四次是不同的男人背的,他們都是因為家裡有事正好從外面回來,就幫背一把。外出撈世界的人怕惹晦氣,本來是不願意背的,但沒辦法,村裡只有你一個大男人,碰上這事,誰也逃不過,哪家沒有老人,誰沒有老死的一天?你總不會坐視不管吧。老人給人們帶來那麼多的煩惱,厚生覺得欠著鳳莊人的人情,老人多活一天,欠的人情便越多。一次,厚生上醫院,見識了一種叫「陪護」的職業,才豁然開朗:只要捨得花錢,陪別人去地府的活也有人幹。厚生便試著雇了女人。 女人的到來使鳳莊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她們恢復了往日的從容和愜意,女人從她們面前經過的時候,她們會拉住女人的手說,你真的不害怕?萬一老人半夜升天了……
女人說,害怕什麼呀?不就是死人嗎?除了不會睜眼說話外,跟活人沒有什麼區別。
女人的勇敢征服了鳳莊的婦人,她們只是想不明白,一個女人怎麼會不害怕死人呢?
「老人不喊叫了,是不是你從家裡拿來擦台布堵住了他的嘴巴?」她們說。
女人說,怎麼會呢?
她們說,那你肯定是把自己的奶子讓他啃——老人就像小孩,有奶才安靜。
沒等女人回答,她們便笑得令各自的奶子劇烈地顫跳起來,鳳莊洋溢著歡快的氣氛。
厚生家的也尷尬地笑。女人說,我睡自己的床——一個快死的人怎麼還會想到奶子呢?可她們笑得更放肆了,女人覺得被別人開了玩笑,又拿不出好的回擊辦法,只好說,反正,我有辦法讓他安靜,即使用奶子,那也是我的本事。
女人知道自己之所以能讓老人在夜裡安靜下來,是因為老人把她當成了李文娟。鳳莊的女人是這麼說的。厚生家的也這麼說,你就充當一回厚生的母親唄,反正吃不了什麼虧。女人說,那也算不了什麼,一個行將就木的老頭難道還能強姦我不成?婦人們覺得是,突然沒話可說了。 老人又不是她的父親,鳳莊的婦人們不相信女人一點也不害怕,沒有男人的陪同,夜裡連厚生家的都不敢踏進老人的屋子,因為誰都知道那是離死亡最近的地方。但女人一點不害怕也不可能,有一次,厚生家的就聽到女人在半夜裡發出了一聲驚叫,雖然不是很尖銳,但那聲音肯定是受驚嚇才發出來的。厚生家的以為出了什麼事,翻身下床,在台階下面大聲地問女人,老傢伙去了嗎?女人良久才回答,還沒有。老人適時地打了一個重重的呻吟,像剛剛緩過氣來。厚生家的又說,要不要叫男人?鳳莊沒有男人了,我得到黃莊去叫。女人說,不用了,睡吧。黑夜又恢復了沉寂。沒有人知道,那天夜裡女人為什麼會突然發出驚叫。鳳莊的婦人們都聽到了她的驚叫,知道她也會害怕,經此一嚇,以為她可能不來了,但當天黃昏,女人還是來到了鳳莊,只是比平時稍晚了一點點。
其實,那天夜裡的那聲驚叫確實是因為害怕而發出的。女人竟然不像她自己所說的那麼勇敢、堅強。在她們意料之中的是,她果然也會害怕。
那晚,老人突然精神煥發,跟女人滔滔不絕地說起厚生的母親。我這一輩子,故事多,遺憾也多,夠說得上十輩子的,就一個李文娟,說到死我也說不完。老人說,在死掉之前,我就只說文娟。「她是一個好女人,我從來沒見過那麼好的女人。」老人為了證實自己的話,舉了很多例子,還用準確的數字說明問題,短短的一年時間裡,文娟幹了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二件活,給我洗了八十二次腳,擂了兩百一十五次背,她生孩子的那幾天裡,還給我修過兩次腳趾甲。她不讓我幹重活,她說那些重活呀你留著等厚生出了滿月我再做,那時我還有力氣,為什麼不能幹些重活?文娟說了,她的前夫就是幹重活累壞了,喪失了生育能力,她不能再讓自己的第二個丈夫累壞了……。
老人說,她不讓我幹重活,連輕活也讓我少幹,捕魚期村裡的男人日夜不停地都在江裡捕魚,她呀,不讓我去,讓我養好身體,我的身體除了胃腸不好喜歡拉肚子外沒什麼毛病。一個季節下來,男人們累得趴在地上起不來,我呀,養得胖乎乎的,皮膚又白又嫩,人們說我像衙門的人,對我嫉妒得要死。結果,我變得越來越懶惰,很快成了遠近聞名的懶漢。外面的人都想到鳳莊來看看,陝西的女人到底是長得什麼樣的,竟然不用男人幹活,一個女人也能把家撐起來!
「結果是她累壞了自己。坐月子還挑糞去地裡培莊稼,還給漁場涮魚。她涮的魚比誰都多、都好,別的女人嫉妒她,說文娟,你不怕魚腥啦?文娟說不怕了。那你還暈船嗎?文娟不作聲。正是她們刺激了她,使她想起了船,結果幾天後便跳上烏篷船跑了。那是一條廢棄了的船,不知道是誰丟下的,擱淺在沙灘上,在江邊風吹雨打好多年了,沒有誰願意修補它,好幾次洪水也沒把它帶走,如果知道它會帶走文娟,我早就一把火將它燒了。那天臨近黃昏,我正給厚生洗澡,有人從江邊回來對我喊,方正德,你家文娟沒洗完菜就跑了。我扔下厚生,從村子裡追出來,沿著岸邊拚命地跑。江面上灰濛濛一片,但我還是看見了那條烏篷船,船篷千瘡百孔,船上只有她一個人,她就站在船尾搖船。我不知道她從哪裡弄來的船撐,她把船划到了江中間。多寬闊的江面呀,像海一樣。我大聲喊,李文娟……但我這一喊,那條烏篷船一眨眼間便在江面上消失得無影無蹤,像鬼船一樣。她肯定看到了我,卻不願回頭,連厚生也不要了。鳳莊的人以為我欺負她,把她氣走了——那時候只有我知道,她有病,舊病復發了,生厚生才復發的,那是一種治不好的病,她知道我家窮,不願連累我……」 女人問,什麼病呀?
老人不肯說。他寧願以漫長的靜默回應女人的好奇。
女人改口讚嘆說,多好的女人!
「我到處找過她,要給她治病,即使把我自己賣掉也要攢錢給她治病——她一個人孤零零的,她要去哪裡啊?她不是到外面等死嗎?但我找了大半年也找不著,有人說那條烏篷船滲水,她走不遠,也許還不到陸家莊就沉了……但我不相信那條船會沉,跑得那麼快、那麼穩,她絕對是一把撐船的好手,一條破船到了她手上也跟好船一樣……後來她肯定在哪裡上了岸,在哪裡躲著我,最後,病死在哪裡了……你看,現在她回來了!她就在窗外,我看到她了——她要帶我走了!」
女人突然感到害怕。她不是輕易害怕的人,這時卻壓制不住自己內心的驚懼,哎喲的驚叫了一聲,像閃電劃過寂靜的鳳莊。
「她跟你一樣身材高大,能說會道,見過大世面。」老人低聲地說。這是老人把女人和厚生母親做的唯一的一次對比。 那天早晨,女人的男人早早就開船在碼頭等她,但她硬是要把老人的被子先清洗了。女人說,你不知道我費了多少口舌老人才肯鬆開抓住被子的手。這張被子真髒,黑乎乎的像一張牛皮,把一江的水都洗黑了,如果江裡有魚,也會被毒死。女人就把被子攤在江邊的蘆葦上面曬,黑麻做成的被子像船帆一樣遠遠就能看見。黃昏,女人下船,把被子收起來,走進鳳莊。
厚生家的正在屋簷下等她,稱讚她說,只有你才能說服老傢伙把被子洗了,連厚生也說不服他,死倔。
女人說,我真想把他背到江邊,澈底把身子涮乾淨……我說了,身體髒兮兮的去了那邊,厚生的母親會罵你邋遢,還要罵厚生不孝順。
厚生家的神情驟然緊張,那無論如何得幫他洗一次澡。
老人洗了一生中最後的一次澡。龐大的澡盆就放在床前,水氣一下子瀰漫滿屋子,水裡滲了一些草藥,散發著淡雅的香氣。女人對老人說,過去呀,只有皇帝才能洗這樣的澡水。但老人死活不願洗。「人都快死了,還洗什麼!」老人氣呼呼地說。女人又勸了一會,老人仍斷然拒絕洗澡。厚生家的覺得沒有辦法,要撤走澡盆。女人說聲不要撤,一把將老人抱起,旋即像嬰兒一樣塞進了澡盆。老人試圖反抗,但沒有力氣,只好死死抓住自己的衣服,但衣服很快被女人強行剝落,赤條條一絲不掛。厚生家的害羞,轉身走了。女人熟練而敏捷地把水澆到老人的身上,用毛巾使勁地擦拭,水很快變成了墨黑。老人反抗不成,便張開嘴巴呼喊「李文娟」,開始時聲音很大,後來被水聲壓住了,最後竟溫順得像個孩子,靜靜躺在澡盆裡並裝出死人的樣子,一動不動,讓女人幫他洗完了這次澡。
鳳莊的婦人們打聽到了女人的很多情況。有些情況是從江南傳過來的,有些情況是從厚生家的那裡來的。厚生打過幾次電話回來,厚生家的向男人表達了對女人的滿意,同時也流露了一些猜疑。厚生也許知道的也不多,但還是隱隱約約地說了一些女人的情況。幾天後,鳳莊的女人對女人便另眼相看了。女人感覺得到她們異樣的眼神,連孩子們也遠遠地躲開她。女人終於忍不住問至善,你們為什麼躲著我?至善說,我沒有。女人說,我是說她們。至善直率地告訴她,她們說你年輕的時候是個浪蕩女,在廣州做過「三陪」,現在是第四陪,陪夜。 女人的臉突然暗下來,抓著手提袋的手不斷地顫抖。至善後悔說錯了話,「她們是胡說八道,」至善想挽回,「她們之前還說過,我的阿婆是舊社會的妓女,在船上做皮肉生意,得了髒病才被船家甩掉的……」 女人手裡的袋子終於脫落,幾個番石榴、枇杷子從石階上滾下來。女人並沒有回頭撿散落的果子,呆站在石階的中間,抬頭往正德老人的房間張望。她猶豫了很久,至善以為她會掉頭跑掉,因為她沿著河岸,還能追上她丈夫的烏篷船。但她還是從容地登上台階,走進屋子,點亮了燈。但這一次,至善沒有聽到女人撒尿的聲音。
從此,女人變得鬱鬱寡歡,甚至變得有些羞怯。第二天一早看見別人也不怎麼打招呼,匆匆忙忙地就走。厚生家的似乎意識到自己說錯了什麼,向鳳莊的女人解釋,厚生說了,女人過去也不專門做那種事,如果不是家裡窮,她也不會……她的男人,幾年前從腳手架上摔下來,聽說已經是個廢人,除了開開船,做點賺不了幾個錢的小生意,幹不了什麼活。鳳莊的女人一陣欷歔,都後悔自己說了一些不該說的話。鳳莊的女人們舌頭是長了點,但實際上她們是很感激女人,為表達她們的謝意,那天晚上,她們不約而同地準備了好些東西,糖果呀,瓜子呀,葡萄乾呀,甚至還有奶粉,都是她們的男人從城市裡帶回來或寄回來的,看到女人來了,便熱情地塞滿了女人的雙手和口袋:「這東西,你夜裡吃著解悶。」漢光家的最大方,把壓在箱底捨不得戴的祖傳手鐲借給了女人。這只血紋路清晰的手鐲在漢光曾祖母的墳墓裡待過,能避邪,漢光家的說,連鬼都怕它三分。女人說,那麼貴重的東西我怎麼敢借你的呢,萬一弄壞了怎麼辦?漢光家的說,不要緊,人平安無事最重要,一隻手鐲算得了什麼!漢光家的把手鐲大大方方地戴在女人的手上,女人羞澀地笑笑:「其實,我什麼也不怕,不過,現在心裡更踏實了。」鳳莊的婦人們看到女人都收下了她們的小禮物,心裡也甚是踏實,好像女人已經原諒了她們。但過後的第三天,女人對厚生家的說,她男人的病又犯了,是舊傷復發,她不會開船,村裡又找不到會開船的人,她只好在家護理男人兩三天,這兩三天,就不算錢。 厚生家的有點始料不及,但不好不同意。女人環顧一下散落在四處的婦孺,抹了一下頭髮,往江邊匆匆走去。一會,有小孩回來報,開船的還是女人的男人。女人們的臉上布滿了愧疚,斷定女人是找藉口開溜了。這天晚上,她們又聽到了老人聲嘶力竭的呼喊。李文娟,這個女人的名字又像鬼魂一樣籠罩在鳳莊的頭上,纏繞在她們的耳邊。宏發家的終於忍不住了,起來罵人,聽起來是罵女人,實際上是罵老人。她一開罵,鳳莊的人都睡不著,穿著睡衫聚在厚生家的院子裡,你一句我一句的,開始是埋怨,後來是想辦法。但想什麼辦法,夜狗不知疲倦地吠,老人依舊一聲一聲地呼喊著李文娟,只是那聲音漸漸弱下去,像從很遙遠的地方傳來的,輕輕地抓著你的耳,然而正是這種聽起來像垂死掙扎的聲音讓人更毛骨悚然和難以忍受。她們束手無策,那只有等女人快點回來。三天後的黃昏,女人終於又來到了鳳莊,大家才鬆了一大口氣。 三天不見的女人明顯消瘦了許多,臉上結實的肉不見了,多了兩塊豬肺一樣的雀斑。
「你家男人的病好了?」
女人說,好不了,臥床了,醫生說再做一次手術看看,不成的話到廣州的大醫院試試……小兒子也湊熱鬧,發高燒,拉肚子,真會煩人。
婦人們關切的程度更深了,「你先把兒子的病治好,發高燒等不得……」
女人說,沒大礙了,由鄰居幫看著。
「你不在,夜裡老人又叫開了。」
女人淡然道,這老傢伙……其實我在的時候他也叫——他每時每刻都在呼喊李文娟,只是你們聽不見。
婦人們覺得女人的話有些深意,像是一個讀過些書的人。
平日裡節儉得可憐的婦人們自覺地從深不可測的口袋裡掏出一些面額不等的紙幣來,塞給女人的褲兜裡。女人百般推卻,婦人們要生氣了,她才收下,說是借,將來一定還,然後爬上高高的石階,走進老人沒有房門的房間。看到老人房間的燈亮了,大家的心也亮了。但幾乎與此同時,婦人們聽到了老人一聲嚴厲的斥喝:
「誰要說文娟得的是髒病,我做鬼也不放過她!」
這句話說得比平時重一百倍,像是積蓄了很久的力量才說出來的,甚至把女人也唬住了。很明顯,這句話是說給石階下的婦人們聽的,是一個將死之人對活人的最後警告。婦人們的臉色剎那間全變了樣,慌裡慌張,隨即爭相向厚生家的否認自己說過李文娟的不是,我們都沒見過她,已經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啊!厚生家的連連澄清事實,誰說啊,誰都沒說過。聽厚生家的這麼一說,婦人們才放下心來。一安靜,便聽到了女人不斷撫慰老人的說話聲。老人的氣估計憋了很久,就等女人來了才發洩。女人語重心長地說,她們都說文娟是一個好女人,沒有人說過她的壞話——她們也沒有說我的壞話,我聽到的全是好話。
老人的氣一下子還緩不過來,不斷地咳嗽。此後很長的時間裡,婦人們再也聽不到女人的說話聲,聽到的只是老人無休止的咳嗽。她們驚疑,到了這時候老人還能說出那麼嚴厲的話,甚至聲音還那麼雄壯、凶悍。她們有點失望,心懷疙瘩各自散去。
這個夜裡她們又聽不到老人的呼喊了,寧靜得好像要發生什麼事似的,她們忽然不習慣這種寧靜,心裡癢癢的,想聽到老人的聲音,甚至希望老人突然用一聲熟悉的、銳利的呼喊打破黑夜的沉悶和驅散她們心頭的不安,讓她們能安然睡去。這種等待一樣也很漫長,她們輾轉反側,又凝神定氣,耳朵都向著老人的方向伸。老人是在下半夜去世的。第一次雞啼後,厚生家的迷糊裡聽到女人叫她,她驚醒了,側耳一聽,果然是女人在石階上頭大聲地喊:老傢伙不成了。整個鳳莊都聽到了女人的呼喊,鳳莊提前醒了,到處傳來長舒一口氣的聲音。厚生家的驚慌地爬起來,雙手抱著肚皮走到石階下面,對是否爬上去正猶豫不決。女人說,你不用上來了,老人不能說話了……厚生家的慌亂地說,那我馬上去黃莊,叫誰家的男人背他到堂屋去。女人說,也不用了,我自己能背。在厚生家的驚疑之際,女人已經把老人從屋裡背出來。老人耷拉著頭,喉嚨裡發出嘓、嘓、嘓的聲音,像被骨頭卡住了。厚生家的小心翼翼地問,老傢伙留下什麼話嗎?女人說,沒有,整晚他就只說過一句話,大家都聽到了,就一句…… 女人從石階上一步一步探腳走下來,搖搖欲墜。厚生家的既為女人擔心,又感到恐懼,本能地往下退卻,把路讓給女人,甚至忘記用電筒為女人照路。當無路可退,女人從她身邊走過的時候,厚生家的怯生生地問老人:大,你沒事吧?
老人沒有回答,緊緊地伏在女人的背上,雙手鬆鬆垮垮地搭在女人的胸前,像一堆不可靠的爛泥。
「人一死,就變重!」女人喘著粗氣說,她頭髮凌亂,沒有穿鞋,「快叫至善,給老傢伙送終。」至善已經躲在屋角的拐彎處,伸出半顆頭。厚生家的說,至善,到堂屋跟阿公叩頭。至善害怕,轉身倏地消失在黑暗裡。厚生家的遠遠地跟在女人的背後,一直來到堂屋。女人摸黑進去了,好像踢到了什麼,罵了一聲。厚生家的說燈在中間的台上,有火柴。女人又踢到了什麼,又罵了一聲,這才把燈點亮。堂屋裡的燈光像瀕危的生命一樣孱弱,厚生家的看不到女人的臉,也不敢靠近,只是站在堂屋的門外,等待女人從屋裡傳出話來。大約過了十幾分鐘吧,女人才從堂屋裡走出來,輕描淡寫地告訴厚生家的:「天一亮,你就可以給厚生打電話了。」 天一亮,女人就收拾東西走了。鳳莊都忙於為老人辦理後事,開始沒有誰留意她的離去,直到有人突然說起,方學明的父親癌症到了晚期,挨不了多久,開始哭苦喊痛,喋喋不休地叨嘮先他而去的老婆,看樣子也需要陪夜的女人,她們才想到女人。聽說女人要走了,連手鐲都還給了漢光家的。她們丟下手裡的活匆匆跑回家裡,胡亂抓了一些東西,麵條、粉絲、醃菜、臘肉什麼的,有的看看家裡沒有什麼送得出手的,焦急得四處去借,借不到東西乾脆從米桶裡飛快地裝了滿滿的一袋米……那是要送給女人帶走的,她畢竟給鳳莊帶來了好多個安靜的夜晚。她們爭先恐後地追到江邊的時候,女人的烏篷船已經離開碼頭。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是女人自己開的船。她男人沒有來。她原來不會開船呀,現在卻開船了。可以斷定的是,昨晚也是她自己開船來的! 人們正驚訝間,至善突然喊了一聲:「她的船要翻了!」至善你能不能不亂說話?婦人們狠狠地瞪了至善一眼,他的母親甚至掄起巴掌要抽他的嘴巴。「我看她的船真的要翻了!」至善依然堅持自己的判斷,也許是要親眼證實自己並非信口開河,他沿江邊追著烏篷船奔跑。 女人站在船頭,手抓著方向盤,動作異常生硬、拙笨,不像是在駕船,而是在試圖制服一條鯊魚。船不聽使喚,負隅頑抗,船體左右搖晃,最後向左側明顯傾斜,看上去就要翻了,把婦人們的心吊到了空中。婦人們屏氣凝神,緊張得渾身是汗,直到船稍稍平穩,才小心謹慎地向女人晃動手中的東西,但依然不敢喊話,生怕一喊話便分散她的注意力,鑄成翻船悲劇。當她們覺得可以鬆一口氣了,船卻已經到了江心,在晨曦中越去越遠。方學明家的突然覺醒,想對著船呼喊,卻連女人的名字也不知道,窘迫得滿臉通紅。就在轉眼間,船消失得無蹤無影,只剩下浩瀚的江水和四向逃逸的霧氣。
「跑得賊快,像鬼船一樣!」
方學明家的悻悻地說。
陪夜的女人
◎朱山坡
女人搭乘烏篷船來到鳳莊。 這是一條很特別的船。除了特別扁小外,尖細而稍向上翹的船頭,古香古色的船板和塗抹了厚厚一層桐油的船篷,還有斷斷續續引人發笑的馬達聲都引起了圍觀者的好奇。鳳莊早就沒有這種船了。其實,由於航道淤塞,又由於無魚可打,不說輪船,連漁船都已經很少見到。烏篷船從下游逆流而上,力氣快用完了,速度越來越慢,宛若一個苟延殘喘的人。
在人們的擔心中,船總算在廢棄了的碼頭靠了岸。船頭擺滿了炊具和其他日常生活用的物品,亂得像開雜貨店。女人從船上跳下來,笨拙地拴好船,撣撣身上的...
目錄
∣輯一∣詩
高鵬程 紙上建築
沈魚 我仍舊無法深知
張二棍 暮色中的事物
顏梅玖 守口如瓶
∣輯二∣散文
胡竹峰 墨跡
謝有順 要文藝復興,先復興文學
徐海蛟 無法抵達
∣輯三∣小說
朱山坡 陪夜的女人
東君 聽洪素手彈琴
楊怡芬 兒孫滿堂
艾瑪 白鴨
鄭小驢 讚美詩
彤子 月光曲
∣輯四∣期刊暨獎項介紹
《人民文學》年度獎項介紹
《江南》雜誌介紹
《作品》雜誌介紹
《當代》年度獎項介紹
《詩刊》獎項介紹
∣輯一∣詩
高鵬程 紙上建築
沈魚 我仍舊無法深知
張二棍 暮色中的事物
顏梅玖 守口如瓶
∣輯二∣散文
胡竹峰 墨跡
謝有順 要文藝復興,先復興文學
徐海蛟 無法抵達
∣輯三∣小說
朱山坡 陪夜的女人
東君 聽洪素手彈琴
楊怡芬 兒孫滿堂
艾瑪 白鴨
鄭小驢 讚美詩
彤子 月光曲
∣輯四∣期刊暨獎項介紹
《人民文學》年度獎項介紹
《江南》雜誌介紹
《作品》雜誌介紹
《當代》年度獎項介紹
《詩刊》獎項介紹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