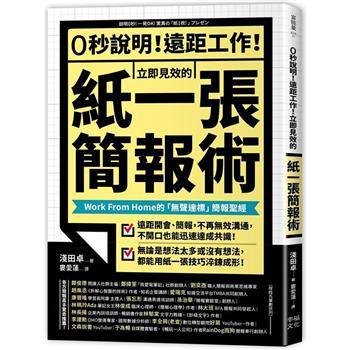爸爸葬禮結束後一個月,媽媽便帶我去南京市和平路小學(現在改名為南京市北京東路小學)報名上學。這所小學歷史悠久,一直是南京市的重點小學。校園占地面積很大,每個年級都有各自獨立的房舍作教室,亦有獨立的課間活動場所。六個年級六排平房,房屋周圍的水泥走道兩旁建有許多漂亮的花壇。一年四季各種鮮花輪番開放,錯落有致,與學校大門內側的兩個小池塘交映成輝,環境可謂優雅。加之學校地處市府大院公交一村內,受到政府的直接關懷,條件相當不錯。特別是學校後面有個大運動場,有當時南京市屈指可數的標準沙坑和跑道,可以用來召開省市級田徑運動會。運動場中的大草坪是一個標準足球場,我們稱之為大操場。只要不下雨,全校師生每天都集中在此做早操,平時各年級的體育課也都在這兒上。這樣的體育運動條件,可以說在南京市的小學中是得天獨厚絕無僅有的,就連絕大多數的中學也望塵莫及。
國民黨時期這所學校叫藍家莊小學,共產黨接管政權後,將學校改了名,主要接收共產黨南京市委和市政府機關的幹部子女入學。當時政府嚴格規定,兒童年滿七周歲才可進小學,有些孩子生日差幾天都不行,往往被耽誤一年。那時無論是校方還是家長,大家都高度自覺,嚴格按規定辦事,基本無人走後門,亦沒有聽說過請客送禮這一套。所以我們姐弟幾人都是七周歲半以後才開始讀書的,比西方的孩子們上學平均晚了兩年。
媽媽從小愛讀書,她說要不是為了抗日而獻身革命,她是一定會上大學的。現在她將希望寄託在我們幾個孩子身上,要我們努力學習,將來能考上名牌大學,讓她上大學的夢想在我們身上實現。她的這個願望從我上幼稚園起就灌輸給我,從而奠定了我日後用功讀書的思想基礎。
我和我的兩個姐姐在同一所小學就讀。我上一年級時,她們兩個,一個上三年級,一個上六年級,學習成績都不錯。尤其是安東,已經拿過幾個學期的「三好生」獎狀,很讓媽媽感到寬慰。這使從小個性要強的我暗下決心,一定要超過她們。我自幼比較聰明伶俐,又什麼都不甘落後,自覺性和刻苦性都較強,,所以一上學就在班上拔尖,每次考試都力爭滿分,博得了老師們的喜愛,指定我當了班長,繼而又當了級長,「三好生」獎狀自然不在話下。我在和平路小學讀書六年,十二個學期拿回了十二張「三好生」獎狀。讀書成績是姐妹中間最出類拔萃的,加之在女孩中又數我最小,因而得到媽媽的格外寵愛,在姐弟們發生口角時,她經常袒護我,我對她也特別親。這些卻遭到了姐姐們的嫉妒。一九五七年春大鳴大放期間,年僅十歲的安東,竟然寫了大字報貼在家中飯廳的牆上,批評媽媽偏心眼兒包庇我。這張大字報只貼了半天,當晚就被媽媽喝令撕下了。可是安東心裡並不服氣,撕下大字報時她氣得臉漲得通紅,過後還好多天不跟我說話。
一九五六年,毛澤東發表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鼓勵全國人民大鳴大放,對共產黨提意見。好多人,特別是知識份子,非常高興,以為毛澤東講民主,給人民言論自由。誰也沒有想到他的「雙百方針」,目的是為了要「引蛇出洞」,誰提意見就整誰,上當受騙最多的是知識份子,其中有很多人是不足二十歲的尚在大專院校就讀的青年學生。一九五七年春夏之際,我上小學一年級下半學期時,反右派運動就在全國大張旗鼓轟轟烈烈地展開了,首當其衝被開涮的就是知識份子。凡是頭年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大鳴大放的人都被打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被開除公職,發配邊疆。
一天夜裡,我從睡夢中驚醒,身邊不見媽媽,卻聽見客廳裡有人說話,便一骨碌爬起來跑到客廳。只見一位面龐英俊身穿軍服的年輕人坐在大方桌旁,與外公外婆和媽媽說著話。這人的軍服上沒有領章和肩章,滿臉是淚,媽媽握著他的手不停地安慰。見我進來,媽媽說這是我三舅,明天一早要出遠門了,他們要說說話,叫我不要打攪。說著她就送我回房睡覺,第二天早晨我起床時,三舅已經走了。
這時候媽媽才告訴我,二十二歲的三舅周汝生是共產黨員,年輕有為的空軍少尉軍官。他畢業於軍事院校,一直表現優秀,原本前途無量。只因他在鳴放中提出中國軍隊不該一邊倒,什麼都學蘇聯,被打成了右派,而後被開除了黨籍軍籍,發配青海勞動改造,社會的棟樑轉瞬間成為階下囚。
五十年代的中國,一切學蘇聯。毛澤東稱蘇聯為「老大哥」,號召全國人民學俄語。共產黨高級幹部們最時髦的事情,就是送子女去蘇聯留學。中國人民解放軍採用的是蘇式軍銜制,共產黨在軍隊中提倡跳蘇聯舞,唱蘇聯歌。
我的三舅從學生時代起就是個很活躍的人,積極參加學校的各項活動,特別是他愛好文藝能歌善舞,經常參加各種演出,是個有天分的文藝活動積極份子。他參軍後也一直是軍隊演出隊的成員,對中國的傳統歌舞情有獨鍾。在鳴放運動中,生性爽直的他,對一切學蘇聯的現像提出了看法,認為不能光唱蘇聯歌跳蘇聯舞,也應該有一些我們自己的傳統歌舞。沒有想到,他的這點直率,使他在剛剛踏上人生旅途之時便遭了殃,被打成了「反黨反毛主席」的右派份子。一個革命的主力一下子就成了階級敵人,斷了前程,毀了青春。最糟的是,由於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所以受了那麼大冤屈人,不允許有任何申辯,有理無處講,只能陷入絕望境地。
那場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使得全國範圍內,受冤枉被打成右派份子的有五十五萬人之多,受牽連的親屬有幾百萬人。其中各大學十八、九歲的年輕學生受害人數最多,因為他們閱歷淺,天真幼稚又敢想敢說,所以成為名為「言者無罪」而實質「言而有罪」的受害者。這些年輕的學生被打成右派後,又被開除學籍,再被遣送到邊遠貧困地區勞動改造,一去就是二、三十年,好多人喪失性命。倖存者們也大多數是九死一生,受盡苦難。這一場反右運動使得多少人才被摧殘,多少家庭被毀滅!在毛澤東統治的中國大地上,連綿不斷地上演著一齣又一齣人間悲劇。
事實上,共產黨中央給各個單位都下達了打右派指標,每個單位都要抓出百分之五的右派份子來,否則單位的領導就要倒楣。當領導的若不想倒楣,就必須抓出替罪羊。為了完成這個混蛋的百分之五的指標,有些領導甚至於把一些在鳴放中沒有說過一句話的人也打成了右派。這種置人於死地的做法,純粹是他們為了向上級邀功請賞,抓出這些人來為那個百分之五充數。不幸的三舅周汝生只不過說了幾句大實話,就莫名其妙地被劃進了那個「百分之五」。
畢竟三舅在部隊一直表現良好,所以在他被發配青海之前,部隊領導動了側隱之心,給了他一天假,允許他回家與親人告別。那天晚上,他在我家對外公外婆和媽媽哭訴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踏上了流放之途。他這一走,竟成了與外公外婆和媽媽的永訣。在他走後的幾年中,媽媽和外公相繼病逝,他都未能獲准回家奔喪。二十八年後,他獲得平反,摘掉了右派帽子,恢復了黨籍,被分配到安徽省一個小縣城的集體工廠擔任廠長。平反後,他到南京來看我。這時我見到的三舅與當年那個瀟灑英俊的青年已完全判若兩人,我見到的是滿頭雪白銀絲的耄耋老者。漫長艱苦的歲月,無情地在他的臉上刻下了一道道深深的皺紋,五十歲的人看上去像七、八十歲。他沒有成家,孑然一身。當他用顫抖的雙手撫摸著媽媽的遺像時,不禁老淚縱橫。看著無聲的淚水像斷了線的珠子一樣從他的雙眼滴落在地,我砰然心動,突然明白了什麼是痛苦,什麼叫創傷。想到三舅的大好年華被無端葬送,同情的眼淚一下子從我眼中奪眶而出。
反右鬥爭後,全國人民沉默了。為了激起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發動了大躍進運動。他號召全國人民「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主觀臆斷地決定要用成倍的高速度發展國民經濟,在最短的時間內趕上或超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此,他對工農業產量盲目地制定了一系列不切實際的指標。
那年我剛九歲,卻已經被教育成狂熱的「共產主義接班人」,上進心非常強,政治熱情相當高。那種政治熱情說給今天的孩子們聽,他們根本就不可思議。在那一年的六月一日國際兒童節,我與其他六位同學一起,被批准加入少年先鋒隊,成為班上的第一批少先隊員。新隊員人數剛好可以成立一個小隊,我本來就是班長,所以一入隊就成了小隊長,左臂戴上了鮮紅的一道杠標誌。
當時我們所受的教育是,實現共產主義是我們最崇高的理想,為了這個理想我們必須跟黨走,老師們諄諄教導我們說,人生三件大事,入隊、入團和入黨。少先隊是共青團的後備軍,而共青團是共產黨的後備軍。所以入隊對於小小年紀的我來說,是很神聖很光榮的事。當紅領巾在我的胸前飄蕩時,當沒有入隊的同學對我投來羡慕的眼光時,我覺得非常自豪。入隊後,我更加積極地投入到學校的各項活動中去,我要用我的實際行動支持大躍進運動,做媽媽的好孩子,老師的好學生。
我們小學生的主要任務是除四害,消滅蒼蠅、蚊子、老鼠和麻雀。四害中的前三害我們就在家裡對付,我家裡基本上沒有蚊子和老鼠,但是一入夏就有成群的蒼蠅在屋內外到處飛舞,很是討厭,所以我們對除四害運動非常歡迎。我們姐妹人手一隻蒼蠅拍,見到蒼蠅就打,打死的蒼蠅都撿起來放在紙盒裡計算成績。每天傍晚,我都將裝有死蒼蠅的紙盒送到蘭園居民委員會去。居委會主任認真清點盒中的死蠅,然後寫個收條曰:「茲收到高安華同學交來蒼蠅屍體XX隻,特此證明。」然後鄭重其事地蓋上居委會的大紅印章。第二天我就將這個收條交給老師,報告除四害的成績。我才上小學二年級,就已經懂得當好班幹部必須以身作則。每天放學後我都不去玩耍,做完了作業就除四害,在我的帶動下,其他同學也都照我這樣做。我們還在老師的帶領下,遍查市內公共廁所,一旦發現有蒼蠅的蛆,就用小鏟子搜羅起來,再挖個小坑埋掉。我們不怕髒不怕臭,積極性很高。我們的努力確實卓有成效,到第二年夏天,南京市內的蒼蠅明顯地減少了。
除四害運動中聲勢最為浩大的是:全民動員,消滅麻雀。毛澤東說麻雀會糟蹋糧食,必須徹底消滅,於是麻雀成為人民公敵。一九五八年整個春夏,一到星期天,安東,衛國和我都要跟媽媽一起去公教一村,參加市委大院裡的集體滅雀大戰。我們用的是人海戰術。市級機關的幹部們,幾乎家家都是男女老幼全體出動,分散站在市委大院的各個角落。每個人手裡都拿著鍋碗瓢盆或者搪瓷茶缸和臉盆,一看到天空中有鳥飛過,就全體齊聲大喊,同時用棍子或小勺敲擊手中的盆盆罐罐。成千上萬的人製造出震耳欲聾的響聲,猶如千軍萬馬馳騁疆場,驚恐的鳥兒們在天上不停地亂飛,根本不敢停下歇息。幾個小時下來,鳥兒們極度疲勞,飛不動了就從天上掉下來。這時候人們就一哄而上,爭先恐後地捉拿落地的麻雀「戰俘」以計算成績。如果落地的鳥兒一息尚存,人們會毫不猶豫地將其勒死,絕不留情。不論打死的是何種鳥雀,一律當作麻雀計數。死掉的鳥兒越多,人們越高興,無絲毫憐憫。
我和媽媽每次參加滅雀大戰,都站在大操場,那兒人最多,而且有鑼鼓家什助威。我左手拿個鋁製飯盒,右手拿個小羹匙,不停地敲打,同時跟著大人們拼命地扯足嗓門對天喊叫。我的手敲酸了,喉嚨喊痛了,都毫不介意,因為這是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啊,怎麼能落後呢?每當我見到有鳥兒從天而降,就像消滅了一個敵人一樣,感到無比興奮,覺得自己也為建設社會主義祖國出了一分力量。
如今,我已到了花甲之年,毛澤東時代在我頭腦中建立起來的抽象的共產主義大廈,早已在中國殘酷的現實生活中土崩瓦解了。但是回想起五十餘年前的我,一個九歲的兒童,一個二年級的小學生,共產主義的教育竟能如此牢牢地印在腦子裡,深深地紮在心窩裡,溶化在血液中,落實在行動上,真是頗多感慨,不得不承認共產黨的宣傳鼓動是相當成功的。
其實,我們當年的滅雀大戰消滅的麻雀,是吃害蟲的益鳥。其他被滅鳥類,亦多為益鳥。第二年全國很多地方發生蟲災,沒有了益鳥,又無足夠的滅蟲農藥,加上其他天災人禍,致使整個神州大地糧食產量普遍大幅度下降,有些地區甚至顆粒無收,從而爆發了連續三年的全國大饑荒。儘管如此,卻沒有人敢懷疑毛澤東的政策是荒唐可笑的,我們仍然堅定地相信,毛主席和共產黨的領導是英明正確的,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對毛盲目崇拜,盲目緊跟,沒有人意識到個人迷信的危害性。抽象的共產主義信仰,像一種宗教,牽著人們的鼻子走。這種宗教在潛移默化地毒害和腐蝕著我們的靈魂,使我們頭腦僵化不去獨立思考,唯命是從。這樣,就為數年後毛澤東發動的那一場史無前例的「文革」浩劫,打下了可悲的群眾基礎,使得自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毛澤東能夠為所欲為,玩弄權術,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終於在六十年代中期,將中國人民拖進長達十年之久的政治動亂,陷入自相殘殺的苦難深淵,從而寫下了中國歷史上乃至世界歷史上最為慘痛的一頁。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高安華的圖書 |
 |
$ 264 ~ 270 | 天邊
作者:高安華 出版社:新銳文創(秀威代理) 出版日期:2011-09-0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418頁 / 14.8*21.0 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天邊
天邊
View more documents from TAAZE 讀冊生活
這是一部根據作者本人親身經歷而寫的回憶錄,講述了一個幼年喪父母,中年喪夫的中國女人個人奮鬥的故事。在中國特定的政治背景下,主人公從小被培養成堅定、忠實的共產主義信徒。但是「文革」大動亂的殘酷無情,生活的變故和個人的悲慘遭遇使她最終拋棄了原來的信仰,奔向西方。充分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三、第四代人的思想演變過程。
故事從作者的父親寫起直至作者離開大陸,歷史跨度八十多年,囊括了這一期間主要歷史事件和政治運動,是一部中國近代史的縮影,既描述了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共產黨中國的青少年的天真無邪,又展示了八、九十年代中國的中青年人新的世界觀。作者也在歷史的長河中幾經沉浮,備受磨難,最後找到幸福。
作者簡介:
高安華,祖籍安徽。1949年3月11日出生於山東,父母均為共產黨老幹部。童年在南京度過,七歲喪父,十二歲喪母。「文革」開始時讀高中二年級,屬老三屆。在校時為歷屆三好生,多次被評為標兵。1968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任野戰醫院護理員。因活思想被親姐揭發遭受批判而復員。當了六年工人,後自學英語,1976年8月調入江蘇省外貿任外銷員。多次參加廣交會和大型對外貿易談判,擔任英文首席翻譯。25歲結婚,育有一女。33歲喪夫,36歲被打成「特務嫌疑」被捕入獄。後經法官營救,逃脫滅頂之災。丟了鐵飯碗,嘗盡世態炎涼。1994年45歲時嫁給英國人海瑞,現在定居在英國。
章節試閱
爸爸葬禮結束後一個月,媽媽便帶我去南京市和平路小學(現在改名為南京市北京東路小學)報名上學。這所小學歷史悠久,一直是南京市的重點小學。校園占地面積很大,每個年級都有各自獨立的房舍作教室,亦有獨立的課間活動場所。六個年級六排平房,房屋周圍的水泥走道兩旁建有許多漂亮的花壇。一年四季各種鮮花輪番開放,錯落有致,與學校大門內側的兩個小池塘交映成輝,環境可謂優雅。加之學校地處市府大院公交一村內,受到政府的直接關懷,條件相當不錯。特別是學校後面有個大運動場,有當時南京市屈指可數的標準沙坑和跑道,可以用來召開...
»看全部
目錄
目次
自序
引子
第一章 我的父母
第二章 為了新中國而戰
第三章 我的幼年
第四章 父親之死
第五章 大躍進
第六章 失去母親
第七章 寄人籬下
第八章 南師附中
第九章 文化大革命
第十章 五朵金花
第十一章 當兵
第十二章 暗箭
第十三章 南京無線電廠
第十四章 乒乓外交
第十五章 深挖「五.一六」
第十六章 埋頭讀書
第十七章 我的婚姻
第十八章 永別了,周總理
第十九章 以工代幹
第二十章 經濟英語培訓中心
第二十一章 生活的變故
第二十二章 坐牢
第二十三章 我的法官
第二十四章 為了生存
第二十五章 幸福...
自序
引子
第一章 我的父母
第二章 為了新中國而戰
第三章 我的幼年
第四章 父親之死
第五章 大躍進
第六章 失去母親
第七章 寄人籬下
第八章 南師附中
第九章 文化大革命
第十章 五朵金花
第十一章 當兵
第十二章 暗箭
第十三章 南京無線電廠
第十四章 乒乓外交
第十五章 深挖「五.一六」
第十六章 埋頭讀書
第十七章 我的婚姻
第十八章 永別了,周總理
第十九章 以工代幹
第二十章 經濟英語培訓中心
第二十一章 生活的變故
第二十二章 坐牢
第二十三章 我的法官
第二十四章 為了生存
第二十五章 幸福...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高安華
- 出版社: 新銳文創 出版日期:2011-09-01 ISBN/ISSN:978986609413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18頁
- 類別: 中文書> 傳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