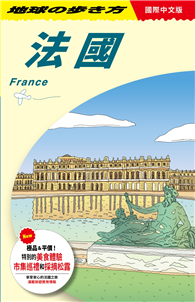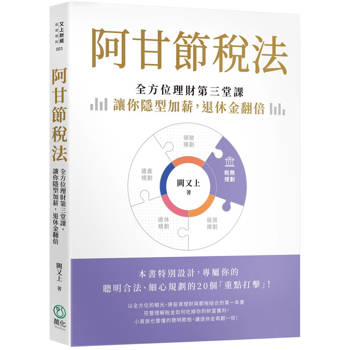序一
客往何處去?
董冰峰(藝術策展人/製作人)
坦白說,在今天嘗試歸納或梳理聞海的獨立電影並非易事。一個是導演的創作仍然處於一種高產的狀態;另外,在過去數年中,聞海的電影創作已經逐漸地表現為一種「之間」的狀態:既在中國大陸之內,又在之外。這裡的意思,不僅僅是說聞海移居香港之後,拍攝和反思中國大陸的社會或政治現實,已經有了相當的距離和「直接性」的矛盾交錯;而是換種角度來說,或者正是緣由這種目前「客居」的「之間」的狀態,更使得聞海的電影創作有了更為寬廣的跨區域的社會政治視角,或可更有力地以獨立電影來進行一種社會批評和介入的行動。
或者無需旁人歸納,聞海已經在專著《放逐的凝視──見證中國獨立紀錄片》書中,巨細無遺地紀錄了他視野中和親身經歷的「中國獨立電影」,甚至書中的不少隱密細節,連我都聞所未聞,可見聞海對行動涉足之深和觀察力之細微。所以,聞海的身分既是電影創作者又是寫作者,既是一位融合獨立電影與實驗影像的藝術家,又在具體的中國社會的政治議題中勤力而為。在本次的回顧展中,觀眾應該可以更為清晰和全面的了解到聞海這一多層次的工作形態及其藝術成就。
討論聞海,無疑同時也需要解釋「中國獨立電影」的問題。的確,從1990年代初期在中國興起的獨立製作的這一潮流,對於中國電影與中國當代藝術來說都是意義重大。我的一個看法是,獨立製作強調的個體行為和實踐,已經完全從1980年代的啟蒙的宏大敘事中解放出來;另外,由於其秉承的個體的自主性和「自治」的特質,也使得1990年代,無論在錄像藝術、紀錄片、「獨立電影」,還是吳文光說的更為包容性的「個人的影像方式」等影像實踐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和一種融合,開發出別開生面的新氣象。同時,也由於1990年代在國內許多非官方的藝術和獨立製作都缺乏一種必要的公共渠道來進行交流和展示,也就產生了類似藝術史家巫鴻所說「實驗」的這種藝術類型和藝術機制的一種替代模式。「獨立電影」、「地下電影」都屬於這一時期的典型稱謂和生存狀態。我們看到,無論聞海(尤其是短片《殼》[2006]),還是王兵、趙亮、吳文光、毛晨雨、邱炯炯等1990年代以來的獨立電影人,對於十數年左右的中國當代藝術都有相當的參與度與藝術實驗形態上的貢獻。
我說的「之間」和聞海說的「放逐」,其實本質來說都在形容一種個體生存的生命狀態。這一點在聞海幾乎可以說是全部的電影中非常強有力的表現出來:無論是《夢遊》(2006)中的藝術家、《我們》(2008)中的知識分子,還是《凶年之畔》(2017)中的工人行動者,聞海幾乎完整地勾勒出全球化進程中的中國社會,最為複雜多變的社會群體的眾生畫像,並且其電影以極具原創風格的影像美學與社會題材表達的緊密張力,近距離帶動和極大的感染了作為觀看和思考電影與實驗藝術的受眾。由此,在聞海即將於台北舉行的電影回顧展上更具期待。
序二
對聞海電影的片面見解
黃明川(台灣獨立電影導演)
聞海從電視新聞攝影專業中培養出身,面對快速變動的中國社會,各地各領域事件頻仍,想更深刻理解核心原因,一出發即自許為現場的攝影採集者、檔案資料保存者的雙重意圖,這個特色從他離開電視台專職紀錄片開拍第一部《軍訓營紀事》(2002)時就存在。
有一種理想深埋其內心,就是希望能將所拍攝到的影音檔案全都呈現在觀眾面前,一鏡到底的長時間談話,不經剪短或剁碎的一再出現,相當程度反應出聞海腦中拍到多少就剪出多少,以及他所見均屬珍貴畫面的隱喻。我們應該將之定位於文化使命的層次,而不僅只於廣納所存資料的想法;他處理鏡頭與鏡頭相接,多數是時間序的概念,那些蒙太奇或經由剪輯產生藝術意義並非聞海所好,尤其是在多人互動的場景中,順理原汁原味,沒有旁白的必要。
長時間且足夠表述深度談話,在聞海紀錄片中也極為重要,這前提具有多重含義:首先微廣角鏡頭長時間不停地觀看所有交談者,可披露他們彼此間的細緻關係,不必經由分鏡來強調個別的表情或反應;也因爲無分鏡與特寫,又每人表露出於鏡頭裡的時間相當,默默地帶有人人平權的概念。亦即在交談中無人是英雄,雙方(或多方)的心理姿態,或誰是這一幕的主客及支配者自然出現,由觀眾自行理解,導演在此立場毋寧是中性的。聞海的主觀選擇倒是流露於題材,而非拍攝與剪輯,攝影機與剪輯軟體都只是工具;對於他,內容才是至上的價值。就中國的巨大與人口數量而言,個別導演想要吞吐其現象核心並不容易,長鏡頭的使用,於是成為涵蓋不完的現實的必然手法,也因此,長鏡頭成為中國紀錄片者,欲於有限觀察中實踐看多、看深的時代美學。
當然,非英雄或反英雄化的平民思想更應該被特別提及,這也是聞海從開始到今天維持一貫的精神關注。《軍訓營記事》的小孩、《喧嘩的塵土》(2004)的群眾、《夢遊》的裸身藝術家、《我們》的異議者、《西方去此不遠》(2010)的佛教徒,到《凶年之畔》(2017)、《女工》與《喊叫與耳語》(2018)的工人,以及《在流放地》(2019)的流亡的文人與藏人等均非英雄,只是希望被體制平等對待的一般人而已,他們從各階層與年齡反射出大社會劇烈變革中的不安與失落,雖逐次放大場域,卻非常整齊訴說著同一時代的壓抑。聞海關心從2002年單純小孩的軍訓營,擴散到藝術、政治、宗教,及2018年最多人口的工廠工人,以至隔年之流亡者,共近二十年,吻合中國國力急速興起的高峰時期,所產生的政治權力集中及社會衝突擴大化的現象。
中國現象吸引西方的注意,其特殊性離不開龐大勞動力與世界經濟整體的密切關係,從而中國市場開放與物價高升所迎來的勞資矛盾,亦必是國際注目的焦點,其物質化、都市化缺乏與之同步中產階級的權力開放,引發更深度複雜、多面向的騷動。難怪聞海在2017-2019年所完成的《凶年之畔》、《女工》和《喊叫與耳語》,已經不再保持單一故事的線性敘事,反而走向多線交織的拼貼風格,企圖以此方式容納舖天蓋地的複雜現實,也正因爲各故事線段彼此無必然牽連,唯靠觀眾自己去猜測如此故事背後真正的主要原因。
千禧年後,聞海移民香港,影片多次放映於歐美並時常獲獎,他理解西方文明,也熟悉西方紀錄片史所記載的理念。其後2014年,在香港創辦「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2016年出版《放逐的凝視──見證中國獨立紀錄片》專著,隔年又開始於香港策展「決絕──1997年以來的中國獨立紀錄片展映」,凡此不但均與中國政府的權力集中,及民間獨立製作的紀錄片及紀錄片影展受到壓制有關,同時也看得到他不再追逐單一題材,除拼貼許多不同地點不相干的事件外,更加入動畫、重音樂以強化故事力道,2018年的《喊叫與耳語》即是此時期此風格的代表作品。
紀錄片的創作與環境息息相關,二十年來聞海始終堅持於「真實紀錄」美學的純粹風格;更因胸懷檔案文獻巨庫而採訪許多位中國紀錄片導演,為他們出書;並在香港策劃中國紀錄片展,讓他們的影片被看見。聞海的努力不僅僅反應出他踏實工作與關心中國大眾的情懷,其足跡也已在中國獨立紀錄片史中深烙下印記。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高長空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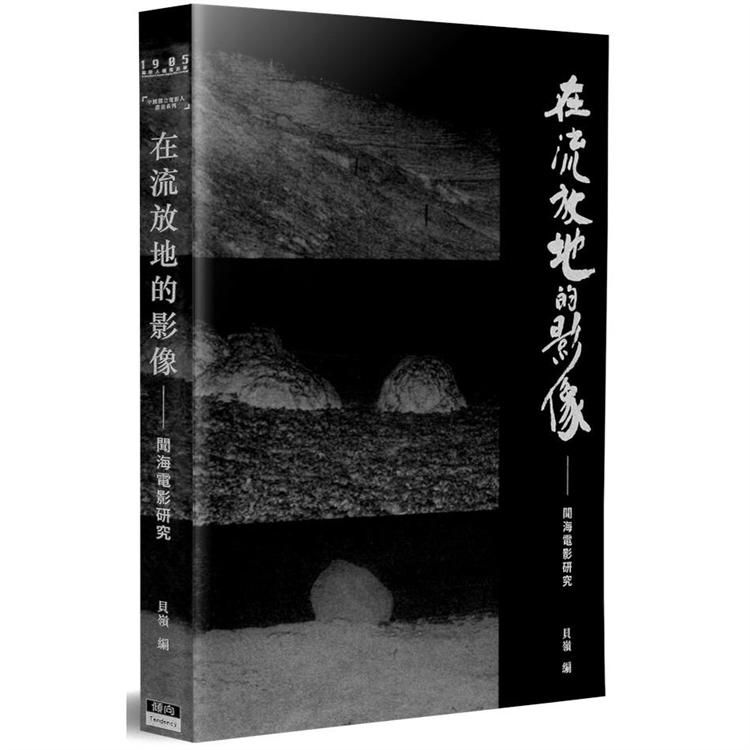 |
$ 263 ~ 269 | 在流放地的影像(精裝):聞海電影研究
作者:曹愷、杜阿梅、崔衛平、黃明川、董冰峰、劉兵、張亞璇、張真、徐匡慈、高長空、鄺老五、艾曉明、貝嶺 出版社:傾向出版 出版日期:2020-01-15 語言:繁體/中文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7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在流放地的影像(精裝):聞海電影研究
2001年,中國紀錄片導演聞海為追求獨立自由,以決絕姿態離開電視台,開始拍攝獨立電影,從第一部電影《北京郊區》至2019年《在流放地》,共拍攝了十多部紀錄片,獲獎無數。《在流放地的影像》為研究聞海紀錄片第一本專著。
全書分四部分:影評、訪談、文論、附錄。評論者包括法國真實電影節主席 Marie-Pierre Duhamel-Muller(杜阿梅)、紐約大學電影系教授張真、中國獨立影像展總監曹愷、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中國獨立導演艾曉明,他們分別從拍攝美學、風格、手法,以及聞海個人創作歷程等面向,深入探討其拍攝藝術,可說是研究聞海個人紀錄片發展的最佳指南。
作者簡介:
董冰峰
藝術策展人/製作人
黃明川
台灣獨立電影導演
曹愷
中國獨立影像展總監/藝術家
杜阿梅(Marie-Pierre Duhamel-Muller)
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選片人、法國真實電影節主席、arte德法藝術台紀錄片部總監。
崔衛平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作家
劉兵
獨立影評人/編劇
張亞璇
獨立影評人/策展人
張真
紐約大學電影系教授/策展人
徐匡慈
香港影評人/策展人
高長空(H.G.Castaño)
西班牙影評人
鄺老五
藝術家/獨立評論人
艾曉明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獨立導演
作者序
序一
客往何處去?
董冰峰(藝術策展人/製作人)
坦白說,在今天嘗試歸納或梳理聞海的獨立電影並非易事。一個是導演的創作仍然處於一種高產的狀態;另外,在過去數年中,聞海的電影創作已經逐漸地表現為一種「之間」的狀態:既在中國大陸之內,又在之外。這裡的意思,不僅僅是說聞海移居香港之後,拍攝和反思中國大陸的社會或政治現實,已經有了相當的距離和「直接性」的矛盾交錯;而是換種角度來說,或者正是緣由這種目前「客居」的「之間」的狀態,更使得聞海的電影創作有了更為寬廣的跨區域的社會政治視角,或可更有力地以獨立電...
客往何處去?
董冰峰(藝術策展人/製作人)
坦白說,在今天嘗試歸納或梳理聞海的獨立電影並非易事。一個是導演的創作仍然處於一種高產的狀態;另外,在過去數年中,聞海的電影創作已經逐漸地表現為一種「之間」的狀態:既在中國大陸之內,又在之外。這裡的意思,不僅僅是說聞海移居香港之後,拍攝和反思中國大陸的社會或政治現實,已經有了相當的距離和「直接性」的矛盾交錯;而是換種角度來說,或者正是緣由這種目前「客居」的「之間」的狀態,更使得聞海的電影創作有了更為寬廣的跨區域的社會政治視角,或可更有力地以獨立電...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