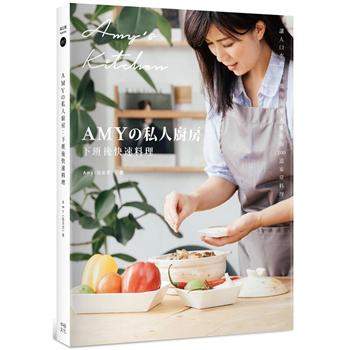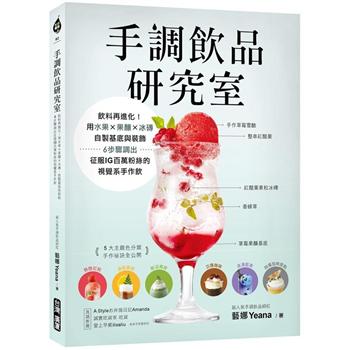真相會不停的改變
端看你 站在哪個角度 用什麼樣的眼 什麼樣的心 去映照
彼得一心惦掛著他對媽媽臨終時的承諾:要好好照顧妹妹。可是收養他的老兵告訴他,他的妹妹一出生就死了。彼得一再想起幼年時爸爸陪他在花園裡嬉戲,大肚子的媽媽微笑看著的畫面,並不真切相信老兵的話,於是懷著姑且一試的心情,用一塊錢去換取算命師的一個答案。算命師告訴他,他的妹妹活著,一頭大象可領他到妹妹住的地方。
彼得很沮喪,因為在這個寒冷的城裡,並沒有大象,他覺得算命師只是開他一個玩笑。
沒多久,城的另一端,有個過氣的魔術師因不滿觀眾的不尊重,倒唸咒語,招來了一個他原先毫無預定的東西──一頭大象。大象穿過帳棚,從天而降,壓壞了一名貴婦的腿,他也因此被關進牢裡。
大象被展示在伯爵夫人的大舞池裡,供民眾參觀,彼得也去看了,眾人興奮談論的時刻,他卻看進了大象的眼裡,看到牠的焦慮與孤單,看到牠的思鄉,所以想法子懇求警察、伯爵夫人、腿傷的貴婦讓魔術師用法術倒退時間,將大象送回牠原本的地方,將貴婦的一雙好腿留住。在一干人和一頭大象浩浩蕩蕩去牢房的路上,經過了一所孤兒院,意外遇見了彼得失聯的妹妹。
大象最後回家了,貴婦的腿傷沒好轉,但她選擇原諒。
學校圖書館雜誌Rocco Staino訪問凱特‧狄卡密歐(Kate DiCamillo)
問:你似乎花了很多心力去創造《魔術師的大象》的背景,它很難精確的點出故事的發生時代和城市。
答:不,我並沒有真的為這本書設想太多,有人說它很像在巴黎或英國,只是看過「在比利時」的影片後,我很訝異的發現它竟然很像我創造的那座城市。為這本書作畫的田中陽子問我,那隻大象是非洲象還是印度象時,我一點想法也沒有。
問:《魔術師的大象》是一本非常適合用來朗讀的書,你寫作的時候就刻意這麼做嗎?
答:老師似乎脫離不了朗讀分享,我覺得共讀時可以和大家一起大聲唸出來,是件很重要的事。作為寫作者,我一直都有大聲讀出作品的習慣,我還錄下來聽,這樣我才能知道它的節奏和韻律。
問:你刻意在小說裡放些比較奇特的詞彙嗎?
答:我喜歡語文,故事裡用的那些字是我認為必須要這麼用的。我知道、也喜歡那些字,我選選可以上下文呼應的詞彙,而且讓那些詞彙變成我獨有的。
問:你最喜歡的童書是哪些?
答:我記得我們老師帶讀過《藍色海豚島》,裡頭的每個細節我都還記得。我也喜歡William Pene du Bois的The Twenty-One Balloons,這本書突破每一條寫童書的規則,我非常讚嘆Beverly Cleary的才華, Ramona和Roald Dahl也是我喜歡的,Christopher Paul Curtis的The Watsons Go to Birmingham也是我會當童書作家的一個原因。
問:你得過紐伯瑞金牌獎,也入選過國際圖書獎,這些榮譽對你有什麼意義?
答:這些書會不斷的被印刷,不斷的被提起,讓有些對童書並不留意的家長也知道我在做些什麼。我知道即使在我死了之後,這些事情仍然會持續,因此我的生命就改變了。
作者簡介:
凱特‧狄卡密歐(Kate Dicamillo)
出生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五歲時因慢性肺炎移民氣候溫和的佛羅里達州。
她居住的地方是個小鎮,生活步調慢,腔調也跟北方不同,大家互相認識,待人真誠,使她立刻喜歡上這裡,而佛羅里達州也成為她前兩本書的主要場景。大學時代她主修英美文學,並從事成人短篇小說的創作,曾經獲得一九九八年邁克奈特基金會的作家獎助金。《傻狗溫迪客》是她的兒童小說處女作,出版後即獲得紐伯瑞獎,並躋身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她說在接到得獎通知時,她又驚又喜,不敢置信的沿著牆邊走來走去。沒想到隔年她的第二本兒童小說《高飛》(The Tiger Rising)又獲美國國家圖書青少年文學銀牌獎。
原先,凱特並沒有想到要為兒童寫作,直到她開始在一家書店的童書部上班,看到許多非常好的兒童書籍,深受感動,才決心朝這個方向努力。
由於白天在舊書店工作,因此凱特只能在早上花一點點時間寫作,一天最多只能寫兩頁,然而她強迫自己每天不間斷。一本書從開始寫到全部修改完成,大約要一年的工夫。
凱特筆下的人物顯得十分真實。她說,她並沒有塑造這些人物,而是專心聆聽這些人對她說什麼,然後把他們想說的東西轉述出來。她不喜歡刻意介入或扭轉故事的發展,也不特意挑選故事的題材或背景,一切都是自然而然流露出來的。
以《夏綠蒂的網》一書聞名於兒童文學界的E.B.懷特曾說:「所有我想要在書裡表達的,甚至,所有我這輩子所想要表達的,就是:我真的喜歡我們的世界。」凱特認為這句話也正是她寫作的心情。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前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所長 張子樟
進入凱特的小說國度,就像生活在真善美的世界中,即便是寫實的問題小說,作者仍在披露人生問題的黑暗面之後,留下溫暖鼓舞的力量,協助小說中的人物脫困,成就大圓滿的歡樂結局,也給予讀者正向明亮的感受,跟隨角色一同獲得重生的力量。在《魔術師的大象》裡,重生力量再現外,作者更進一步渲染了濃烈的藝術氛圍。
素樸、帶有詩意般的文字與童話/寓言般的氛圍及風格征服了讀者,先是著迷,接著是感動。她在一個不完全是童話的故事裡,使用了古典童話的元素。她使用極為簡約的文字,主要是顧慮到要讓角色內心深處的情緒,能在讀者心中更清楚的展露出來,而非以令人暈眩的句子,或過度考究的字眼而自陷於不知。故事雖陰沉哀傷,但常被希望之光所淡化,這道光同時也是寬恕、自覺、移情與憐愛同類之光。
名人推薦:前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所長 張子樟
進入凱特的小說國度,就像生活在真善美的世界中,即便是寫實的問題小說,作者仍在披露人生問題的黑暗面之後,留下溫暖鼓舞的力量,協助小說中的人物脫困,成就大圓滿的歡樂結局,也給予讀者正向明亮的感受,跟隨角色一同獲得重生的力量。在《魔術師的大象》裡,重生力量再現外,作者更進一步渲染了濃烈的藝術氛圍。
素樸、帶有詩意般的文字與童話/寓言般的氛圍及風格征服了讀者,先是著迷,接著是感動。她在一個不完全是童話的故事裡,使用了古典童話的元素。她使用極為簡...
章節試閱
上上個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巴爾蒂斯市的市集廣場上,有個男孩頭上戴著帽子,手裡握著一枚銅板站在那兒。男孩叫彼得•奧古斯都•杜舍納,手裡的銅板不是他的,是他的監護人的。他的監護人是個年老的士兵,名叫維爾納•魯茲。他派這個孩子到市場來買魚和麵包。
那一天,廣場上許許多多魚販、布商、麵包師傅和擺滿廉價銀器的銀器攤子間,突然出現一個算命師的紅色帳篷。帳篷外貼著一張紙,上面用難以辨認的字跡斬釘截鐵的寫了一句話:「你所知道或所感覺到最深刻、最困難的問題,將會在裡面得到解答,代價是一枚弗洛里。」
彼得讀完紙頭上的字,又再看一遍。話裡神勇的口氣,文字裡令人暈眩的承諾,讓他一下子有些喘不過氣來。他低頭盯著銅板──他手中那一枚弗洛里。
「可是我不能這麼做。」他對自己說:「真的,我不能,因為要是我這麼做,維爾納•魯茲問我錢到哪裡去的時候,我就得撒謊,而撒謊是非常可恥的。」
他把銅板放進口袋,摘下頭上的軍帽,又重新戴上。他背對著紙條走開,沒一會兒,又走回來,站在紙條前面,緊緊盯著這句不合常理卻又棒透了的話。
「可是我很想知道。」過了很久,他這麼說著,然後從口袋裡取出這枚弗洛里。「我要知道真相,所以我會這麼做,可是我不會用說謊來掩蓋;這樣至少我還能保住一些榮譽。」在這些話的支持下,彼得走進帳蓬,把這枚銅板交到算命師手中。
她看都沒看他一眼就說:「一枚弗洛里可以讓你買到一個答案。只有一個。你明白嗎?」
「明白。」彼得說。他站在帳篷掀開的隙縫處、一小塊射進來的光線裡。他讓算命師握住他的手,來來回回仔細的看,好像他的手上刻了許多細小的字,好像他的手掌上是一整本有關彼得•奧古斯都•杜舍納的書。
「嗯。」好一會兒後,她說。她鬆開他的手,斜眼打量他的臉。「不過,當然啦,你還只是個孩子。」
「我十歲了。」彼得取下頭上的軍帽,盡力讓自己站得很挺。「而且我正在接受訓練,要成為一名勇敢又忠誠的士兵。我今年幾歲並不重要,你收了這枚弗洛里,就必須解答我的問題,給我答案。」
「一名勇敢又忠誠的士兵?」算命師笑了,笑到口水都掛下來了。「很好,勇敢又忠誠的士兵,你要這樣說,那就是這樣囉。提出你的問題吧。」
彼得被恐懼刺痛了一下。萬一經過這段時間後,他沒法忍受聽到的真相,那該怎麼辦?萬一他並不是真的想知道真相,那該怎麼辦?
「說吧。」算命師說:「你問吧。」
「我爸媽……」彼得說。
「這就是你的問題?」算命師說:「他們死了。」
彼得的雙手微微顫抖。「這不是我的問題。」他說:「這件事我已經知道了。你必須告訴我一件我不知道的事。你必須告訴我別的。你必須告訴我……」
算命師瞇起眼睛。「噢。」她說:「她?你妹妹?你要問的就是這個?很好。她還活著。」
彼得的心緊緊抓住這句話不放。她還活著。她還活著!
「不,拜託。」彼特說。他閉上眼睛專注的想。「如果她還活著,我就得找到她,所以我要問的是,我該怎麼做,才能到那裡,到她那裡?」
他一直閉著眼睛等待。
「大象。」算命師說。
「什麼?」他說。他張開眼,覺得一定是自己聽錯了。
「你必須跟著那頭大象走。」算命師說:「牠會帶你到那裡去。」
彼得的心臟才從胸口往上衝,這下子又落回原來的位置。他戴上軍帽。
「你在開我玩笑。」他說:「這裡沒有大象。」
「你說的……」算命師說:「的確沒錯,至少目前是這樣。不過你也許沒有注意到:真相是會不停的改變。」她對他眨了一下眼。「再等一段時間,」她說:「你就會看到。」
***
彼得走出帳篷,天色灰暗,烏雲密布,四周的人群仍然有說有笑。小販叫賣、孩子呼喊,一個乞丐帶著一隻黑狗站在熱鬧滾滾的市集中間,正唱著一首有關黑暗的歌。
放眼望去,哪有什麼大象。
可是彼得那顆頑強的心安靜不下來。它一次又一次的蹦出簡單無比、卻不可能是事實的幾個字:她還活著,她還活著,她還活著。
有可能嗎?
不可能。這件事不可能是真的,如果是,就表示維爾納•魯茲撒了謊,對一名軍人來說,撒謊絕對是一件可恥的事。一名上級軍官竟然說謊。毫無疑問,維爾納•魯茲是不會說謊。沒錯,他一定不會。
他會嗎?
「冬季裡,」這個乞丐唱著:「天好黑,天氣好冷,事情並不像你看到的那樣,真相會不停的改變。」
「我不知道什麼是真相。」彼得說:「我只知道,我必須坦白承認。我必須告訴維爾納•魯茲,我做了這件事。」他挺起胸膛,調整一下頭上的帽子,邁開腳步往回走,朝著遠方的「波洛涅茲公寓」去。
他走著走著,冬天的下午暗得很快,灰濛濛的光一下子就轉黑。彼得想,算命師在撒謊;不對,是維爾納•魯茲在撒謊;不對,是算命師在撒謊;不對,不對,是維爾納•魯茲……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在反覆推想。
到了波洛涅茲公寓門口,他爬上樓梯,來到閣樓,抬起一隻腳,慢慢的、警慎的跨到另一隻腳前面。每走一步,他心裡都在想:是他撒謊;是她撒謊;是他撒謊;是她撒謊。
這名老兵在等他,就坐在窗邊的椅子上。屋裡點著一根蠟燭,老兵膝上擺著幾張寫著作戰計畫的紙張,放得很大的身影,投射在背後的牆上。
「你遲到了,二等兵杜舍納。」維爾納•魯茲說:「而且你手裡什麼都沒有。」
「長官。」彼得說著,取下他的帽子:「我沒有買魚,也沒有買麵包。我把錢給了算命師。」
「算命師?」維爾納•魯茲說:「一個算命的!」他用左腳輕輕敲打地板,這隻腳是木頭做的。「一個算命的?你最好給我說清楚。」
彼得一個字也沒有說。
噠,噠,噠。維爾納•魯茲的木腿繼續敲著,噠,噠,噠。「我在等著。」他說:「二等兵杜舍納,我在等你提出你的理由。」
「因為我心裡有疑問,長官。」彼得說:「我知道我不應該有疑問……」
「疑問!疑問?你說清楚吧。」
「長官,我沒法說清楚。我一路上都在想要怎麼說,卻找不到一個可以說清楚的理由。」
「很好,那麼,」維爾納•魯茲說:「我就來幫你說。你花掉你不該花的錢,你用一種笨方法花掉不屬於你的錢。你的行為很可恥。你要受罰。今天晚上你別想吃東西,空著肚子上床睡覺吧。」
「長官,是的,長官。」彼得說著,卻沒離開,還是拿著軍帽,站在維爾納•魯茲的面前。
「你還有別的話嗎?」
「沒有。有的。」
「到底是有還是沒有?」
「長官,你說過謊嗎?」彼得問。
「我?」
「是的。」彼得說:「你,長官。」
維爾納•魯茲在椅子上坐挺身子,舉起一隻手捻鬍子,確定它們的末端整齊的收攏在一起,像個十足的軍人。最後才說:「你,花掉別人的錢的你;你,用笨方法把別人的錢花掉的你;你,還敢跟我談什麼撒謊不撒謊的?」
「抱歉,長官。」彼得說。
「我確定你是該抱歉。」維爾納•魯茲說:「還有,解散。」他拿起那幾頁作戰計畫,就著蠟燭的光,含糊的自言自語:「就這樣,一定得這麼辦,然後……就是這樣。」
那天夜裡,當燭火熄滅,房間陷入黑暗,老兵在床上打呼時,彼得•奧古斯都•杜舍納躺在鋪在地上的毛毯上,盯著天花板深思。是他撒謊;是她撒謊;是他撒謊;是她撒謊。
一定有人說了謊,可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個。
如果說謊的是她,加上她又說了一些有關大象的荒謬話,那我的確就像維爾納•魯茲所說的,是一個笨蛋了──大笨蛋才會相信有一頭大象會帶我到那個早就死掉的妹妹面前。
可是,萬一說謊的是他,那我妹妹就還活在世間了。
他的心猛烈的跳著。
要是他說的不是真話,亞黛爾就還活著。
「我希望他說的是假話。」彼得大聲的對這片黑暗說。
由於背叛帶來的震驚,由於一點也不像軍人的情感表露帶來的驚奇,他的心再一次怦怦跳起來,這一次,跳得更猛烈。
***
在距離波洛涅茲公寓不遠的地方,越過一片屋頂,穿過冬夜的幽黯,就是布里芬朵夫歌劇院。那天晚上,這間歌劇院的舞臺上,有一個上了年紀、過氣的魔術師,演出他一生中最驚人的一場魔術表演。
他原本想變出一大束百合,沒想到花沒變出來,卻召來一頭大象。
大象砸破歌劇院的屋頂,牆壁的粉塵與屋頂的瓦片飛濺四射,然後硬生生的落在一名貴婦的大腿上。這名之前還沒提到她姓名的貴婦就叫貝婷•拉馮爾夫人──原本魔術師是想把花束獻給她的。
拉馮爾夫人的雙腿被壓碎了,從此必須坐輪椅度日。她經常在跟人聊天,話題與大象或屋頂完全無關時,會突然激動的、用驚奇的口氣大聲說:「或許你不曉得,我是被一頭大象弄跛的。被一頭從屋頂上掉下來的大象弄成跛腳的。」
至於魔術師,在拉馮爾夫人的命令下,隨即被關進監獄。
這頭大象也被關進了監獄。
***
彼得站在市集廣場上,在魚販子的攤位前排隊,心裡想著算命師、他妹妹、大象、發燒和特別小的魚;同時想到各種謊言。誰說了哪些謊?誰沒有說謊?當軍人是什麼意思?榮譽和忠誠是什麼?腦袋裡裝著一堆事,所以他只用了一半的心思去聽魚販告訴排在他前面的那位女士的話。
「唔,那個魔術師沒什麼了不起,其他那些觀眾也不認為會看到多棒的演出,你曉得──這才是重點。大家並沒有預期會看到什麼了不起的東西。」魚販的手在圍裙上抹了抹。「他事先沒有答應觀眾要作任何特別的表演,同樣的,觀眾也沒期待要看到特別的演出。」
「這年頭有誰會期待看到特別的東西?」那位女士說:「我可不會。我早把我的期待消耗光了,不再指望會遇見任何特殊的事情。」她用手指著一條大魚,「你為什麼不給我一條這種鯖魚?」
「這是鯖魚沒錯。」魚販一面說,一面把這條魚啪的一聲扔到秤上。這是一條非常大的魚。維爾納•魯茲不會准許他買這條魚的。
彼得仔細看看魚販擺出來的魚。他的肚子咕咕叫。他餓了,而且很憂心。眼前的魚沒有一條是小到不行,小到會讓那名老兵接受的。
「我還要鯰魚。」那位女士說:「三條。給我鬍子長一點的好嗎?鬍子長的味道比較鮮美。」
魚販把三條鯰魚放到秤上。「就是那樣,」他繼續說:「他們全坐在那裡,那些貴族,那些貴婦人,還有那些王子和公主,全坐在歌劇院裡,每個人心裡都沒有抱著太高的期望。可是,猜猜他們碰到了什麼事?」
「我一點也不想假裝我知道。」那位女士說:「有錢人會碰到什麼事,對我來說絕對是一個難解的謎。」
彼得緊張起來,他一點一點的移動腳步。要是他沒能買到一條夠小的魚回去,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當維爾納•魯茲陷入反覆發作的恐怖高燒時,沒人能預測他會說出什麼話,做出什麼事來。
「唔,他們並沒有期待要看到一頭大象──這話大致不假。」
「一頭大象!」那位女士說。
「一頭大象?」彼得說。聽到別人口中說出這個原本不可能出現的字眼時,一股震驚的感覺立即從他的腳尖傳到他的頭頂。他往後退了一步。
「一頭大象!」魚販說:「從歌劇院的天花板直通通的掉下來,掉在一位名叫拉馮爾夫人的貴婦身上。」
「一頭大象。」彼得低聲說。
「哈。」那位女士說:「哈,哈。怎麼可能發生這種事。」
「的確發生了。」魚販說:「還壓斷了她的兩條腿!」
「哎呀,真有趣,我的朋友瑪賽爾不就在幫拉馮爾夫人洗亞麻布的床單桌巾嗎?這世界可真小,不是嗎?」
「一點不假。」魚販說。
「可是,請問一下,」彼得說:「一頭大象。一頭大象。你知道你剛才說了什麼嗎?」
「知道。」魚販說:「我說,一頭大象。」
「從屋頂上掉下來?」
「我剛才不就是這麼說了嗎?」
「請問現在這頭大象在什麼地方?」彼得說。
「警方帶走了。」魚販說。
「警方!」彼得說。他舉起手,取下頭上的軍帽,然後重新戴上,又再拿下來。
「這孩子是不是得了某種跟帽子有關的毛病?」那位女士對魚販子說。
「跟算命師說的一模一樣。」彼得說:「一頭大象。」
「什麼一模一樣?」魚販說:「誰說的?」
「這個不重要。」彼得說:「只要大象出現,其他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件事所代表的意義。」
「這件事又代表了什麼意義?」魚販說:「我倒很想知道。」
「代表她還活著。」彼得說:「她還活著。」
「這豈不是太棒了?」魚販說:「聽到有人還活著,我們總是高興的,不是嗎?」
「當然,怎麼會不高興呢?」那位女士說:「我想知道的是,這一切都是他帶出來的,那他現在怎麼樣了?魔術師現在人在哪裡?」
「他被關起來了。」魚販說:「他們可不就這麼做了嗎?把他關進最恐怖的牢房裡,再把鑰匙扔掉。」
***
彼得站在波洛涅茲公寓閣樓的那個房間的窗口。他還沒看到李奧•馬尚尼的身影前就先聽到他的聲音。每次都這樣,由於吹口哨的關係,彼得總是先聽到聲音,後看到人。
彼得等到這名警察出現時才打開窗戶,探出頭去,大聲喊:「李奧•馬尚尼,真的有一頭大象從天花板上掉下來,現在在警察局裡嗎?」
李奧停下腳步,抬起眼睛往上看。
「彼得。」他露出笑容,「彼得•奧古斯都•杜舍納,你這個波洛涅茲公寓裡的住戶,這個閣樓世界裡的小布穀鳥啊。的確,有一頭大象出現了。這是真的。還有一件事也是真的,那就是牠現在被警方拘禁。這頭大象被關起來了。」
「關在哪裡?」彼得問。
「我沒辦法告訴你。」李奧•馬尚尼說:「我沒辦法告訴你,因為很抱歉,我不曉得牠被關在哪裡。他們把這件事看成極機密,你知道,大象是很危險、很容易把人惹惱的罪犯。」
「窗戶關上。」躺在床上的維爾納•魯茲說:「現在是冬天,很冷。」
現在是冬天,這是真的。
天氣相當冷,這也是真的。
但是,即使在夏天,維爾納•魯茲,當他被他那怪誕的高燒掌控時,還是會抱怨天氣寒冷,要求窗戶必須一直關著。
「謝謝。」彼得對李奧•馬尚尼說完後,關上窗,轉過身,面向這個老人。
「你剛才在說什麼?」維爾納•魯茲問:「你在窗口往外喊,胡說八道些什麼?」
「一頭大象,長官。」彼得說:「這是真的。李奧•馬尚尼說,的確有這麼一件事。一頭大象來了。一頭大象到這裡來了。」
「大象。」維爾納•魯茲說:「去他的。全是想像出來的野獸,活在動物寓言裡的東西,從沒人曉得的地方冒出來的魔鬼。」惡意的謾罵讓他感到筋疲力竭,他重重的躺回枕頭上。過了一會兒,又猛然直起身子,「注意聽!我是不是聽到步槍開火的聲音?是不是有大砲的轟轟聲?」
「沒有,長官。」彼得說:「你沒有聽到。」
「魔鬼,大象,想像出來的野獸。」
「不是想像出來的。」彼得說:「是真的有。真的有大象。李奧•馬尚尼是執法的警察,他是這麼說的。」
「呸。」維爾納•魯茲說:「我要對那個留八字鬍的執法警察和他那隻想像出來的動物說『呸』。」他躺回枕頭上,頭轉到一邊,又轉到另一邊,「我聽到了。」他說:「我聽到戰爭的聲音。開始打仗了。」
「所以,」彼得輕聲的對自己說:「這一定是真的,對不對?現在有一頭大象出現了,所以算命師是對的,我妹妹還活著。」
「你妹妹?」維爾納•魯茲說:「你妹妹死了。要我告訴你幾次才行?她連一口氣都沒來得及吸進去,就死了。她沒有呼吸。他們全死了。看看這片原野,你就會明白。他們全死了,你爸爸是其中的一個。你看,你看!你爸爸躺在那裡,死掉了。」
***
巴爾蒂斯市的民眾對這頭大象著迷的程度與日俱增。
在市集廣場上,在跳舞的大廳裡,在馬廄和賭場裡,在教堂裡,在各個廣場上,人們熱烈的談論「這頭大象」、「穿透屋頂掉下來的大象」、「被魔術師召來的大象」、「壓壞貴婦兩條腿的大象」。
這個城市的麵包師傅把麵糰壓得又扁又大,裡面包了奶油餡,外層灑上肉桂粉和糖粉,還叫這款點心為「大象耳朵」,市民們吃了又吃,彷彿永遠也吃不夠似的。
街頭的小販用昂貴的價格,叫賣大象戲劇性的墜落時,從天花板掉到舞臺上的石膏碎塊。「大災難!」他們叫:「故意傷害罪!買一塊災難現場的石膏吧!」
公園裡的木偶戲演出大象從舞臺上方掉下來,壓壞坐在舞臺下方的幾個木偶,讓小孩們樂得拍手大笑,直說好看。
在教堂的講臺上,牧師談到上帝的介入、意外的遭遇、犯罪的代價,以及魔術走偏了以後造成的可怕後果。
這頭大象戲劇性的、出乎眾人意料之外的出現,改變了巴爾蒂斯市民眾講話的方式。舉例來說,如果某一件事物令某人感到驚奇或感動,這人會說:「你知道,我就像看到這頭大象一樣。」
至於城裡的算命師,每個都忙得不可開交。他們專注的凝視他們的茶杯底部和水晶球,他們仔細的探索幾千隻手掌,他們認真的推敲他們的牌,然後清清喉嚨,預測說,有一些神奇的事物即將來臨。如果大象可以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出現,那麼宇宙裡必定發生了什麼劇烈的變化。星星自動排列,好讓更壯闊的事情發生;必定是如此,放心吧,放心吧。
同時,在跳舞的大廳裡,上流階級和下層階級的男男女女,都跳著同一種舞蹈:一種搖來晃去、步伐笨重的兩步舞,當然,它就被稱為「大象舞」。
無論在什麼地方,人們談論的話題永遠是「這頭大象,這頭大象,魔術師的大象」。
***
「這件事絕對會毀掉這個社交活動頻繁的季節。」昆特伯爵夫人對她丈夫說:「大家都在談論這件事。哎,簡直跟打仗一樣糟糕。事實上,情況可能還要更糟些。發生戰爭的時候,至少還有一群穿戴整齊的英雄,讓人家可以跟他們聊點有趣的話題。但是現在,在這裡,我們有什麼呢?除了一頭臭烘烘、叫人作嘔的野獸,什麼也沒有,一無所有;而大家要講的也只有這個,其他什麼都不談。我真的覺得,我可以保證,我絕對相信,要是再聽見別人提起一次『大象』這個字眼,我一定會瘋掉。」
「大象。」伯爵含糊的說。
「你說什麼?」伯爵夫人問。她猛然回身,目不轉睛的瞪著她的丈夫。
「我什麼也沒說。」伯爵說。
「總要做點什麼事。」伯爵夫人說。
「的確如此。」昆特伯爵說:「由誰來做呢?」
「請再說一遍?」
伯爵清了清喉嚨。「我只是想說,親愛的,你必須承認,之前發生的那件事的確很不尋常。」
「我為什麼要承認?它有什麼不尋常的?」
那件決定命運的事爆發的夜晚,伯爵夫人並不在歌劇院裡,因此她錯過了這場災難事件,她很不高興,她最擔心的也就是,錯過任何重大的災難事件。
「唔,你明白的……」昆特伯爵說。
「我不明白。」伯爵夫人說:「你也沒法讓我明白。」
「的確。」她的丈夫說:「我想你說得沒錯。」
伯爵夫人那晚沒有去歌劇院,但是伯爵去了。他坐在非常靠近舞臺的地方,大象要現身前,他感覺到一陣急劇翻動的風吹到他身上。
「一定有某種作法,能夠扭轉這個局面。」昆特伯爵夫人說。她來回踱步:「一定有某種作法,能夠讓社交季節恢復原來的樣子。」
伯爵閉上眼睛。他再次感覺到,大象出現前那一刻的風。整個經過在一瞬間發生,然而又是如此的緩慢。他從來沒有哭過,但是那天晚上他哭了,因為大象彷彿在對他說話:「事情的真相跟表面的樣子完全不同;哦,不一樣,徹底的不一樣。」
親眼看到這種事,體會到這種感覺,是多麼美好!
昆特伯爵張開眼睛。
「親愛的。」他說:「我有辦法了。」
「你有辦法?」伯爵夫人說。
「對。」
「你究竟有什麼辦法?」
「如果每一個人都只談這頭大象,不談別的,如果你很想成為社交季節的中心,成為最重要的核心,你就必須跟大家喜歡談的那個東西在一起。」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伯爵夫人說。她的下嘴脣微微顫抖:「你這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親愛的,你必須把魔術師的大象帶到這裡來。」
***
這頭大象成為昆特伯爵夫人的財產。
***
巴爾蒂斯市有好些小市民自動自發的去敲大象所在的那棟宅邸的大門。沒有人來開門時,他們竟然試著要打開這扇門,但是門鎖得很緊,牢牢的上了門閂。
你們在外頭。這扇門似乎這樣告訴他們。
裡面的,還是會繼續在裡面。
在一個這麼寒冷這麼灰暗的世界裡,這樣的事格外讓人覺得不公平。
不見得雙方都有同樣的渴望。巴爾蒂斯市的市民也許很想見到這頭大象,牠卻一點也不想見到他們。還有,察覺到自己被關在伯爵夫人的舞池裡,對牠來說,是一個可怕的轉變。
水晶吊燈的燦爛光芒,管絃樂團的撥弄吹奏,響亮的笑聲,烤肉、抽雪茄、女人的粉香,所有的味道加起來,在牠心中引發了一種無法相信眼下處境的強烈痛苦。
牠試著驅散這種感覺。牠閉著眼睛,一直閉著,能閉多久就閉多久,不過這樣做也沒什麼差別,因為每當牠一張開眼睛,所有的情況還是跟之前一模一樣。沒有任何改變。
大象的胸口湧上一股強烈的痛苦。
牠幾乎無法呼吸。牠覺得這個世界實在太窄小了。
***
昆特伯爵夫人跟她的許多憂心忡忡的顧問進行了相當多的、極度審慎的諮詢討論後,作出決定,認為為了啟迪和娛樂這個城市的居民(也就是那些沒有受邀參加她辦的舞會、晚宴和黃昏派對的那些人),並讓此事成為一種民眾感謝伯爵夫人重視社會正義的一種理由,可以讓他們在每個月的第一個禮拜六免費進來參觀,一分錢也不收,讓他們來看這頭大象。
伯爵夫人命人印製了許多海報和宣傳小冊,在市區各地張貼與發送。李奧•馬尚尼從警察局走回家的途中,停下腳步來看這張海報。他發現,由於伯爵夫人的慷慨,現在他也可以見到這個驚人的奇蹟──原本屬她一個人的大象──了。
「哦,好感謝你,伯爵夫人。」李奧對著海報說:「這個消息太棒了,這消息真是太棒了。」
有一個乞丐站在海報旁邊的一扇門前面,他的身邊有一隻黑狗。李奧•馬尚尼剛開口說出這句話,乞丐就聽了去,將它編成一首歌。
「這個消息太棒了。」乞丐唱道:「這消息真是太棒了。」
李奧•馬尚尼露出笑容。「是的。」他說:「這個消息太棒了。我認識一個小男孩,他急著想見到這頭大象。他求我幫助他,我一直在想,要怎麼做才辦得到。現在答案就在面前。他聽到這個消息,一定非常高興。」
***
李奧終於走到波洛涅茲公寓的門口,他聽到閣樓的窗子嘎的一聲打開了。他抬頭,看到彼得那張充滿企盼的小臉,從上面俯瞰著他。
「請問一下,」彼得說:「李奧•馬尚尼,你想出讓伯爵夫人願意見我的辦法了嗎?」
「彼得!」他說:「閣樓世界裡的小布穀鳥。我正想見你。但是等一下:你的帽子到哪裡去了?」
「我的帽子?」彼得說。
「是的,我給你帶來一個很棒的消息。我覺得你會想戴著軍帽,用比較合乎禮儀的裝扮,聽我說出這個消息。」
「等一下。」彼得說。他從窗口退下,過了一會兒,重新探頭出來,帽子在頭上戴得穩穩的。
「現在,既然你已經穿上正式服裝,準備好要聽這個令人開心的消息,本人李奧•馬尚尼,我,很榮幸能擔任傳遞這個訊息的人。」李奧清了清喉嚨:「我很高興能讓你知道,為了薰陶與啟發民眾,這頭魔術師的大象即將公開展示給大眾。」
「這表示什麼?」彼得問。
「這表示每個月的第一個禮拜六,你可以見到這頭大象;換句話說,你可以在這個禮拜六去看牠,彼得,就是這個禮拜六。」
「哦,」彼得說:「我即將見到牠。我就要找到牠了!」他的臉龐突然亮起來,這張小臉是如此的亮,就連李奧•馬尚尼也轉過身去──儘管他知道這麼做實在很蠢──看看是不是因為太陽從雲朵後面探出頭來,直接照在彼得的小臉上。
***
當彼得在稍晚時分,在巴爾蒂斯市冬日午後持續籠罩、一成不變的昏暗天光下,終於踏入關著大象的那扇門,走進昆特伯爵夫人燈火輝煌的舞池裡時,他聽到大笑的聲音。
一開始,他沒有看到大象。
有太多人包圍著牠,牠完全被遮住了。但是,隨著彼得愈走愈近,愈走愈近,牠最後,牠終於,露出來了。牠比他原先想的更大一些,也更小一些。光是看到牠低垂著頭,閉著眼,光是看到這幅景象,就讓他的心緊縮起來。
「往前走──哈,哈,嘻嘻!」一個拿著鏟子的矮小男人叫道:「哇哈哈!你們必須往前移動,這樣才能讓大家,每一個人,都看到大象。」
彼得從頭上取下帽子,把帽子放在心口上。他一點一點往前湊過去,一隻手放在大象粗糙堅實的側腰上。牠在動,左右搖晃著。牠的身體散發的暖意讓他感到驚奇。彼得從人群中往前擠,把他的臉靠到牠的臉旁邊,好讓他說出他來這裡要說的話,好讓他向牠提出他要來這裡提出的請求。
「拜託妳。」他說:「妳知道我妹妹現在在哪裡。妳能告訴我嗎?」
然後,他覺得糟透了,他什麼也不該說的。牠看起來好疲倦,好悲傷啊。牠是不是睡著了?
「往前移動,往前移動──哈,哈,嘻!」矮小的男人叫道。
「拜託一下。」彼得輕聲對大象說:「妳能不能──我需要你這麼做──妳能不能──可不可以張開眼睛呢?妳能看著我嗎?」
大象停下來,不再搖晃身體。牠靜靜的站著。過了好一會兒,牠睜開眼睛,直視著他;用崇高而絕望的眼神看了他一下。
突然間,彼得忘了亞黛爾,忘了他的母親,忘了算命師,忘了那個老兵和他的父親,忘了那些戰場、那些謊話、允諾和預言。除了他此刻見到的可怕真相,除了他從大象的眼睛裡了解到的事情之外,他什麼都忘了。
牠的心碎了。
牠必須回家。
大象必須回家去,否則一定會死掉。
就大象這一邊來說,當牠張開眼,看到這個男孩,牠感覺到一陣輕微的震驚電流般穿透牠全身。
他在凝視牠,彷彿他早就認識牠。
他在凝視牠,彷彿他了解牠的處境。
從歌劇院的屋頂墜落下來後,牠頭一次感覺到,心中有一種類似希望的東西。
「別擔心。」彼得低聲對牠說:「我一定會讓妳回家去。」
牠目不轉睛的看著他。
「我答應妳。」彼得說。
「下一個!」拿鏟子的矮小男人喊道:「你們必須,你們就是必須,往前移動。哈,哈,嘻!還有其他人也在等著看這頭──哈,哈,嘻!──大象。」
彼得往前走。
他轉過身,頭也沒回的就這麼走出昆特伯爵夫人的舞池,走出大象所在的那扇門,走進外頭的那個黑暗的世界。
他答應大象,但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承諾?
這是最糟糕的一種承諾,這是他無法實現的一種承諾。
他這個人,彼得,有什麼能力確保大象一定可以回家去?他連大象的家在哪裡都不知道。在非洲?還是印度?這些地方究竟在哪裡?他要怎麼做,才能讓一頭大象去到那邊?
他還不如答應大象說,他一定可以讓牠長出一對大翅膀還來得好些。
太可怕了,我剛才做了什麼事,彼得心想。太可怕了,我根本就不應該作出這個承諾。我也不應該向那個算命師提出我的問題。我不應該,不應該。我應該讓眼前的情況持續下去就好。這個魔術師所做的事也很可怕。他根本就不應該把大象帶到這裡來。我很高興他現在被關在監獄牢裡。他們應該絕對不要,永遠不要放他出來。他竟然做出這種事來,真是個糟糕透了的人。
過了一會兒,彼得突然想到一個奇妙的主意,這個想法讓他停下腳步。他把帽子戴上,又脫下帽子,再重新戴上。
這個魔術師。
如果這個世界存在著擁有強大力量的魔法,力量強大到足以讓大象憑空出現,那麼一定也有一種具有同等力量的魔法,力量強大到足以破除已經作出來的事,讓一切回到原狀。
一定有某種魔法可以送大象回家。
「那個魔術師。」彼得大聲喊出來,而後唸著:「李奧•馬尚尼!」
他戴上帽子,開始往前跑。
上上個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巴爾蒂斯市的市集廣場上,有個男孩頭上戴著帽子,手裡握著一枚銅板站在那兒。男孩叫彼得•奧古斯都•杜舍納,手裡的銅板不是他的,是他的監護人的。他的監護人是個年老的士兵,名叫維爾納•魯茲。他派這個孩子到市場來買魚和麵包。那一天,廣場上許許多多魚販、布商、麵包師傅和擺滿廉價銀器的銀器攤子間,突然出現一個算命師的紅色帳篷。帳篷外貼著一張紙,上面用難以辨認的字跡斬釘截鐵的寫了一句話:「你所知道或所感覺到最深刻、最困難的問題,將會在裡面得到解答,代價是一枚弗洛里。」彼得讀完紙頭上的字...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