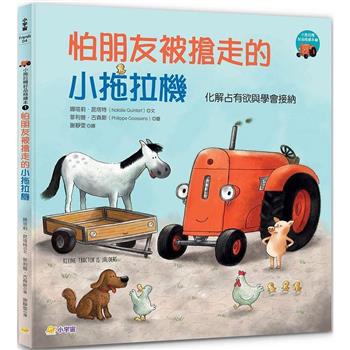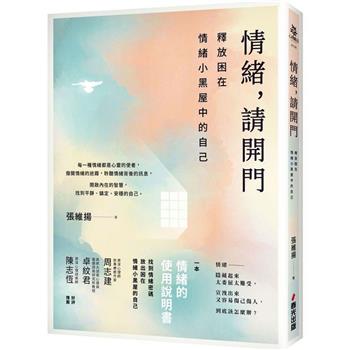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黃大德的圖書 |
 |
$ 461 ~ 660 | 裝置一切:技術-生命-政治
作者:駱頴佳、陳家富、鄭政恆、黃大德、陳錦輝 出版社: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01-10 語言:繁體書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一切生命都是技術生命。
生命必須在其技術環境中思考、尋問和行動,藉以不斷實現生命還未實現的意義。然而,並非所有技術環境都是等價的,不同的技術環境亦為生命的表達帶來不一樣的後果。我們可以想像,有些裝置給予我們較多實驗和構作的空間,容讓我們探索生命的繁多和豐饒;有些裝置則為我們代理了思考和行動,同時又剝奪了參與和創造。如何應對種種技術環境,在其中思索價值和意義的問題,在今日的資訊社會裡至為重要。我們不知道資訊社會為我們生活帶來更多確定還是不確定、秩序還是失序,但它真正帶來的變革在於將資訊重新定義,將連續、不可量度的資訊,空間化成離散的單元和語法關係。
大半世紀以來,隨著資訊理論而大量衍生、高速更替的技術環境,以及超工業(hyperindustrial)時代下消費社會的來臨,種種新型的生命治理技術得以冒現,以靈活若水的方式裝置了生命一切。「技術─生命─政治」的佈局,不但沒有令我們的生活失去了「可能性」和「選項」,反而令我們深信任何事物都是可能的。一方面,我們的生活變得極具效率,擁有更多選擇,我們的「潛能」發揮得更極致;另一方面,這個技術環境又壓倒性地令所有個體和社群失去了岡圭朗所言、多如星數的生命形態和生活方式。
在《裝置一切》中,讀者會發現,問題遠比解答多,一切都關乎技術生命和生命政治的纏繞。技術-生命-政治:在技術與政治之間,在這道間隙中,生命得以實現,得以在某時某刻被決定;但這道間隙裡頭還有另一道不易察覺的間隙,一道切口,生命同時潛伏其中靜待,尋索生命被裝置的意義。
作者簡介:
陳錦輝
本書主編。另編《一切:聖保羅與當代思潮》(香港:德慧文化,2016)。
駱頴佳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高級講師,荷蘭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哲學博士,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哲學碩士。著有《情感資本主義:從情感獨裁到情感救贖》(香港:dirty press,2020)及《邊緣上的香港:國族論述中的(後)殖民想像》(香港:印象文字,2016)。
陳家富
山東大學猶太教與跨宗教研究中心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學術興趣包括近代及當代基督教思想、歐陸宗教哲學。著有Life as Spirit: A Study of Paul Tillich’s Ecological Pneumatology(Berlin: De Gruyter, 2018;中譯本即將出版);合編有Paul Tillich and Asian Religions(Berlin: De Gruyter, 2017)。近年關注阿甘本思想及政治神學,正撰寫《政治神學:權力與神聖的鬥爭》。
鄭政恆
文化評論人。著有《字與光:文學改編電影談》、散文集《記憶散步》、詩集《記憶前書》、《記憶後書》及《記憶之中》,主編有《香港文學大系1950-1969:新詩卷二》、《沉默的回聲》、《金庸:從香港到世界》、《民國思潮那些年》四集,合編有《香港粵語頂硬上》及《香港粵語撐到底》等。2013 年獲得香港藝術發展獎年度最佳藝術家獎(藝術評論)。2015 年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現為《聲韻詩刊》、《方圓》編委。
黃大德
比利時列日大學哲學博士,現為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師,負責講授倫理學課程。個人學術專業為柏格森和岡圭朗的生命哲學,研究範圍主要為當代歐陸哲學,尤其是法語哲學的知識論、倫理學、宗教研究及人文思潮之討論,又特別關注生命倫理與生命政治於當代社會及全球文化交流中的複雜關係。
致謝 /030
一、法外狀態下的生命政治:論傅柯及阿甘本的修煉轉向——駱頴佳 /035
二、新型管治術裝置:主權例外、經世神學與抵禦策略——陳家富 /079
三、論田立克的神律科技——陳家富 /103
四、科幻電影:並觀海德格與田立克對技術的思索——鄭政恆 /145
五、集置的政治:海德格的技術追問與政治糾葛——林子淳 /177
六、一切的裝置——陳錦輝 /207
七、綿延、直覺與生命:柏格森和他的生命哲學——黃大德 /229
八、裝置生命:《小偷家族》的案例集——陳錦輝 /267
作者們 /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