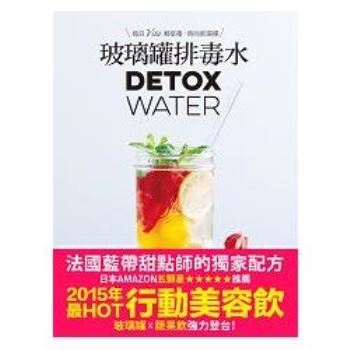出版題記
人生的境遇不是一座「城」、一扇「門」,而是一條奔騰不息的河流,一幀漸行漸遠的風景……
愛、自由、創造是我們生命之河源遠流長的動因。
#兩性婚姻
引子:身心合一的愛
把「圍城」拆掉,進出自由,盡可能多地感受生活,感受激情,感受愛。
爐火純青的感情與相濡以沫的情緻,令人欣慰而安寧。
婚姻不再作為一種形式存在,兩情相悅獲得了真正的自由。
三十八歲,當然不是做夢的時候了。但有一個夢,依然深深地縈繞著我,我怕失去它,又不得不遠離它,我抖落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的往事,來觀望回味這個夢,這個與「情」有關的夢。是誰說過,當一個人臨終的時候,想的最多的是他一生中難以釋懷的情人。
一百年前,有個記者問孫中山:「你生命中的最愛是什麼?」
「是女人」。這位國父的坦誠表述,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天地、陰陽、正負、生死、醜美、善惡似乎都能在男女之間撲朔迷離的關係中得到應驗,我們用婚姻、道德、家庭、社會維繫著看得見的人際關係,而一種看不見的情愫,像空氣、陽光一樣飄散在我們周圍,我們孤獨地默默承受,我們欣喜地暗暗流淚,我們尋找靈魂呼應的一絲感動,不為人知,但卻永恆。這種東西,叫做「愛」太濫,叫做「情感」太酸,叫做「情慾」太俗。「心」字旁加一個青年的「青」,此心常青,那是什麼呢?是介於愛與慾之間的「思緒」,從人出生之日起,它就開始發生作用,直到生命的結束。如果你有愛,說明你還有顆年輕的心,如果你有慾,說明你還活著。
男人和女人組成我們這個奇妙的世界,愛慾情仇,斗轉星移,世上所有美妙,神奇;罪惡,毀滅;似乎又都源於兩性之間某種奇異的關係,這個女人與這個男人在一起可能會幸福無比,與另一個男人在一起也許就痛苦萬分;更要命的是沒有人能清醒地判斷出哪一個人是自己的最愛;更沒有多少人能贏得、能感受全身心的愛。虛偽、冷漠、自私、偏執、麻木……我們對每天要面對的情感知之甚少,甚至忽略不記。最美麗的時刻是愛著一個人,最幸福的時刻是與愛著的人分享成功的喜悅,我總是在捫心自問,在我三十八歲的生命中,有多少這樣美好的時光呢?夢中的情人與生活中的丈夫、妻子,心中的遠景與現實的煩瑣庸常;物慾、精神;污濁、清純;卑鄙、高尚;庸俗、聖潔;死亡、永恆……如同愛與慾一般纏繞在一起,迷惑著可憐的人們、幸福的人們、渾然不覺或清醒苦痛的人們,他們探索著、前行著、懷疑、迷惑著……如果有愛,你還有顆年輕的心,如果有慾,你還活著。
認識我現在的丈夫是我二十二歲的時候,一年後我們結婚並有了孩子。婚姻是在該結婚的時候找一個合法的終生伴侶,於是一個人就變成了兩個人,兩個人就變成了三個人,幾個人形成的家就變成了社會的一個單元。人與人最隱秘、最基本的關係,大概就是家庭關係、夫妻關係了。每個人都必須在婚姻家庭中了此寂寞平淡的一生,而婚姻之外的無功利、無意識的情感呼應才是人心嚮往的永恆情愫。
小說家感興趣「愛情」,政治家關注名譽,商人在乎利益。但每個人都逃脫不了靈魂中最隱秘的誘惑,尋找另一個傾心愛著的、足以戰勝孤獨的自己。結婚前的愛情只能是荷爾蒙在起作用的結果,而結了婚以後,你們相敬如賓、度日如年、平淡無奇也好;風雲變幻、同甘共苦、幾經考驗也好,親情讓你們無法分離,可你的心卻被另一個人緊緊牽扯著,你欲愛不成,欲罷不能,你痛苦而巧妙地維持著生存,又抗拒著命運。這時候你懂得了什麼才是最合理的情愛關係,可是你已失去了愛的機緣。
社會賦予你的對家庭的責任和義務,更多的時候不是出於自覺自願的愛,而是你為當初的衝動和幻想所付出的代價。
美國華人女企業家、作家陳瑜在《30歲前不要結婚》這本書中,這樣寫道:社會教導我們說人無完人,所以我們得降低標準,隨遇而安。我們應當迅速行動,早早結婚,保險起見,以免我們再也碰不到更佳人選。但是,婚姻不應當是一個保險計畫。再沒有什麼比一個充滿無愛婚姻與婚外戀的社會令人更沮喪,令我們的生活岌岌可危了。
而當我們降低求偶標準,我們將再次向下一代強化這一觀念:世上無愛情。
如果人生還會有選擇的話,我寧願選擇身心合一的愛情,把「圍城」拆掉,進出自由,盡可能多地感受生活,感受激情,感受愛。我夢想著,在四十歲或五十歲時,與另一個孤獨、激情的人相遇,我們有各自的房間,各自的朋友圈子和事業追求,相遇是機緣,相知卻源於心靈的互動,源於對自由與愛的深刻理解和超然境界。爐火純青的感情與相濡以沫的情致,令人欣慰而安寧。婚姻不再作為一種形式存在,兩情相悅獲得了真正的自由。這時的愛與年齡、地域、時間、金錢、性別無關,或者說已超越了這一切世俗的羈絆,真正達到了獨立自由,兩情相悅的狀態。
一、日常與超常
與其說,他是我生命中的真愛,不如說,他是生活中的另一個自我:憂鬱、孤獨、聰慧、熱烈,我們之間,無需理解,只管傾訴;即使沉默,也是最好的交流。
如果不是有真正藝術家的激情和筆墨,生活是不會留下多少痕跡的。血淋淋的戰爭也罷,殘酷的死亡也罷,都不過是一個自然、客觀的過程,沒有死那有活呢?一場戰爭,可能是一次政治玩笑;一種死亡,不過是利益驅動的產物。再深重的災難都會以某種適當的形式被塗抹地冠冕堂皇。更不必說人生本來就是日常地不能再日常的生活了。這樣的生活本來是可以忽略不記的。
丈夫王一大很早就出門上班了,在工作上的應酬有時會拖得很晚,直到睡覺的時候才回來。下午,我早早地把飯做好,打電話問他今天是否回家吃晚飯,他熱烈地說,我很快就回來。終於又有人可以給他做飯吃了,我聽出了他話語的自負滿足,心裡既悲哀又有些許欣慰。我仿佛又回到了十幾年前的生活中,每天最認真做的一件事情,實際上就是做頓晚餐,然後等丈夫回家,如果丈夫在妻子眼裡還算過得去的話,妻子就願心安理得地一切以丈夫為中心,把婚前的聰明才智,理想幻想,拋到九宵雲外,夫貴妻榮去了。可是十幾年的生活怎麼會沒有變化呢?當初我是那樣心滿意足、興致勃勃、樂此不疲地裝修房屋,配置傢俱,洗衣做飯,好像不是他娶我,而是我娶他似的,我以為得到了世上最優秀的男人,自己是最幸福的女人。
可現在我這樣做,已談不上絲毫的興趣,不過是認為大多數人都是這麼活過來的,我現在還沒有能力選擇另一種更健康、更主動的生活方式罷了。吃飯、看電視,到該睡覺的時候上床睡覺,這樣的每一天可以重複到不知道什麼叫「麻木」為止。好在我在北京工作了一年多,剛回來不久,我們還是有可以釋放激情的空間。孩子是維繫我們關係的紐帶,做愛是顯示對方存在的途徑。「做愛」,這是誰造的詞?「愛」,要讓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水乳交融、甜蜜生動,忘乎所以地「做」出來,是怎樣地神奇美妙啊!在做愛面前,人人平等坦誠,人人真實可信,自然生動、瘋狂激情、熱烈激蕩。如果妳愛一個男人,做「愛」,的確可以讓妳達到生命的巔峰狀態,僅「做愛」所釋放的人體能量是正常狀態下的幾十倍,就足以證明「性愛」的力量多麼偉大!他說,只有做愛的時候,妳才是女人。我想,是的,在我臆想的世界中,我不僅超越了世俗規定的女人角色,而且超越了男人,我早已成了非男非女的異類。
當肉體亢奮的時候,可以喚醒沉睡的靈魂,撫摸、擁抱、湧起的潮汐般的愛意,一次次地衝撞,醉酒般地升騰……一切都像波濤、海洋、風雨、雷電似地激蕩起來,進來吧,快進來,我的身體仿佛已經變成了一個燃燒著的慾望火爐,我要讓他那剛勁無比的傢伙溶解、熔化,就像饑餓的嬰兒吸吮母親的乳房,就像小時候的饞嘴終於嚼到了甜蜜的方糖,我要讓兩個人變成一個人;我要讓他的整個身體,他的頭、他的腳、他的雙手都到我的子宮裡去,我把他溫暖著,再生下來。他應該變成兩個、三個、四個、五個人,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地方,讓這個女人得到最充分的快感和釋放……只有這樣瘋狂地「做愛」,才能引動我的思緒,讓我產生暫時的幻覺,我是「愛」他的,他曾經成為了我身體的一部分,而且還將繼續存在下去。
言語交流的方式越來越平淡,每天說的話不下三句:「你去倒垃圾」、「我又打死了一隻蚊子」、「快睡覺吧」。但還能做愛,這是我們得以交流的最後殺手鐧。赤裸裸的男人與女人的關係,被掩蓋在一個叫做家的房間裡,法定的,所以習以為常,心照不宣。我常常想,如果沒有孩子,沒有做愛,(親情與激情)我們還會剩下什麼呢?做愛的時候,我還是隱約聽到了床頭櫃裡的手機在響,今天是星期五,我知道是誰打來的,過了一會兒,又有發送資訊的聲音。
直到第二天中午,丈夫出門了,我想,可以抽空給徐中堅打個電話了。手機的資訊顯示是:「妳好嗎?」我好嗎?我算不算好呢?女兒已是十四歲的大姑娘了,我以為我必須要回來照顧她才行,但她似乎並沒有對我的回來表示歡迎。「媽媽妳為什麼不在北京待了,是不是那裡的工作幹不下去了?」她的率真讓我無言以對。是啊,她需要的是一個成功、自信、有能力的母親,而非整天圍著她轉的婆婆媽媽的保姆。現在不是她需要我,而是我需要她了。我在她身上感受到了新新人類的睿智,更感受到了自己這些年來的失敗和懦弱。當我還是穿著幾年前的衣服,隨心所欲,不修邊幅時,她提醒我說,媽媽妳該好好打扮打扮自己了。當我在家裡懶懶散散,東翻西翻,無所適從時,她說,媽媽妳怎麼總是無精打采,為什麼不好好做點事情呢?而她確實已經是個活力四射的美少女了,學習成績總是第一名,穿著時尚,觀念前衛,求知欲強,她的成功、痛苦、煩惱、喜悅都自有她成長的軌跡,並不需要大人過多干預。
大學畢業就結婚,到現在十六年了,我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女兒帶出了新疆,把丈夫苦苦期盼到了身邊。現在我該幹什麼?與女兒和丈夫相守餘生,可為什麼與他們真正在一起時,我卻什麼也不是,整天心神不定,焦慮不安?是啊,總該尋找到更有價值的東西來承接生命,來喚醒生命中的激情、智慧、美麗,哪怕再次經受磨難、苦痛、悲哀。
我給中堅打電話,告訴他:我不好,這裡的環境髒亂,空氣污濁,生活慵懶,觀念陳舊,我雖然是心甘情願回到家,也想做點事,但眼睛發炎,鼻子不通,也時常耳鳴,仿佛七竅生煙,江南小城,已不再是我想像中的山清水秀,鳥語花香,到處是基建工地,到處是糟雜的人群……我真有種無處藏身的悲哀。
他安慰我說:「妳好好靜下心來,寫點東西吧,然後想辦法再到上海來。」
「只能這樣了,這一次回來,我再不能荒廢時光,一定好好寫點東西出來,包括寫你。」
他在電話那頭笑了:「隨妳,只要有事幹,就好好幹,相信妳一定會寫出些好作品的。」
我也笑了,由衷地說:「謝謝你的鼓勵,你呢?你還好嗎?」
「整天上課,也很累,沒辦法,先賺點錢,八月份要到美國去訪學半年,妳最近能到上海來一趟嗎?」
「我現在也該定下神來,過段讀書寫書的日子了,到時候肯定會去上海看你的。」
「好吧!我等著妳把書寫出來。」
自從又回到了這個小城市,我一下子就封閉了起來,不願意與工作之外的任何人交往,過著無思無欲的平靜日子,像大多數家庭主婦那樣順其自然,與世無爭,甚至也不想再與中堅有任何瓜葛了。但我內心深處卻掩藏著一個更大的恐懼:哪一天我 離他真的越來越遠了,直到他完全從我的生活中消失,那時的生活就真的對我再沒有什麼意義可言了。
從我們相識的那天起,到現在已經有七年時間了,我們之間,不知道誰更需要誰,大概我們都是這個紛繁熱鬧、變幻莫測的世界上最孤獨無助,而又最不甘落寞的人吧。我們需要真正來自心靈的溫暖與關愛。與其說,他是我生命中的真愛,不如說,他是生活中的另一個自我:憂鬱、孤獨、聰慧、熱烈,我們之間,無需理解,只管傾訴;即使沉默,也是最好的交流。
以前我在北京,他在上海的時候,幾乎每天晚上我們都用手機發信息,三言兩語的問候之後,互道晚安,然後睡覺,好像是生活在一起似的。現在我回到了家,他也該結婚了吧,我們不可能像以前那樣相伴入眠地通電話了,但每個週末,我們都會不由自主地想到要聊幾句。他已讓我習慣了生活之外,還有一種更詩意的期待。儘管我極力迴避,但我依然不得不服從心靈的感應。
「喂,你好嗎?」
下個星期的這個時候,我或者他,還會這樣激情而熱烈地問候對方。
二、女孩遠在天邊
「天上的雲,地上的人喲,
匆匆地合,匆匆地分,
天上的雲,地上的人喲,
只有心路沒有阻隔……」
多少年後,我也像雲一樣漂泊,這首歌一直陪伴著我,讓我想起許許多多的人,他們是怎樣地讓我刻骨銘心──懷想而又憂傷。
大地與藍天並不在乎某個生命的誕生,而一個嶄新的生命卻在對日月星辰、人間真情的不盡探索中,寄託著對這個世界的全部激情與渴望。每當我對日常現實中的平庸、乏味、自足、荒唐、焦慮,感到忍無可忍時,心頭就會湧出這樣一段詩句:「讓黑夜降臨,讓鐘聲吟誦,時光消失了,我沒有移動。」
是的,讓我停下來遙想寧靜的星空,讓我靜下來,抒寫心靈的悸動。我總是在心裡默默地呼喚著自己的名字:夏雲,夏雲,在新疆玉安那片遙遠的地方,湛藍湛藍的天空上,晚霞塗抹著天際一片血紅,大朵大朵的雲彩鑲嵌著金邊,在高遠、燦爛的無邊蒼穹中,自由自在地流動、漂浮,變換著無窮無盡的千姿百態……而我像一個傻瓜似地久久凝望著浮雲,仿佛世界上只剩下了我一個人,我可以肆無忌憚地快樂而長久地與這個世界做著神秘而美妙的對話……小時候,大概是五、六歲吧,我常常到一個地方去,那是一個很少有人去,但卻美妙之極的地方。夏季的傍晚總是特別令人欣慰,吃過晚飯,還有很長一段時間無所事事,而空氣是那樣清新、涼爽,夕陽眷戀著遠處的雪山,遲遲不肯離去,一戶戶人家搬著小板凳出來,坐在門口的大樹下說著閒話……
我父親總是很晚很晚才下班回來,他在玉安一所唯一的大學工作,從單位到家,剛好穿過整個一個玉安城,他每天騎著一輛飛鴿牌自行車,慢慢悠悠地,好像是在邊思考深奧的哲學問題,邊騎車漫步似地回到家。據說他的那輛名牌自行車是在我出生的時候買的,當我二十多歲的時候,他還是騎著那輛車,儘管只剩下孤零零的兩個輪子,一副把手和腳登,但絲毫不影響他騎車的雅興。到後來,他當了學院的院長,別人要給他配備小汽車上下班,他說什麼也不肯,他不願放棄騎自行車的那份悠閒、自在,尤其是這輛歷史悠久的破車,不怕人偷,也就免去了麻煩。有一次,單位的同事向他借自行車,說是有急事要用,他二話不說把車子推來,同事這才發現世上還有這麼簡陋的車,連起碼的車閘也沒有了,父親說,他遇到緊急情況就把腳後跟向後一靠,用鞋底來摩擦車輪,同樣可起到剎車的作用,同事因為事急,也只好騎著車子走了,回來的時候發現自己的鞋底磨出了個大洞,又好氣又好笑地向父親訴苦,父親說,我可是騎了多少年也沒有損壞一雙鞋啊。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黃姝語的圖書 |
 |
$ 237 ~ 270 | 一個時時想逃家的女人
作者:黃姝語 出版社:博客思聽數位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11-18 語言:繁體/中文  共 8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8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一個時時想逃家的女人
一個出生在沙漠深處的女孩,因為內心夢想的引導,從新疆到上海,從北方到南方,帶著父母家族的記憶,帶著戀愛婚姻的懵懂,帶著對後代教育的懺悔,帶著那個時代的印記──這期間發生的故事令人深思。
作者簡介:
黃姝語
1965年出生在新疆喀什,熱愛寫作的語文老師。
願世間:美妙的文字,能穿越時空,落地生根;願美好的願望,如璀璨的群星,在心田閃爍。
章節試閱
出版題記
人生的境遇不是一座「城」、一扇「門」,而是一條奔騰不息的河流,一幀漸行漸遠的風景……
愛、自由、創造是我們生命之河源遠流長的動因。
#兩性婚姻
引子:身心合一的愛
把「圍城」拆掉,進出自由,盡可能多地感受生活,感受激情,感受愛。
爐火純青的感情與相濡以沫的情緻,令人欣慰而安寧。
婚姻不再作為一種形式存在,兩情相悅獲得了真正的自由。
三十八歲,當然不是做夢的時候了。但有一個夢,依然深深地縈繞著我,我怕失去它,又不得不遠離它,我抖落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的往事,來觀望回味這個夢,這個與「情...
人生的境遇不是一座「城」、一扇「門」,而是一條奔騰不息的河流,一幀漸行漸遠的風景……
愛、自由、創造是我們生命之河源遠流長的動因。
#兩性婚姻
引子:身心合一的愛
把「圍城」拆掉,進出自由,盡可能多地感受生活,感受激情,感受愛。
爐火純青的感情與相濡以沫的情緻,令人欣慰而安寧。
婚姻不再作為一種形式存在,兩情相悅獲得了真正的自由。
三十八歲,當然不是做夢的時候了。但有一個夢,依然深深地縈繞著我,我怕失去它,又不得不遠離它,我抖落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的往事,來觀望回味這個夢,這個與「情...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給自己 給未來
二○○三年,這部十八萬字的小說,一氣呵成後,仿佛是給自己的生命留下了一串驚嘆號和休止符。
二○二○年三月,一股莫名的衝動,讓我把書稿寄給了臺灣博客思出版社,不久就收到了出版社的回覆。此時,離處女作的完成,時間已過去了十七年,千言萬語,萬語千言,不知從何說起!
出版社編輯來信說,原稿的三個題目《無婚姻狀態》、《自由的心》、《渴》都很好,我們也有一個建議《一個時時想逃家的女人》或許更搶眼與貼近市場。我欣然同意!
一個時時想逃家的女人,真正想逃離的,到底是什麼呢?為什麼她自作主張...
二○○三年,這部十八萬字的小說,一氣呵成後,仿佛是給自己的生命留下了一串驚嘆號和休止符。
二○二○年三月,一股莫名的衝動,讓我把書稿寄給了臺灣博客思出版社,不久就收到了出版社的回覆。此時,離處女作的完成,時間已過去了十七年,千言萬語,萬語千言,不知從何說起!
出版社編輯來信說,原稿的三個題目《無婚姻狀態》、《自由的心》、《渴》都很好,我們也有一個建議《一個時時想逃家的女人》或許更搶眼與貼近市場。我欣然同意!
一個時時想逃家的女人,真正想逃離的,到底是什麼呢?為什麼她自作主張...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給自己 給未來 4
題記 10
引子:身心合一的愛 11
一、日常與超常 14
二、女孩遠在天邊 19
三、秘密 26
四、生命之源 34
五、愛的困惑 45
六、紅莓花兒開 57
七、找個標準丈夫 81
八、婚後生活 91
九、太陽出世 99
十、第一次出門遠行 116
十一、華師、華師 131
十二、心中的戀人、身外的世界 158
十三、讀研 173
十四、離家出走 188
十五、漂泊上海 210
十六、何處是歸程? 226
十七、掙扎 240
十八、沸騰北...
題記 10
引子:身心合一的愛 11
一、日常與超常 14
二、女孩遠在天邊 19
三、秘密 26
四、生命之源 34
五、愛的困惑 45
六、紅莓花兒開 57
七、找個標準丈夫 81
八、婚後生活 91
九、太陽出世 99
十、第一次出門遠行 116
十一、華師、華師 131
十二、心中的戀人、身外的世界 158
十三、讀研 173
十四、離家出走 188
十五、漂泊上海 210
十六、何處是歸程? 226
十七、掙扎 240
十八、沸騰北...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