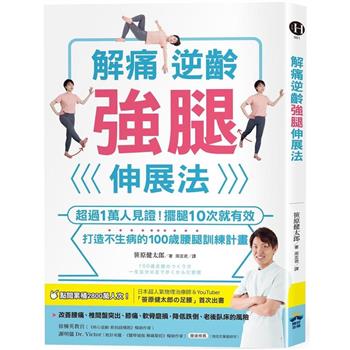媒體推薦:
朱天文專序:願未央
志不盡,願未央。
讀上個世紀六○至七○年代末胡老師寫給黎華標的信,七十二封信,與我同時收到這批出土古物的老友暨胡蘭成專家,他徹夜讀畢,但我遲遲停停,分了五天才讀完,怕一下子讀完就沒有了。當然也是,回回不能盡讀,投袂起身,我得出門走走,因為這些信,太煽動了。我說的煽動,用胡老師信中語是,「孟子曰憂,佛語是大悲,壯士得其悲痛慷慨,憂思難忘,尚為思有濟於天下,把歷史的弦彈得錚錚響。」
「人可各執一學,猶百工眾技皆為有益於世,而惟聖賢之志願無邊無盡,故憂思不盡。」
但不忘其憂,跟它配套的一句,不改其樂,那是孔子。而我親眼見過人老了,閱讀求知並不為了什麼的依然如年少時那樣專一,生活裡看人看物新鮮有味,他的執念依然親近著現實和具體細事而並不走向皇皇如大理石銘文的抽象建構,大家都講如來佛色相第一,那是不改其樂,那是我們遇見的老年時候的胡蘭成。(我想起康德傳記作者描述,康德臨終時有人把他的三大批判巨著托在他手上,他掂了掂,彷彿意思說:「如果這是個孩子該多好。」)
所以,誰是黎華標?
這位讓胡蘭成對之寫了七十二封信的年輕人是誰?這些信,簡直,如果在缺乏任何背景資訊下忽然讀到了,簡直得不是情書是什麼。才第二封信喔,胡就這樣寫:「我把你的照片與幾個日本朋友看了,但是像詩經裡的『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不知要能怎樣幫助你才好。我很想你能來日本留學,但是不知道你的家境,不知道你離得開離不開,而我請日本友人資助中國留學生,雖前時曾有此說,亦是等一邊決定了,又還要等另一邊進行來看,一切都不能說先有把握。又而且各人有各人的路,他人的代謀也許反為是一種不當的干涉。是如此輾轉思維,自己抑制著……」
第三十封信:「我所以曾想對唐君毅先生爭你這個學生……」(讓人想到現在粉絲們皆朗朗上口的邵之雍的警句:「如果是男人,也要去找他,所有能發生的關係都要發生。」)
黎華標乃新儒家大儒、唐君毅的學生。
不過大陸八○後,甚或台灣的六年級,恐怕也要問,誰是唐君毅?那麼只好請君自理。我只說,距今六十年前──稍微岔題一下,我曾寫下一個小說篇名,至今僅存其名、〈淮海戰爭時代所知的植物〉,想寫一位父執輩的長輩,國共內戰期間的水利工程師,北奔南跑,每到一地他總找得出空隙以圖鑑式的描繪敘述法把就近新發現的果菜記下,然後航郵寄去英國皇家植物協會。他很早就是協會會員,早在北伐後到西安事變,他說那是中國的黃金十年。黃金?想必指的是終於不打仗可以過安定日子了,他從那時候便默默持續著這個遠東植物觀察員的身分向倫敦投寄圖鑑報告一直到在台灣去世。所以六十年前,內戰兩分,卻有那麼一批人,不從毛,亦不隨蔣,他們在香港居留下來,於是有儒者錢穆、唐君毅創辦新亞書院,十多年後而有香港中文大學。
我們最早聽見黎華標,江浙口音「里挖標」,還是胡老師住我們家隔壁寫《禪是一枝花》的半年間,不時寫了信就走十五分鐘紅磚路到街上寄航郵。一九七六夏始春餘,至秋末胡老師離台的那半年,獰綠爬牆虎茂盛覆滿了屋壁窗前,玉蘭花樹油油高過樓窗,冷冽的花香卻讓人感覺像是地底有鐘乳泉淙淙流淌。暑夜,曇花輪番開,屋壁下一開七八朵像放煙火,花氣像漲潮,牽了電線燈泡出來照亮著看,週末聽完胡老師課的大人小孩在花影裡躡手躡足穿梭,悄聲掩笑的,果然花在酣放就怕驚擾了。這樣鬧到無人知曉之深夜清晨,沉睡去的曇花低低窩在葉底,看起來好重,重得真是昨夜做了一場千年繁夢。
那年聯合報開辦小說獎,副刊主編馬各,非得記他一筆,是他,不但策劃了小說獎促使友報隨後跟進,亦執行了支持青年小說作家寫作方案,作家每月五千基本生活費,有小說即給聯副,稿費另計。我大學三年級,妹妹朱天心大一,怯場只敢共同簽一份約平分五千塊,即便如此,也支薪寫小說壓力太大,愧對馬各兩年到期再不續約了。春節報紙只出單張,除夕前發稿催急到馬各親自來取件,夜晚計程車等在門外,門內一屋子年菜味,熙攘笑聲那幾年家裡天天人來人往辦三三,倚馬立就,朱天心寫完交件,小說叫〈綠竹引〉。已返日本的胡老師收到這篇剪報即寄去香港,盼黎華標讀了能寫評。黎的評文刊出後寄東京,胡轉來給天心,寫信說黎君:「人極真誠,二十年來,信上稱我為師,而未曾見面……請你寄一部三三給他……請用你的名字寄給他,他一定很高興,我一面寫信告知他,要他自己出錢訂閱,並請他投稿。」
通信近二十年,不料將黎君跟三三連繫上,由三三承接了吧,通信遂止。此後四年,胡去世。胡老師那樣的熱情寫信,當時只道是尋常,如今回想,豈只不尋常,根本僅見。我遂想到盛九莉將與邵之雍斷絕前的喟然:「其實他從來不放棄任何人,連同性的朋友在內。人是他活動的資本。」
人是他活動的資本。
非常刺耳之評讚,幾乎可以是惡評,然則是惡評嗎?
胡老師連兩封信將〈綠竹引〉與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窮人》並談,那俄羅斯人的深刻純情,直通於神,在〈綠竹引〉是那不幸的女人寒子,「天心的筆使人間的不幸都成為柔和的淚,如基督使哀哭的人得了柔和。文中寫那小孩對寒子的身體的現實的感覺,那臉,那背,那腳,那衣穿。寫小孩對寒子的人那種細心的體貼,那種親情,深入到寒子的人生全部,而仍是小孩的不懂,小孩是有一種像天道的不介意,與不識不知。她在雨中追著寒子哭叫,而事後是小孩的會忘懷,但又是永遠也不曾忘懷。」
「綠竹引於寒子的事沒有下一個結論或提出意見,而讀之使人思之不盡,叫你自己去提出疑問與意見,此才是啟發人的聰明,使人思,使人興。我讀此文是覺得寒子的美,美到了感動人,為了她我可以什麼都願意做。」
最後一句,正典是胡式煽動。
隨便翻一段,都是煽動,就說黎君研究所讀完開始教書,胡老師寫道,「你信裡對女學生的態度,使我想起我在溫州教書時。我又想起小時的想頭,假使我所知的女人落難,我必定救她,又假使所知的女人成了殘廢,我亦必照常愛她敬她,乃至在路上見跛足的或乞丐的婦人,我都設想我可以娶她為妻,愛敬之念日新。此是年青人的感情,如大海水,願意填補地上的不平。亦因有此感情,故山川草木以及女學生,皆映輝成為鮮潤的了,而要說是仁字,這亦即是你的仁了。」
「後世儒家藏仁以要人,不如你之身行仁而不自知也。但是你教學生,解釋仁字,大約又是解釋得困難吃力而不討好,落於藏仁以要人,此仁字成了積在心裡的痞塊,反為是病了。」
「我如此從你自身來啟發你,使你對你自己成為知己,而學問道德文章是要與天下人成為知己,此是於新亞書院諸君子之外,另闢一途徑也。」
孔子講仁知,孟子講仁義,義是仁的現實作為和造形。孔孟之學的通關密語,仁與義。當時新儒家盡在新亞書院,胡老師便拿仁字百般詰難唐君毅(胡致唐信現存八十七封),更不滿意新亞諸君子對於仁的行動性和造形性的欠思量。胡老師亦一而再、再而三對黎君譬喻仁,簡直得若不是在一種情話綿綿而只有情人樂聽的互動關係中,任誰也會覺得是給騷擾冒犯了。胡云黎君:「你的來信,我都保存著,因為你太真心,太聰明了,我惟恐你讀書生障,尤其你得值唐先生這樣的名師,得值名師是一大幸,而亦是一關,會使你終身跳不出這一關。」(此言完全也可以拿來說三三跳不跳得出胡師這一關。)
易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孔子講仁,仁是感的新字新語。
仁是淹然。是啊淹然──有人雖遇見怎樣的好東西亦水滴不入,有人卻像絲綿蘸著了胭脂,即刻滲開得一塌糊塗。
更近的新語,仁是即溶顆粒,當場溶入對方,溶於情境。史記寫漢高祖劉邦仁而愛人,那種即溶顆粒的體質,他既是溶於市井走卒之間,又不可思議能立即溶入張良者流。胡式煽動語是、「上與星辰近,下與庶人親」。
仁是忘私無我。胡云:「你有一次來信,講到你提出的一篇學術論文,唐先生稍有批評,你即刻無條件的感覺到自己的解釋真是錯了。其實你的亦不見得怎麼錯。這使我想起張愛玲,她把她的以為好的西洋文學作品講給我聽,見我聽了不覺得怎樣好,她就即刻對我抱歉,好像塵瀆了我的清聽似的。這種無條件的從善,不執自己,至於無我,這是真的謙卑,如海洋的謙卑,而那忘私無我就是仁了。而你當下並不曾想到論語上的仁字……」
孔子說顏回,其心三月不違仁,他人則一天兩天而已。這樣的顏回,動靜舉止讓我們想到誰?我想到──她又非常順從,順從在她是心甘情願的喜悅。且她對世人有不勝其多的抱歉,時時覺得做錯了似的,後悔不迭,她的悔是如同對著大地春陽,燕子的軟語商量不定(語出《民國女子》)。
仁是格物。
格物致知,與對黎君相反,胡老師對三三,多講致知,而少談格物。黎君做學問,胡老師就只跟他說格物,反覆說,說得自己也動氣起來:「你已迷惘前事,以學問來障了人生,怎得有太白金星下凡來提醒你纔好呢?」而三三是文學為強項,我們寫小說,做的都是格物的事,胡老師便只說我們要致知,要用功,要死心塌地的讀原典。孔子教兒子學詩學禮,「不學詩,無以言」,連跟他要講話都沒法講。胡老師因為三三而特別著重於禮,「不學禮,無以立」,憂念三三也許才高但學疏無以立,文運怕要不長的。
世間有王陽明格竹子,當代我最愛敬的小說同業舞鶴,曾經對談時他問格物,這是第一次有人用格物來談寫小說:「格物很難,活用格物在小說敘事中更難,必需適切地拿捏精細入博大。〈世紀末的華麗〉格了服飾時尚,《荒人手記》格了同性戀衍及的知識,《巫言》可能格了現象不忍看的。在我,往往書寫前以『小說田野』的方式進行一段長時間的格物,有意無意間在日常中格物,累積到一定的厚度深度它自會吵著進入書寫。如此格物當然比不上妳類『專業式』的格物。很早以前妳就意識到格物的必要嗎?如何下功夫格物,你發展出一套方法將格物運作在書寫嗎?」
當時我說格物對我也許是本能,舉了波赫士的小說〈強記者傅涅斯〉為例,把那位有著照相式記憶的傅涅斯當成一個格物的隱喻。當時說本能,正確說,女人的本能,女人天生是格物的,常識的說法,女人是直覺的動物。女人跟世界的接觸和交涉,自自然然從色相始,自然到我從未意識過有格物這件事。實物實體,色相寶妙,那是女人們都會的呀。(朱天心新作《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寫〈女人與男人〉的幾節有很生動的描述。)現在聽見舞鶴同業竟提出格物,好像窺得武林祕笈,原來他是用一段長時間的田野調查讓自己浸泡在內,泡到讓自己出芽。原來他用這種功夫,讓自己與物無隔,素面相見(胡蘭成語)。
沒錯,常識很知道,禪僧棒喝人,一棒喝掉隔,叫人直見性命。但常識不太知道,禪宗不立文字不做學問的一面,恐怕正給了懶怯不用功之人一個好藉口。舞鶴自謂他的小說是亂民,以別於典雅者,但亂民小說是在高度專注清澈的狀態下一字一字寫出來的。朱天心曾說自己是野生動物,我看起來不野很多,不過也只是比她野法不同,我們毋寧是要學禮知禮,約於禮。舞鶴的小說田野,在他為格物,在我似乎是致知。
而且常識也不太知道,小說有它勞役做苦工的一面。較之寫詩寫曲常靠爆發力的逸品絕品每在迷狂神啟中寫出,小說就真是勞役。雖然年輕開始寫小說的時候像寫詩,我們大家,女人男人,沒有誰在做田野調查,每個天才不都是每篇小說拿來就寫了,素手揮成,沒有誰去致知的。嘆氣的是小說越寫越只能認分,不管怎樣怎樣,最後仍然只能乖乖坐到紙張前坐得夠久夠長,頭腦明白四肢強健的一字一字把字老實寫出來。無關靈感,倒是要有好體力,不,好體魄。寫小說需要有強健的體魄。
舞鶴田野以格物。我當然也做田野,或者鋪地毯式的細密做,或者跑野馬式跑到忘了題目跑到烏何有之鄉的做,那種狀態比較像採集。採界中的礦材薪火,邂逅奇異的平常的元素,然後閉門冶煉,煉出何物,在一半能預見一半也不知的操作中,物出。太高興了,格物致知。孔子說「人而不仁,如樂何」,仁似乎始終與喜樂相伴。而我的經驗,格物帶著愛悅,致知也是愛悅的。
於格物,我跟朱天心如果是《牡丹亭》裡唱的、「我一生兒愛好是天然」,舞鶴那種自覺和後天學習來的格物,就有一種刷新。自覺,像新發於硎。像把格物這件事,拿到磨刀石上刷了一刷,所以舞鶴的、他們男性的格物,宛如男性友誼最好的時候那種如燃燒至白熱化青輝如庾信的〈鏡賦〉、「鏡乃照膽照心,難逢難值」。我嚮往男性友誼的湛然不必多言,因為都是值逢之人,知君用心如日月。
第十三封信:「讀你的信,我每每如此生出感激之意,實因你真得了『好學的』的一個好字。論語惟顏回以好學稱,又孔子自稱好學,此好字非親身經驗不能知也。」
此好字,是愛悅嗎?可不是,吾未見有好德如好色者。把黎君跟顏回跟孔子並列說,這自是胡式煽動。然則距今三十三年前《三三集刊》創刊,若非胡式煽動,會有三三嗎?這樣就還有一位不可忘失的好學人,好學亦好善,是的,他是我去世已十二年的父親朱西甯。
今天我的年紀,已超過我父親當時接胡老師到我們家隔壁租屋而居的年紀,我能像父親那樣從第一面見胡便侍以弟子之禮至終?父親上陽明山文化學院初訪胡回來寫的文章〈遲覆已夠無理〉,覆的是張愛玲三年前的兩封信,那樣興高采烈報佳音的報知見到胡:「我喜歡見真人,蘭成先生也真是真人……是他的真也叫我深感受到器重,叫我說不出的感念。這我又要說是恩寵,為何我能獨得承受這些個豐富,自然我是會珍視和善用這些個豐富。」我會這樣寫嗎?我覺得不會,我會比父親世故。
父親說恩寵或恩賜,乃基督徒語,按胡語是說仙緣,世緣深處仙緣新。事實上,父親這封信成了張愛玲趕寫《小團圓》的動機之一。
父親對胡老師,像孔子說顏回的:「於吾言無所不悅,不違如愚。」二十歲左右的我們,一樣。但我們的不違,是因為壓根連提問題的能力也沒有,白紙一張,朱天心形容說彷彿盧貝松電影《第五元素》中,負有拯救地球使命的神父極想在最短的時間將有人類以來所發生的大小歷史全數灌在那初履地球白紙似的天人腦裡。可是我父親?他的紙上寫滿了字,任何方面來看,他都足以與胡老師大大抵觸的。便看父親同代之人,因愛張必憎胡,因抗戰必仇日,父親正為這兩件,與文壇交誼半熄,亦老友不相往來十幾年。我回想他曾經動搖過嗎?或者,至少恍神過一下下?就我記憶所及,我覺得,沒有。也不是因為父親從來不苦相,不戲劇化,不勉強人,也不是他基督徒的因信稱義所以信心堅定,我回想也許他只是,本該如此,理應如此,當時只道是尋常。其實父親不僅不違,他是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他也許比任何人都篤志於胡學。
那麼,胡老師怎麼回應他?是的,胡為我父親開筆寫〈宗教論〉,此論不久編入《中國禮樂》由三三書坊出版(化名李磬,十二年後恢復本名重新印行,書叫《中國的禮樂風景》)。
父親是虔誠基督徒,一直致力於基督教中國化,他晚期在寫的長篇《華太平家傳》五十五萬字未完去世,真像夸父追日力竭於地,執杖化為林。胡老師說:「自從認識朱先生以來,我每每思索基督教的問題,希望有一新的開拓。」胡跟我們一起去基督之家做禮拜,我心想那些牧師的講道肯定幼稚,焉知胡一句句全聽進耳裡竟也成了新知。父親寄基督之家講道週報的年度合訂本去東京,我心想不要寄吧叫胡老師讀這個?但胡一一讀之且感欣寇牧師提出來基督教最基本的幾個問題在講,讓他〈宗教論〉寫時易於爬梳出體系和條理。
胡早年全讀聖經當做是歷史,喜舊約多過新約,認為舊約仍觸及天與人之際,是偉大次於印度人的以色列人,仍有雅各與天使摔角到天亮瘸了腿的鬥天得勝。《今生今世》裡說舊約至〈約伯記〉,以色列人到底對耶和華無條件降伏了,約伯是最後的抗爭者,〈傳道書〉便是這抗爭失敗後的空虛。胡張同看傳道書,張非常震動,說是從來厭世最徹底的文辭。我曾聽胡老師言,讀〈利未記〉感動至深,那通篇的在教導人生活行儀,怎麼吃,怎麼穿,怎麼祭祀,怎麼分配,那樣認真厚重的對待現世,絕不荒失。舊約還講建立屬世的國度,新約不講了。這個悲壯的民族,亡於埃及四百年,又亡於巴比侖四十年,「以色列人是尚在被羅馬所滅之前,已被這超自然力量的驚嚇折斷了脊椎骨了。此後上帝變為慈愛,且才有了天堂地獄,而人類的社會遂亦整然了。耶穌是這新社會的紳士兼英雄。」(最近唐諾專欄「世間的名字」有一篇叫〈神〉,他真勇敢,在基督教神學領域已密密麻麻開發殆盡的景觀中談神,他提出一點,耶穌是「在野的神」,令人視角為之一轉而拓開。)
然則許多年後胡寫〈宗教論〉,卻是貼著新約四福音書與使徒保羅來說,旁及印度的吠陀和佛經、日本的神道、中國的禮樂之學,分辨諸教之所同與所異,唯鍾情於中國的有祭祀而非宗教。
胡寫此論,讓我覺得最是張愛玲講他的:「你是人家有好處容易你感激,但難得你滿足。」他寫各個宗教之好處好到那樣令人神往,但終究又是不得滿足的那樣嚴厲不留情。就說基督教,我是幼年受洗過,成長後不再上教堂也不信基督教,凡宗教,我也許只能做到不出反聲亦不露評色,但胡寫基督教,有這種好法,讓我只想一句句抄經一樣抄下來。而父親說〈宗教論〉把一池的水都攪渾了,胡聞言笑起來,給我父親的信上寫:「我是凡事必求其真,為此說話每致被本來很相好的朋友所憎。以我的經驗,在求道的路程上,到了那十分的去處,友誼是靠不住的,只有知己纔靠得住。我今對朱先生說話沒有禁忌,是因為你我同在神前。」
胡也評論了我父親的長篇小說《八二三注》,感激處是煽動,不滿足處是嚴厲。父親呢?怎麼回應胡?我想起子貢比較自己跟顏回,子貢自謂聞一以知二,顏回卻是聞一以知十。父親的《華太平家傳》未完,就是他對胡〈宗教論〉的聞一以知十。
我有文集《黃金盟誓之書》,心裡想的是他們兩人。民歌唱、山高也有人呀行路,他們高高的走在峰上倒以為是平地,連盟誓也沒有的。
時值此時,胡正當我現在及未來的年紀,我能像胡給一個未曾見過面的青年那樣寫信嗎?我不能。我四周有誰會像胡那樣不吝且不怕煽動對方?不怕,是因為煽動了對方,就得承接那煽動的後續效應,喊停嗎?胡是不喊停的,除非對方停。也許有一位朱天心,她會寫煽動語,近年的傑作是推介一個她驚為奇葩至今仍未出書的寫小說的人張萬康,她那種推介法,不是最高級,是唯一級,她半點不怕的像一名賭徒把口袋裡的錢全部拿出悉數押上。胡老師稱頌人,也是唯一級。
這種不喊停與唯一級,寫到張愛玲的現代小說裡是這樣:「她根本沒想通,但是也模糊的意識到之雍迷信他自己影響人的能力,不相信誰會背叛他。他對他的朋友都是佔有性的,一個也不肯放棄。」
現代小說,在文學史上如果要記一大功,那必定是它的除魅性。張的時代沒有除魅這個詞,她只說「思想上沒有聖牛這樣東西」,又說「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腳』,否則就站不住,不可信」,對方是日神,她也從小地方看見了黏土腳。而中國現代小說的領頭羊,早在上海孤島時期,胡已白紙黑字表現出胡式唯一級的評論風格:「魯迅之後,有她。」魯與張,他們除魅,他們絕對不手軟。小說《小團圓》,這會兒張亦絕對不手軟的把自己給除魅了。朱天心的說法是:「我留著對張最後的敬意,做為一個現代小說家,她像盡忠職守的老將軍戰死在她的沙場上,戰到最後一刻。」
如果叩問世界,對於問者,我們說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現代小說的除魅性,註定它要叩問陰影,叩問黑暗,叩問那一切難以逼視不可追究的神祕幽微。此亦所以叩惡鳴惡,叩善鳴善。當然,叩假鳴假,叩仁鳴仁。胡的《今生今世》,也許是一部叩仁之書?
是吧叩仁之書。汲汲魯中叟,遲遲去魯時,人是他活動的資本。
周遊列國十四年,然而他思念起魯之狂士了:「歸與,歸與,吾黨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怎麼好像在說當年三三的青年!)孔子遂返魯,教學。吾黨小子裁之。
所以三三怎麼回應胡?三三像孔子在匡差點被殺而顏回走散了待趕上大家時孔子好安心說以為你死了呢,顏回答道:「子在,回何敢死。」那樣的完全順從,純良稚兒般給了晚年的老師鮮潤的生之輝。
時值此時是父親的年紀,胡的年紀,我的年紀,照花前後鏡疊疊交映著過去未來和現在,我能做到他們這個年紀時候所做到的嗎?胡說:「絕對的相信就是永遠不會失去。我相信天文的。」這是教誨?情話?還是盟誓?波赫士在河邊遇見年輕時候的自己而展開一段對話,我亦遇見三三時候的那個我們,日之出町陶人岡野家,大波斯菊蘺蘺如煙的草莖在五月鬱金香盛開的午後裡,似疏似密,似迷似陽,樹下盪鞦韆的笑聲是天心仙枝和雙胞胎姊妹,那個年輕的我坐在胡對面,心想,這是教誨。
我又也似大江健三郎走入森林遇見老年時候的自己,我問六十三歲時候的那個我,你會像胡那樣為筑波山梅田學堂的成立而寫字辦書法展以籌款?六十六歲梅田學堂機關報《風動》(是的孫中山愛講「四方風動」並書之為字)創刊,胡題字且發表文章〈天下有新事〉?那筑波山,梅田家門前有小桃一樹初開,漸漸暮色,遠遠是太平洋,星辰下潮聲裡,往事霸圖如夢,胡佇立久之?
六十九歲了,你會像胡來台執教,一邊把日文草就的《革命要詩與學問》用中文重新寫過,改名《華學科學與哲學》出版?七十歲你會上書蔣經國嗎?一幅書法就說的這七十歲還在要打天下:「始皇帝三十六年,秦社稷之末,數年少項籍,劉季約莫半百,老了酈食其七十,天下事猶未晚也。」(此時現代小說的除魅之光發出了聲音:你確定這不是職場退休男人癥候群?由於家中妻小無人有耐心聽他們訓話或發表高論,他們便紛紛跑出來結社組黨弄各種名目的基金會俱樂部或什麼什麼協會次團體好高談闊論?)
志不盡,願未央,天下事猶未晚也。
世間有地藏菩薩本願,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有阿彌陀佛四十八願心,只要一願未成亦不成佛。看哪胡七十四歲還在寫信煽動:「我為你們求證女人的創造力,比賈寶玉更證說得女孩兒們的好在哪裡。原來新石器文明全是女人發明的……」這是胡最後在寫的〈女人論〉,未完。
胡後十年,三三書坊為出版胡全集的事宜,我不抱希望按舊址姑且連絡黎華標,不料連絡上了。一年間往來三封信,他出手就把胡手稿及書法一幅相贈,說是供製版交給我們收藏,勝過寂寂淹沒於彼處。我當然要寄還他。他道「此間來日大難,不知道尚能保存東西多久,存放您們那裡是最恰當的。這是老實話,東西寄來寄去,只令郵局賺郵費也。」那是一九九○年。那幅書法一直壓在我書桌玻璃墊下,便從此與黎君無事不通音訊也要二十年,直到這回為胡的書信集他試探來連絡,不料連絡上了。我與黎君,我們互不面識,如日月在天之不相望,寥寥數語,已知永遠不會失去。這一切,自然由於胡而起。但也不必由於胡,因為黎君自個兒的存在,他就是昭信的。
那幅黎君轉贈給我們的胡字,壓縮著過去和一刻刻立即已成為現在的未來,字曰、
浪打千年心事違,還向早春惜春衣
我與始皇同望海,海上仙人笑是非。
二○一○年三月
朱天文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