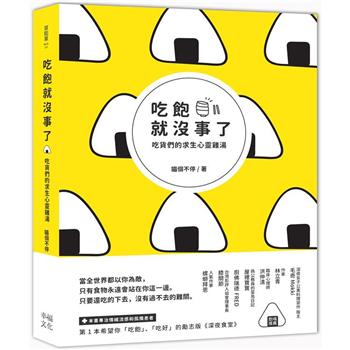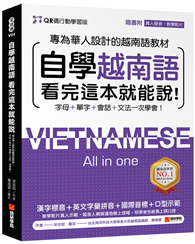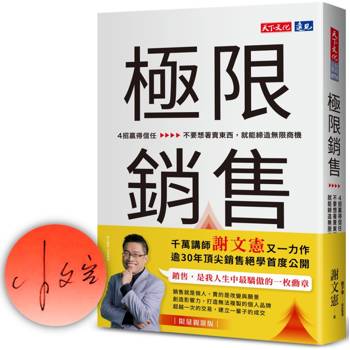導讀
文化差異中的溝通與衝突:
三種閱讀《喀布爾美容學校》的方式
輔仁大學英文系副教授 劉紀雯
西方(基督教)國家自二○○二年起對伊斯蘭教文化的興趣有驟然增加的趨勢,可以看見一般大眾已逐漸消除自美國九一一事件後對「伊斯蘭教」(或是纏頭巾的)男子所懷有的無名恐懼,並開始改正「伊斯蘭教=基本教義派=恐怖份子」的錯誤觀念。舉例來說,曾執導《何處是我朋友的家》的伊朗導演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二○○二年申請入美簽證被拒,導致不能出席紐約影展,但許多介紹他的影片、影展和討論他的專書則一一出現。此外,阿富汗裔作家胡賽尼(Khaled Hosseini)二○○三年出版的小說《追風箏的孩子》,出版後備受矚目,榮登二○○五年美國最暢銷排行榜,隨後更改編為電影發行。
這股伊斯蘭文化旋風同樣也吹到台灣。國內的出版界近幾年也推出了不少和伊斯蘭社會與文化有關的書籍,如《在德黑蘭讀羅莉塔》、《我在伊朗長大》皆與伊朗女性相關,後者改編為二○○八年上映的電影《茉莉人生》。另外,還有《三杯茶》是在巴基斯坦與阿富汗建校的故事;《喀布爾的書商,和他的女人》、《誰殺了喀布爾女人──美國女記者在阿富汗的現場直擊》則深入呈現阿富汗的政治、文化和女性。
在這波出版風潮之下,《喀布爾美容學校》(以下簡稱《喀》)是一部既典型又不失其獨特性的作品。和其他作品類似的是:它讓我們看到中亞地區的風土民情和受戰亂摧殘的地景,體會伊斯蘭教文化、西方民主與個人主義的衝突,以及更深刻了解伊斯蘭教極端教義和政權所造成的社會結構中的女性處境。然而,《喀》作者的發言位置卻和前述其他作品都十分不同。概括而言,前述作品的發言位置有三種:一、作者採虛構小說形式寫出所見所聞,自己全知卻隱形(如《追風箏的孩子》和《喀布爾的書商,和他的女人》);二、移民作家以第一人稱書寫「由在地到移民」的親身經歷(如《在德黑蘭讀羅莉塔》和《我在伊朗長大》);三、新聞或社會工作者以外來者的立場,用較客觀、宏觀的角度觀察和紀實(如《三杯茶》和《誰殺了喀布爾女人》)。
反觀《喀》的作者,美國密西根州來的美髮師黛博拉.羅瑞葵,她既沒有當地人「生於斯長於斯」的文化體驗,也沒有記者、社會工作者或小說家的專業素養。她擺脫對她暴力相向的丈夫,參加非政府組織到阿富汗擔任療傷工作,之後又回到阿富汗協助建立「喀布爾美容學校」和經營「綠洲沙龍」。在這段期間,她以自身的熱情與開放的個性,傾聽許多阿富汗女性朋友的故事,同時也讓自己走出家暴陰影。她毫不掩飾自己對阿富汗生活習俗的不適應,但也一步一步去了解、妥協文化差異和進入阿富汗社會。和其他「外國人」作者最大的不同是,她並未企圖回答任何和政治民族衝突相關的大問題,也沒有掩飾自己生活中的缺陷──如喜歡抽菸、遭受家暴、頻頻轉換工作等。於是,在她充滿感情又風趣的筆調下,我們看到她在喀布爾街上和市集被性騷擾而抓狂,她在美容學校教書受挫折,她聽了許多阿富汗女性的故事而哭泣,甚至她為了要長居在阿富汗而接受媒妁之言,嫁給一位已婚的阿富汗男人。
聯合國人道關懷和媒體平台(IRIN)二○○七年的報導指出,阿富汗女性中八七%是文盲,七○%到八○%的女性婚姻非自主,每三人即有一人遭受身體、心理或是性暴力。透過羅瑞葵的故事,我們可以了解阿富汗女性如何被歧視、束縛、責打,而她經營的美容學校和美容院如何提供一些阿富汗女性教育和工作能力,以作為這些女性可能的生存之道。羅瑞葵透過親身經歷所寫下的故事,最難能可貴的是,它既是對於阿富汗女性嚴重遭奴化事實的具體呈現,也是對於這個現狀的一個積極回應──雖然她的努力最後被迫中止。
詮釋和呈現歷史原本即不容易,跨文化的深入了解更難。一個作者(不論是本地人或是外國人)在處理伊斯蘭教的禁忌議題,甚至對其習俗有所批評時,必須面對的往往不只是非議,甚至身家安全也堪虞。《魔鬼詩篇》作者魯西迪的遭遇是眾所周知的,電影《追風箏的孩子》裡的兒童演員只因為在西方電影裡演出強暴戲而受到恐嚇。即使不是人身攻擊的回應力道也都很猛烈。《在德黑蘭讀羅莉塔》被指責對伊朗的革命和男性呈現不公,甚至有一位作家學者法蒂梅.克沙瓦茲(Fatemeh Keshavarz)寫了一本《茉莉花與星星:在德黑蘭不只讀羅莉塔》(Jasmine and Stars: Reading More Than Lolita in Tehran)來加以駁斥。《喀布爾的書商,和他的女人》中的書商主角蘇爾坦的本尊瑞斯(Shah Mohammed Rais)在小說出版後憤憤不平,不僅揚言要控告作者誹謗,而且自己還寫了一本《從前從前喀布爾有個書商》(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Bookseller in Kabul)來呈現故事的不同版本。
同樣地,《喀布爾美容學校》也頗受矚目。一方面它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被哥倫比亞公司買下了版權,要以珊卓布拉克為女主角來拍成劇情片,但另一方面各方批評之聲不斷。有人批評作者羅瑞葵過度膨脹自己,對其他西方美髮師的貢獻隻字未提;有人則認為她將美容學校遷移出「阿富汗女性事務部」是為了自己賺錢;也有人懷疑部分角色(如羅莎娜)是否確實存在。後來更有報導揭露本書出版後的戲劇性發展:作者的阿富汗丈夫薩姆性騷擾美容院女性,導致書中名為羅比娜的扎拉.荷仙(Zahra Hossein)唯恐生命有危險逃到印度,並對羅瑞葵突然離去失望且不滿。《星期泰晤士報》的報導甚至有個聳動的標題:「救星『拋棄』喀布爾的美容院小姐。」在這許多褒貶聲中,出版商李查.派恩(Richard S. Pine)認為,我們不能對身為一個美髮師的羅瑞葵要求更多:「記者知道查證,美髮師知道(的是)染髮劑和洗髮精。」其實,在「追究事實」與「只知道洗髮精」這兩種極端的觀點之間,羅瑞葵愛上阿富汗、走入阿富汗社會、最後倉促逃離的經驗,還有諸多可以閱讀的空間。在此我提供三個觀點供讀者參考。
個人生命的投入
為什麼羅瑞葵會到阿富汗參加重建工作?其實,她並非「救星」,而是試圖在救援工作中尋找生命的意義。她在美容院工作提不起勁,在監獄當警衛害怕同流合污,於是投入宗教以及一個一個可以發揮愛心的工作:到印度幫助飢民、到世貿中心救災,又因為九一一開始對阿富汗產生興趣,發現「自己的處境和阿富汗女性沒兩樣,生活均受到箝制」。另一方面,作者也誠實又幽默地呈現她生命軌跡中的戲耍和矇混;例如,她氣公雞每天早上吵她,就把牠的雞爪擦上紅色指甲油;利用簽證上「單次入境」(single entry)的single字樣向審理結婚申請的法官辯稱自己是單身的;看朋友和薩姆為了她的嫁妝爭論,她「看得津津有味,不禁捧腹大笑」,而且心想最壞的打算就是一走了之回美國。因此,我們面對這樣一個不自以為是的敘述者,不需要用高超的道德標準去評斷她,反而在她的各個抉擇中反身自問:我會如何做呢?我會離開家人,到遠方參加救援,使自己的生活有意義嗎?我會為了克服寂寞和在客居社會久待,和只認識二十天、彼此語言不通的已婚男子結婚嗎?
即使羅瑞葵投入阿富汗社會出於個人需要,而且投入的方式並非完全理智的抉擇,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她在這段過程中為認識的阿富汗女子所付出的情感,和在她們生命中所產生的「有限度」的意義。在敘述中,我們常常看到她溫暖又富同情心的表現:除了為了她們的故事哭泣外,她在交談中常常握著她們的手,安慰她們時則伸手把她們摟在懷裡。此外,羅瑞葵了解美容學校提供學生一技之長,美容院提供了女性互相扶持的空間,都是讓女人得以擺脫男性箝制,或被丈夫重視的方式。因此,她錄取學生的標準往往不是她們的專業知識,而是她們有多需要美髮技能。例如,巴席拉的經驗感動了她,她就一定要錄取她;哈瑪的年齡太小,但她還是錄取了她,並且為了讓她脫離房東阿里的控制,試著安排她的移民美國之路。羅瑞葵關心美容院的每位女性,甚至包括金牙管家夏茲,希望她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和自尊。
如果我們把此書的故事看成是一個生命的投入,而不是美國女超人拯救世人,就可以了解羅瑞葵對這些阿富汗女性的幫助必然是有限的。因此,本書的確有幾位女子(如:托比凱、巴席拉、巴賀兒和娜西達)收入有增加、生活和夫妻關係有改善,但同時也有不少個人難以對抗現實環境的例子(如女性被當成父親或丈夫的財產,或因沒受教育而受控於情人),使得許多自我改善的努力功敗垂成──夏茲、米娜和哈瑪的故事都是如此,羅莎娜最後神祕的結局也費人猜疑。
活靈活現的美國觀點和差異協調
在面對伊斯蘭世界時,羅瑞葵既有美國身分的優勢,又因為是女性而處於弱勢。在關於本書的訪問中,她坦承自己和她的阿富汗女性朋友的關係不平衡,常常處於解決問題者而非求援者的地位。她和薩姆也因為她擁有較多文化優勢而關係緊張(後記)。本書中,她毫不掩飾自己的美國觀點和價值判斷,因此我們看到許多很直接、生動又稍誇大的描寫和譬喻。比如,她把阿富汗的八卦視為「全民運動」;在婚宴上用手吃飯,她說她「掉到衣服上的食物還是比吃進去的多」;她把阿富汗傳統彩妝比作「戴著嘉年華面具」、把婚宴的裝扮看似「主題派對的變裝皇后」。當她手腳全是代表吉祥的指甲花彩繪(henna)時,她感覺自己「和馬戲團的怪胎沒兩樣」;外出時女性圍上披巾,她認為像「木乃伊」一般。
即使居於文化優勢,羅瑞葵並不文化本位主義。在日常生活中,她身為女性弱勢必須妥協;在教學和婚姻生活上,她更為了溝通和協調差異作了許多努力。處在阿富汗傳統的社會裡,她碰到性騷擾或是惡勢力,必然直接反擊或是報警,但是她也學到報警可能沒用──因為警察居然要用她的車運送惡棍,如此一來他們都可能遭到綁架。在教學上,她試著使用學生的語言解釋色彩理論,說底色是「必須殲滅的惡魔」,需要對比色來中和;她找較能領會的學生當小老師,用大家都懂的語言來解釋她的觀念。她還發現西方的化妝技巧在阿富汗行不通,因此從第二期開始,課程重心放在改善阿富汗式美妝技巧,並鼓勵她們由此發揮,將彩妝當成藝術。
羅瑞葵的婚姻其實是她在阿富汗社會作的最大妥協:在這個社會開美容院,她需要一個男人撐腰,她也必須忍受伊斯蘭文化一夫多妻的制度。在他們的婚姻中,我們看到更多、更切身的文化差異。羅瑞葵對她和薩姆之間的語言與文化隔閡直言不諱:有時他們兩人會拿這些文化差異互開玩笑;有時則「各自用母語衝著對方吼叫,結果落得其中一人睡客廳的下場」。一本「達利語-英語」字典和混用英文與達利文,或許能幫他們克服部分的語言隔閡,但夫妻在不同的文化和宗教影響下,對婚姻、表達愛情的看法不同,就不是翻閱字典可以解決克服的。她必須了解薩姆為何在朝聖之後一天禱告五次、看到她喝酒抽菸就怒容滿面;薩姆也慢慢學習接受美式的身體語言、親密方式,也為太太舉辦一個「穆斯林耶誕派對」。透過作者的親身經歷,本書提供了兩種文化的親密接觸,和在其中協調融合的可能與不能。
敘述技巧與社會脈絡
閱讀《喀布爾美容學校》這本回憶錄時,你可曾想過書中的「我」和作者羅瑞葵之間的關係?即使本書所呈現的句句屬實,真正的羅瑞葵和我們讀者之間「至少」還是有執筆者克莉絲汀.歐森(Christine Ohlson)、翻譯者,以及她們所使用的文字為中介(如果不考慮封面、行銷、導讀和書評的影響力)。人生比任何一個故事都要混亂,要把它說成有意義的故事,必然需要重新組合,編排成有頭有尾的情節。本書「情節」的安排甚有其寓意:它由羅莎娜的故事為首,呈現羅瑞葵幫羅莎娜做出她是處女的假證據,最後一章則處理她婚後的發展,藉此暗示羅瑞葵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至少她們的對話比其他善心人士送性感丁字褲要來得搭調;她所教的美髮、美容技能,比別人送阿富汗小孩各種顏色的橡膠鞋更為管用。
本書最有特色的是它的倒敘技巧:它往往由故事高潮開始,然後才解釋背景和發展故事。例如,第一章先描述羅莎娜的訂婚宴,然後才解釋她在婚宴上為何這麼悲傷,以及她「天大的祕密」;第五章以薩姆的鄙視眼神開始,然後才解釋他朝聖歸來後的改變。這種倒敘技巧讓每章、每節的開頭都引人入勝,增加閱讀的趣味和懸疑感。
本書的倒敘手法也提供讀者逆向思考的空間:讀者可以問問本書自己恐怕都沒有想到的問題。例如,為什麼本書要從羅莎娜「天大的祕密」開始?為什麼只有羅瑞葵知道這個祕密?為什麼進入阿富汗面紗的第一步,是呈現訂婚宴前的去毛,和宴會中男男、女女分處兩邊、充滿性欲的熱舞?同性間奔放的性欲和整個婚禮的高潮──證明處女的血手帕──所造成的對比,是本書預期的、還是意外的諷刺?
或許沒有人可以為本書(和其他許多回憶錄)所引起的爭議下定論。但是,爭議可以促使我們看得更廣、思考更深入。比如,本書的重要轉捩點是二○○五年以來阿富汗境內開始發展的爭戰,以及日益高漲的反美與反非政府組織情緒。這些動亂和美容院是否要課稅的問題迫使美容學校關閉。或許,我們也無法得知美容學校引發的爭議孰是孰非,但是如果我們多了解當時的社會脈絡,就可知道阿富汗人的不滿其來有自,因為二○○二年以來,大部分的外國援金都流到援助國的專家、承包商和官僚手中(美援的八○%到九○%是如此;參考《誰殺了喀布爾女人》)。
喀布爾美容學校第二期開始,聘用的多是當地的美髮師,因此它應該不是吸金的機器,《喀》也並未將「阿富汗」轉化為異國情調化的商品。它呈現羅瑞葵個人的生命投入與她所代表的文化位置;它讓我們了解在阿富汗試圖進行跨文化溝通的重要意義與現實的困難;它也暗示了「作者」在社會脈絡下,對事件發展和情節敘述所可以與無法掌控之處。不論她個人的成就有多少,重要的是,本書已經為讀者在阿富汗打開了一扇窗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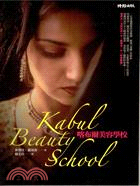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