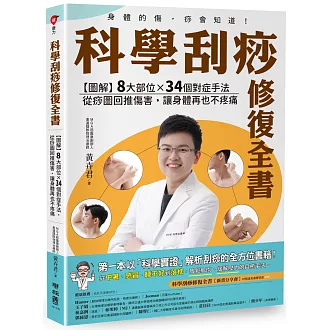導讀
再思聖經詮釋的基礎
如果觀察當代華人教會的熱心現象,我們會赫然發現有一種兩極化的困境正在發生:高舉聖靈啟示的靈恩傳統,以及堅守聖經無誤的基要傳統。前者放大聖靈上帝在生活中的工作,強調的是今生所能經歷到一切幸福與豐盛;後者則高舉聖經在信仰中的地位,強調永恆啟示的絕對性與排他性。願意委身在這兩個傳統中的基督徒都非常熱心,但兩者都出現在詮釋上對聖經本質的迷思。靈恩傳統因為強調了啟示的超驗性以及認知的直觀經驗,以致在聖經詮釋上忽略對經文脈絡的深入分析;基要傳統則是強調了啟示的權威性以及認知的客觀精神,導致在聖經詮釋上缺乏對啟示的上帝的直觀體悟。面對這樣的困局,我們亟需重新平衡認識聖經的本質,才能建造成熟的信仰群體。不論是缺乏神學訓練基礎,而只好放大主觀體會,或者是看重聖經字句,卻把啟示的上帝擱置一旁。我們委實需要一個詮釋的典範,幫助我們在兩難中開出一條動態平衡的道路。沃爾什和姬絲瑪蒂在《顛覆帝國》一書中,嘗試要做的就是這樣艱困地建造典範。
一、反思聖經詮釋的基礎:脈絡
沃爾什與姬絲瑪蒂清楚地勾勒出當代信仰群體所身處的世代文化,是一個後現代與資本主義帝國交織而成的氛圍。在這樣的實況中閱讀聖經,究竟能夠產生出什麼樣的意義?首先,作者嘗試從意義產生的最基礎單位入手──聖經。由於本書的作者曾經分別是賴特(N. T. Wright)的同事和學生,對於歷史脈絡在聖經解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極深刻的洞見與細膩的詮釋。由於上帝的永恆啟示所發生的場域,就在歷史之中,祂使用人的有限性,作為真理無限的載體,歷史脈絡自然成為一個真實且必要的過程。作者嘗試藉由猶太群體詮釋經文的「他爾根」(Targum)傳統,作為詮釋歌羅西書經文的基礎。所謂「他爾根譯文」,是指猶太祭司向流亡在外、離鄉背井的猶太人宣讀妥拉(Torah)時,知道會眾都不懂希伯來文,於是在宣讀時加以翻譯。而為了使經文更加合乎時代、適應不斷變遷的文化背景,他們會加入當代的習慣用語,自然就不是照字面的原意逐字翻譯。這種對經文有解釋功能的翻譯就稱之為「他爾根譯文」,也是全書詮釋歌羅西書的策略。基本上,這個傳統高度重視經文啟示所在的第一時空,就是還原初代教會對理解真理的內在機制,以及外在文化氛圍。
這個「還原」的過程必然需要適度想像,許多堅持認為真理只有單一解釋的著重客觀性的群體,會憤怒地斥責這個路徑充滿太多不可預期的危機,特別是永恆的啟示絕不可以從歷史的脈絡出發,而應當從永恆的啟示出發。這種反對真理具有歷史脈絡的傳統認為,因為真理屬於「永恆」,所以應當以一種無時間性(timeless)的形式展現,才能保持那不被時空、文化所玷污的超越性與絕對性。這種真實尊重真理、致力保存真理的態度,無疑應當得到肯定,但有可能因此踏上反對「真道具有肉身形式」的初代教會異端──「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的後塵。在《顛覆帝國》的詮釋中,作者藉由描繪歌羅西書背景中可能出現的人物,以及他們生活的世界,巧妙地向我們展現出脈絡在聖經詮釋中,有豐富可能性。這個詮釋進路,對於把現代性精神所高度推崇的客觀性內化的讀者而言,必然感受到強烈的焦慮。作者深諳這種焦慮必然影響讀者對本書的理解,所以採用問答邏輯的敘事技巧,一一回答了讀者心中可能出現的疑惑。
事實上,脈絡作為一個由文本形成的世界觀,也是一種詮釋學的循環。伽達默爾(H. G. Gadamer)嘗試恢復傳統在詮釋活動中的意義,這樣看的話,脈絡則致力消解啟蒙運動以來從個體知識論出發,否定歷史與傳統的現象,為我們提供了認識聖經一個重要的理解基礎。由於本書的寫作意圖是表達一種倫理實踐,缺乏歷史的真實脈絡將完全無法認識任何倫理,更遑論實踐了。當代倫理學家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認為教會是敘事的群體,他提醒我們,敘事並不是自我指涉的,而是去建立一群能向世界作見證的人,向他們訴說神創造計畫的美好目的。這樣的話,教會是講故事的人,也是故事中的角色。正是讀者與他的世界所連結的脈絡,為真理實踐提供了倫理的處境,這樣作者看似把脈絡「讀入」(read in)的帝國類比,反而成為足以檢視倫理觀的絕佳判準,更是這部作品令人拍案叫絕之處。
二、重返聖經詮釋的基礎:關係
哲學詮釋學大師利科(Paul Ricoeur)認定,聖經是基督徒群體在歷史中,見證神聖相遇的記錄。而詮釋的目的,則是要啟發聖經文本世界的開顯,使讀者能聆聽聖道在當下的信息,生命得以轉化,見證聖道。正是這種轉化、更新讀者的意圖,聖經不應當被視為靜態、等候被詮釋的文本,而是一個充滿主觀相遇的場域。作者在書中指出,「客觀主義認識論看重疏遠、分離、普遍性與抽象性,相反,聖經文學中對真理的理解,堅持親密、連結、特殊性與具體性。」對比兩者的認識論,客觀主義傾向希臘式的,強調「因果邏輯」;而聖經文學則是希伯來式的,聚焦「關係邏輯」。一位原本自有永有的上帝,藉由創造的行動,產生出一個與祂有直接關係的受造世界。人類獲賦予受造的自由意志,並用之決定如何回應跟上帝的關係。之後,這個受造世界進入墮落、揀選與救贖的旅程──這是神人關係的一系列旅程。
作者在《顛覆帝國》的敘事中,極力向我們展現了聖經世界中兩個不斷鮮活存在的關係,一個是信仰群體與她身處世代的關係,另一個則是啟示的上帝與祂子民在每一個世代中的關係。這兩個明確的動態關係向度,讓聖經得以從摩西五經的時代一路傳承到今日的教會群體。若不是指向上帝對祂子民的揀選,聖經閱讀便淪為只是客觀知識堆疊的材料,哪怕是宣稱這些知識叫做「啟示」,也脫離啟示者上帝要藉著聖經達致更新、轉變子民生命的目的。作者在本書中藉由歌羅西教會在羅馬帝國統治下的生存經驗,勾勒出上帝要百姓在壓迫、敵對環境中的抵抗策略,據此作為當代教會面對資本帝國的壓迫下,得以建造新群體的信仰基礎。
如果上帝啟示聖經的目的,就是要與一個被造、被愛的世界建立關係,那麼這個「關係」就不會只是觀念上的關係,而是持續沒有停止的連續互動。上帝如何藉由保羅寫給歌羅西教會的書信,與一群在帝國壓迫下生存的百姓建立關係,祂也同樣藉著歌羅西書的閱讀,幫助我們這一代的教會,在資本帝國統治下與祂建立親密的關係。這是一種「生存論式」(existential)的聖經閱讀,不是為了累積有關聖經的知識,而是為了在真實的生活中依靠上帝生存下去的真理。因此,每一次閱讀聖經都應當是一種「生存性的詮釋」(existential interpretation)。沃爾什和姬絲瑪蒂在《顛覆帝國》中非常成功地使用了這個雙重向度的文本互涉,讓當代的讀者得以清楚地,從歌羅西教會往返自己所身處的教會實況。
結語
如果保羅藉由歌羅西書的啟示,幫助初代教會在帝國壓迫下得以生存,並積極地建造出一個新的見證群體;沃爾什和姬絲瑪蒂也嘗試藉由《顛覆帝國》引導當代的讀者帶著生存論的態度進入歌羅西書,並與那位啟示歌羅西教會的上帝,同心建立起顛覆資本帝國的見證群體。然而,詮釋未曾停歇,我們的閱讀與生存經驗仍持續向前。當今華人教會所面對現代主義的衝擊,讓教會以上帝國之名,渴望建造出一個強盛的信仰帝國來榮耀祂的聖名。當教會追求一種想要規範世界的宏大敘述時,我們可能忘卻了保羅的捆鎖與基督的十架。誠心地期勉華人教會中的靈恩傳統能夠重返聖經的脈絡,以嚴謹的解經呈現基督信仰面對生存的深度,而不是鎮日談論沒有聖經的幸福家庭、美滿人生;也期勉基要傳統能夠重返啟示的關係,以面向位格上帝的動態旅程,將近乎教條式的教義宣告,轉化為唯獨恩典的實踐倫理。作者在文末以受苦作結提醒我們,教會經歷患難乃是面對帝國壓迫的必然旅程。當代華人教會在實踐倫理時,格外需要從保羅對歌羅西教會的勉勵得到啟示:
現在我為你們受苦,倒覺歡樂;並且為基督的身體,就是為教會,要在我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西一24)
深願我們如保羅最後對歷代聖徒的期勉──「你們要記念我的捆鎖」(西四18)──深願華人教會以此作倫理實踐的信仰基礎。
莊信德
台中磐頂長老教會牧師
前言
所謂「混音版」的概念,其實是有模稜兩可的弦外之音。就最壞的方面來說,重新合成的混音版其實就是翻新一首老歌的錄音,令其耳目一新,目的在於讓已經過氣的搖滾明星與惟利是圖的唱片公司可以再海撈一筆。或者,有時候是將一段音樂混入一首新歌當中,導致原創者的藝術價值與經濟收益全部毀於一旦。不過,就最好的方面來看,混音版是對某個老舊過時的藝術表現賦予嶄新的風貌。就這點而言,混音版就是一種「重新表達」,在當代的背景之下再次演唱一首老歌,展現文化與藝術方面的新面貌。這類的混音版促使不同文化鑑賞力的人重新聆聽與感受樂曲,同時也對原作品的完整卓越,表現敬意與尊重。
這本《世界是耶穌的:歌羅西書的想像與實踐》究竟是嘗試依其古老風格,重新聆聽一份古代文本,還是對原作者的抄襲仿冒,抑或是將這封古代基督教的書信用足以讓二十一世紀了解的方式,完整地重新表達,就交由各位讀者去決定了。不過,我們至少應該清楚地說明我們的目的。我們認為,在當時羅馬帝國的背景下,歌羅西書是一本具爆炸性與顛覆性的文宣小冊,而當今的現實是,我們也身處帝國之中,歌羅西書有能力也有必要扮演類似的角色。這封書信宣揚一個不一樣的現實願景,鼓舞一種對當時羅馬帝國的民族精神而言,具有破壞性的生活方式。我們相信,惟有當基督教信仰的這個激進願景,透過這封保羅寫給歌羅西信徒的信,在我們信徒當中激起類似保羅所言、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這封信才可能在我們的時代被完整地理解。
另外,這本書也有一點「反註釋書」的意味。我們知道學術界已經有針對歌羅西書的重要解經著作,我們也不願意對註釋書的撰寫表示不敬,因此,我們計畫嘗試讓本書在三方面跟一般註釋書的書寫類型有所不同。第一,本書的內容基本上不具備註釋書的專業架構。我們懂得希臘文文本的複雜難懂之處(或者至少齊思美懂!),我們也明白那些支持或反對保羅是否為此書仿作者的爭論,而且我們也持續關注針對「歌羅西理學」(Colossian philosophy)之特性的爭辯;我們很清楚,這些都是正確且重要的主題。但是,我們並沒有把焦點放在這些主題上,因為它們與我們對這封書信提出的問題不太相關。註釋書提出的大部分議題仍然陷於現代文化問題的困境當中,然而我們提出的問題,則是屬於後現代文化的(我們也會提供我們對後現代的解讀,可能與一般的解讀有些微差異)。因此,我們提出的問題,是要尋求在當代的文化脈絡之下,重新聆聽歌羅西書。
第二,註釋書是為了一些像是牧者與教授等專業宗教人士所寫的。我們兩個都是教授,而華樂時同時也是牧師,因此我們並不輕看這些優秀的專業著作。雖然也希望在這些領域的同事們能從我們所寫的內容得到幫助,只是我們寫作本書並不是為了牧師與學者。相反地,我們的讀者乃是你們會在第一章所讀到的,像威廉那樣的人—那些無法在所身處的時代背景之下,聆聽聖經對他們說話的人。我們的目的,是以文化、政治、社會及生態的角度來理解這卷經文,因為這些都是我們的朋友與學生會提出的問題,也是我們會提出的問題。而這也導致了為何這是本反註釋書的第三層面原因。
那就是,不僅因為我們的讀者不同於傳統註釋書的讀者,我們的問題也不一樣。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要告訴你寫這本書的源由:說來奇怪,那是起因於與一位註釋書作者的談話。
一九八二年,華樂時在蒙特婁市(Montreal)的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開始研讀博士課程,在那裡認識了一位年輕的聖經學者賴特(Tom Wright)。賴特那時正在為《丁道爾聖經註釋全集》(Tyndale commentary)撰寫歌羅西書與腓利門書註釋,並且詢問華樂時能否幫他閱讀草稿。他們就此展開了長達數月的對話與一段恆久的友誼。賴特都會在禮拜二的下午,把寫好的草稿交給華樂時;華樂時晚上回家就會閱讀,然後他們會在禮拜三的早晨花幾個小時討論。在這些討論當中,華樂時不斷提出一個問題,就是「那又怎樣?」賴特的釋義圍繞著一些名詞意義的解釋,像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與掌權的」等等,但他的作品讓人想到的事物,遠遠多於他容許自己在註釋所表達的。華樂時要求他清楚地指名道姓,在如今等同於那些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執政掌權者,是否就是國防部五角大廈(Pentagon)、IBM電腦公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而如果基督真的如同歌羅西書裡的詩文所極力訴求的,是「所有一切」的創造者與救贖主,那麼,這樣一個驚人的整全世界觀,對於我們的生態、政治與經濟生活又能帶來什麼啟示?
然而,賴特所寫的畢竟是一本註釋書,而這些問題卻都不是這類型的書可以回答的。因此,這本書可以說在二十年前就開始醞釀。自從那些與賴特一同進行討論的許多個週三早晨之後,華樂時持續不斷地教導歌羅西書,並且從中仔細反省他所做的幾乎每一件事。而當齊思美於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二年在牛津大學受教於賴特時,她也鑽研類似的主題。當我們於一九九三年結婚時,就很清楚兩人最後一定會合寫一本書,來嘗試回答華樂時在多年前所提出的那些問題。同時也很清楚,針對這份古代經文所提出的「那又怎樣」的問題,我們的答案必須能具體展現在身為夫妻與共組家庭的每日生活當中。因此,我們對彼此承諾,也向讀者們承諾,我們絕對不會提出一種生活方式,是我們自己無法身體力行的。
使徒保羅知道,如果他所提出的願景無法形塑基督徒的家庭生活,使其足以取代居主導地位的羅馬式家庭生活的話,這份願景就毫無意義。因此,測試這本書中所說的每一件事,最重要的實驗場所就是我們的家。我們的三個孩子,祖柏(Jubal)、瑪德琳(Madeleine)與莉底亞(Lydia)並不需要「忍受」我們撰寫本書的過程,如果他們需要的話,就表示這本書事實上缺乏可信度。我們並沒有為了蒐集資料與寫作而成為缺席的父母,以致「犧牲」了家庭生活。因此我們不用向孩子們道歉。反而要謝謝他們,讓我們的生活因著重視重要的事情而建立在堅固的基礎上,像是學習與打理家務、玩耍與成長、分享故事與睡前禱告、淚水與歡笑。
歌羅西書是一篇足以顛覆生活的顛覆性短文,而且堅稱此種不一樣的想像力與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必須在群體當中才得以形塑與維持下去。所以,這本書雖然是始於我們兩人所建立的共同生活,也始於與賴特的友誼,但也立刻就進入了一個更大的群體當中。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