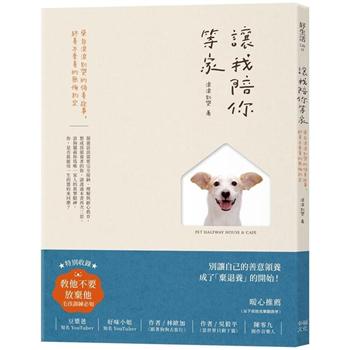|Track 17 數你|
原唱/楊千嬅
作詞/林夕
作曲/蔡德才
想 從幽幽的眼圈
逐公分那樣轉 為你點算著疲倦
願歲月難被我數完 地老天荒能轉多少個圈
想 從撕開的戲飛
逐分鐘掛念你 是哪一套最回味
從每日然後每星期 你我一起能看多少套戲
無奈肉眼看不到 用兩手摸不到
怎麼計算亦難料沉迷程度
同偕到老還餘下多少步
還能捏著你抱緊幾秒鐘擁抱
誰又會知道 憑每下心跳繼續數繼續數
只願延續下去數得到蒼老
想 從洶湧的髮堆
逐公分看下去 直到擁抱著沉睡
命與運埋在你手裡 你那些掌紋有多少愛侶
無奈肉眼看不到 用兩手摸不到
怎麼計算亦難料沉迷程度
同偕到老還餘下多少步
還能捏著你抱緊幾秒鐘擁抱
誰又會知道 憑每下心跳繼續數繼續數
只願延續下去數得到蒼老
誰願意知道
憑每下心跳繼續數繼續數
數著何時流淚才能被看到
還能與你再聽幾多音樂
還能伴著你再跳幾世紀的舞
其實我知道
迷上你一分一秒煎熬 一寸傾慕
只願容貌讓我數得到蒼老
一秒煎熬 一寸傾慕
數著何時望到彼此也蒼老
|Sirena’s Story | 017
每次我去看醫生的時候,不管是綜合診所,還是醫院,都會特別留意每扇房門上醫生的名字。
三年前跟我交往過一年的男人到底是否真是醫生?我從未刻意去確認,可是心裡始終希望他告訴我的事情不全是謊言。
我們開始得突然,結束也突然。起初他用手機交友程式跟我打招呼,那程式沒有照片,只有一些自我簡介,我跟他聊起發現挺投契,才交換照片,後來很快就發展成情侶關係——至少有段時間我是這樣以為。
「你可不可以多告訴我一些你的事?」坐在家中客廳的地毯上,我把頭靠在他的肩膀,他在低頭看外送薄餅的菜單。
像這些時候,我覺得是難得的好機會,試探關於他的更多事情。
「我已經告訴你很多事了。」如我所料,他總是這樣笑笑推搪過去,誰教他的笑容這麼令我無法招架呢?但今次我可不容易算數。
「我連你姓什麼都不知道,你不覺得很誇張嗎?」我說。他仍是笑笑望了我一眼,又重新看菜單去。
我和他已斷斷續續交往一年了,如果不是我和他工作都忙,真難以想像我對他的了解可以那麼少。
「我不是給你看過我家人的照片,也告訴你我的工作了嗎?」
他總有把事情說得理所當然的能耐。
關於他的家庭,我只知道他一家四口,有一個感情不錯的哥哥,哥哥沒有他帥,父母都是很尋常的父母,頭髮花白,但衣冠楚楚,他似乎來自一個教養不錯的家庭,難怪他的氣質這麼吸引我;工作上的事是交往三個月後才知道,有一次約了他吃晚飯,他說「教授在手術室做示範,可能要你等一兩小時」,我才知道他是實習醫生,自那之後他會跟我聊到病人或者同業的情況,並沒有刻意避而不談,自然得就像一般的情侶一樣。
但這其實只是假象,我對他所知的,真是十根手指頭也數得完。
我知道他的電話號碼,但我不知道他的地址,我沒有他的電郵,他連一張照片都不肯跟我拍,他說他沒有經營社群軟體,因為沒有這個閒功夫。
我知道他喜歡點最簡單的番茄水牛起司薄餅,我知道他穿42號的男鞋,右腳比左腳大個半號,我知道比起Marvel英雄片他更愛恐怖片,我知道他一天喝三個膠囊咖啡但最近聽說不環保才戒掉,我知道他左耳有一個穿過現在卻癒合了的耳洞,我知道他的手相預言他會活得比我長久,雖然五十歲的時候可能有一個大難……
他雖然會說,不是熟人不會告訴他們這些,但這些東西說沒意義也真沒意義,真正的關係不可能一年後仍停留在這樣似是而非的了解,至少我很介意,每次當我想到一點——只要他不找我,我們就會從此在人海中失散——我就會抓狂,可是我的在乎卻不能讓他知道,我不敢肯定,他到底願不願意被一個女人過份深愛。
「我姓林,如果你一定想知道的話,我從來沒有刻意隱瞞你什麼。」他摸摸我的頭說。
我數算著,我又擁有多一項他的資訊,我捉緊關於他的一點點什麼了,不過是知道他的姓氏罷了,我居然這麼開心。
自這天起,我偶然會無意識地書寫「林太」兩個字。
他就是害怕我太容易想得太急太遠,而不讓我知得太多,是吧?
最初的時候,朋友知道我交了男朋友,而且發展火速,都替我高興,可是幾個月下來,我還是無法具體說出他的事情來,朋友就覺得奇怪了。
「他可能只是有點害羞。」一個朋友替我打圓場說。
「還害羞啊?都上床啦。」另一個朋友說。
咖啡店裡幾乎全是女性,環境很靜,我「噓」了她一聲。
我聽著朋友你一言我一語。
「會不會是玩玩的?」
「可是除了有些時候抓不住之外,找你的時候他又好到沒得抱怨。」
「這才可疑,就怕你遇到玩家。」
「那又不必太悲觀,就是有這種人吧?肉體關係是一回事,打開心扉又是另一回事。」
「慢熱也不是這個程度。」
「其實你為什麼不找遍每間醫院,我就不信找不到。」
我終於插話:「我不想這樣,好像愛得力竭聲嘶的樣子。」
「你和他都是怪人呢,如果是我被人這樣對待,一定發飆。」
誰料到我有朝一日會栽在他這種人手上呢?
跟他一起的這一年,我覺得自己真的改變了許多。
我本來是不把事情弄得清楚明白不死心的類型,但我們從沒以男女朋友相稱,我知他逼不來,我只得漸漸習慣這種曖昧的方式,我對他不能有太多期待,只能開心的時候別想太多、別想太遠。
而我保護我的尊嚴的方式,就是收起我的熱情,有時對他冷淡一些。
如果我發飆,他一定會以無法理解的冷漠神情望向我,我的自尊不容許我這樣認輸。
他有什麼了不起。我對自己說。我也並不是真的那麼在乎他。我也可以只是玩玩而已。我也可以。
我們有時一個月也見不到一次,有時連續兩個週末都見,他會理所當然地說「今個星期來不及去的地方,下星期去就成」,如果我反問:「下星期又見?」他反而會露出受傷的表情,彷彿生氣我不想見他,那時候我就會很開心。
有時說了今天晚上來我家,他可以完全不出現也不道歉,讓我平白無事在家裡等了一整晚。可是我絕不要生他的氣,不讓他知道我在等。所以當他若無其事地打電話來,聊些工作的事卻不提那次失約,我也絕口不提自己那晚等了多久。
我們之間是在角力,比併著誰不在乎對方多一點。
但這也許,正正是這段關係吸引我的地方。
「你是不是還有其他人啊?」有一次我問他。
「我不是那種人啦。」
「那你是怎樣的人?」我悻悻然問:「你不告訴我,我怎知道你是哪種人呢?」
「我以為我們是不說自明的,人與人之間,資料是死的,惟有交往時所感受到的才是千真萬確的。」他說這話時像個天真的小孩,反倒像是被所謂正常的戀愛方式所限制的我太俗氣。
「真不懂你腦袋在想什麼。」每次我都只能沒好氣地笑笑。
「我正式到醫院上任之前,你說我們去希臘的小島度假好不好?」有一天他跟我逛街時輕描淡寫地說。
「你說的啊!那我找資料了。」我興奮極了。
「嗯。」他點點頭,然後視線被商店裡的有趣新玩意吸引過去,我們沒有再說這個話題。
回家後我花了幾個晚上上網找尋酒店機票的資料,我對這次旅程已開始有幻想了,既然是他提議的,我想這幻想是他所容許的。一起去旅行,他將無可避免地讓我知道很多個人資料吧。
「給我護照號碼和地址,訂酒店要。」我在電話裡問他時,他竟然告訴我:「我已答應了跟我哥一起去。」
我呆了半晌,認為他至少該跟我講句對不起,但他只是說:「那天跟哥講起,他說也想去許久,立即就買套票了。」
他甚至沒有對哥說答應了女朋友一起去,我也絕口不問。
「那玩得開心點。」我什麼都沒說,只能故作大方。
兩星期後,他給我傳來希臘小島的沙灘照,照片中真見他跟哥哥穿著泳褲合照,兩個人在看得見藍天與白色小屋的海邊孩子氣地笑著。
他完全不覺得令我失望了。
他回來的時候,還送我紀念品鑰匙圈,是一間白色小屋。
「我是不是該高興?又多知道一件關於你的事了,原來你去旅行回來會送鑰匙圈給朋友,真是謝謝了!」
他聽到我話中有刺,問:「怎麼啦?」他搖了搖我的手:「我們又不是朋友。」
「你們玩得很開心吧?」
「還不錯啦。」
我們去看電影,整晚我都冷著一張臉,他跟我說話我的反應只是「是或不是」。但他既沒有發脾氣,也沒有忍無可忍問我:「你這算什麼意思?」就像沒有任何事可以影響他的心情,我又算什麼?
電影散場時他還問我覺得好不好看,我終於將情緒一口氣爆發出來。
「我不知我們這樣算怎樣。」
「什麼怎樣?我以為你也挺喜歡這樣的關係……」
那麼就是我裝得太好了。
「我們這個根本算不上『關係』。」
他還是一臉不明白地望著我,如果他拂袖而去,至少我能恨他。
「你答應了跟我去旅行,為什麼忽然變成跟哥哥去?」
「啊,原來你在氣這個嗎?」他好像現在才懂得。
「不只是這個的問題。」
「我以為你沒所謂,你在意的話為何不說呢?」
「還要我說嗎?明明是你答應了的事……」
「我哪有答應過,我只是隨口說了一句……」他好像終於有點生氣,但更多的是無奈:「你不要無理取鬧啦。」
「我無理取鬧?是你給了我期望!」
他抿著唇站在馬路邊,良久沒有回答。
「對不起,如果我的方式讓你這麼困擾……」他小聲說。
「真的很困擾,困擾到不得了,怎會有像你這麼糟糕的人!」我一疊連聲地罵著。
然後我轉身走,他沒有追上來。
自那天起,他沒有再找我,一如我預期,我從此失去他的消息,就像從未認識過他一樣。
那種空虛失落感,很乖離,彷彿過去一年我只跟身邊一個朦朧的影子演對手戲,關於他的細節,我所擁有的也許一直是零。
三年後的今天,我因為行山摔斷了腿,被轉介到一間私立醫院看醫生。
站在門前,手已轉動了門把,看到醫生名字時,我停下了動作。
是他?還是只是同名同姓?
「可以進來了。」門後響起他的聲音。
他真的沒騙我嗎?我所能數算的東西都是真實的嗎?
我打開門,低頭在書寫的他,抬頭望向我。
「是你啊。」三年前我愛過的那個人,對我綻放出熟悉的笑容。
他看到我是腳傷,起來扶我過去,坐下。屬於他的氣味令我懷念。
他的視線有一瞬間停留在我手袋的白色小屋鑰匙圈上面,然後他只跟我四目交投,沒有問起。
「原來你真是醫生啊。」我說。
「我都說我沒有瞞你。」他重新坐好,定睛望著我,感歎的語氣。「真是太意外了。」
「我也很意外,先旨聲明,我沒有指明找你。」我說。
他沒好氣似地一笑。
「你還是那麼冷淡。」他竟然說。「害我都不敢找你了。」
「我冷淡?你是不是搞錯了?冷淡的是你才對吧?」我忍不住搶白。
「雖然我有很多話想跟你說,但我是不是應該先看你的腳?」他笑問。
晚上,他傳簡訊給我。
「嗨。我下班了。」
「你竟然還有我的電話。」
「病人紀錄有嘛,剛才有些話,不適合說。」
「例如?」
「那時候我很不成熟,比較收藏自己,不過我真的沒有騙過你。」
「已經沒關係了,我有男朋友了。」
我傳出這句,心情有點複雜。
他給我傳來一個哭臉,我噗嗤一笑,他失望嗎?
「這幾年,你一次都沒試過找我?」他竟然問。
「沒有。你不是不想我找到你,才什麼都不告訴我嗎?」
「正好相反,我一直等著你找我呢。」
「我不是那種女人,我不喜歡死纏爛打。」
「對,你什麼都很爽快,是我個性彆扭。」
我沒答話,他說得對,不過這也是我喜歡他的地方。
他的神秘感,既讓我仰慕又讓我煎熬。
「我們還可以做朋友嗎?這麼難得重遇了。」他又說。
「當然。」
所謂的男朋友,其實只是一個謊言。
我已經急不及待再去見他了。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要決心忘記 我便記不起(限量附贈 | 林夕親筆簽名藏書票)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90 |
中文書 |
$ 290 |
現代詩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要決心忘記 我便記不起(限量附贈 | 林夕親筆簽名藏書票)
鄭梓靈 故事 X 林夕 詞.詩
林夕的18首歌詞,有感悟有感想有情節有情緒,由鄭梓靈就著歌詞衍生了18個有人有物的愛情故事。除了一首序詩,林夕在故事之後再補上18段介乎歌詞與詩之間的文字,堪稱「情詩十九首」。
這是一次四手聯彈的文體交集,是一場美妙的感情接龍遊戲。
你
只是忘不了他的愛
你其實並不記得
他這個人
你只能記得
他能給你的
其他
你要不來的
一概與你無關
——林夕
在愛上一個人之前,我們不懂什麼是青春,在為一個人受傷之後,青春卻又已消逝。
如果我們曾經互相傷害,那我該慶幸的是,至少我成就了他的青春。
我想他已找到屬於他的幸福,而我沒有他幸運,只能繼續飄泊。
我想我可能會一直站在這裡。
就像我的心一直停留在過去的時空,那裡只有疼愛我的你,只有快樂,沒有背叛,沒有傷害。
——鄭梓靈
●隨書限量附贈 | 林夕親筆簽名藏書票
作者簡介:
鄭梓靈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畢業,副修法文、日本研究、曾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做交換生,香港中文大學跨文化研究碩士。
生於四年一次的二月二十九日,是情緒化的雙魚座,容易笑,更容易哭。
愛貓、愛海、愛書、愛音樂、愛攝影,討厭偽善,拒絕受約束。
有飛行恐懼症,但偏偏自虐地喜愛旅行。
喜歡寫愛情,慶幸還相信愛。
林夕
畢業於香港大學文學院,主修翻譯,曾任港大中文系助教、快報編輯、亞洲電視節目部創作主任/節目部副經理、音樂工廠創作總監/總經理、商業電台廣告創作及製作部主管/商業電台創作顧問/商業電台顧問。現全職寫字。
章節試閱
|Track 17 數你|
原唱/楊千嬅
作詞/林夕
作曲/蔡德才
想 從幽幽的眼圈
逐公分那樣轉 為你點算著疲倦
願歲月難被我數完 地老天荒能轉多少個圈
想 從撕開的戲飛
逐分鐘掛念你 是哪一套最回味
從每日然後每星期 你我一起能看多少套戲
無奈肉眼看不到 用兩手摸不到
怎麼計算亦難料沉迷程度
同偕到老還餘下多少步
還能捏著你抱緊幾秒鐘擁抱
誰又會知道 憑每下心跳繼續數繼續數
只願延續下去數得到蒼老
想 從洶湧的髮堆
逐公分看下去 直到擁抱著沉睡
命與運埋在你手裡 你那些掌紋有多少愛侶
無奈肉眼看不到 用兩手...
原唱/楊千嬅
作詞/林夕
作曲/蔡德才
想 從幽幽的眼圈
逐公分那樣轉 為你點算著疲倦
願歲月難被我數完 地老天荒能轉多少個圈
想 從撕開的戲飛
逐分鐘掛念你 是哪一套最回味
從每日然後每星期 你我一起能看多少套戲
無奈肉眼看不到 用兩手摸不到
怎麼計算亦難料沉迷程度
同偕到老還餘下多少步
還能捏著你抱緊幾秒鐘擁抱
誰又會知道 憑每下心跳繼續數繼續數
只願延續下去數得到蒼老
想 從洶湧的髮堆
逐公分看下去 直到擁抱著沉睡
命與運埋在你手裡 你那些掌紋有多少愛侶
無奈肉眼看不到 用兩手...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鄭梓靈|台版序
成長的那段歲月,我讀台版書,聽台灣的流行曲,看台灣的MV,喜歡那種唯美的氣質,深受感動。
與情感有關的認知想像與畫面構成,似乎都與台灣密不可分。
這次出版台灣版,仿似一次緣份回歸。
這本書要選取林夕的歌詞時,很自然地選用了幾首國語歌,另外一些則基於故事想要表達的主題和延伸性的考量,選用了廣東版歌詞,我想台灣的讀者也不會感覺陌生,因為情感和音樂本來就是人類共通的語言。
也許,當音樂前奏響起的一刻,我們已經投進自己的感情,在腦裡重播著自己鍾愛的幾句旋律也說不定。
可幸的是,時間賦予了我們...
成長的那段歲月,我讀台版書,聽台灣的流行曲,看台灣的MV,喜歡那種唯美的氣質,深受感動。
與情感有關的認知想像與畫面構成,似乎都與台灣密不可分。
這次出版台灣版,仿似一次緣份回歸。
這本書要選取林夕的歌詞時,很自然地選用了幾首國語歌,另外一些則基於故事想要表達的主題和延伸性的考量,選用了廣東版歌詞,我想台灣的讀者也不會感覺陌生,因為情感和音樂本來就是人類共通的語言。
也許,當音樂前奏響起的一刻,我們已經投進自己的感情,在腦裡重播著自己鍾愛的幾句旋律也說不定。
可幸的是,時間賦予了我們...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鄭梓靈|台版序
林夕|台版序
鄭梓靈 |港版序| 從此我們的心不可能再完整
林夕 |港版序| 要決心忘記我便記不起
林夕十九首 | 第一首
track 01 春秋
林夕十九首 | 第二首
track 02 金剛圈
林夕十九首 | 第三首
track 03 下次愛你
林夕十九首 | 第四首
track 04 不如不見
林夕十九首 | 第五首
track 05 償還
林夕十九首 | 第六首
track 06 大城小事
林夕十九首 | 第七首
track 07 左右手
林夕十九首 | 第八首
track 08 約定
林夕十九首 | 第九首
track 09 不來也不去
林夕十九首 | 第十首
track 10 飛...
林夕|台版序
鄭梓靈 |港版序| 從此我們的心不可能再完整
林夕 |港版序| 要決心忘記我便記不起
林夕十九首 | 第一首
track 01 春秋
林夕十九首 | 第二首
track 02 金剛圈
林夕十九首 | 第三首
track 03 下次愛你
林夕十九首 | 第四首
track 04 不如不見
林夕十九首 | 第五首
track 05 償還
林夕十九首 | 第六首
track 06 大城小事
林夕十九首 | 第七首
track 07 左右手
林夕十九首 | 第八首
track 08 約定
林夕十九首 | 第九首
track 09 不來也不去
林夕十九首 | 第十首
track 10 飛...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