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帝國想像
在歷史的後窗裡
我們生活在由數個帝國打造出的世界裡。事實上,今日世界大多數地區是帝國的遺物:殖民時代和殖民時代以前非洲、亞洲、歐洲、美洲之帝國的遺物。今日世界的歷史和文化,充斥著這些帝國留下的記憶、追求、建制、怨憤。其中,由英國人歷經三百多年歲月辛苦打造的帝國,即使不是最偉大的帝國,也是最遼闊的帝國。今日的主權國家,有多達四分之一出自這個帝國。光憑這點,其影響便可謂居歷來諸帝國之冠。
大英帝國歷史激起激烈難解的爭論:可說是必然之事。一個世紀前,當大英帝國國勢正盛,毫無衰敗之象時,史學家的評斷通常是正面的。那時,大英帝國的確已犯下錯誤,已行不公不義之事,已做盡傷天害理的事。當時,改革來得太遲,誤解已然滋生。但最終,一切,或大部分,都走上正軌。因為在這帝國的核心,存在著自我糾正機制:一個讓政治權力藉以向有識之見回應的自由主義體制。確實,這良善的結果似乎是為大英帝國史裡,較見不得人的章節提供辯解的最佳藉口。順這思路走去,征服與殖民那段歷史,制伏其他民族、使其他民族流離失所那段過往,就可視為野蠻、落後、困在自身「停滯狀態」、不清楚何為有利自身之事的民族進步的代價。將民族從迷信、野蠻狀態中救出,必然招致混亂,且往往要有人流血。
在此觀點下的帝國史,其自負還不止於此。因為它表明英國人本身已在道德上更上層樓。在強烈的良心驅策下,他們廢除了使他們變得極富有的蓄奴制度,向全球支持該制度者展開猛烈反制。他們也已不再從事欲將殖民地社會強納入倫敦中央控制的徒勞之舉,且透過給予自治,贏得社會的輸誠效忠。最明智之舉,據自由主義者的看法,乃是他們拒斥貿易保護,選擇自由貿易之路。英國人的高尚道德情操和追逐私利,都已得到回報和報應。自由貿易是英國繁榮的祕鑰,也是促進世界和平的最佳憑藉。馬歇爾(H. E. Marshall)的暢銷歷史著作,出版於一九○八年的《我們帝國史話》(Our Empire Story),始終抱持樂觀心態,也就不足為奇。
這正面觀點的確存在好長一段時間,久到幾乎和這帝國同時消失。其中某有力的遊說團體,甚至提倡大英帝國雖有某些弊病,卻是一股「造福(世人)之力」的觀點。當「白人自治領」(加拿大、紐西蘭、澳洲、南非)成為主權國家(一九三一年正式取得這身分),同時留在帝國範疇內時,可是被高舉為國際合作的典範、國家聯盟該如何運作的榜樣。經濟蕭條的一九三○年代,典範開始生變。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弊病的批評,反而更能打動人心,帝國自此被斥責為金融家、實業家的工具,成為知識界的主流。約翰.霍布森(John A. Hobson)的批評性大作《帝國主義研究》(Imperialism: A Study),一九○二年初問世時,未造成什麼衝擊,此際卻獲得一批熱情的新讀者肯定。來自千里達的非洲裔史學家(後來出任該國總理的)艾瑞克.威廉斯(Eric Williams),當時是牛津大學的研究生,完成一篇博士論文,以支持英國工業革命(英國富強的主要根源)建立在奴隸制(帝國勞動體制)之獲利的主張。這些著作預示了觀念的轉向,可惜影響有限。判斷當下觀念的更可靠指標,乃是偉大的「帝國建造者」塞昔爾.羅茲(Cecil Rhodes)的名聲。羅茲於一九○二年過世時仍未能完全免於他人的貶低。但他的英雄地位得到英國王室的認可背書。威爾斯親王於一九二五年拜訪他在布拉瓦尤(Bulawayo,今辛巴威境內)的墓地,日後將成為喬治六世的亞伯特王子則於一九三四年到訪。一九五三年,羅茲百年誕辰那天,伊莉莎白女王之母和女王之妹瑪格麗特公主,在眾多要人簇擁下,來到羅茲墓前向他致敬,西敏寺則為他揭開一面紀念匾。《非洲的羅茲》(Rhodes of Africa, 1936)這部影片,則把羅茲塑造為粗暴、陽剛、專橫,帝國的真正指標性人物。
一九六○年後,情勢丕變。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預示了帝國的解體,此際,解體的腳步加速。殖民統治作為一種開明託管方式,其道德正當性本已所剩無幾,這時更是蕩然無存。體現在聯合國憲章的戰後世界秩序觀,拒斥各種形式的殖民統治,支持主權民族國家的普世理想。在英國境內的進步派人士眼中,帝國傳統已似乎是沉重的負擔,其看重秩序與等級體制的過時心態,阻礙文化變遷和社會流動。原本可用於使英國經濟現代化的資源,虛擲在統治的負擔上。「易銷貨」的帝國市場,寵壞製造業,長遠觀之,後果不堪設想。在這種思維下,很容易就認為,帝國的歷史,在最好的情況下,都是不值一顧;在最壞的情況下,則徒然讓人不安的想起使英國在後帝國的世界裡擱淺的一個過時願景。在這幻滅心情下,人們輕易便接受去殖民化在剛獨立社會裡助長的那種「民族主義」歷史。一如英國境內的帝國史著作曾頌揚帝國的建立和締造者的豐功偉績,民族主義歷史著作,則為獨立國地位的取得和向帝國主義壓迫者奮力爭取自由之事喝采。得意洋洋的歷史學家,憑著同仇敵愾之心,恣意對著帝國冰涼的屍體,展開光榮的抗擊。
事實上,帝國退離歷史舞台愈遠,對帝國的論斷就愈不堪。一九七○年代,全球經濟看似混亂,於是馬克思主義的剝削、階級衝突歷史觀重獲信任。從這個角度審視,這段帝國歷史似乎正是普世性苦難的極致展現。殖民主義強行施加一道殘酷的經濟依賴枷鎖,使所謂「第三世界」的許多地方淪入以日益廉價的未加工產物換取進口製造品的困境之中,陷入使其日益貧困的循環裡。革命和階級戰爭是唯一出路。在本土勞動力和土地遭殖民地開拓者奪走的殖民地社會,剝削和帝國似乎融為一體。對研究南非(和南非境內)的歷史學家來說,不人道的種族隔離制度,幾可說是白人殖民的必然結果。南非悲慘歷史揭露的另一個道理─或許有人會宣告這是這段歷史給予世人的最大「教訓」─乃是殖民地開拓與帝國始終建立在種族特權與種族壓迫的平台上。在種族歧視與不平等仍牢不可破(尤以在西方最富裕、最強大社會最為明顯)的去殖民化世界裡,邪惡的種族主義成為帝國的重要遺產,成為推動所有帝國主義作為的意識形態核心,成為帝國經濟不可或缺的成分,成為帝國統治的指導原則。
將帝國形容為(最主要)種族壓迫體制的說法,則是更大範圍攻擊的尖銳之矛。在此,帝國成為使種種「屬下」(subaltern)群體受壓迫、失自由的系統化工具(「屬下」一詞借自義大利馬克思主義革命分子安東尼奧.葛蘭西之語)。「屬下」歷史描述帝國加諸在那些無緣取得政治權力的弱勢者身上的社會不公、經濟不公,而這些弱勢者包括:農民族群、邊緣群體,例如印度境內的「部落民」、森林居民、賤民等、非洲境內的移民、游牧民、四海為家者、短期工、女性工作者和妓女以及大多數女人。帝國代表了當地支配階層和帝國政權基於現實利害擬出的陰謀。
「屬下」理論或可擴大適用於帝國「母土」。「母土」也存有受騙於帝國主義精英之詭計的平民大眾,他們繳稅,獻出鮮血,少數人因而得以享有顯赫地位、利潤、娛樂。「母土」的女人弱勢,在男性支配的社會裡地位相對卑下,而殖民地開拓、殖民戰爭、帝國統治所強調的陽剛精神,更強化女人的卑下。「屬下」歷史激起另一個大問題。提倡「屬下」歷史者主張,強制是帝國權威的核心要素,殘暴之事比經過淨化的帝國史所坦承的還要多見。顯然地,運用武力和揚言運用武力,無法完全說明帝國母土和其領地為何默然接受帝國的強制。英國統治南亞時,歐洲人遠少於印度人,但除開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只碰到非常局部性的叛亂,而且叛亂的頻次不多。要說「帝國觀念」(imperial idea)的接受取決於母土境內的強制(若非對女人的強制,就是對其他任何「屬下」群體的強制),將更站不住腳。然有一新論點主張,只要搬出英國「文化帝國主義」的衝擊,就能填補這段解釋上的空白。此一看法來自以下這個在其他地方深具影響力的見解:掌控人與觀念被代表(represented)的方式,乃是社會支配、政治支配的祕鑰。關於何為犯罪或精神失常、何為道德或不道德、何為進步或原始所提出的界定,一旦得到公眾接受,就能悄然宰制人的思想和行為。文化精英也能操弄那些界定,以保護他們本身的特權。不難看出這可如何擴大用於帝國身上。
|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未竟的帝國:英國的全球擴張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358 |
二手中文書 |
$ 406 |
歷史 |
$ 423 |
世界史地 |
$ 458 |
世界歷史 |
$ 458 |
Books |
$ 510 |
中文書 |
$ 510 |
世界國別史 |
$ 510 |
Books |
$ 522 |
歐洲史地 |
$ 522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未竟的帝國:英國的全球擴張
在這個不穩定的世界裡,沒有哪種帝國能維持現狀永遠不變,有暫時的喘息,沒有帝國的「最終狀態」。
要了解帝國體系,就要先了解英國!
我們生活在由數個帝國打造出的世界,今日的主權國家,有多達四分之一出自英國。大英帝國以各種方式塑造了世界:移民數個大陸、創造新國家,並將其語言、科技、價值觀強加在其他民族身上。近兩百年時間,其擴張至垮台,乃是決定歷史進程的最大因素,如今它仍為迷思、誤解、爭議所籠罩。
大英帝國歷史激起激烈難解的爭論
一個世紀前,當大英帝國國勢正盛,毫無衰敗之象時,史學家的評斷通常是正面的。那時,大英帝國的確已犯下錯誤,已行不公不義之事,已做盡傷天害理的事。當時,改革來得太遲,誤解已然滋生。但最終,一切,或大部分,都走上正軌。因為在這帝國的核心,存在著自我糾正機制:一個讓政治權力藉以向有識之見回應的自由主義體制。
一九六○年後,情勢丕變
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預示了帝國的解體,此際,解體的腳步加速。殖民統治作為一種開明託管方式,其道德正當性本已所剩無幾,這時更是蕩然無存。體現在聯合國憲章的戰後世界秩序觀,拒斥各種形式的殖民統治,支持主權民族國家的普世理想。在英國境內的進步派人士眼中,帝國傳統已似乎是沉重的負擔,其看重秩序與等級體制的過時心態,阻礙文化變遷和社會流動。原本可用於使英國經濟現代化的資源,虛擲在統治的負擔上。
英國擴張的過程
英國擴張史呈現為一連串的帝國遭遇,這些遭遇始於接觸,終於殖民地社會的誕生。這是帝國誕生的過程。但為看清楚動作,我們必須用慢動作播放:將它拆解為數個組成部分和階段;挖掘出使帝國顯得「合理」的觀念;探明帝國統治者倚賴的策略;說明導致叛亂的民怨;追索英國人通常用來平亂的方法;跟隨傳教士的足跡(和辛勞)走一趟;剖析帝國對鄉土觀和認同感的影響。接觸、占有、發動戰爭、定居(或試圖定居)、(以正當或不當手段)進行買賣、統治、叛亂、鎮壓、成為基督教徒、改造認同:這一切和其他未列出者,全是帝國誕生過程的一部分。
本書說明大英帝國內部多元並存、矛盾,又混亂,這個帝國受水火不容的利益團體所控制,其擴張除憑藉本身的強大,也得益於他國的衰弱。同時以英國為例,探討在歐洲境外擴張的三百年期間帝國的建造過程,並以中世英格蘭帝國主義史為這些擴張行動的根源。
【名家推薦】
「約翰.達爾文寫出一部出色的大英帝國史,廓除籠罩這主題的意識形態濃霧,說明我們如今仍受到這帝國多大的影響。」——卜正民(Timothy Brook),《維梅爾的帽子》、《掙扎的帝國》作者
「令人耳目一新、富有見地、經透徹研究、令人折服之作。」——安德魯.羅伯茲(Andrew Roberts),《假如日本不曾偷襲珍珠港》作者
「本書這般從多方面了解帝國過往,使我們能更清楚、更深刻理解種種權力與暴力。為帝國史著作立下更高的標竿。」——《BBC歷史雜誌》
「無人能及的大英帝國興亡概述」——《週日獨立報》年度好書
「達爾文學識之深厚令人嘆服……從頭至尾保持令人讚賞的客觀、嚴肅學術立場……一部鞭辟入裡、富有見地、讀來有趣、不慍不火的書。」——《紐約時報書評》
「達爾文先生讓人增長知識、眼界大開的著作,寫作嚴謹,充滿有趣的統計資料和敏銳的觀察心得。」——《華爾街日報》
「擲地有聲的帝國史著作……極重要且有用。身為英格蘭人,對於他的國家所曾管轄的那個帝國,達爾文既未吹捧,也未刻意自我批判,而是以明澈的眼睛予以檢視。他在這點上的成就已達到值得嘉許、乃至出類拔萃的程度。」——《華盛頓郵報》Jonathan Yardley
「面面俱到……達爾文的博學使他得以避開狹隘的辯護、批判窠臼,深入介紹英國那段稱霸全球的不凡時期。」——《週日泰晤士報》
「在本書中,約翰.達爾文提醒我們,帝國是人所締造。這本書從建造、經營大英帝國的男女的視角講述這帝國的歷史,身為帝國史權威的作者,針對這個史上存續最久之一且影響力最大之一的帝國的複雜運作方式,提供了新且客觀的檢視。凡是有意尋找清楚易懂、面面俱到、跟得上時代的探討大英帝國之作的人,有此一部即夠,毋須他尋。」——Timothy Parsons(The Rule of Empires作者)
「概括性且毫無教條主義氣息的專題著作,研究大英帝國漸進且並非總是安穩的發展過程……作者精闢描述了英國人在印度的不凡統治……一部立場公允、旁徵博引的著作,精細入微呈現帝國的建造過程。」——科克斯書評
「寬廣的歷史視野、令人耳目一新的看法、出色的寫作風格、過人的學識……此書一出,其他任何同一主題的著作都可以束諸高閣……終於擺脫掉扭怩不安情緒的大英帝國史著作;我們所引頸期盼的著作。」——《今日歷史》
「鞭辟入裡的剖析……熔個人淵博學識、言所當言的公正立場、優美筆法於一爐,達爾文寫出振奮人心的精彩之作。」——《經濟學人》
作者簡介:
約翰.達爾文John Darwin
長期關注專研帝國的興衰史,著有《帖木兒之後》、《未竟的帝國》、《大不列顛和去殖民化》、《大不列顛帝國的終結》、《埃及和中東》。曾於牛津大學教授帝國史和全球史。二○○八年因《帖木兒之後》獲頒沃夫森歷史學獎、二○一二年成為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二○二○年因對全球史的貢獻獲頒大英帝國勳章。
相關著作:《未竟的帝國:英國的全球擴張》
譯者簡介:
黃中憲
政大外交系畢,專職筆譯,譯有《貿易打造的世界》、《維梅爾的帽子》、《帖木兒之後》、《太平天國之秋》、《帝國暮色》、《戰後歐洲六十年》、《意外的國度》、《湖南人與現代中國》、《未竟的帝國》、《成吉思汗》三部曲等。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帝國想像
在歷史的後窗裡
我們生活在由數個帝國打造出的世界裡。事實上,今日世界大多數地區是帝國的遺物:殖民時代和殖民時代以前非洲、亞洲、歐洲、美洲之帝國的遺物。今日世界的歷史和文化,充斥著這些帝國留下的記憶、追求、建制、怨憤。其中,由英國人歷經三百多年歲月辛苦打造的帝國,即使不是最偉大的帝國,也是最遼闊的帝國。今日的主權國家,有多達四分之一出自這個帝國。光憑這點,其影響便可謂居歷來諸帝國之冠。
大英帝國歷史激起激烈難解的爭論:可說是必然之事。一個世紀前,當大英帝國國勢正盛,毫無衰敗之象時...
在歷史的後窗裡
我們生活在由數個帝國打造出的世界裡。事實上,今日世界大多數地區是帝國的遺物:殖民時代和殖民時代以前非洲、亞洲、歐洲、美洲之帝國的遺物。今日世界的歷史和文化,充斥著這些帝國留下的記憶、追求、建制、怨憤。其中,由英國人歷經三百多年歲月辛苦打造的帝國,即使不是最偉大的帝國,也是最遼闊的帝國。今日的主權國家,有多達四分之一出自這個帝國。光憑這點,其影響便可謂居歷來諸帝國之冠。
大英帝國歷史激起激烈難解的爭論:可說是必然之事。一個世紀前,當大英帝國國勢正盛,毫無衰敗之象時...
顯示全部內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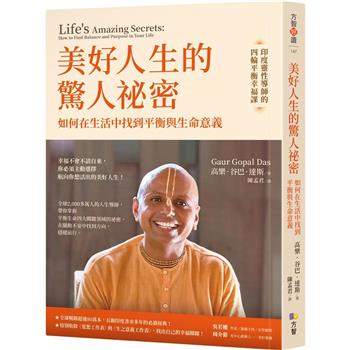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