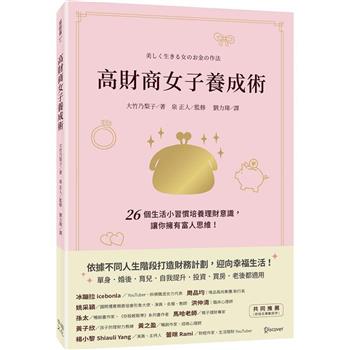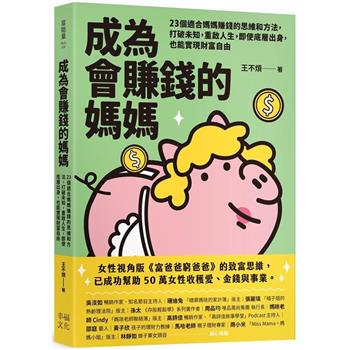圖書名稱:無足輕重的女人
維吉尼亞‧霍爾
一位現代間諜史上被低估的傳奇人物
改寫並顛覆人們對「戰爭」的定義
她是謎樣般低調的終極情報員,超前時代的女性!
蓋世太保眼中最難對付的間諜,神秘的「跛腿女士」( ""the limping lady"" )
一位看似無足輕重的女人,卻扭轉了二戰的歷史潮流
§————§
比好萊塢電影更刺激的真實人生!
二〇二〇年十月.繁中版傳奇上市.英雌無悔
§————§
維吉尼亞.霍爾曾是美國上流人士。二戰前,霍爾曾多方試圖加入美國正式外交人員的行列,但因先前意外失去了一條腿,也因她的女性身分而屢被拒之門外。直到她被英國特勤局吸收,為英國情報機關特別行動處(SOE)工作,並在二戰期間潛伏在法國維希(Vichy),不僅吸收各式線人、克服萬難向盟軍傳遞資訊,更想方設法解救身陷囹圄的同僚。霍爾身體上的殘缺,使得她的成就更顯難能可貴。
霍爾展現出一個成功間諜所有的必要特質:大膽而又紀律嚴明、勇敢無畏而又足智多謀,同時在1941年至1945年的兩次重大任務期間,達到驚人成就。後來她加入美國戰略情報局(OSS),亦即CIA的前身。
這本傳記兼具史詩般真實故事的勇敢、犧牲,以及尋找真愛,述說從未公開的情節。本書作者索尼亞.普內爾(Sonia Purnell)為得獎傳記作家,她苦苦追索有關霍爾的足跡與機密資料;在她筆下,首次揭露第一位現代女間諜維吉尼亞.霍爾的諸多代號;拼湊出霍爾的一生,以及她與夥伴在時代動盪中充滿人性的故事。
▍ 必讀原因
★ 隻身前往法國臥底,進行組織籌畫抵抗與情報工作。納粹頭子克勞斯.巴比(Klaus Barbie)認為她是最危險的盟軍間諜。
★ 揭露傳奇間諜的神秘面紗:神出鬼沒,一生奉行低調。「她生前絞盡腦汁偽裝自己!」
★ 不斷挑戰對女性身分的限制,也努力克服身體缺陷。為自由與理念的浪漫而戰,挑戰命運的真實故事!
作者簡介
索尼亞.普內爾Sonia Purnell
得獎傳記作家暨記者,以其細緻的研究及活潑的寫作和演講風格而著稱。曾任職於《經濟學人》、《每日電訊報》,以及《星期日泰晤士報》。她的第一本著作《Just Boris》即入圍英國歐威爾獎初選名單。她的最新出版著作《Clementine》,在大西洋兩岸都受到熱烈的讚揚,同時入圍Plutarch獎2016年最佳自傳獎,亦獲得《每日電訊報》和《獨立報》2015年年度之書的讚譽。
譯者簡介
黃佳瑜
臺灣大學工商管理系畢業,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企管碩士。曾任聯合利華行銷企劃、美商麥肯錫管理顧問公司管理顧問。現為自由譯者,譯作有:《Jack》、《但求無傷》、《敦克爾克大撤退》、《發光體》、《孤獨的反義詞》、《財團治國的年代》、《精神病院裡的歷史學家》、《向50位頂尖管理大師學領導》、《成為這樣的我:蜜雪兒‧歐巴馬》(合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