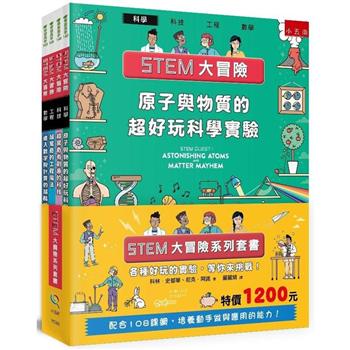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2 項符合
親愛的艾文‧漢森(同名電影&百老匯大獎音樂劇小說)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一封寫給自己的信
一個孤單的靈魂勇於接納自己的承諾
同名電影&百老匯大獎音樂劇小說
【原作榮獲葛萊美獎】【東尼獎】【2021多倫多影展開幕片】
【《奇蹟男孩》、《壁花男孩》導演執導】
李偉文(牙醫師‧作家‧環保志工)李豪(作家)洪仲清(臨床心理師)陳慧翎(導演)膝關節(影評人)劉育豪(高雄市港和國小教師、高雄市性別公民行動協會理事長)《西蒙與他的出櫃日記》作者貝琪‧艾柏塔利 鄭重推薦
已售十三國版權
繼《漢娜的遺言》後的話題之作
DEH以及劇中台詞#Youwillbefound已成為Twitter上的熱門關鍵字
=內容簡介=
親愛的艾文‧漢森:
我想要改變。我希望自己能有所歸屬。
真希望有一個人能好好聽我要說的話。
只是,說真的,
假使我明天消失,難道真會有人注意到嗎?
艾文曾經想要努力「參與」生活——例如,接近同學,但同學從來不會離他很近;媽媽嘴裡說他很棒,眼神卻透露完全相反的心思。至於父親,只是在遠方不停要他看繼母的孩子照片。直至意外從樹上跌下、摔斷手的那一天,艾文發現他身邊只有一個人——他自己。
依照心理醫師的建議,艾文練習寫給自己的一封信,竟然意外公諸於世;接連而來的是怪咖同學康納的離世,迫使艾文成為康納家庭的好朋友,也促成他從角落走向聚光燈下。這一切究竟是夢幻、謊言,還是艾文沒有勇氣面對的真實人生……
跌下大樹時、孤單一人躺在地上的艾文,望向無邊際的晴朗天空,他發現終於有機會不再需要屈服於過往的陰霾,
只是在掙扎中,為什麼謊言總是掩蓋想說出真相的勇氣?是不是原本每一個想放棄生命的背後,其實都有與外界連結的渴望。
但,孤單的靈魂們又該如何才能逆轉人生,尋得最後的歸屬感……
=內文精采分享=
※你眼前有這麼多美好的人事物。記得這一點就好。爬上山頂的路途本來就很辛苦漫長,但一路發生的點滴都值得珍惜。
※好不公平:無論好壞,地球照樣運轉,康納這種人就被人們遠遠拋在腦後。前一天,他才被刺上某人的胸口,第二天,卻被扔進了垃圾箱。怎麼會這樣啊?
※我們穿梭在大樹之間,小心翼翼不打擾大自然,但我們肩負一項任務。我們不是來找麻煩的,我們代表了許多人,全是孤獨的靈魂。
※未來,人們將繼續看著這裡茁壯。那些我們不小心失去的人們。我們會攜手一起前進,努力往上攀爬,向下墜落,憑風翱翔天際。努力接近萬物的中心點,努力看清自己,理解自己,也認識彼此,共同觸摸真實的美好世界。
※這些人都渴望能與外界有所連結。如今有機會能分享自己獨特的個人經歷,他們深感鼓舞。其中有人或許無法達到外界期望,或有人跟人借錢卻還不起,也有人擔心自己可能永遠無法離開寄養家庭,或有人孩子早夭,還有人欺騙了唯一支持自己的好友,或是工作丟了,或遇上濫用權力的主管,或再也沒有努力的目標,覺得一切都不值得了。也有人每天連起床、外出或上班都使不上力。甚至有人不知如何發洩憤怒,或該如何忍受孤單,或扭轉錯誤。或者,不知道該如何不放棄生命...
=作者的話=
親愛的讀者:
今天會是美好的一天,原因如下:
你正翻開一本全新的小說。或許你因為看過音樂劇,對書中角色都很熟悉;要不就是聽過它的原聲帶,甚至看過網路上的影片,也有可能你對艾文‧漢森這個人毫無概念,但你覺得封面那棵大樹滿酷的,總之,我們很高興能與你在此相遇。我們期待你愛上每一位人物,正如當初我們創造他們時那種打心底喜愛他們的心情,也希望本書訴說的一切,能讓你反思、感受,並有所連結。
謝謝你。
作者簡介
瓦爾・艾米奇Val Emmich
瓦爾・艾米奇為作家、歌手暨作詞家,同時也熱愛表演。他的首部小說作品《The Reminders》是B&N discover選書,《圖書館月刊》讚譽「古怪、動人且令人上癮」。
史提芬・列文森Steven Levenson
史提芬・列文森因百老匯音樂劇《親愛的艾文・漢森》榮獲東尼獎最佳編劇的肯定,並有其他數部成功佳作。他也是Showtime頻道系列影集《性愛大師》的製作人。
班吉・帕薩克Benj Pasek
與杰思汀・保羅為知名作曲雙人團隊,奧斯卡獎、葛萊美獎、東尼獎與金球獎莫不給予他們的作品最大的肯定。《親愛的艾文・漢森》、《耶誕故事音樂劇》都是兩人的精心結晶,此外,他們更跨足影壇,製作《越來越愛你》、《大娛樂家》以及《魔法精靈》的配樂與歌曲。最近即將上檔的電影音樂劇則是迪士尼公司的《白雪公主》與《阿拉丁》。
杰思汀・保羅Justin Paul
與班吉・帕薩克為知名作曲雙人團隊,奧斯卡獎、葛萊美獎、東尼獎與金球獎莫不給予他們的作品最大的肯定。《親愛的艾文・漢森》、《耶誕故事音樂劇》都是兩人的精心結晶,此外,他們更跨足影壇,製作《越來越愛你》、《大娛樂家》以及《魔法精靈》的配樂與歌曲。最近即將上檔的電影音樂劇則是迪士尼公司的《白雪公主》與《阿拉丁》。
譯者簡介
陳佳琳
台灣大學外文系畢,華盛頓大學東亞碩士,蒙特雷國際學院口筆譯碩士。譯作包括《門》、《嬉皮記》、《邊緣人的合奏曲》、《親愛的小小憂愁》、《跟大師學創造力》、《飄浮男孩》、《喬治女孩》、《我要帶你回家》、《騙徒》、《布魯克林》、《來自無人地帶的明信片》、《大師》與《在我墳上起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