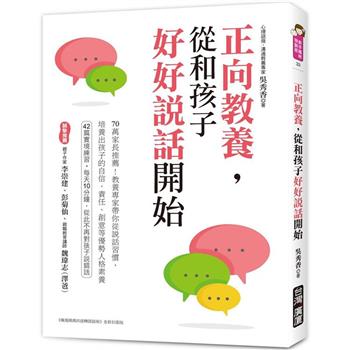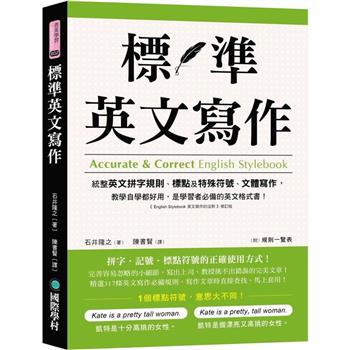導論
「野蠻的」和「文明的」兩個用語經常在談話和書籍中出現,因此,無論誰用思想去考察人類的行為和歷史,都有機會仔細考慮這兩個詞通常要傳達的意義,以及歷史學家和道德哲學家應該在什麼意義上使用它們。——詹姆斯.鄧巴(James Dunbar):《粗野和有教養時代的人類歷史文集》(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in Rude and Cultivated Ages,1780)
在十七世紀晚期的英格蘭,人們常常隨意地提到所謂的「文明世界」(civil world)、「人類的已開化部分」(civilized part of mankind)、「已開化諸民族」或「已開化世界」等等,但並不總會清楚說明他們指的是哪些國家。一六九○年,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問道:「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有多少個?他們是誰?」他沒有自己回答,但他拒絕接受「最文明」民族必然是信奉基督教民族的觀點。他以中國為例,指出中國人是「非常偉大和文明的民族。」在查理二世的一位主教看來,巴比倫、阿勒坡(Aleppo)和日本也包括在「文明世界」之列。
到了十八世紀後期,東方學家威廉.馬斯登(William Marsden)按開化程度把人類分為五個等級,最高級的是「精煉的歐洲諸民族」,中國人緊隨其後,底層的是加勒比人(Caribs)、拉普蘭人(Laplanders)和霍屯督人(Hottentots)。他說最後這幾種人「表現出人類最粗野和最丟臉的一面。」按他同時代人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的觀察:「所有程度的野蠻狀態和高雅狀態都是我們可以同時看到:歐洲和中國的非常不同的文明,波斯和阿比西尼亞的野蠻,韃靼和阿拉伯的古怪舉止,北美洲和紐西蘭的生番狀態。」這個概念架構將會有漫長的後續歷史。正如愛德華.泰勒在一八七一年所指出:「受過教育的歐美人實際上是透過把自己的民族放在社會系列的一端和把生番部落放在另一端而設定一個標準,再按其他人接近野蠻或有文化的程度,把他們安置在這兩端之間某處。」這是一種洛克時代的人會認同的世界觀。對他們來說,「已開化」民族是那些以「文雅」或「光鮮」方式生活的人,與「未開化」民族的「野蠻」和「原始」形成鮮明對比。
這種劃分人類的方式有顯赫的古代血緣。在西元前五世紀的雅典,所有不會說希臘語的外國人一律被稱為「野蠻人」(barbaroi),意指這些人的語言費解。一開始,這個詞是中性的、但後來變得越來越有貶義。慢慢地,「野蠻人」不僅被認為語言上有缺陷,而且在政治、道德和文化上也有缺陷。關於這些缺陷是什麼,人們沒有達成共識,不過常被提到的特徵包括了不知節制、殘忍和甘於接受專制統治。希臘人的身分認同端賴把希臘人的價值觀對比於野蠻人的價值觀。然而,不同作家強調外國人的不同屬性,不存在一個單一的野蠻概念。柏拉圖(Plato)是那些認為把所有非希臘人放在同一個籃子裡是荒謬做法的人之一,反對(例如)把不識字和游牧的西徐亞人(Scythian)跟高度有教養的波斯人和埃及人相提並論。
在希臘化時期(336-31 BC),希臘人/野蠻人二分法的重要性縮小了。斯多噶派哲學家強調人類一體。科學作家艾拉托斯提尼(Eratosthenes,c.285-194 BC)反對將人類二分為希臘人和野蠻人,指出有許多希臘人毫無價值,也有許多野蠻人高度開化。實際上,希臘人對其他民族的態度往往比希臘人/野蠻人的簡單對比所暗示的更為微妙。
對羅馬人來說,蠻族是帝國邊界之外的民族。蠻族常常(但非一成不變)被認為是暴力和無法無天,出了名的「凶殘」(feitas)和缺乏「人文」(humanitas)──即缺乏溫文、文化和知性深度。這些野蠻人的屬性(特別是「凶殘」)被揉在一起,弄成了「野蠻」(barbaria)的概念:那是一種反社會衝動的混合體,即便文明人也可能陷入其中。實際上,帝國的疆界是可滲透的,而「野蠻」的外來者很容易就被同化。但刻板印象已經確立。日耳曼人在四至六世紀對西羅馬帝國的反覆入侵也沒有能消除這種印象,儘管這些所謂的蠻族中有許多實際上已經高度羅馬化。
隨著基督教的傳播和古羅馬世界的解體,蠻族的概念變得越來越無關緊要。從七世紀中葉開始,當阿拉伯人因征服北非和伊比利亞半島而對歐洲構成了威脅以後,情形更加是如此,因為伊斯蘭文化在知性上比西歐文化更為精密複雜,稱之為「野蠻」不再能令人信服。但維京人卻不是如此,他們在九至十一世紀期間對不列顛群島和北歐進行多次襲擊,導致他們有時被指為野蠻人。然而,直到十七世紀,關鍵的二分法仍然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分,是十四世紀詩人傑佛瑞.喬叟(Geoffrey Chaucer)所說的「基督教世界與異教世界」(christendom and hethennesse)之分。作為一個地理區域的「基督教世界」觀念是從九世紀之末開始流傳,並在一○九五至一二七○年間從反對穆斯林控制耶路撒冷聖地的十字軍東征得到鞏固。在喬叟的時代,鄂圖曼土耳其人的崛起加劇了歐洲人與伊斯蘭教的衝突。這些異教徒征服了巴爾幹半島,占領了君士坦丁堡,摧毀了拜占庭帝國,在在威脅著中歐和地中海。
然而,除了基督徒和異教徒的固執二分法之外,「文明」和「野蠻」的古老二分法並沒有完全被遺忘。這兩種分裂人類的方式有時會被混為一談,即把基督徒視為文明人、把異教徒等同於野蠻人(拉丁文單字paganus便是同時指異教徒和野人)。在十二和十三世紀,西歐的城市化和經濟進步讓它可以將自己的物質繁榮與不發達的社會對比起來。這個時候,歐洲人也重新發現了古典學問(特別是重新發現了阿拉伯學者研究已久的亞里斯多德著作),而這意味著希臘和羅馬的野蠻/文明觀念的復活。以他們使用的外語為標識,野蠻人再一次被說成是非理性,無法無天,凶殘,精神和物質文化水平低落。最典型的野蠻人變成是歐亞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但一些基督教民族也被貼上這個標籤:在十二世紀,不列顛群島上的英格蘭人基本上把塞爾特人地區視為野蠻地區。
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的軍事衝突本來一直被視為相互競爭宗教間的一場聖戰,但在十五世紀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借用古典的刻板印象,以更俗世的方式來表現這場戰爭,把它描繪為象徵文明的西歐和象徵野蠻的伊斯蘭教之間的競逐。文明的範疇慢慢開始取代宗教的範疇,成為一個國家在外交上是否可被接受的重要指標。
在十六世紀,大多數歐洲人仍然認為區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至關重要。然而,那些去到新發現美洲和亞洲的旅人雖然強烈意識到它們的居民信奉異教,但他們對這些地方的記述絕大多數是以野蠻/文明的世俗架構寫成。面對美洲土著文化的廣泛多樣性,西班牙作家巴托洛姆.卡薩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和何塞.德阿科斯塔(José de Acosta)創造出一種野蠻類型學,在非歐洲民族中間建立高低等級。按照他們的分類,擁有法律、統治者、城市和使用文字的中國人位居最頂,最底層則是加勒比人之類的生番,他們沒有任何政府組織,也缺乏與其他民族溝通的手段。多個世紀下來,認定野蠻人的標準發生了變化,使用的術語也是如此。學者、旅行家和到過其他大陸的人現在不再把野蠻視為一種絕對狀態,改把它看成一種程度上的問題。他們以文化的等級高低而不是單一的「文明/野蠻」二元區分來思考問題。但在許多其他人,基本的二分法維持不變。它被籠統地套用,並沒有參考民族學家和哲學家提供的細微差別。
在十七世紀的英格蘭,「文明的」(civil)民族越來越常被稱為「開化的」(civilized)。後者是一個更複雜的詞,因為它既意味著一種狀態,即文明狀態,也意味著一個過程、即擺脫野蠻而到達文明狀態的過程。「開化」(civilize)就是從一種狀態轉變到另一種狀態。這種情況可能發生在一個民族身上,例如古不列顛人(據說他們是被羅馬人變成文明人),也可能發生在野生植物──十七世紀的園丁把栽培和改良野生植物稱為civilized(馴化)。到了十七世紀後期,開化的進程開始被稱為「文明化」(civilization)。例如,一位作家在一六九八年評論說:「歐洲首先要為他們的文學和文明化(civilization)而感謝希臘人。」一七○六年,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研究員(後來的教務長)安德魯.斯內普(Andrew Snape)把人類之結合為「社會與政治體」稱為「人類的文明化」。律師們還用這個詞來表示將刑事案件轉變為民事案件的過程。civilization一詞最初被用來描述開化的過程或行動,後來也被用來指該過程的最終產物,即指一種開化了的狀態。很難考究出這層新的意思是在什麼時候獲得。前一種意義逐漸被後一種取代。例如,在一七四○年代,當肯特郡比克斯利(Bexley)的亨利.皮爾斯牧師(Henry Piers)在佈道中談到「civilization和禮貌行為」時,他就非常接近於在狀態的意義下使用這個詞。但只有從一七六○年代起,英國作家們才毫無歧義地用civilization來指開化了的狀態。晚至一七七二年,約翰生還著名地拒絕把這個新字收入他編的《字典》中。為表示「開化了的狀態」(「擁有免於野蠻的自由」),他堅持使用較古老的字眼:civility。
civility曾經是(現在也是)一個棘手和不穩定的詞。不過雖然它在近代早期被用來指一堆不同的意義,但這些意義都以某種方式指涉一個秩序井然的政治共同體,以及指涉共同體內成員的恰當素質與行為。在十六世紀初,civility像它的義大利前驅civiltà和法國前驅civilité那樣,也有了「非野蠻的生活方式」的更大意涵──這種生活方式最終會被稱為civilization(文明)。然而,civility意味著一種靜態的狀態、並沒有任何開化過程的意味。在十六世紀期間,它也有了一個較狹隘的意義,被用來指良好舉止和禮貌行為──正如「應該要以共同禮貌(common civility)待人」這句話所表達的那樣。正是這種歧義性讓詹姆斯.鮑斯威爾(James Boswell)試圖說服約翰生把《字典》裡的civility只解釋為「禮貌」,而把「開化了的狀態」這層意思保留給新字civilization。但他沒有成功。
儘管受到約翰生的抵制,civility在十八世紀晚期還是窄化為只剩「良好舉止」和「良好公民行為」的意義,而civilization一詞則進入了一般的英語,既用來指開化的過程,也用來指開化了的人的文化、道德和物質狀態。「文明」(civilization)這個詞被廣泛使用,帶有不加掩飾的種族優越感,意味著「開化的」民族是人類社會的最完美狀態,與之相比,其他生活方式或多或少是低劣的,是貧窮、無知、管理不善或完全無能的產物。這一假設將被證明對形塑西歐人與其他人群之間的關係至關重要。
在十九世紀,當歐洲國家試圖界定接納其他國家加入國際社會的條件時,它們推出了一套「文明的標準」,要求希望被承認為主權體的亞洲人和非洲人政府符合。它是近代早期法學家推出的《萬民法》(ius gentium)的最新版本。自然地,這套標準體現了西歐本身的法律和政治範規。它不考慮其他文化傳統。如果其他民族達不到其要求,國際法就拒絕承認它們為主權國家,並允許外國干涉其內政。
在歐洲列強看來,此舉與其說是要肯定它們的優越性、不如說是要在國家間實現必要程度的互惠。一個「開化了」的政府應該能夠訂立有約束力的合同、進行誠實的行政管理、保護外國人和遵守國際法的規定。歐洲人認為這些是「未開化」民族總是達不到的要求。就此而言,他們當然是正確的。然而,國際法本身是歐洲的產物,反映的是先進商業國家的利益。缺乏代議制政府、私有財產制度、自由貿易和正式法律的國家不被視為擁有自己獨特的文明形式,而是被視為「落後」的,等待著被按照西方的模子來形塑。以歐洲為中心的單一文明標準反映了對其他文化的行為規範的蔑視。西方優越感被援引來合理化對所謂的野蠻人的殖民或商業剝削,打著「開化使命」的名義向全球的愚昧地區輸出歐洲的合法性標準和正確的管理制度。
一次大戰後成立的「國際聯盟」聲稱只包括「開化」的國家,並堅持把文明傳播到世界其他地區是成員國的責任(話雖如此,它照樣承認蘇聯、納粹德國和法西斯義大利。)要直到一九四五年國際聯盟的後繼者「聯合國」成立,「開化」與「未開化」國家的正式區分才最終被拋棄。當時的一位主要法學家說︰「在承認的問題上,現代國際法不區別開化國家和未開化國家,也不區別國際開化國家社群之內和之外的國家。」
在近代早期的英格蘭,「文明」和「野蠻」的古老和持久對立經常被用來表達一些基本價值觀。當時關於文明理想(ideal of civility)的論述是在自我描述的話語中進行的。當探險家和殖民者對他們在非歐洲世界遇到的「野蠻」和「蒙昧」表示遺憾時,他們乃是隱含地表達了他們對自己生活方式的珍視。他們透過闡述自己不是什麼來定義自己。就像後宗教改革時代英格蘭的其他大忌(例如「教皇」和「巫術」)那樣,「野蠻」的觀念體現了許多時人感到厭惡的東西,並因此間接透露了他們所讚賞的東西。正如神學家為了顯示什麼是善而闡述罪的意義一樣,「開化」民族的概念需要「野蠻」民族的概念(最好是還有實際存在的「野蠻」民族)來澄清自己的獨特之處。文明(civilization)的概念本質上是對比性的:它必須有一個對立體才能被理解。哲學家暨歷史學家柯靈烏(R. G. Collingwood)在一九三○年代寫道︰「我們創造了生番這種神話人物,他們不是歷史上的真人實事、而是我們所恐懼和厭惡的一切的象徵。我們把我們裡面為我們不齒的所有欲望和我們鄙視的所有思想放入他們之中。」今日的學術術語說得好︰「身分是透過創造他性(alterities)所構成。」詢問近代早期的英格蘭人何謂「文明的」和何謂「野蠻的」,事實上就是在探究他們對於社會應該如何組織和生活應該如何進行的基本假設。它也提供了一個重新考慮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想法的視角。
本書希望證明,在十六世紀早期的宗教改革到十八世紀晚期的法國大革命這段期間,文明(civility and civilization)的理念在英格蘭非常重要。本書顯示出它們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了當時人的思想,並描述了它們如何被使用。它還探討了它們受到挑戰和甚至被拒絕的一些方式。在可能的情況下,它會考慮全體英格蘭人民的觀點,但它無可避免要強烈依賴能言善道者的意見。因此,文中充斥著大量直接引語。有些人可能會覺得這種做法很笨拙。正如自然哲學家羅伯特.波以耳(Robert Boyle)在一六六五年所言:「我知道,如果我在引用時不那麼準確和謹慎,大多數讀者會更容易接受。許多人認為少引用別人的文章,只說出作者的名字,然後用轉述的而不是直接引用,是一種更為文雅和高明的寫作方式。」儘管有這樣的提醒,我還是和波以耳一樣,認為引用別人自己的原話比轉述要好,因為後者無可避免會造成扭曲。
當然,我們必須記住,就像關於其他任何議題一樣,所有關於文明和野蠻的評論都是有特定的語境、而且是帶有特定的目的。關於這一問題的許多近代早期的聲明都是在跨文化接觸的過程中產生,所以常常帶有議論目的。自從羅馬史家塔西佗(Tacitus)透過描寫野蠻人的美德來揭露文明人的罪惡而寫了《日爾曼尼亞誌》(Germania)以來,對異邦人生活方式的討論通常都是別有用心。在近代早期的英格蘭,很多人會細細描述愛爾蘭人和美洲土著的野蠻行為,目的都是為了掠奪他們,反觀那些強調土著是文明人的人則是意在約束土著的征服者。在這兩種情況下,何謂「文明」或「野蠻」的隱含定義都是為服務特定的目的而建立起來。這些用語的意義會按脈絡的不同、使用它們的人的不同和文學形式的不同而發生變化。還必須考慮的是賴以建構論證的特定「語言」或「論述」所帶來的限制。清教徒神學家、自然法法學家、古典共和主義者、推測史史家(conjectural historians)和政治經濟學家都在特定的知識傳統中寫作,並以不同的方式研究他們的主題。如果對引文來源的語境和形式沒有足夠的重視而將不同來源的引文並列在一起,有可能會引起誤導。正如一位學術評論家指出的,把一文本中的命題看成是自足的那樣進行評估是危險的,必須避免,應該改為把它與其他文本中的類似觀念加以比較。
然而我相信,在近代早期的英格蘭,人們對於何謂文明和何謂野蠻有著共同的想法和假設,而這些想法和假設是可以透過關注人們的所言所書來重建而不受脈絡變化的影響。當然,這是一個經歷了重大變化的時期,經濟上、政治上、宗教上和文化上莫不如此。儘管如此,人們對禮儀和文明的觀念仍然有著很大的連續性。我努力對時間的變化保持敏感,但每當看起來合理,我會毫不猶豫地從不同的世紀「採集」證據。
關於什麼是良好的舉止和文明的生活,許多英格蘭人公認的觀念是其他西歐國家所共有。英格蘭人的文明概念特別得益於義大利和法國的文獻和實踐:部分透過書籍的翻譯,部分透過到歐陸去旅行,他們對這兩個國家越來越熟悉。英格蘭人試圖「開化」世界其他地區之舉是在西班牙征服中美洲和南美洲之後推行,而英格蘭對我們現在所說的「國際法」的觀念是受歐陸思想家所形塑,其中包括西班牙神學家法蘭西斯科.德維托利亞(Francisco de Vitoria, c.1483-1546)、荷蘭法學家雨果.格勞秀斯(Hugo Grotius, c.1583-1645)和德意志自然法法學家薩繆爾.普芬多夫男爵(Samuel Pufendorf, 1632-1694)。
然而,我的重點是放在一七○七年與蘇格蘭統一前的英格蘭,那之後是放在英國。儘管威爾斯在十六世紀初就在政治上與英格蘭統一,但它卻像一七○七年後的蘇格蘭一樣,許多方面保持著文化上的獨特性,所以我在本書裡基本上不去考慮它。不過,我倒是把十八世紀蘇格蘭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對文明的高度自覺反思納入了討論。
在「跨國史」和「全球史」的研究風靡一時之際,以這種方式集中精力於某個特定國家是非常不時髦的。在美國,近代早期英格蘭的歷史曾被廣泛研究,因為美國的第一波移民潮就是從英國來的。英格蘭文化的影響──特別是新教、普通法和代議制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這個國家的早期發展。然而,如今多元文化的美國與英國已不再有特殊的關係,而在英國(就像美國那樣)試圖將自己與世界其他地區分離開來之際,英格蘭歷史可理解地被視為狹隘的專業而不是歷史課程的基本組成部分。
然而,對近代早期英格蘭的研究仍然有教益,因為它提供了一個在近代早期歐洲的獨一無二例子,即一個高度一體化的社會,其人民講一種單一的語言,被安排在一個等級性但相對流動的社會結構中,並且長期以來被強大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所統一。那是一個經濟轉型、知識創新和文學成就非凡的時代。在十八世紀,英國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經濟體,並將其帝國擴展到世界其他地區。
這些都是繼續研究近代早期英格蘭的好理由。但我之所以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五三○年到一七八九年之間的幾個世紀,主要理由則是這種對禮儀和文明的探究是構建一部近代早期英格蘭歷史民族誌(historical ethnography)的一部分,而這一規劃多年來斷斷續續占據著我的關心。身為威爾斯人、我某種程度上是個局外人,所以我一直設法用人類學家對待一個陌生社會的方法去研究英格蘭人,試圖確立他們的思想範疇和行為範疇,以及主導他們生活的原則。我的目標是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中展示過去經驗的獨特質感和複雜性。
本書前兩章致力於探討近代早期的「良好禮儀」(good manners)觀念:它們考察了「良好舉止」在統治菁英的自我定義中所佔的地位、在人口其他部分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加強了主流社會結構。第三章探討當時人對何謂「開化」的觀念變化,第四章討論他們對英格蘭是如何成為一個開化國家的看法。第五章考察英格蘭人的文明優越感是如何影響了他們與其他「未開化」民族的關係,特別是如何讓國際貿易、殖民征服和奴隸制變得有正當性。在最後兩章,我展示了近代早期的文明理念(它們絕對沒有得到普遍接受)是如何受到同時代一些人的猛烈抨擊。最後,我思考了這些理念在現代社會還有何現實意義,探問了如果沒有這些理念,社會凝聚力和人類幸福是否可能實現。
【看到這裡的讀者您好!因試閱刊登的形式限制,為求較好的試讀體驗,此摘錄均省略注釋,還請見諒!】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追求文明:從近代早期英格蘭的禮儀,重探人類文明化進程的意義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460 |
世界史地 |
$ 514 |
世界史地 |
$ 514 |
新書推薦79折起 |
$ 553 |
旅遊 |
$ 572 |
中文書 |
$ 585 |
歐洲史地 |
$ 585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追求文明:從近代早期英格蘭的禮儀,重探人類文明化進程的意義
英國社科學院院士、重量級歷史學家 基思.湯瑪斯爵士
作品首度登「台」
我們以為自己對「文明」的概念/反思已經知道夠多,但歷史學家總能打撈、組合並展示出令人拍案叫絕的歷史材料,敘事引人更進一步省思!
§ Courant書系 § 楊照選書 §
透過了解「文明」概念在16至18世紀的各個時期,如何形塑每一個英格蘭人不同的言行舉止,歷史學家基思.湯瑪斯的作品,讓你重新了解「英格蘭人的驕傲」從何而來,不同階級/地區的人切劃我群與他群的分歧微妙之處,以及反思「文明」的意義以及這個概念當今發展的價值。
【台灣在地 專業推薦】
李若庸/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林美香/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
張義東/國立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副教授
陳建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陳禹仲/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助研究員
黃春木/臺北市立建國高中歷史科教師
楊肅献/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詹偉雄/文化社會學研究者
蕭宇辰/「臺灣吧 Taiwan Bar」執行長
顏擇雅/作家、出版人
(依姓氏筆畫排列)
【 英國在地 佳評如潮】
「湯瑪斯是應該予以複製的國寶,好讓未來世代可以從他的睿智和典雅感受力受益……他的研究讓人驚艷,但更讓人驚艷的是他有能力透過讓笛福和斯威弗特自己說話,令歷史栩栩如生。這是一本非常文明的書。」── 傑拉德.德.格勞特(Gerard DeGroot),《泰晤士報》
「引人入勝。」── 伊森達.格雷厄姆(Ysenda Maxtone Graham),《每日郵報》
「博學、人道和範圍廣闊。」── 安.休斯(Ann Hughes),《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
「這書是關於英格蘭人如何定義自己和四周的人,以及異議聲音是如何持續地批判這種作風。它也提醒我們,我們是一場很古老的全球性對話的一部分,這對話是關於多元主義、差異和何謂人類物種的成員。」── 艾蜜麗.鍾斯(Emily Jones),《金融時報》
「《追求文明》是湯瑪斯參考書驚人的經典佳作。」── 約翰.加拉格爾(John Gallagher),《倫敦書評》
「以讓人望而生畏的眾多學術研究成果為基礎……這本書是供人深思、品嚐和享受。」── 馬丁.威靈斯(Martin Wellings),《循道會記錄者報》
「你不會讀到一本處理同一個時期但興趣範圍更廣闊的作品。」── 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 布萊爾.沃登(Blair Worden),《文學評論》
「活潑、投入和有見地……一本範圍和野心都讓人動容的作品。」── 倫敦國王學院講師 瓊.雷德蒙德(Joan Redmond),《歷史評論》
【來自其他英語系/半英語系國家的迴響】
「作者透過回溯有關文明的歷史,強調這種把原本分歧的社會所聯繫起來的「社會黏著劑」,從來沒有那麼重要或如此備受爭議……令人驚豔的研究。」──《華爾街日報》
「極有可讀性、極博學和極有歷史闡發性……湯瑪斯異常細緻地追溯了英語世界重視公共場所和家庭內得體行為心態的興起過程。」── 伊恩.唐納森(Ian Donaldson),《澳洲書評》
「問近代英格蘭人民對什麼是文明或什麼是『野蠻的』看法,就如同問他們社會如何運作以及該怎麼過生活這樣的基礎前提……這本旁徵博引、經過深思熟慮並充滿人性的作品,充分達到了這個企圖宏大的挑戰。」──《加拿大歷史期刊》
「透過同時檢驗狹義與廣義的『禮儀』與『文明』,作者試圖捕捉英國人對自身與其文明所感到的『特殊與優越』,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The New Criterion(來自紐約的藝術與文學評論月刊)
「來自重要近代史歷史學者的研究,引人深思……非常推薦。」── Choice(「美國圖書館協會」旗下,「大學與研究型圖書館協會」出版單位)
【必讀原因】
文明要讓人卑躬屈膝?野蠻能否展現驕傲?
儘管現今跨國史和全球史的研究風靡一時,本書聚焦於近代早期英格蘭的做法,更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視角,即一個近代早期歐洲、獨一無二的例子:一個高度一體化的社會,人民講單一語言,被安排在具有等級性但相對流動的社會結構中,並且長期以來被強大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所統一。此外,那是一個經濟轉型、知識創新和文學成就非凡的時代。英國更在十八世紀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經濟體,並將其帝國擴展到世界其他地區。
用誰的文明說服誰?
因此,考察英格蘭人如何「追求文明」的歷史,在追溯狹義和廣義的「禮儀」和「文雅」時,釐清近代早期的英格蘭人為何認為自身生活方式最為特別和優越,也是讓我們反思這些概念的絕佳切入點。最後,作者更是探問:這些理念在現代社會還有何現實意義?若我們不「做一個『文明』人」,社會凝聚力和人類幸福是否可能實現。
文明或不文明,這才是問題!
本書作者基思.湯瑪斯爵士著有《宗教與魔法的衰退》(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等多部重要作品,在歷史學界擁有舉足輕重的學術地位。本書主要根據他在二〇〇三年耶路撒冷The Menahem Stern Jerusalem Lectures講座內容加以擴充,可以說是集其對近代早期英格蘭研究之大成。
關於文明的歷史研究不勝枚舉,但作者認為相關詞彙所連結的概念仍舊十分棘手與不穩定。即便帝國主義、去殖民主義、文化相對主義諸浪潮來來去去,但進一步探討「文明」概念的歷史、意義、實踐與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在今日仍然深具重要性。
作者在書中處理下列問題:
• 在近代早期英格蘭,「開化的」(to be civilized)意指為何?
• 英格蘭菁英認為自己更加優越文明,這樣的信念如何影響他們與其他較低階層的互動?以及與威爾斯、蘇格蘭與愛爾蘭的關係?
• 禮儀——有關人的身體舉止和社會行為的日常慣例,在近代社會中扮演什麼角色?
作者簡介:
基思.湯瑪斯Keith Thomas
Sir Keith Thomas, 1933-
英國歷史學家,威爾斯人,專長領域為近代早期英格蘭社會與文化史,研究取徑深受人類學影響。學術生涯主要在牛津大學,曾任牛津大學副校長、基督聖體學院院長、牛津大學出版社代表與《牛津國家人物傳記大辭典》辭典顧問等。一九七九年成為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一九八八年因為對歷史學的貢獻,被授予爵位。目前是牛津大學萬靈學院、貝里歐學院、基督聖體學院與聖約翰學院之榮譽院士。
首部著作《宗教與魔法的衰退》(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1971)即榮獲沃夫森歷史學圖書獎。其他經典作品包括《人類與自然世界》(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1983)以及《生命的目的》(The Ends of Life : Roads to Fulfilmen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2009)。
譯者簡介:
梁永安
台灣大學人類學學士、哲學碩士,東海大學哲學博士班肄業。目前為專業翻譯者,完成約近百本譯著,譯有《李維史陀:實驗室裡的詩人》、《老年之書》、《文化與抵抗》、《帕德嫩之謎》、《非洲失落的白色部落》、《盧比孔河》、《人權的條件》、《愛的藝術》、《波希戰爭》、《1917列寧在火車上》和《伊凡的戰爭》等書。
章節試閱
導論
「野蠻的」和「文明的」兩個用語經常在談話和書籍中出現,因此,無論誰用思想去考察人類的行為和歷史,都有機會仔細考慮這兩個詞通常要傳達的意義,以及歷史學家和道德哲學家應該在什麼意義上使用它們。——詹姆斯.鄧巴(James Dunbar):《粗野和有教養時代的人類歷史文集》(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in Rude and Cultivated Ages,1780)
在十七世紀晚期的英格蘭,人們常常隨意地提到所謂的「文明世界」(civil world)、「人類的已開化部分」(civilized part of mankind)、「已開化諸民族」或「已開化世界」等等,...
「野蠻的」和「文明的」兩個用語經常在談話和書籍中出現,因此,無論誰用思想去考察人類的行為和歷史,都有機會仔細考慮這兩個詞通常要傳達的意義,以及歷史學家和道德哲學家應該在什麼意義上使用它們。——詹姆斯.鄧巴(James Dunbar):《粗野和有教養時代的人類歷史文集》(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in Rude and Cultivated Ages,1780)
在十七世紀晚期的英格蘭,人們常常隨意地提到所謂的「文明世界」(civil world)、「人類的已開化部分」(civilized part of mankind)、「已開化諸民族」或「已開化世界」等等,...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
導言
第一章 文雅行為 Civil Behaviour
禮儀的年表、禮貌與斯文、精化
第二章 禮儀與社會秩序 Manners and the Social Order
社會階層、禮儀類型學、中間階層的文雅、人民的舉止、開化的推手、庶民的文雅
第三章 文明狀態 The Civilized Condition
文明社會、文明的戰爭、文明的同情、開化的生活方式、文明的果實
第四章 文明的進程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文明的上升、野蠻的鄰居
第五章 輸出文明 Exporting Civility
直面野蠻人、用武力開化、發明人種、攻擊與奴役
第六章 文明的重新省思 Civilizati...
導言
第一章 文雅行為 Civil Behaviour
禮儀的年表、禮貌與斯文、精化
第二章 禮儀與社會秩序 Manners and the Social Order
社會階層、禮儀類型學、中間階層的文雅、人民的舉止、開化的推手、庶民的文雅
第三章 文明狀態 The Civilized Condition
文明社會、文明的戰爭、文明的同情、開化的生活方式、文明的果實
第四章 文明的進程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文明的上升、野蠻的鄰居
第五章 輸出文明 Exporting Civility
直面野蠻人、用武力開化、發明人種、攻擊與奴役
第六章 文明的重新省思 Civilizati...
顯示全部內容
|